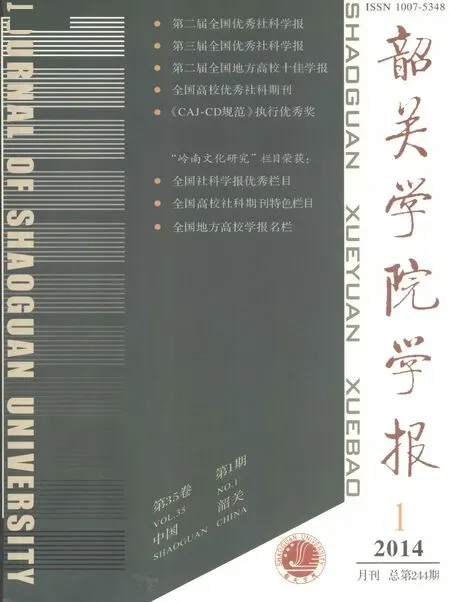王骥德与李渔戏曲理论之异同
郑小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王骥德和李渔作为我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两名重要的名家,历来颇受人们的重视。杜书瀛先生的专著《论李渔的戏剧美学》、《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对李渔戏曲理论有过系统研究,目前学界对二人单向研究的论文颇多,而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研究却甚少见。本文结合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二人代表作,从戏曲文体特征、文体创作、文体结构、文体批评、文体功用等方面对两人戏曲理论作如下比较:
一、戏曲各要素中见同
(一)戏曲语言
戏曲与正统文学诗文相比,只是一种通俗文学,它主要靠听觉起作用,要求语言浅显、质朴。
在语言上,历代曲论家都推崇本色语言。“本色”是明代戏曲理论家常用的范畴[1]339。“曲之始,止本色一家”(《曲律》),可见王骥德对本色语言的推崇。王骥德还提出了语言运用度的问题:“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王骥德还指出“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主张本色与文采并重,既克服偏重“本色”而“易流俚腐”,又避免偏重“文词”而“每苦本文”,要求作家对“雅俗浅深”,“酌之而已”。王骥德较好地处理了“本色”与“文词”的矛盾,对戏曲创作具有指导意义。李渔结合演出经验,认为戏曲语言必须浅显。他极重视戏剧语言的通俗化、群众化。他在“词采第二”中对戏剧语言提出了四点要求:“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李渔还提出戏剧语言应雅俗共赏,浅显通俗及形象生动等特点。他强调“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与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李渔还从舞台角度提出不同人物须使用符合人物性格的不同语言。显然,李渔的这些主张与王骥德等人提倡的本色语言颇有几分相近。
另外,二者皆重视戏曲语言的另一部分——宾白,并肯定其作用。王骥德是论述宾白的第一人[2],他特别重视宾白。前人往往重曲轻白,而王骥德认为宾白应与戏曲并重,宾白可以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主题思想。他要求“定场白稍露才华,然不可深晦”,要文而不晦涩,使观众人人听得明白,“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他还说,宾白之多寡,取决于剧情的需要,然而“大要多则取厌,少则不达,苏长公有言:‘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则作白之法也。”李渔认为宾白在戏曲中有曲文不可替代的作用[3]。李渔将宾白与曲文“等视”、并重,从理论上要求 “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简”、“自分南北”、“文贵洁净”、“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等等。从这些要求可见,李渔注重宾白的“观听咸宜”,善于用宾白刻画人物、表现故事情节。李渔还指出“作宾白者,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人物语言“一句可当十句”,言简意赅,宾白之多少,应根据剧情发展和刻画人物的实际需要,详略得当,力求洁净,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多不觉其多,多即是洁;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芜”。
(二)曲词音律
所谓 “音律”,是指填词制曲用韵与合律的问题,它是通过音乐形式体现出的一种曲词风格。
王骥德非常重视音律。他在对吴江派与临川派的论争做出客观评价的背景下,提出“法与词两擅其极”,主张音律与词义兼顾、和谐。王骥德从“词”的角度评价戏曲,极为推崇汤显祖,将汤与渭并列为“今日词人之冠”;对其音律上“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独字句平仄,多逸三尺”之类的缺失和疵病一一予以指正,并有所讥议。“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须烟波渺漫,姿态横逸,揽之不得,挹之不尽。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所谓‘标韵’,所谓‘动吴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被王骥德视为戏曲创作的最高境界。他从戏曲的历史流变出发,仔细考察了曲调的来源与分类、宫调的音乐归属与表现特点、字音的平仄与阴阳及曲韵、腔调、板眼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将“法”与“词”结合起来,“不废绳检,间妙神情”,方可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妙境[1]343。李渔作为精通音律的专家,特别强调戏曲的音乐美。他继承了汤显祖关于音律的主张,重词采而不轻视音律。他将文词置于音律之前,以明“才技之分”,并非不重音律。他说:“文词稍胜者即号才人,音律极精者终为艺士。”《词曲部·音律第三》分八款来讨论戏音律问题,认为作填词应“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使戏曲作品韵律谐美,达到声韵铿锵的舞台效果。李渔不仅在唱词方面讲究音律,同样对戏剧的宾白部分也很重视音律。他言:“世人但以音韵二字用之曲中,不知宾白之文更宜调声斜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间仄,仄间平,非可混施叠用,不知散体之文,亦复如是。”
(三)戏曲结构
明人郑之文说:“传奇之难,不难于填词,而难于结构。”(《旗亭记·凡例》)处理戏剧的结构,首先得通观全局,然后再取决于主题的确立,人物、事件的选择和安排,虑及继承与创新等问题。
王骥德在《曲律》中强调戏曲结构的整体布局。他以“工师之作室”、“必先定规式”相比,说明戏曲家须对全剧通盘考虑,事先加以酝酿。他还提出戏曲整体结构 “贵剪裁”,“贵锻炼”:“以全帙为大间架,以每折为折落,以曲白为粉垩、为丹。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于此,王骥德论及了戏曲框架布局问题,要求井然有序:论者提出戏曲的结构布局应次序分明、重点突出、整体合一。此外,《曲律·论章法》中也阐述了戏曲的结构问题:“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尺寸无不了然胸中,而后可施斤斫。”[4]121论者将结构安排比喻为建房子,各个因素必不可少,进行步骤也须井然有序,这段话生动贴切地表达了论者的结构观。李渔更是将结构放在曲论的第一位来论述,并且李渔继承了王骥德的“建宅说”。他亦以“工师之建宅”为喻,认为“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具锦心,扬为绣口者也。”有些作品之所以“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是因为“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一也。”可见,二者均强调戏曲结构的整体性,有序性。
有了整体布局以后,还得考虑主题。王骥德在《曲律·论剧戏》里提及到“大头脑”这一朦胧的主题概念。在文质上,也涉及“紧要处”,即今之所谓中心人物与中心事件。他主张立主意,抓头脑。李渔在《闲情偶寄·结构第一》中将“立主脑”即确定和突出主题思想放在首要位置。他主张戏曲要围绕“一人一事”的戏剧冲突,来发展剧情,即通过戏剧情节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体现出主题思想。显然,二者对戏曲主题都很重视。
(四)人物形象
关于人物形象的论述,二者都涉及到人物类型化或典型化以及性格特征的刻画等问题。
“古人往矣,吾取古事,丽金声,华衮其贤者,粉墨其慝者。”《曲律》王骥德认为给贤者披上画面的礼服,给邪恶者抹涂以粉墨,以使“奏之场上”,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是就人物品德的“贤”、“慝”加以夸张,使之更加突出。王骥德已初步提到人物类型化问题。又言剧作者“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要求作者设身处地,准确把握人物思想、性格特征,努力做到人物行动和语言的性格化:不同人物,因身份、性格不同,应使用不同的行动和语言。李渔的戏曲理论也有不少包括人物形象的论述。“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着,悉取而加之,亦犹绉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率同于此”,李渔以为凡是能够“劝人为孝”的人物形象,并非生活中某个“孝子”的复制品,而是作者集中概括的结晶。假如戏曲家的艺术表现是成功的,那么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就可能比生活中的“孝子”更概括,更具普遍意义。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戏曲家对生活中习见的“孝亲”言行及具体的人物故事,进行观察体验、分析选择、加工概括、想象虚构、提炼升华等一系列创造性劳动。李渔用如此明确的语言确认概括化之必不可少,确认塑造人物形象不能离开概括化,这在我国戏曲史上比较少见。李渔还认为成功的剧本,其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个性。他要求人物形象鲜明如《水浒传》之一百零八将,神情生动似吴道子笔下的人物画,其内心世界“随口唾出”,惟妙惟肖,不雷同,不浮泛,表明他对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从外形到内心,从语言到行动到情态风貌各方面都注意到了,考虑得相当缜密。
(五)戏曲的教化作用
戏曲是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而直接呈现给观众,有没有文化的观众都能欣赏其艺术魅力。因此,它与其他文体相比对大众更易产生教化作用。
《曲律·杂论》中说戏曲演出能“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为有关世教文字……故不关风化,纵好徙然”。并以“关世教”、“关风化”的准则,推《琵琶记》为众曲之冠,而指斥《拜月记》为“宣淫”。《琵琶记》早为明统治者所重用,后为复古派如王世贞等所推崇,王骥德的“关风化”,正是对明初正统教化说的继承,意在提倡戏曲创作有益于世道人心。李渔将戏曲的娱乐作用与教化作用相联系,认为戏曲更能广泛而有效地教育民众。他写道:“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字,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弥灾之具也。”并宣称,他之所以创作剧本,既不是“发愤著书”,更不是“托微言以讽世”,不过是“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点缀剧场,使不岑寂而已”。甚至还说:“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这些可以反映出李渔“劝善诫恶”、“归正风俗”、“警惕人心”,为封建统治“粉饰太平”的立场。李渔把其著作视为减少世人“瞌睡”、增加人们“谈锋”的读物。李渔看到了戏曲艺术给人以愉悦,给人以知识这样的社会功能[5]315。
二、戏曲批评方面存异
(一)文体特征
王骥德十分重视戏曲的情感作用,要求戏曲以表现情感为主。他师从徐渭,又受汤显祖等人的影响,将徐、汤诸人重情感的思想加以发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曲情感理论。首先,在戏曲创作的内容选择上,他认为戏曲要快人、动人,关键在于传情、写情。优秀的戏曲作品应该揭示人的内心,描写人的真情,并以这种真情来感动观众。从这一点而论,他认为明代戏曲创作之所以没有元代繁荣,正是因为戏曲创作缺乏真情。王骥德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缘情”、“言志”的美学传统,认为戏曲比其他文学样式更能“近人情”、“快人情”,这比李贽、公安三袁等人的“主情”论有所进步。它突破了“情理冲突”,带有反礼教、争取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色彩,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
戏曲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李渔的戏曲理论始终与舞台演出实践紧密相联。李渔,作为资深的导演,更看重戏曲的舞台魅力,戏曲的表演性。他认为立曲的目的在于演出,所谓“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戏剧活动需要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的积极参与。李渔在《闲情偶寄》的《演习部》和《声容部》详尽地论述了戏曲表演等相关问题。他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把中国古典戏曲表演理论和编导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创作论
王骥德注重戏曲家的个性,强调天赋才能与广泛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创作应是作者有了深切真实体验之后而作。他主张戏曲家在创作中张扬个性。另外,王骥德将《曲律·论套数》中 “套数之曲,有起有止,有开有合。先须定下间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调,然后遣句,然后成章,切忌凑插,切忌将就。务如常之蛇,首尾相连,又如鲛人之锦,不着一丝纰类。意新语俊,字响调圆,增减一字不得,颠倒一调不得。有规有矩,有声有色,众美俱矣”[4]138列为创作论的总纲。而他对于具体的戏曲情节、题材、科诨、格局等方面很少作深入论述。
李渔讲究戏曲创作的创新之处,指出“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6],并为戏曲批评树立了相应的准则。他要求戏曲创作“脱窠臼”、“戒荒唐”,从理论上批判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他还从历史演变的创始、变革、保守中探索创新的理论依据,认为戏曲创作“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他不仅认为戏曲创作要创新,舞台表演也要“变旧为新”。
王骥德赞赏汤显祖“二梦”时,提出“以虚而用实也难”。他已谈及戏曲体式中的“虚实”问题,以为“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但王氏并没就虚实问题作详细的论述。李渔论戏曲题材的“古”、“今”、“虚”、“实”时,提出可以“随人拈取”,但“又不宜尽作是观”。如果写今人今事,能虚不能实;写历史题材,则能实不能虚。
关于科诨,李渔提出了更精辟的见解。他将科诨作为全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是李渔不同于前人的创见。一直以来,插科打诨被视为填词之末技,不受剧作家重视。而李渔“使人不倦”,不可作小道观。他指出,“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非“太俗”,科诨不只是观众的笑料,更是剧情发展、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对于科诨的运用,他还强调必须自然。
此外,李渔对于戏剧的格局,即他所说的开场、冲场(戏剧的开端)十分重视。他要求开场数语应“包括通篇”,而冲场则须“酝酿全部”。让观众瞬间进入剧情非看一个究竟不可,这是中国古代戏曲一种极高明的手段。对于角色的出场,李渔认为主角不宜出场太迟。关于结尾,李渔也特别重视。他认为应有大、小两种收煞。小收煞,给观众制造悬念,而大收煞要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团圆之趣。李渔关于戏曲格局的理论,对中国小说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悬念和小团圆的结局,至今仍是小说家进行创作的一种艺术构思模式。
(三)戏曲评论
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出了著名的全面评论原则[5]121;李渔在《一家言》中提到了鉴赏批评[5]323的观点。
《曲律》几乎涉及戏曲艺术理论的各个方面,暗含统筹兼顾、全局着眼的思想。在创作上,王骥德就套数之曲而论,要求做到纵美俱全,包括立意、间架、曲调、章句、照应、规矩、声色等。他把创作当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在论曲时,他要求“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其次,王骥德把对真性情的表现视为评判剧作家功力高下的标尺。《杂论下》言:“世之曲,咏情者强半,持此律之,品力可立见矣。”[4]210戏曲大多是“咏情”的,所以可以拿对情的表现作为判断戏曲家品力的标准。
李渔认为鉴赏戏曲必须懂得戏曲 “观听咸宜”的特点。他让观众在欣赏戏曲时“易心换眼,别置典型”。正所谓:“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不仅是李渔对观众的要求,更是对鉴赏家的要求:不懂得戏曲的基本特点,就谈不上有真正的鉴赏。戏曲批评既要懂“文字之三昧”,又要知“优人搬弄之三昧”。李渔比较重视戏曲鉴赏中“情”的因素。在他看来,戏曲鉴赏离不开“人情”的沟通。只有当观赏者与作品在“人情”上相通,方可产生情感的共鸣。这是明代李贽、“公安派”、汤显祖“人心人情”理论之延续。李渔还提倡“细尝其味,深绎其词”的批评方法,要求欣赏作品与思考同步才能对作品作真实的评价。此外,李渔还把“情”、“事”、“文”三者联系起来,将其作为作品“可传与否”的标准。这是他对“三事”、“三美”所做的贡献[5]325。
三、结语
王骥德和李渔,两个不同时代的戏曲理论集大成者,其戏曲理论大同小异,各具特色。他们都是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对前人丰硕的曲论成果作全面的总结,并提出自己独创性见解,与之融会贯通,形成更具系统性、完整性的戏曲理论。王骥德的戏曲理论为李渔的戏曲理论奠定了基础,李渔在全面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将中国的戏曲理论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阶段。他们的戏曲理论为近现代的戏剧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王思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57.
[3]邹然.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65.
[4]王骥德.曲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