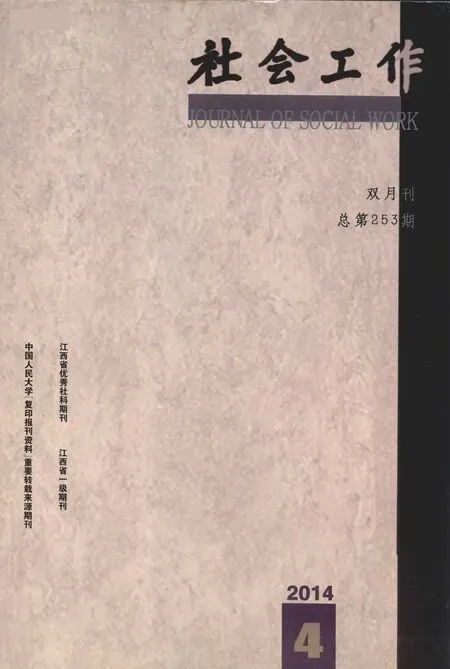内生的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
周晨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被称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Assets-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ABCD)在美国兴起,并在世界各国的社区发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资产为本”代表着西方社区发展的一种模式转换与实践创新,从强调社区的需求与问题转向建设社区的能力与优势。“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内生型的社区发展。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学者Kretzmann和Mcknight指出,“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发展必须始于社区的内部,对于大多数城市社区来说没有别的选择”(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6)。从“资产为本”的角度来看,社区发展就是通过增加社区资产、提升居民能力,以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有计划的过程(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内生型社区发展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区发展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全面挑战的反映,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区发展理念与实践路径。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进行了很多引介,分析了这一模式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发展的借鉴意义(文军、黄锐,2008),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我国扶贫减贫、灾区重建、城市移民等研究领域中。为了扩展这一理论与实践模式在我国的应用,还需进一步了解西方“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兴起背景、理论内涵以及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社区发展的未来走向。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动阶段,城乡社区发展承载着更为复杂多样的艰巨任务。通过全面社区资产建设提高社区内在能力与优势,促进社区内生发展,有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战略目标。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的兴起背景
1993年,美国学者Kretzmann和Mcknight提出,传统社区发展的“需求”导向模式已面临终结,一种新的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将成为社区发展的现实选择(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3),“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随之在美国广泛推广开来。众多社区开始以促进和影响社区资产的方法来建设自己的社区,很多基金会、组织和机构也采用“资产为本”的发展方法作为其工作的关键基础,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近年来“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模式,“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面临全面挑战的反映;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改革也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反映了社会理论不断适应社会变革的实践趋向。
(一)西方社区发展面临的全面挑战
西方社区发展至今已走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区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于社区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西方社区发展面临困境的主要背景。全球化威胁着社区的经济基础,对世界各国的社区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益国际化的市场对于本地投资与劳动力成本带来新的竞争压力。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使得社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从很多方面来说,全球化都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区已经被整合进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Warren,Roland L,1978)。
第二,快速的城市扩张。世界范围的城市扩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使得社区需要应对更多的问题。首先,城市扩张破坏了“地域”的独特性,造成了阶级与种族的隔离。将日益破败的市区改造为中产阶级居住区使贫困群体难以得到支付得起的住房,由于支付不起高额税负而被赶出他们居住的社区。其次,城市的扩张所带来的隔离,削弱了民主和公民参与。正如普特南所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大量涌入的移民增加了社会服务的需求并对公民参与产生挑战(Putnam,Robert.,2007)。
第三,社区贫困现象蔓延。西方国家很多社区持续出现的集中贫困现象,给社区居民带来极大的困境。贫困社区居民在基本服务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如银行、购物等。由于中产阶级搬到具有更好教育住房条件和更安全的社区,年轻人缺少好的角色榜样,没有了追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精神动力(Gray Paul Green,Ann Goetting,2010)。有限的社区网络也限制了贫困社区居民获得就业信息,贫困群体很难与外界建立联系渠道以增加就业机会。
第四,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压力。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使得社区可持续发展成为西方社区发展追求的新目标。社区可持续发展是社区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交融的新型理念,是当代社区发展的更高境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于社区经济、生态与社会三个维度之间的协调平衡,要求在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机会的同时,有效应对本地环境问题、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并为社区中的边缘化居民提供发展机会,实现本地的社会公正(R.Warren Flint,2013)。社区可持续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本地的社区资产或资源,对于社区发展内在动力的要求更加迫切。
(二)西方政府职能转变对社区发展模式的影响
美国是西方社区发展的典型代表,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对于社区发展的影响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不断退出社区发展的主导地位,将社区发展的权力更多下放到地方政府与社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社区转向自我发展。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社区发展的阶段,此后的美国社区发展都是以联邦政府在满足社区需要中的强有力角色为主要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逐渐减少对社区发展直接的财政支持,而将更多的权利下放到州和地方,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参与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社区发展是随着基于地方的政策实施、职业培训计划以及以社区发展为目标的正式组织兴起而走向成熟的(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从约翰逊总统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一直在重塑联邦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角色,给予地方以更多的决定社区发展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社区发展越来越重视基于地方的社区发展,特别是少数族群和低收入社区的社区发展;同时加强了社区发展中的公共参与和社区控制,公共参与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环境、健康、交通、住房和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将更多社会经济福利的责任置于社区层次之上,社区组织越来越多地负担起社会服务供给、满足住房需求和实施福利计划等职责。这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地方社区组织是否有充足的资源承担这些任务?这些组织能否在社区发展计划中建立起有效的公共参与?社区是否有能力和优势应对各种社会与经济压力?社区发展真正希望来自于当地社区的草根组织,因此,加强社区内在能力建设,尤其是社区组织建设就成为社区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社会理论不断走向实践的反映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以至于有些学者将其作为社区发展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理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资产为本”社区发展与很多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社会资本理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参与社区组织、建立社会联系和信任是动员社区居民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理论构成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比其他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更加紧密地把理论与实践连接起来(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当然,关于这一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如,缺乏实证基础、理论深度以及对宏观原因的思考等。对“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界定,理论本身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近年来很多西方学者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补充。如,澳大利亚学者Gretchen Ennis等人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理解“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功效,通过强调和建设社会网络激活社区资产以促进积极的社区变革(Gretchen Ennis,Deborah West,2013)。这也说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存在着进一步扩展的理论空间。
二、从“需求”到“资产”:西方社区发展的导向转换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是西方社区发展的模式转换,即,从“需求”导向转向“资产为本”。社区“需求”导向的核心是社区“需求”。所谓“需求”一般是指社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通常包括失业、贫困、犯罪、适用住房匮乏等。社区“需求”导向一直以来被社区发展实践者看作是最有价值的社区发展模式之一。从很多方面来说,社区发展就是通过社区集体行动、满足社区需求来建设社区的过程。不能否认,社区需求使居民获得极大的动力,通过集体行动发出更强大的声音(Jonhson,Donald E,1987)。但“需求”导向作为一种依赖外部支持的社区发展,在21世纪以来的各种挑战面前已显现出明显的不足。
(一)对外部资源的依赖问题
“需求”导向社区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社区为了应对挑战转向外部寻求资源支持,这些资源包括技术、商业投资或者专家。外部资源提供了一种“快速奏效”解决本地问题的可能性,但对外部支持的依赖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1.外部支持使社区专注于提出需要,而不是培养提升居民能力。外部支持基于以下假设,即,社区有问题,而专家有答案。专业化的服务创造了需要持续关照其需求的客户,这种关系容易使社区产生依赖性。2.外部支持与当地设置的不相匹配。外部支持对社区问题只是进行一般的处理,很少能够理解本地背景。专业训练与经历建立于一般的过程和任务之上,需要在本地层面进行转换,而理解社区背景以及影响社区发展成功的社区动力都需要花费时间。3.外部支持很少能够提供持续的支持。持续的支持对于社区发展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而外部专家模式则欠缺这种因素。作为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支持通常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而大多数社区发展项目需要的时间和任务都超出外部专家所能提供的范围。一般而言,专家不能长期居住在社区,难以在项目的实施和监测上投入更多的时间(Gray Paul Green,Ann Goetting,2010)。
(二)社区合作关系的不可持续问题
由于“需求”导向只是针对社区问题,因而在社区发展中难以确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需求”导向的集体行动往往不是建立于社区居民对社区发展目标清晰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由外部组织、顾问、咨询专家等来发动。这种断裂导致了阶段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集体行动。因为一旦问题得到解决,就很难将居民发动起来去应对新的问题或基于某种需求建立正式的社区组织。如果社区转向新的需求,已经形成的合作伙伴和联盟就可能解体。正如Kretzmann和McKnight所指出,“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实际上是在贫困社区与外部社会之间建了一堵“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堵“墙”不是以仇恨而是以“帮助”为名义建立起来的(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6)。
(三)社区居民的能力下降问题
“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容易导致社区居民的无力感或疏离感。在这种社区发展模式中,居民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改变个人与社区的命运。特别是当居民将社区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来自社区之外的制度性力量的时候,这种无力感就会更加突出,社区居民被社区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压倒了。在“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模式中,社区需要外来专家告诉他们最严重的关切是什么,因为社区认为,这些问题对居民来说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自己认识并加以处理。在“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模式中,社区居民把自己作为“客户”或者是被动的服务消费者,而不是作为积极的公民和建设者(Alison Mathie,Gord Cunningham,2003)。
“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社区外部力量推动的依赖性,因而是一种外生型的社区发展模式。如果将“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作为贫困社区发展的唯一方法,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3)。美国社区发展的很多案例研究也证明,社区发展项目如果不是来自于社区内部自身的推动力,则很难获得成功。如,在美国前总统卡特执政时期,亚特兰大州乔治亚市曾经由本地企业提供经济援助,支持20个社区进行社区发展项目,结果由于没有得到来自社区居民的支持而收效甚微(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来自社区外部的经济资源虽然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一定支持,但在产生社区自身动力方面却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三、“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实践路径
与“需求”导向的社区发展相反,“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不再把社区“需求”作为社区发展的重心,而是转向社区内部的资产与优势,追求以社区资产为基础、以社区关系为驱动力、内在的社区可持续发展。“资产为本”社区发展不仅仅帮助社区居民实现其利益,而是找出有助于发展的“资产”,引导动员社区居民,通过提高社区的内在能力来提升社区生活质量。当然,“需求”与“资产”的导向对于社区发展实践者来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很多情况下,评估社区“需求”仍然是很有必要的,但“需求”导向的问题在于不去明确社区的目标和内部力量,而是直接向外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建立于完全不同的前提之上,具有“需求”导向社区发展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
(一)以社区资产为出发点激活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社区资产是“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Kretzmann和McKnight认为,所谓社区资产是指社区中的个人、组织与机构所拥有的天赋、技巧和能力等。在社区发展中这些资产往往被忽视了(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6)。福特基金会前副主席奥利弗•麦尔文(Melven Olive)对社区资产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所谓社区资产,是个人、组织或者整个社区用于减少或阻止贫困与歧视的一种特殊资源,作为资源,社区资产是一种可以存取或者增殖的存量,同时可以共享和代际传递”(Olive.M.Forward.,2001)。社区资产具有以下内涵:第一,“社区资产”采用社区资本的形式。社区资本投资于社区,并能产生资产的增值。第二,不同形式的社区资本投资,带来集体性的社区收益。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排除利益动机,但社会目标必须与经济目标结合在一起。第三,社区资产蕴含着社区发展直接面向本地(locality)或者地方(place)的取向(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
社区资产是社区内部的能够激发社区发展活力与动力的各种资源。了解一个社区的内部资产状况,主要通过制作资产地图(Asset mapping),如,通过社区居民个人技能和工作经历确认社区经济的发展机会;考察社区自然资源是否可以通过发展旅游等方式促进社区经济发展;通过消费者调查了解社区潜在的商机;为社区居民列出可以相互提供便利服务的项目等。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把社区资产划分为不同类型。美国学者Gray将社区资产分为七种社区资本形式,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这些社区资产在社区发展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功能,具有不同的建设重点与发展策略。通过发掘与建设不同类型的社区资产,能够增强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社区的内生发展。
(二)重视社区内部的所有资源和关键力量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是一种包容的发展模式。社区中的个人、组织与机构都拥有能够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资源,所有人的作用作为“资产”都应得到承认与尊重。“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尤其注重被忽略的弱势群体的潜在能力,如,老年人、妇女、失能群体以及其他低阶层群体,为其提供机会,建立自信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虽然没有直接解决权力的不平等以及带来的压力问题,但是力求提高受损阶层对于权力运用的诉求,使他们能在公共物品的共享利益中发挥作用,发现他们当中被低估的力量。社区实践者需要通过各种方法获得个人资产的信息,如,面对面的个人或小组的调查访问、个人档案和社区事件等。这种能力调查的目的在于确认所有居民对社区贡献的潜在能力,不是确认社区问题。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也需要培育社区领袖。因为社区资产建设是社区内部驱动的,不能依赖于外部机构。为了保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领袖的培育就成为“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关键任务。无论作为参与的个体,还是作为领导者来说,社区领袖的品质与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了解社区领袖的基本情况,社区领袖是个人还是一个群体?只是一种形式,还是能够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发挥出功能?什么样的组织能培养出最好的社区领袖?社区领袖怎样将社区内部组织与外部资源连接起来?(Alison Mathie,Gord Cunningham,2003)社区领袖作为社区资产建设的关键力量,必须具有相应的素质与能力。
(三)发挥社区内部组织与机构的作用
“资本为本”社区发展理论认为,在社区发展中存在着很多个人行动无法克服的制度性障碍,必须通过社区组织的行动才能解决,本地社区组织更能有效克服与社区发展相关的集体行动困境。如,社区中需要招募员工的单个雇主,可能会由于害怕雇员接受培训后离开而不愿意投资于职业培训项目,同时单个雇主也可能没有充足的资金提供职业培训,而有着共同需求的许多雇主联合起来形成社区组织则能够有效实现这一目标。通过社区中已存在的资源基础,“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为社区问题提供了集体性的解决方式。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通常要确认社区中的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由于有组织者通常是明显的;而非正式组织,如,街区俱乐部、邻里守望组织、或者花园俱乐部等,由于没有列入正式的名单或者没有支付薪水的员工而常常被忽略。确认这些网络和社会关系有助于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同时,“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也将社区内的机构作为社区发展的重要资源,如,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社区内机构通过购买本地服务和产品、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等方式,有效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同时社区内的机构拥有举办社区节庆大事的场地或设施,有助于增加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成员的整合。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必须依靠本地社区组织与机构来实现社区发展目标。巩固本地社区组织的基础、加强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是“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最为关键的实践路径。当然,“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并不完全排斥外部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外部组织和机构可以为社区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其他资源,但是社区发展最终还是要由本地社区组织来推动。外部机构在最初发展阶段只是过程的促动者或者说是社区扩大外部网络的节点(Alison Mathie,Gord Cunningham,2005)。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是一个社区系统自我强化、自我建设的过程。通过发掘社区内部资源,动员社区内部力量,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为此,“资产为本”社区发展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建立共享的意义。促进社区居民积极的自我评价,推动社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第二,发挥社团的潜能。以社区组织作为社区资产建设的主体力量,在实际社区发展中增量社会资本。第三,提升社区的经济能力。以资产为驱动力的社区发展策略,必须由社区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第四,重构社区权力结构。关注社区中的弱势群体的能力建设,并力求改变社区不平等的关系状况(Alison Mathie,Gord Cunningham,2003)。总之,“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是内生型的社区发展模式,通过明确与激活社区内部的资产,以社区内部组织与机构为主导来进行全面的社区资产建设。
四、内生的社区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社区发展方向
我国社区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展开的。为了应对体制转轨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我国政府在制定社区发展战略时一直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主要目标,以政府直接、大量的投入作为实践方式,形成了以各级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种社区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境。如,政府社区发展项目的效益低下,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甚至有些产生了社区腐败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已经面临着“需求”导向社区发展的“不可持续”困境。外生型的社区建设只带来“增长”,并没有带来“发展”。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为我国城乡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完成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任务,城乡社区发展也应转变思路与发展模式。以增强社区内在能力与优势的内生型发展为方向,通过全面的社区资产建设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根本目标。虽然中国的社区发展基础与西方有着巨大差异,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对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社区发展的未来走向有着重要启示。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视角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我国的社区发展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将有形社区资本与无形社区资本有机结合,有效运作与管理社区资产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显示,社区资产的有效运作与管理可以使社区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各种风险并取得进步;而社区冲突则是错误利用或没有利用好社区资产的结果(Mukesh Kanaskar,2013)。我国城乡社区中蕴含着丰富的社区资产,但在我国城乡社区发展中,对社区资产的运作和管理还存在着诸多误区,特别是强调有形的、实物形态的社区资产的开发利用,忽视无形的、潜在的社区资产的建设,这些问题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中忽略了农村社区文化资本的保护与开发,造成大量具有保留价值的传统乡村面目全非;农村社区居住方式的变化也使得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消减现象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城乡社区发展应合理配置并运作社区有形社区资本和无形社区资本,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殖。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与能力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说到底是“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观,鼓励贫困社区与群体的积极自我评价,通过提高社区居民的组织与能力,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面对自身贫困状况以及其他社区问题时都有一种被动依赖的心理,认为政府应该包办一切,“等、靠、要”成为唯一能做的事情。即便是在政府积极动员的情况下,仍然处于消极参与的状态。在这种“需求”为导向的社区发展环境中,大量外部资源被消耗殆尽后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实际成效。当然,并不是说外部支持不重要,而是说只有在一定的居民素质发展的基础上,外部支持才能够发挥其作用。具有外部依赖性的社区发展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社区发展。因此,我国城乡社区发展仍然要以提高居民素质与能力为主,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发展的能力与优势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城乡社区发展的主要资源。
(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社区组织与机构进行社区资产建设
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视角来看,成功的社区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运作社区政治资本并有效解决社区问题。政治资本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社区资产,是指对社区发展项目的控制以及对与居民生活质量有关的其他社区事务的影响力(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我国社区发展的权力主体是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同时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也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本。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促进城乡社区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目标之一,就是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推进城乡社区发展,应通过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进行政府、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资本建设。近年来城乡居民的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逐年增强,各种类型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兴起,为社区资产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社区内的机构对于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如,近年来大学等机构面向所在社区的社会服务逐渐增多,社区参与也成为“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
(四)重点保护社区环境资本,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各种社区资产中,社区环境资本具有特殊的意义。社区环境资本对于社区形象和居民生活质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环境资本是指社区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壤、动植物等。环境资本能够带来更多的社区资产,也可以为后代留下更好的发展机会(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任何社区发展都要考虑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处理排水、垃圾处理等社区环境问题。自然资源也可以带来直接的市场利润或无法估价的利益,如,娱乐或旅游景观等。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社区的环境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关系,倡导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模式。但我国有些地方的社区发展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破坏性地开发社区环境资本,竭泽而渔,破坏社区生态平衡,损害后代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应坚持“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观,高度重视本地社区的环境资本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来促进城乡社区发展。
借鉴西方国家社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我国城乡社区发展应树立以“资产为本”的理念,注重社区资产的有效运作与管理,实现社区资产效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核心”,注重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与能力,从社区内部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之尽快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注重社区组织建设,通过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促进社区主动发展;推动社区公共参与,发挥社区内外社会组织与机构对于城乡社区发展的资源支持作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内生社区发展为导向,能够探索出符合现代社区发展一般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发展之路。
[1]文军,黄锐,2008,《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
[2]Alison Mathie,Gord Cunningham,2005,Who is driving development?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Vol.26,No.1,January,pp.175-186.
[3]Alison Mathie,Gord Cunningham,2003,From clients to citizens: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 a strategy for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13,No.5,November,pp.474-486.
[4]Gray Paul Green,Anna Haines,2012,Asset build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Sage Pubilcations,Inc.,p.25,12,36,59,124,239,213.
[5]Gray Paul Green,Ann Goetting,2010,Mobilizing communities:Asset building as a community developmen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p.2,17.
[6]Gretchen Ennis,Deborah West,2013,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a case study,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Vol.48,No.1,January,pp.40–57.
[7]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6,Assets-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National Civic Review,Vol.85,No.4,Winter,pp.23-29.
[8]John Kretzmunn,John McKnight,1993,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inside out: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Chicago:ACTAPublications,p.51,69.
[9]Jonhson,Donald E,1987,Needs assessment:Theory and methods,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205.[10]Mukesh Kanaskar,2013,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Assets,Indian Streams Research Journal,Vol.3,Issue.10,January 11,pp.1-11.
[11]Olive.M.Forward,2001,In T.M.Shapiro(Eds),Asset for the poor:The benefit of spreading asset ownship,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p.5.
[12]Putnam,Robert,2007,“E Pluribus Unum”,Scandinavia Political Studies,Vol.30,No.2,Feb,pp.137-174.
[13]R.Warren Flint,2013,Practice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A Participatory Framework for Change,Springer New York,p.35.
[14]Warren,Roland L,1978,The Community in America,3rd Edition,Chicago,IL: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