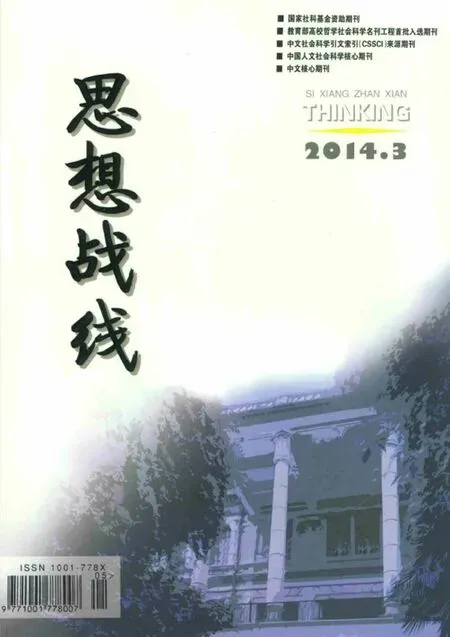鲁迅作品中的变异仿拟修辞刍议
黄 曼,肖 洒
鲁迅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因创作题材和表达目的等特殊语用需要而产生了诸多的仿拟和变异仿拟修辞。那么,什么是仿拟?在中国,最先提出仿拟修辞的是陈望道先生。他划分了三十八中修辞格,仿拟格是其中一种,即“为了讽刺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在鲁迅作品中,除却传统仿拟手法以外,还有许多创造性的仿拟形式,我们称其为变异仿拟,即区别于传统仿拟的新的仿拟形式。变异仿拟的本体来源众多,仿体形式多样,本体和仿体之间形成的出乎意料的联想关系也是别具一格,并且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变异仿拟自然也属于仿拟修辞的范畴,是区别于传统仿拟的一种特殊手段。
变异仿拟除了是一种特殊的仿拟手段以外,同时还属于变异修辞学的范畴。最先提出变异修辞学的是冯广艺。他认为“言语变异是建立在言语艺术的基础之上的”,[注]冯广艺:《变异修辞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不同于语言规范的规则性、相对稳定性和全民性,言语艺术则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因而言语变异具有言语艺术的特点。他认为“变异性修辞就是这种创造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在修辞现象中的反映”。[注]冯广艺:《变异修辞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7页。变异使人们言语表达的内容更为丰富。同时,根据表达者在修养、阅历、文化水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言语变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以此为基础提出变异仿拟的概念,将其与传统的基于语义相关或相反的仿拟手段区分开来,并在文中辅以实际语料进行说明。也就是说,变异仿拟不是简单地基于语义相关或相对而成,其本体和仿体之间的联想关系更加新颖奇特、与众不同。本文将着重对鲁迅作品中区别于传统仿拟的创造性的特殊修辞手法——变异仿拟修辞进行探讨。
一、鲁迅作品中的变异仿拟手法的分类
毋庸置疑,鲁迅作品中自然运用了许多传统仿拟手段,比如基于语义的相关或相反等形成的近义仿拟、反义仿拟以及数字仿拟等。例如:“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念,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是恶客。”[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苦趣”仿自“乐趣”,是基于直接的语义相对而来。作者创作出“苦趣”这一简练的表达,贴切地体现了旧社会人民生活之疾苦。当然,鲁迅作品中更多的是创造性仿拟修辞,即我们认为的变异仿拟。变异仿拟不同于传统仿拟的是其本体选择以及变异成分选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通过对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语料的收集和观察,我们根据仿拟过程中变异成分的数量将其分为以下3种类型:
其一,单语素变异仿拟。单语素变异仿拟指的是本体表达式中仅有一个语素发生改变从而形成仿体。这个发生改变的成分可以是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或者数量词。[注]一般来说,单语素变异仿拟中若是通过改变数量词而来,通常会将该数量词进行虚化处理,即不再具备其原有的实际意义。例如:“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8页。“下坑”是仿“下野”而来。若脱离具体语境来看,“下坑”一词是意义不明的非常规语言表达,甚至是语法错误的表达。但是在该句的语境中,与“坑”对应的是“野”。那么,此例中的仿拟路径首先是将“野”从“下野”一词中剥离,去除其在“下野”一词中“朝野”之意,凸显“野”的其他义项,即“野外”,然后通过语义的相关,在该义项与“坑”之间建立联想关系,从而形成变异仿体“下坑”,影射并暗讽的是白色恐怖。
其二,双语素变异仿拟。双语素变异仿拟指的是通过改变本体表达式的两个成分而形成的仿体。这两个变异成分的位置可以相邻,也可以间隔。例如:“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歪人奴子”是仿“正人君子”而来。在仿拟过程中,本体表达式的两个构成成分发生了改变。“正”和“君”对应的是“歪”和“奴”。此类变异仿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歪人奴子”这一变异仿体的产出,也是基于本体表达式构成成分“正”和“君”的语义剥离以及变异成分其他义项的凸显而来。这一特征也是变异仿拟的一个重要的句法特点。
其三,多语素变异仿拟。多语素变异仿拟,顾名思义,发生改变的构成成分的数量大于等于三。此类变异仿拟因发生改变的成分较多,因此可以是仿句,甚至仿篇。一般来说,多语素变异仿拟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本体表达式基础上仅通过改变构成成分而形成仿体,表达形式保持不变;二是将本体表达式进行拆分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仿体。因为本体表达式中发生改变的成分较多,故而相较于前面两种变异仿拟而言,这种类型的仿拟中本体和仿体的区分度较大,或者说本体的辨识度较低。试看下例。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此例是典型的仿篇,作者通过对崔颢《黄鹤楼》一诗进行多语素变异仿拟,从而表达出对国民党当局借文物保护之名卖国求荣、镇压抗日大学生这一丑恶行径的痛恨和嘲讽,文辞练达又犀利。多语素仿拟的使用也是语言文字美和变异美的体现。
二、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的句法和语用特点
(一)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的句法特点
其一,本体和仿体并不总是同现。传统的仿拟修辞中本体和仿体一般都会同时出现,但是在鲁迅作品中,我们观察到许多仅出现仿体而省略本体的情况。例如:“我近年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全不觉得怎样。”[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神经过钝”就是仿自“神经过敏”,当然这一仿拟过程与本体构成成分的语义剥离不无关联。若仿拟的本体表达式是具有一定语义习用性和结构稳定性的专有名词或熟语等,那么在该变异仿拟中本体不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其辨识度也较高。
其二,本体和仿体出现的顺序。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的本体和仿体出现的顺序并不总是本体在前仿体在后,仿体在前本体在后的变序使用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上,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摘句’。”[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极境”是仿体,“绝境”是本体,但出现的顺序却是仿体在前本体在后。这种本体和仿体的变序使用可以使语言的表达更为灵活和多变。
其三,本体的来源。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的本体既可以是一般名词或词组,也可以是专有名词或熟语,可谓来源丰富。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以笔当枪的民族英雄精神。
其四,一词多仿与多词一仿。一词多仿指的是对同一个本体表达式进行多种形式的仿拟形成多个仿体的连用,多词一仿则指的是多个不同的本体通过仿拟形成同一个仿体的情况。例如:“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O’”。[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生命圈”和“生命线”为两个不同的本体,但只有一个仿体,即“生命O”,形成了多词一仿。其实,不管是一词多仿还是多词一仿,都是对仿拟修辞的灵活使用,并且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其五,不局限于本体的结构和形式,往往产生成分拆分的仿用。鲁迅作品中通过变异仿拟形成的仿体,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其句法形式的多变,不拘泥于本体的结构或形式,对于构成成分的拆分使用时有发生。这也使得语言更加生动灵活,意义表达更加深刻,同时又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通过有限的语言表达出事物的多个方面。例如:“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文人不免无文”是对仿拟本体“文人无文”的拆分使用,而“武人也一样不武”则是对仿体“武人不武”的拆分使用。这样的拆分使用使语言表达更加灵活多变,同时还体现了语言的文字美和变异美。
(二)鲁迅作品中变异修辞的语用特点
其一,仿体的意义理解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鲁迅作品中的文辞风格多变,对于仿拟修辞的使用时而清楚简练,时而含蓄隐晦。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读者对于仿体的理解需要依赖仿拟生成的具体的小语境,甚至是文章发表的社会背景这一大语境。因此可以说,较强的语境依赖性是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意义理解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语用特征。比如对上文语料中仿体“歪人奴子”的理解,首先便要基于其本体“正人君子”。本体和仿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仿体产生的小语境,调侃揶揄之味甚浓,具有讽刺幽默的功效。此例的大语境是1926年刘半农于厂甸庙市中无意寻得《何典》,决定校点付印,并在《语丝》上多次为其广告,然而广告刊出后备受所谓“正人君子”、“文士之徒”的指责,鲁迅则在《语丝》上发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以示回应。
其二,变异仿拟的语用目的往往比较明显。鲁迅的作品,尤其是杂文向来以文笔洗练、犀利、辛辣、讽刺而闻名,因此作者使用变异仿拟多是基于讽刺或抨击时政和旧习等具体语用目的。这些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突显了变异成分不同于在本体中的意义,形成了许多谬仿。这些缪仿在诙谐讽刺的言辞中反映了作者对反动当局、民族败类或者错误思想的愤怒、嘲讽和抨击。
其三,求新逐异的语用诉求。求新逐异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语用诉求,也是修辞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还是美学上的陌生化的表现。人们往往通过使用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来满足这一语用诉求。比如“神经过钝”等都是偏离常规的表达。这些新奇的表达往往能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并使其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从而产生共鸣。
此外,通过变异仿拟的修辞手法还可创造出许多新词。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更期待新奇的、不同于以往的事物。通过变异仿拟创造出的新词虽然具有临时性,但是经过长期或多次的使用,也有可能得到语言使用者的认可,从而转为真正的、具有习用性的新词,进而被纳入规范语言的范畴。作为语言大师,鲁迅在其作品中通过使用变异仿拟修辞创造了诸如“拿来主义”、“武化”等许多新词。“拿来主义”表现出的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方法,形象直观生动,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和概括性,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习用性较强的固定短语。这也是鲁迅仿词的一个特点和一大贡献。这些新词随着鲁迅作品的流传,从而进入了汉语常规语言系统,变成了汉语词库的“正式”成员。
三、变异仿拟的认知机制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认知的表征,语言研究必须与认知研究相结合。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变异仿拟其实也是对客观外界进行概念化的研究。鲁迅通过变异仿拟修辞形成的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中产生的语义冲突,也就是对作品的现实背景中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等冲突在人类认知上的体现,这也符合了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理,就是说语言是在人们对客观外界进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各种修辞格也便是基于人类对客观外界的认知加工而来。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是语言表达的内在工作机制。从这一观点出发,认知自然也是各种修辞格的工作机制。
我们认为,鲁迅作品中变异仿拟修辞的认知机制包括图形—背景的突显、意象图式以及类推等三种。读者可以通过这三种认知机制更好地理解鲁迅作品中诸多形式各异、新颖奇特的变异仿体,以及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学素养。
(一)变异仿拟修辞中图形—背景的突显
可以说,鲁迅作品中所有变异仿拟修辞的生成和理解都离不开图形—背景的突显。[注]图形—背景分离的观点是由丹麦心理学家Rubin所提出。就是说,人们通过知觉来选择和辨别注意的对象,将其从其他信息中分离出来便成为图形,其余的信息则褪为背景。他还设计了著名的“人脸/花瓶图”。突显原则的认知基础,就是人类所具有的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Langacker认为:“从印象上来说,一个情景中的图形是一个次结构,人们在感知上赋予其较之其余部分(背景)更‘突出’的关注,作为一个重要的实体它被给予特殊的突显,情境围绕它而组织,并为其提供环境。”[注]Ronald W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20.我们也可认为,事物的突显或选择何种突显与人的主观认知因素有关。根据这一原理,在读者理解鲁迅作品变异仿拟辞格的过程中,发生语义偏离的仿体比本体获得更多的关注从而在读者的认知中得以突显,仿体中发生改变的成分是图形,其余部分则褪为背景。图形获得更多的关注并得到突显,其所代表的语义和语用信息也随之得以突显。若读者能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发生改变的成分,将会提高其阅读鲁迅作品和理解变异仿体新义的效率。
(二)变异仿拟修辞中的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是认知语言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注]李福印:《意象图式理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简单来说,意象图式是基于人类经验所抽象出的、具有某种特定结构的完形。这一完形所对应的结构或信息可映射到另一类似的事体或事物之上,从而在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建立联系、对事物的形象“查缺补漏”并对语言表达赋予新的意义。鲁迅在其作品中将变异仿拟修辞本体对应的意象图式映射到仿体上,并对其发生“完形功能”,将其意义的残缺处补充完整,并赋予其不同以往的新意义。这就是本体和仿体之间建立映射关系的过程。例如:“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乍看之下,“狭人”是一个生造词,属于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因此,该仿体的意义理解需要借助其本体的意象图式。“阔人”中的“阔”,其对应的意象图式除了包括有钱有势,还包括宽阔、宽广等。这一意象图式被映射到仿体中,其“完形功能”得以发挥。形式上,“狭人”中的“狭”便是基于与“宽阔、宽广”对立的语义而来,但是语义上影射的是帮闲文人,从而讽刺了“阔人”身份的统治者。语义上,阔人本义为富人或有钱有势的人,那么其中成分“阔”的意象图式应强调的是“富有”,其对立词应为“穷人”。然而,在该变异仿拟修辞中,鲁迅突显了“阔”所对应意象图式中的其他方面,即“宽广”,映射到对立语义的仿体中变为“狭窄、不宽广”之义,形成仿体“狭人”。鲁迅在文字创作中对于意象图式的发散性应用和扩展,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创新写作方式,更是他对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三)变异仿拟修辞中的类推
类推,又称类比推理,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索绪尔认为“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必须有一个模型和对它的有规则的模仿”。[注][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6页。类比推理大量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语言当中,究其根源离不开象似性原则,即客观外界中万事万物所具有的普遍联系性。类比推理既具有类聚性又具有对比性,并因此成为语言创新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人们对新事物进行概念化的体现。在变异仿拟修辞中,本体的既成形式和结构通过类推而附着于新事物之上,从而形成仿体。这也是仿体意义产出和理解的过程。本体和仿体的关系既可以是基于语义相近的类推,也可以基于语义相对的类推。此外,鲁迅作品中基于数字类推而来的变异仿拟也比较常见。例如:“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注]鲁 迅:《鲁迅全集》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
如果读者在理解鲁迅作品时能动地发挥这三种认知机制的作用,则可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一代语言大师对于语言文字灵活创新的运用。同时,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也可仿效鲁迅作品中各种变异仿拟修辞甚至其他变异修辞的使用。鲁迅作品对于现代文学甚至于民族语言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姑且不论他在作品中创造出的众多新词,单是这种文字创作的方法已是让读者获益匪浅。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