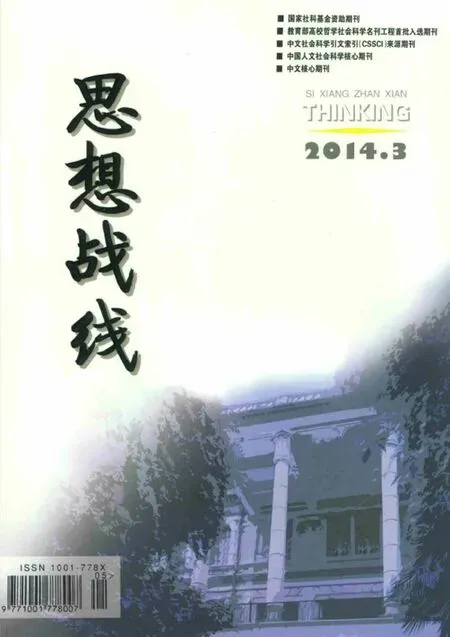“常情善性”:孟子人道思想的本根
鲁建辉,陈学凯
先秦诸子从来没有离开情欲谈论人性。可是秦后的两千多年,人们对情、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多顾此失彼。
一、对情性认识的历史回顾
春秋时,晋军主帅栾武子答复欲与楚军作战的将士,讲“夫善,众之主也”,[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1《成公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4页。认为欲当从善。孟子讲“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孟子·告子上》)善性本是人之常情的表现,可以通过才能外显。如果有了人之常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庄子说众人不知如何滋养情性,故“离其性,灭其情”(《庄子·则阳》)。郭店楚简有“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由外及内讲了道、情、性、义四者间的关系。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认为性、情、欲三者关联相通。
自秦建立君主专制以后,思想家们推崇禁欲主义,高度配合政治权力。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比照阴阳二分,区别了情与性。认为人性未善是因为有情欲,“谓性已善,奈其情何?”建议“损其欲而辍其情”,[注]苏 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0《深察名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98页、第296页。强调抑制贪得无厌的情欲。之后300余年至汉末,皇权独尊,使儒术成为紧固情性的镣铐。随着天下三分,魏晋时代来临,皇权高压略减,人们压抑太久的情性蠢蠢欲动。何晏讲“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反民情于太素”。[注]萧 统:《文选》卷11《景福殿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2页、第537页。他一面主张人们至情素情,一面认为“圣人无情,无喜怒哀乐”,王弼却非常反对,讲“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注]王 弼:《王弼集校释》附录1何劭《王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0页。认为情是普遍的存在。魏晋人物对情的强调不但表现在口头上,而且积极地付诸实践。这是对汉代儒术教条的反动,对先秦情性并重的回归。当天下再次一统后,隋唐重走汉代的老路,再次鞭挞情欲。在《五经》注疏中,孔颖达把人欲直接等同为贪欲,又把贪欲直接视为人情,“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性别矣”。[注]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47《乐记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69页。他认为政治的功能就是消除情欲对天道人理的威胁,一是教化善性,“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须人君教之”;[注]阮 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12《洪范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9页。二是压抑情欲,“裁制人情以礼义”。[注]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48《乐记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02页。佛教在唐代异常兴盛,佛性说即佛教的人性说。流行甚广的禅宗,大意不离“去欲见性”之旨,惠能所留《自性真佛偈》有“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注]魏道儒:《坛经译注·付嘱》,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5页。佛教一面力主绝去情欲,见性成佛;另一面极力宣扬“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注]龙 树:《大智度论》卷27《释初品中大慈大悲》,南京支那内学院,1929年,第351页。佛法也正是凭借慈悲情怀感动世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然而把情性分裂开,性善情恶已经成为当时的强势话语。李翱的复性说在反佛的同时,吸收了佛与儒共通的地方,在论述性情关系中,提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注]董 诰:《全唐文》卷637《复性书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33页。情性虽然互动相关,但情更多地起副作用,所以分离和抑制情欲就成为善性的重点。宋代最有先秦遗风的理学家,莫过于张载。他力倡实学,反对虚言情性,更反对情性分裂、情恶性善的观点。他崇尚情,提出“天地之情”和贞情说。在解释《乾文言》“利贞者,性情也”时,说“以利解性,以贞解情……利,性也,贞,情也……情尽在气之外,其发见莫非性之自然……情则是实事,喜怒哀乐之谓也”,认为民性以利为要,情与性互为表里,情实性真。又说“五常出于凡人之常情”,批评佛老之说“遁辞者本无情,自信如此而已”,最终提出“心统性情”。[注]章锡琛:《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3页、第78页、第264页、第314页、第338页。程颢在《定性书》中讲“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人之情各有所蔽……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注]程 颢,程 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461页。此语有两个要点,一是人情必有遮蔽,所以未善;二是怒情不好控制,发作则忘理,所以最好制怒。抑制人情是核心要点。这与张载的重实顺情大不相同,然为朱熹“明天理,灭人欲”[注]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学六·持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页。之说铺平了道路。《四书集注》中,朱熹把天理人欲的观点灌注到性情说里。他认为学者当“以克人欲存天理为事”。[注]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1《论语·雍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3页。将理欲矛盾推至极端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注]程 颢,程 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2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1页。一语,虽是程颐提出,但经朱熹综合编定,加以推广,至元、明、清时被奉为金科玉律,影响极大,成为束缚民众情性的一道沉重枷锁。清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过度之处做了猛烈抨击,直斥其人“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反对假道学以“意见”为“理”,乃至“后儒以理杀人”。戴氏充分肯定了人的正当欲望,重视人之常情,讲“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将情欲统一于人;以情、欲解理,“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凡事“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从根本上打破了理欲二分的桎梏,回归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注]戴 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第188页、第327~328页、第265页、第328页、第275页。这样一条合情合理的亘古坦途。
两千余年来,主流理论割裂情性,直接导致普通人的情性受到严酷地限制和压抑,君主们却由于拥有特权,几乎不受这些理论的约束,情性放纵到了极致。绝大多数人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铁钳捏为一个个泥偶,谈不上多少生趣,人的创造力随之消失殆尽,麻木不仁,生机不盛。至清末,国土遭列强瓜分,生灵涂炭,贫弱不堪,作为民族之根的常情善性枯萎凋敝。有鉴于此,今人可借助孟子,重识常情善性,以其为思想武器,保卫生机盎然的权利。
二、合人道而生的常情善性
人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情性随之逐渐化生。从物种起源上讲,人从动物演变而来,不可避免地带有兽性。当兽性和人性对称时,兽性代表自然、原始、恶,人性代表社会、进化、善。人的真正飞跃是,在兽性之上发展出了人性。大趋势是人性越来越多,兽性越来越少。至战国中期,孟子认为,虽然现实中的人心人性非常复杂,难于揣摩,但可以通过四种常情,对应人性的四个开端来把握。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常情,与人性中的仁、义、礼、智四个善端,对应统一于人心。认为一个人有常情善性和有四肢一样的自然,它们都是继承而来的。进而人性和兽性有巨大的鸿沟,“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犬牛所代表的兽性,与人的自然性虽然相似,但也有差别。犬牛这样的动物,食是生命的主要意义。可是人不同,即便饥饿难耐,也不会“殄兄之臂而夺之食”(《孟子·告子下》),原因在于人的自然性是升级状态,其中已经凝结承继了前代的社会性,与禽兽几乎不更新的自然性有巨大差别。进一步,人与禽兽在社会性上表现出更大的差别。兽求生存无所谓善恶,但人求生存就分别善恶。合于义,有善性之端,面临祸福时,可以依此做出趋避生死的抉择,“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渴望常情善性,超过渴望生存;厌恶异情恶性,超过厌恶死亡。正因深知此理,所以孟子言必称尧舜。甚至他直斥墨子、杨朱这样的思想大师,“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认为极端的无私与极端的自私一样,都容易藏奸纳垢;不懂得亲亲长长,总以虚假或片面的情性来代替常情善性,不能算人。从客观、综合评价人的角度来讲,孟子的“禽兽”断言显然是荒谬的。但他正是以这种荒谬的语言,警告人们,要把禽兽与人截然分开。在孟子的人的世界里,没有给禽兽留下任何余地。只能是保留人性,去除兽性。性善只是讲人,而且一定是抽象意义上、类别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有恶、兽性、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在特殊时空下,甚至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孟子恰恰是以人性善为武器,向兽性恶发起攻击的。他不承认人性不善不恶、无善无恶、善恶相混,更不会承认人性恶。在孟子那里,善恶如黑白一样分明,拒绝恶越是严厉,迎受善越是笃定。孟子认为人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半兽半人,更不是兽。其发展趋势是:在初阶时,虽然兽性多于人性,但是人性已经产生而且不可遏止;在中阶时,兽性与人性参半;在高阶时,人性多于兽性。到最高阶段,人则进入一个属人的世界,人性得以全面的实现,从而每个人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此时,情性自然常善,真美无缺。在兽性向人性转换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阻碍、困难,甚至暂时的倒退,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拒绝人性成长的理由。人性成长需要开始,不能停止。
从人自身讲,人人都有利欲的需求。利欲是人存在的根基,是维持生命尊严必需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不可须臾离开。孟子认为好货、好色、好勇是人有为的重要动力,关键要归之于常,与民共享。对个人来讲,合情合理的私欲私利就是常欲常利。符合常欲常利的情性必然是常情善性。由此区分出三条路线:常人路线,圣贤路线,恶人路线。恶人路线的典型特征是异情恶性,一种是极端无私,“灭人欲”、“斗私念”,空喊大公无私,必是矫情灭性,如墨徒;另一种是极端自私,肆意极欲,损人利己,同样毁情害性,如杨朱、张仪、公孙衍之流。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思虑不周全和逻辑悖谬的表现。很多人迷惑于一时一地的利益,激荡出大量的异情恶性。在异情恶性的巨大破坏作用面前,人们被迫重新审视原有的情性。对其分析批判后,能够延续人道,符合属性要求的部分,会被保留和发展下去;不再适宜的部分会被冻结或抛弃。那么,新萌发的情性也会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反复产生上述的情况。如此,常情善性来自两个部分:旧情性中可以继承的,新情性中可以接纳的。所以,常人路线和圣贤路线的典型特征都是常情善性,两者境遇和程度有所不同。孔子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求富贵有道时,做赶车的人就属常人路线。得富贵无道时,从己所好的人就属圣贤路线。要之,努力追求自己的常欲,这是人之常情;承认、尊重、助成他人的常情,这是善性。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立欲达欲是人之常情,立人达人是人之善性。这里有一个必然的逻辑顺序,即从己及人,由私而公。此时的公,是有私之公,是有基础的大厦。己存而与人共存,方可成常,成真善美。如果把每个人的常情善性比作一个点,那么,这个点与那个点不必重合,不必大小一样。千千万万个点,构成了整个社会常情善性的主线。这条主线是流动的、有层次并波澜起伏的。常情善性在人和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形成,跨越时空给人以指示。在孟子心目中,常情善性就是自尧舜时具备,传续下来的人的情性,最能体现人道。
三、常情善性的返本开新
常情善性同人道一样,是与时推移的。这样才能保证,主体在方向上不偏离人道,在精神上不断更新,进而获得创造历史的自由。孟子讲:“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天道本是至诚,人道亦本是至诚。人要得人道,进而与天道合一,至少需两步:第一步,思诚。思诚得人道之端,即人道的逻辑起点。第二步,达诚。达诚得人道之全,是人道的逻辑终点。两步属于一体,但有逻辑先后的区分。两者实现,人道得全;备全人道,合于天道。人要诚于人道,必然要诚于生机;诚于生机,必然要诚于自身;诚于自身,必然要诚于人性;诚于人性要明善,即诚明于常情善性。孟子讲了人道的发端、状态、对象、目标、归宿,即思、诚、身、明善、天道。但天道悬远于人,不能骤然接得,应从人道开始。“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孟子·离娄上》),亲亲长长之类的人事,既容易做,又近在身边。只要人人做好它,天下自然泰平,大道自然可得。结合孟子一贯的说法,可知,常情善性就是道、天道、人道的核心,三者都通过常情善性得以生发。换句话说,常情善性就是孟子人道思想的本根。由此,孟子的诚的“内容”就是常情善性,思“诚”就是思“常情善性”。人只有诚成于常情善性,方能诚成于自身人伦,方能得达人道天道。“诚成”的功夫在于“充实”常情善性于己。孟子曾评价弟子乐正克是善人、信人,还有待提高。他讲:“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常情善性可欲,故可称之为善。常情善性得于己身,他人安心不疑,故可称之为信。常情善性在己,久而不懈,充实无缺,则己美矣。常情善性是道在情性上的展现。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新、旧事物的交替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人的新、旧情性中的精华和糟粕,往往也混杂难分。以异为常,以善为恶的极端情况多有出现。所以,择善固执,不驰心旁骛,洞悉常情善性的“四守”功能非常重要。
第一,守常。常不是平庸,也不是偏激,而是长久的中和。它既符合人的认识要求,又能指导和支持人的行为。战国时,墨家纪律严明,但教人过于俭刻,久处贫困不合常情,其道难以长久。杨朱强调个人是一种自然的独立存在,与他人是平等的,互不侵犯。这是反抗等级制和人身依附最为激进的思想武器。但杨氏平等,是一种互不关心的平等,无视社会性的平等。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两者都片面重视人的个体性或社会性,都只强调了常情善性中的一个方面。虽然片面的东西可以深刻、犀利地揭示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但是若用于全面的状况,必然招致谬误。社会性与个体性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都无法成长立足。
第二,守道。常情善性本来藏而不露,是人道自然和必然的表现。它的存在,对异情恶性的膨胀与扩张,始终起到抑制作用,能够防止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在国人的心目中,善永远是主流,恶永远是支流。由于异情恶性一直受到常情善性的抑制,恶事恶人也就一直没有强大到毁灭国人的程度,国人及其文化也一直存续至今。这至少说明:1.异情恶性在某些时候,确实非常强大,压迫得常情善性难以作为。2.总体上,常情善性还是胜过异情恶性。所以,国人总能在危亡关头,返而复安。由此得到一个根本性结论,常情善性和常人的存在,是社会延续和发展至今的关键。
第三,守衡。它需要人们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不过头,也无不及。常情善性理念的萌发,导出了后世两千余年儒者的处世原则:无论社会如何不堪,总愿“救之使安”,而不是“推之使烂”。儒者在面临旧事物的消亡时,总是力图使其中的精华得以继承,总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对人产生过大伤害。如果伤害不可避免,也总是力图通过改良旧事物的办法,降低其衰亡的烈度,从而使处于其中的人,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新事物。所以,儒者通常较为保守。迎接新事物的到来,顺应历史潮流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人为的拔苗助长会带来重大伤害。即便是新事物,也不是人的目的,不能为了新事物而新事物。更不能以其为名,伤害社会中的人。人的目的是人,既要迎接新事物中的人,又不抛弃旧事物中的人。
第四,守德。德,得也。常情善性,对人对己,于心于物,都有利有益,能实现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进而,常情善性可作为自检和检人的标尺。它发于修身,常情善性具于己,则自足。自足则邪不能侵。遇到他人的不足或过度,则可产生映照和影响。它发于政治观念,在孔子,就表现为努力维护鲁国公室,贬抑诸大夫;在孟子,就表现为愿时君行仁政,无论是邹、鲁之君,还是齐、魏之王。它发于经济,梁惠王所言“有以利吾国”(《孟子·梁惠王上》)实指“何以利我梁惠王”,孟子知此,故深否之以“何必曰利”。若梁惠王言“何以利吾民”,孟子必然赞叹,大讲恒产井田。对于自检和检人,曾子讲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其实,忠恕的比照原则和内容,就是常情善性。忠者,忠于常情善性,忠于人道。对于违背常情善性之人、事、言,则不必忠诚,否则为愚。恕者,以常情善性为恕,以人道为恕,不是一味宽容,乃至放纵,以至于溺情害性。自己具备常情善性,别人无有,则推己之常、善达至其人。
总之,具备常情善性的常人是社会的栋梁。孟子思想中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性善说”、“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以及其中蕴涵的常情善性、常人观念等精华,都可汲取。当今社会分工体系的精密化,人对人的依赖高度增加。人人在自己掌控的环节,可以扮演关键先生,影响乃至决定他人的性命,这也倒逼着人们必须具备常情善性。如此,对个人来讲,成为常人,离不开常情善性、人道思想、自我担当。对社会来讲,发展常人观念,促进思想转型,不必是圣人,亦不必是超人,而必然是千千万万个常人,来完成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之路的寻找与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