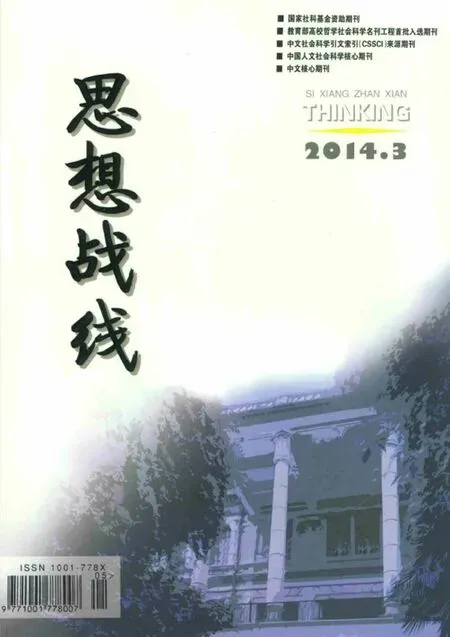“文化现代性”的实践伦理与精神生活的正当性逻辑
——现代个体合理的心性秩序吁求何以可能
袁祖社
20世纪80年代社会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实践进程中,与经济高速发展、财富急剧增长相伴随的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现状以及所致根由究竟如何评判?长期以来,文化的研究者迫于新颖的研究视点的缺乏,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现实的解释处于无力、失当和主体性建构方面的无名、无由境地,于是只能简单和现成地借用西方学者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和范式。于是,我们看到了被过分陈示和渲染着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潮的泛滥,看到了用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来评价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苍白。先进文化引领下民众优良心性心灵秩序的养成问题被边缘化,陷入无力自救的“自我放逐”境地。
一、伪“意识形态”对文化灵性的主观钳制:中国式“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实践与精神生活的深重病症
自19世纪40年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后,中国开启了筚路蓝缕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对文明演进逻辑判别和把握的乏力,更由于知识界缺少高屋建瓴般的对新历史理性引导下新制度设计和对中国社会未来演进方向预测的足够准备,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程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波澜,甚至几度陷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原因很简单,我们所选择和坚持的,是一条可以被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政治国家片面强调所谓“社会现代化”(物质和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坚持传统的意识形态理念,不愿意以兼容并蓄的胸襟与气度,与主流文明保持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对话张力,拒绝推进和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有关“现代性”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撇开诸多表象层面的无谓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社会现代性的进程,本质上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新生的世界历史主体在摆脱了宗教的、等级的压迫和奴役的过程中,遵照“世界精神”的逻辑,力图开展“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自己”的运动。因此,现代性向我们所彰显和呈示的精神生活逻辑一定是“主体性人学”的逻辑,是解放和自由的逻辑,是人性自主、人权保障的逻辑。现代国家在谋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为了某种借口,曲意违背“现代性的逻辑”,那么,这种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定会陷入精神生活缺失和前进方位严重缺位甚或迷失的境地。
不仅如此,在人的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与生存空间自由度不断延展的意义上,文明进程中的“现代性”,同时还意味着如德国社会思想家滕尼斯所谓从“共同体”(宿命般的定在,人一旦离开和丧失,就很难回复其中)到“社会”(集体理性自主建构的新的定在)的转变。而从“共同体”到“社会”,就是现代公民社会诞生的标志。公民社会为现代人的“自由结社”从而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自主、自觉展开,提供了充分必要的前期预设。不难想象,如果一个社会一味强调在经济生活和物质层面上“全面的现代化”,但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依然是总体性“同质化”的,没有或者不愿意促进英国法律思想史家梅茵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实现,普通民众的“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等处处受到严苛的限制,这样的社会以及精神生活一定是残缺的、非健全的。
由片面的“社会现代性”所导致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异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具体表现就是:包括一代中国民众在内的“现代人”在精神和生存信仰方面,普遍缺乏扎根于“心灵整体”的那种深刻的“知性”:他们有情感和欲望的躁动,却没有心灵对世界、对存在、对自我的敏感与感动;有悟性,却没有灵魂;有对物质、性欲、感官快乐的无穷无尽的知性,却没有对生命存在、对人的存在的“自神”、“自圣”的精神向往;有物质幸福论和感性快乐主义的忙碌活动,却没有普遍的伦理理想和道德欲望。生活在当代处境中的人类,内心躁动着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理想和绝对经济技术主义浪漫情怀,其生存的目光始终投向当下、投向现实、投向实在的利害得失,因而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看世界和人、看事物和问题,即一方面按照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图式而谋求生存,另一方面又按照不属于任何时代而只属于适合于自己的图式来谋求生存,物质—性肉主义和感官—享乐主义构成了当代人类的存在精神,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构成了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信仰。无所不在的“征服”和“占有”的欲望成了人们获得、体验幸福、快乐和享受的惟一手段。
2012年12月23日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节目,以“中国的国民精神”为主题,围绕“在国家经济建设,国民物质财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中国国民应该有怎样的心理精神状态?”这一话题,邀请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作客《听风录》,从中国现阶段国民精神状态出发,对照后发国家,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民主崛起时期,国民的精神世界成熟问题。参与对话者明确认定,中国崛起一方面令中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极大增强;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有一些“鱼目混珠”和思想混沌。而在国际历史上,“由于缺乏民族精神的集体洗礼,崛起期国民精神状态的混沌很容易走向反面,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就很值得人们研究。同时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相当的复杂。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既有理性的,也有情绪化的,所以处于一种高度混乱状态,有高度的不稳定性,有高度的异变状态”。[注]杜 平:《中国国民精神处在高度复杂状态》,参见2009年12月23日凤凰网、2009年12月24日凤凰电子周刊。
如欧洲启蒙思想家所认定的那样,精神生活的本性和品质,一定是学者们称之为“自由”的那个东西的现实化。如果公民社会的个体的思想始终受制于强大的意识形态的钳制,所谓心性秩序的形成就因为缺少了必要的前提,而只能被外在赋予(所有智慧公民都认识到,这样获得的心性秩序是何等虚假和缺少实质性内涵)。这种心性秩序,绝对不是一种有机性,绝对不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开放体,其可持续性也是大可怀疑,是根本靠不住的,也是不值得认同和践履的。事实上,践履一种违背现代个体优良心性秩序本性的精神生活规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二、直面精神生活的失度与“粗鄙化”:实现由“社会现代性”向“文化现代性”的艰难转型
现代化历程开启以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塑造民众的心智问题。如果现代化的过程,是那个曾经塑造了民族精神气质、精神风范和民族气节和风骨的心智模式的被同化,这无疑是最大的文化悲哀。尽管这种情势早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初次相遇时,由于我们文化之动能和势能的明显劣势,就已经开始发生,且一直在持续着,情形未有多大改观。应该说,面对这种情形,许多中国文化与知识界学人不愿或不甘心承认和接受。
现代性自身本有的“双重”涵义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注意。对于现代性的真实内蕴,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按照公认的看法,第一个比较准确地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人、批评家波德莱尔,他在1863年写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如此,现代性被描述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时间意识”;[注]转引自[英]艾伦·斯温伍德《现代性与文化》,汪 伦译,载周 宪主编《文化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直接坦言:“现代性是一种宏大叙事。”在鲍曼眼里,作为现代性,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心理体验”;吉登斯则从社会结构合理化进程的视角,将现代性归结为“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等。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带有复数性质的概念,就其内容构成而言,“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注][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质言之,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方面,一是“文化心理”方面。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自从18世纪终结以来,现代性话语已经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主题,这个主题有若干非常新颖的名称:社会纽结力量的削弱,私人化和分裂——一言以蔽之,引起宗教的统一力量的某种等价物之必要性的片面理性化的日常实践的变形。”[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刘 东,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令人遗憾的一个不争事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接受、践履“现代性”理念并为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实践辩护的过程中,都没有能很好地理性规划和实现现代性两个方面之间的“有机耦合”。
研究现代性的学者并且注意到了一个由哈贝马斯最先发现的属于“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其具体表现是:1.由于“理性自身”的分裂所导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和冲突;2.由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所不可避免地导致的“人自身的严重异化”;3.普遍的“世俗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以“意义的失落”、“信仰的迷茫”等为标志的人文理性追求的丧失。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学者钱永祥先生对照哈贝马斯的思想贡献和启迪,对“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差别,做出了义理层面的甄别。钱先生指出,现代性不仅不同于单纯的现代化,并且由于文化现代性具有反思与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特色,现代性内部其实涵蕴着丰富的批判能量。[注]参见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原文刊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第37期,载贺照田主编《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问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哈贝马斯发现,尽管韦伯明确掌握到了现代性问题的起源(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趋势在世俗世界的延续),却由于概念架构的限制,他将‘现代’局限在‘社会现代性 ∕社会理性化’(societal modernity / societal rationalization)的面向上。结果,韦伯心目中的现代,等同于目的∕工具理性所界定的理性化,也就是单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官僚国家所呈现的现代。 相对于‘社会现代性’,哈贝马斯建议我们正视‘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的历史意义。”[注]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原文刊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第37期,载贺照田主编《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问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钱永祥先生仔细梳理了哈贝马斯意义上“文化现代性”的蕴含与意义。“在哈柏玛斯的心目里,文化现代性——以及随之而生的价值领域的分化——的重大意义,在于自然、社会、与主体内在这三个世界得以独立地发展出丰富的文化意义。……在文化现代性之 下,价值与规范必须由当事者藉沟通自行提供正当性。”“哈柏玛斯的现代性概念强调,在传统的、形上的、或其它种类的规范基础流失之后,文化现代性指向一种用后传统、后形上、后理性主义的方式,建立引导性的(regulative)价值理想的可能。这也代表一种建立内在的批判标准的可能。这种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虽然内在于特定的实践活动,却由于不是任何特定实质传统的禁脔,又对挑战与对话保持开放,它们具有超越一时一地实践脉络的普遍性。”[注]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原文刊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第37期,载贺照田主编《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问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第5页。钱先生引述的哈贝马斯的文化现代性用语中所谓“自我正当性”,依笔者之见,就是社会现代性实践过程中必须被关照的现代个体“精神生活的正当性”,就是对现代社会个体如何过一种优雅、体面、有尊严的精神生活之必要性的吁求。因为,当社会现代性(结构合理化过程)被等同于社会现代化(以对财富的片面追求为表现的发展实践)以后,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心完全倒向了财富增长最大化,没有人愿意花费心思去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
精神生活的内容本质上是丰富多彩的,有层次的。但是,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活却被简单地认定或被理解为是对某一种确定的经济秩序或者政治秩序的认可。中国式现代性具有的鲜明时代性内蕴,充当着一种需要辩护的精神生活之当代性内在特质和逻辑前提。如上已述,中国式现代性充满了或者一直充满着权力主导下文化和道德实践的恶。我们没有在关键点上按照现代性文化理论和实践所要求的方式,实现和证成属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新基础的现代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如下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追问:社会现代性进程中那个有独立人格和精神气质的“我”和“我们”在哪里?“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吗?“我们”形成了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相适应和相匹配的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精神生活”了吗?谁的现代性?何种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的无序,个体自我实践的困难,精神生活内容的犬儒化,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使得很多思考精神生活秩序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眼光和重点投向“精神生活本身”,开始严肃思考所谓精神生活的“粗鄙化”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就指出了弥漫于精神生活中的一种不断扩散的深重病症:“普遍粗鄙化。”邵燕祥注意到,“粗鄙化的背后,是官僚气、市侩气、流氓气的沆瀣一气(惟独没有“士气”即体现文化命脉的正气),弥漫在官场、商场、市井以至穷乡僻壤” 。[注]邵燕祥:《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书摘》2001年第1期。2013年4月号的《中国周刊》的封面报道“粗鄙时代”的编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粗鄙为荣,是一种暴发户心态,流氓无产者心态。”
三、致力于“天道”与“人道”有机合一的“公民性”实践性伦理:民众优良心性/心灵秩序的合理性诉求
当社会因市场化体制的实施,全球化场景的合法化,以无可逆转的趋势进入准文化多元建制的时代,那么,不同价值主张的文化思潮,就完全获得了平等共生、民主共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属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性的伦理精神势必出现悖反——以看似更为道德化的方式反对和阻滞精神生活的道德化。于是,“精神生活正当性”变得非常可疑。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对于现代性社会精神危机的动因、机理和实质,有深刻的剖析和精湛的见解。依照他们的识见,精神危机的根由,在于社会精神体系发生病变导致个体精神体系产生病变,即所谓“潜意识”、“无意识”、“前潜意识”世界出现机能障碍。由此所导致的人的安全心理体系决裂,感到生存的周遭危机四伏,因而出现恐惧、漂泊、隔离、孤独、焦虑、反抗等情绪,幻灭感控制着人的心灵。
整肃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秩序,拯救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必须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以现代性“公民性”实践伦理的名义,化育并逐渐养成现代个体优良的心性/心灵秩序。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杰出著作《爱弥尔》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对于上述问题应有的理智性、前瞻性卓识:“人的心灵之所以有其特点,正是由于观念形成的方式。能够按照真正的关系形成观念的心灵,便是健康的心灵;满足于表面关系的心灵,则是浅薄的心灵;能看出关系真相的人,其心灵便是有条理的;不能正确判断关系真相的人,其心灵便是混乱的。”[注][法]卢梭:《爱弥尔》,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76页。虽然,此处卢梭对于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关系”,如何“关系真相”以及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判断关系”等,语焉不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卢梭所提示的思想方式,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式现代性理念的自主建构实践中,寻索民众优良心性/心灵秩序生成的合理方式和路径。
没有人否认,当现代性文化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伦理社会,传统思想和文化规制中那种曾经异常自信的形成中国社会个体心性/心灵秩序的方式和有效性遭遇严重挑战和颠覆。当曾经威严无比的道德规范被严苛的法制化信条一一取代以后,似乎作为社会精神生活之核心内容的心性秩序的内蕴,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对外在的法制的单一遵从和信仰。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因为人的尊严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对来自心灵深处的内在秩序的寻求和自觉遵从。传统中国之儒道传统非常推崇所谓“心性之学”, 心性之学、性情之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成为显学和主流,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那么,古代中国学人为什么能够将其学问用心的方向,合力凝聚在“匡扶时弊,救正心性”这样一个专一的共同问题上?
先秦儒家所谓“心”,由“性”和“情”构成。儒家称之为“情识之心”。其中,“性”为“心的本体”,是人人均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资质;同时儒家认为这种“人性含灵,待学而成为美”。[注]裴汝诚等:《贞观政要译注·崇儒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页。此处“灵”意即为“善、美好”,是指一种自觉的精神状态。儒学经典名言,人性之灵源于“天命”,“灵”类似于孟子之“端”,为“善”之才,是一种“见德思义”、“闻善而徙”的道德能力。从进一步的学理渊源上讲,在儒家观念中,人的本性是“至善无恶,至粹无暇”,但因受“气质之性”的剥蚀、逆转,以致丧失了“至善本性”,出现了种种的“过”,甚至沦为“卑鄙乖谬”的小人。受心性之学之学术风气影响的几代儒家学者,也多是立志要“匡正人心,就正天下”。以“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顒为例。他明确认识到:“天下治乱,由于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于学术之悔明”,“故学术明则正人盛,正人盛则世道隆,此明学术所为匡时救世第一要务也。”[注]李 颙:《二曲集》,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第93页。不仅如此,“主持正道,就正人心者,责不在君贤相,即在吾儒”。“无人发志立愿,须是砥德砺行,为斯世扶纲常,立人极,使此身为天下大关系之身,庶生不虚生,死不徒死。”[注]李 颙:《二曲集》,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第76页。
依照英国著名文化学者英格尔斯之见,“文化是为社会的精神生活提供和甄别道德标准的”。[注][英]英格尔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页。或问:为什么总是希望文化承担起某种拯救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性使命?为什么人类精神生活重建的诉求总是要归置于文化个体优良的心灵秩序的达成?优良心灵秩序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其实就是一种后天养成的“本能”。一如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样,它俨然就是一种不需任何人提醒的习惯、一种深厚的教养、一种自觉的人格特质和境界与修为。但是,反观漫长的中国历史,我们难免疑惑:中国人拥有和体验过这种优良的心灵秩序吗?中国文化有过这种建构的成功实践吗?
传统社会以及制度文化设计,显然无法培育出作为现代社会优良心性和心灵秩序之有效载体的“公民性”特质。“公民性”英语为“civility”,也可译为“公民品格”、“公民属性”或“公民精神”等等。依照当代美国学者希尔斯的说法,所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体现公民性(civility)的社会”。[注]Edward Shils,The Virtue of Civility: Selected Essays on Liberalism, Tradition, and Civil Society,Steven Grosby,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7.引自[美]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李 强译,载王焱等编著《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86~305页。希尔斯提出了“公民性”的3个基本内涵:1.关怀整体社会福祉的一种态度;2.共同体成员自身所拥有的“良好风尚”;3.自我意识被集体性自我意识(collective self - consciousness)部分取代时的一种行为。当代中国知识界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创制新的精神文化之能力的严重欠缺,我们面临着因模式、话语逻辑的平面性移植、模仿而产生的精神生活的“魅影化”现象,使得现代个体处于无名、无着状态。我们这个时代因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并不断被各种力量阻滞,因此缺少一群为了某种崇高的文化理想而坚守的积极理性的“知识公民”,缺少一群为“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真理得以呈现的“守道人”、“护道人”。心性秩序的漂移不定,导致的是精神与道德价值追求的无所依托。如果中国人的心性秩序完全等同于(我们也清楚地明白,在文化与文明发展的现阶段,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完全不可能)美国人、日本人等,那么它所带来的就是文化的无差异化存在。或问:我们究竟因何种担心而不能或者不敢固守一种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精神生活方式呢?
文化的性质各不相同,文化的类型千姿百态,文化间的差异更是人所共知。对于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代之不同的文化实践样态及其结果,文化的接受者只能是“解释”,而无法期望形成一种传统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统一性图景”。那么,文化真是有某种确定的、内在的、永恒的意义吗?或者说文化本身一旦被产生、被实践,就和别的存在物无有二致,没有或者放弃了按照文化自身本有的方式成为自己的要求,文化的产生和与生俱来的使命是提供、建构某种意义?还是要不断地消解和疏离某种意义?或者文化自身就是或者甘愿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殉道者”,在以牺牲自己的方式的过程中成就、昭示某种所谓的“意义”?文化在成为自己或生成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某种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深刻的两极冲突。“任何文化,在繁荣、驳杂和精致之后,由于创造力的枯竭,精神的远离和挥霍,文化的各个方向在改变,它被指向实现实际中的强盛,使实际生活变得有序并在地球上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扩展它。‘科学与艺术’的繁荣,思想的深入与精致,艺术创作的高涨,圣者和神祇的直观——所有这些都不再作为真正实在的生命被感觉,所有这些已不能鼓舞人,应运而生的是愈益紧迫、争取‘生命本身’的意志,即争取实践‘生命’、强大‘生命’、享受‘生命’、主宰‘生命’的意志。这种过于紧迫的追求‘生命’的意志危害着文化,给文化带来死亡……人们太关心‘生命’,希冀建设和组织文化没落时代的‘生命’。”“文化并非要实现一种新生命、一种新存在,文化要使若干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见诸实现。所有的文化成就都是象征性的,不具有实在性。”[注][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70~171页。“任何文化,当它发展到相当的阶段,破坏文化精神的本质就开始显露出来。文化与崇拜不无关系,文化从宗教崇拜中得到发展,是崇拜异化的结果,它把崇拜的内容推广到不同的方面。”[注][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加速行进中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在精神文化方面究竟应该有何种作为和历史性担当?有学者指出:“文化总是要具体化为制度的建构与批判,伦理的反思与变革,精神模式的转折与更新,如若不然,文化就不仅具有海市蜃楼般的虚幻,而且充满了腐朽气息。”[注]宋玉波:《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当中国的现代性刚刚发生,需要在辩护、反思的理论实践中促进其发育、完善、成熟、壮大的时候,却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现在看来大多是不着边界的无谓的严重的“批判”。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长期以来,一代中国学人已经习惯了总是用西方学者在几百年前批判西方文化的方式反思中国的文化现实。符合人类文明正道的人类精神的成长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意味着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成为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匹配,且符合人类文明大道的真正“思想的主体”,不被迫盲目地受制于“他者”的话语,开始大胆地“说自己的话”。
精神生活一定是为了某种意义的,而民众优良心性秩序的养成,同样必须被某种确定的“意义悬设”所引导,精神生活的主体必须以此为参照获得生存的方位和确定感。没有“意义体验”为主导的精神生活,谈不上所谓“品味”。但问题是,这种“意义”具有太大的、太多的主观性,因而经常是变移的。客观上讲,这种意义其实从来没有获得过多少确定的品质。现实中,民众心灵秩序可以完全被“政治话语支配下的意识形态”所模塑,中国社会以及普通民众在20世纪60年代可以完全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引导,就是一个实例;一个时期又可以被“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财富最大化”的自由主义话语所引导;当中国社会完全进入现代性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市场化社会以后,人们又会被后现代思维引导下的思想主张和话语逻辑所支配。
当市场化社会之自由主义迷蒙破灭以后,当“无我”的“虚假的共同体”的秩序被证明是一种伪建制以后,沉思、寻求并确证精神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试图找到足以使我们对作为精神生活之灵魂的那个东西的应有的敬畏之心。当代社会精神生活之最大的悲哀,可能就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东西。过一种严肃的庄严的精神生活是否可能?注视并直面“完美、高尚”的神,获得一种纯粹的“自我意义体验”是完全不可能的吗?这一观点可能令许多精神文化的从业者们感到疑惑以及疑惑基础上的愤慨和不理解,并且出于应对和辩驳的需要,必然会引经据典,提供许多看似确凿无比的经典案例,做必要的自我辩护等。学者苏国勋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的开篇引用过里尔克的诗句:“这样的人,总在这样的时刻现身/行将终结的时代,再一次结清了它全部的价值/于是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负,把它抛入自己内心的深渊。”[注]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当今中国社会,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背负传统,并在“内心的深渊”重新奠定传统根基的人。而这意味着我们该“如何将散失在日常生活角落中的传统重新转化为亲切贴己的生活之道这一真正艰巨的伦理任务,重新赋予被外在的技术理性化洗劫的伦理生活真正的‘神’(ethos )”。[注]李 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当精神生活的神圣性不断遭遇市场化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与商业合谋的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遭遇世俗社会的利益的引诱,使得精神生活领域无法形成一种“自性”的品质而被迫自我沉沦甚或甘愿自我放逐以至于堕落时,当许多曾经信誓旦旦的“知识人”在利益面前说出“茅台酒添加塑化剂不会影响人的健康”、“李天一案社会影响非常小”这样的言论时,当精神界开始变得猥琐而不堪时,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大喝一声:“请尊重我自由生存的空间!”“请停止对于我的精神世界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