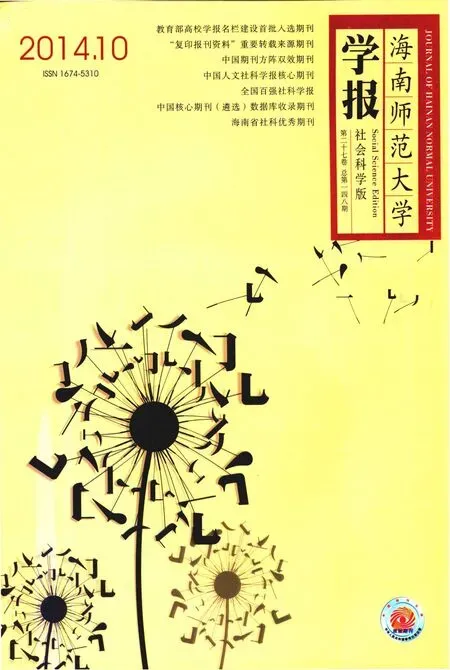权力宰制下的狂欢化叙事——读阎连科《柳乡长》
张 童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阎连科自1979年以《天麻的故事》登陆文坛,眼光始终盯牢乡土,不管是写军人还是农民,他都遵循自己内心的现实,描摹“本土中国”。①王尧在谈到阎连科写作时说:阎连科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语言、结构书写了独特的“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而“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又时常重叠在一起而成为“本土中国”的。(《为信仰写作——阎连科的年月日》,《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 期)。以往对阎连科作品的解读大都围绕生命、苦难、抗争等展开,而忽视了他文本中呈现的政治文化忧虑。写于2003年底的小说《柳乡长》,②《柳乡长》发表于《上海文学》2004年第8 期,文中文本引用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标明。以颇具寓言性的叙述,展现了作家对权力宰制下的民间文化③对于此处民间文化的内涵,文中有论述。的精心凝视。
小说以椿树村和九都市为基本的叙事空间,讲述了在权力宰制下“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柳乡长将全村的青年男女骗到九都市,任其用“原始资本”进行财富的掠夺与积累,从而获取巩固自己权力的资本。民间文化的可鄙处,并没有因为财富的积累而改善,反欲显出顽疾的牢不可破。而这一狂欢式叙事又时刻为权力所宰制,以权力为象征的主流政权充当了这种疯狂掠夺的庇护者,主流话语沦为滑稽的反讽之语,主流价值体系遭遇虚假的尴尬。“乡下人进城”,本质上是为追逐现代文明的步伐(作品中表现为“治疗”贫困的“绝症”),却在半推半就间暴露了其可憎的本相,也宣告了“治疗”的艰难。
一 权力宰制下的“进城”
在进入《柳乡长》文本解读之前,不妨对“乡下人进城”历史叙事简单梳理一番。
社会进入资本化以后,都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问题。在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中,“进城”是叙事的逻辑起点,是表现主题的必然情境。自古中国长期处在城乡同构的传统农耕文明社会,至清末民初城市化发展,大规模的人口动态的城乡空间流动开始出现。《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多部小说讲上海城市的繁华和城市罪恶的一体两面,非常具体地呈现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城乡文化的交融,彼时已经涉及一个事实:进城的乡下人如何安身立命。
自近代以来文学就一直对资本入侵造成的城乡二元互动给予关注,1930年代抗争以前,现代文学不断出现描写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的作品,大都从阶级压迫、资本入侵、社会动荡的角度展现他们在社会转型、文化冲突过程中的际遇。30年代农民进城小说显示了作者本人以及作品本身都与中国的社会动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农村自然经济的溃败和个人奋斗的失败。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王统照《山雨》、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等。抗战爆发使描写乡村破败和农民被迫进城的文学暂时中断。建国后的30年里,特别是1960年建立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户籍身份等级体制,形成了农民与市民两种基本身份群体,也最终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限制农村人口进城。其时直接反映“乡下人进城”的作品几乎不可见。值得一提的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敏锐触及特定时代夫妻之间价值观念的冲突。①萧也牧的这篇小说发表以后遭到严厉的批判,被定性为丑化歪曲工农干部、反对工农兵方向。一体化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批判导致“乡下人进城”题材小说被禁,导致这类文学叙事在当时的稀缺乃至空白。80年代虽然户籍制度尤在,但社会发展、城乡差距明显,城市作为一个诱惑,吸引着来自乡村的“闯入者”。“乡下人进城”的模式有《人生》中高加林式的努力“闯入者”,类似的还有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有《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式的“过客”。如果说80年代,众多“高加林们”还在为进不了城而心绪难平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户籍制度的松弛、城市化进城的加快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边缘化与贫穷,使大批农民以民工的身份大量涌入城市谋生,他们是城市生活方式和文明的追求者、城市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又是城市的底层和牺牲者。”②该段话出自逄增玉的发言。见陈军《“乡下人进城”论题的多向度对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 期)。当下小说叙述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已成为表达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个体生命的途径和方式。
《柳乡长》中的槐花和尤凤伟的《泥鳅》中国瑞、蔡毅江、小解等进城农民一样,已经没有了对土地的依恋。大量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有类似的倾向。农民在失去昔日拥有的优势政治地位的情况下,在经济的入侵下,乡村已不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但城市也并非其栖身之地。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乡村一直被作家寄予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向往,它往往是作者的精神栖息地,最早的如陶渊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对故乡美好人、物的描写与赞美是乡土文学主题的一个分支,像废名和沈从文都在作品中展现出对故土的向往,借此抵制目下的都市文化。从师陀到后来的路遥、李佩甫,他们的作品都是在城乡对峙中借助展现自我对乡的眷恋完成对城的控诉。在当下,城市的迅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渐增大,引发了两种文明更大的冲突,导致乡下人在城的不适乃至疯狂。尤凤伟、陈应松、鬼子、孙惠芬、刘庆邦等作家,以城乡之间的冲突来展现城市在现代化进城中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崩塌,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社会被撕裂,人性被扭曲的社会现实。就当下“乡下人进城”这一母题来讲,昔日乡土的诗意早已荡然无存(或许这诗意只残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的乡土想象中),因着现代化进程催逼,乡村正以自我劫毁的方式参与着现代生活。在生活远大于观念的时代,乡村开始呈现“非驴非马”的形态,其发展不仅透支着现代文明成果,也透支着传统文化精神。
当下大量“乡下人进城”小说,由于创作者情感立场的绝对化,叙事策略的雷同化,作品往往充斥强烈的激愤和控诉,无法真正构筑厚重的艺术空间,因此样品多,精品少。《柳乡长》的叙事设置在“乡下人进城”这个框架内,但是与以往同类母题的写作不同,它不再是自虐式地展示进城的遭遇及心理挣扎,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完全是概括性的写作,而用力在“进城”的动作上,这“动作”包括为何进城、如何进城、如何讲述进城。
令阎连科声名鹊起的是那一曲曲“耙耧天歌”,称最的要算《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长篇“三部曲”。他笔下的耙耧山是个宗法势力强大、农民权力崇拜痴狂、生活贫苦的场所,权力渗透在山脉的每一条褶皱里、每一个人的心底。阎连科清醒地认识到权力对百姓的束缚和制约。他曾多次谈到“老百姓对权力的普遍恐惧”:“我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中原农村的人们都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西那样的世外桃源。我家是农村的,从几岁开始,对村干部是什么、乡干部是什么、县干部是什么,都有直接的认识和领教。那时候,你的工分、口粮都控制在上边有权力的人手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权力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比别人过得好的砝码,也可以成为改变你命运的砝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样的环境,自然就形成了普遍对权力的敬畏和恐惧。你说这是不是民间的心理个性?这种对权力的敬畏与恐惧,一年一年,一辈一辈,便会扩展为你对无所不在的能够左右你的一切力量的恐惧、厌恶和敬畏。”[1]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一个偏远小镇田湖镇,位于耙耧山下。离田湖镇几里远之外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的故乡。正是亲身体验到了浓重的官本位思想,才使得阎连科走进城市拿起笔,回头来审视他最熟悉的耙耧山脉。
《柳乡长》中,耙耧山深处的椿树村人之所以进城,表面上当然是缘于乡村的贫穷,村民住草房泥屋,吃沟水,点油灯。柳乡长对此“一咬牙,一跺脚”,下了决心:“不吃断肠草,就治不了这绝症。”作为底层乡村的缩影,椿树村如此处境在现代社会无异于患上了绝症,向城市“索取”是惟一救治之法,然而小说旋即指出这样的后果:一旦被逼进城市,毫无文化的底层乡下人就会蜕化为可鄙的众生。进城后经历波折,最终男为偷女为妓,竟也“治愈”了贫穷的“绝症”,而且出了槐花这样“最有成就”的“致富模范”,在九都市里开着“最大的娱乐城”,那可真是“山鸡”变作了“金凤凰”。槐花们以一种“男盗女娼”式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疯狂姿态,追逐城市的脚步,这种行事的观念是与主流政权体制所倡导的价值规范相左的,但在此处却恰恰是在该主流制度合法执行者的淫威下得以实践。
是柳乡长“派”车来,拿“骗”的方式,将椿树村青年男女带进城市,并拿“罚”相威胁,“说发现谁在市里呆不够半年就回村里的,乡里罚他家三千元,呆不够三个月回到村里的,罚款四千元,呆不够一月回到村里的,罚款五千元。若谁敢一转眼就买票回到村里去,那就不光是罚款了,是要和计划生育超生一样待着的。”对于“逃”回村的青年,“罚”完了再“押”进城。一系列带有强势政治意味的动作,足显出权力的淫威在椿树村人“进城”之事上才是关键。当进城的男人因盗窃被抓进收容所,柳乡长领出他们后,又打又骂,说“做了贼我不罚你们,可二年内你们几个必须在村里办出几个小工厂,要办不出几个厂,再被押回来我就让你们在全乡戴着高帽子游街去”;当柳乡长从公安局领出“精赤条条”的槐花们,她们像“学生”,排着队跟着柳乡长,领受“老师”“父亲”一样的柳乡长的教育;柳乡长没有先去槐花的娱乐城看过,连槐花的爹都不能去看;柳乡长在给槐花立碑大会上讲话时,“上百个村干部,都立在那日光里,或席地坐在自己的一只棉鞋上,再或铺了干草的石头上,端端地盯着柳乡长的脸,看着柳乡长一张一合的嘴,就像看着一个角儿在唱一出大板儿的戏,还有那村里来看热闹的百姓们,他们立在人群的最后边,老老少少的,为了看清柳乡长的脸,谁也不坐哩,都拉长着脖子踞着脚,生怕漏了柳乡长的一句话,一个手舞的姿式儿。”……作品中处处感受到权力的笼罩。对于没有权力的村民(被奴役者),阎连科展示出权力意识对他们的渗透,村民是毫无自我意识的一群,把柳乡长的话奉为圣谕,脸上写满了崇拜。乡长是农村基层权力的代表,是庞大的权力金字塔的底层,然而在百姓眼里却是一个很大的“官儿”。因为他的权威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领域,辐射到每一个角落,影响到每一个人,所以农民形成了严重的“权力崇拜意识”。因着“权力崇拜”,村民对与权力相伴相生的暴力也一并领受。作品中多有柳乡长的语言和肢体暴力。
“把从市里逃回来的几个青年揪出来,罚了款,又押着送回到了那市里的人海里”、“椿树村里的青年在市里集体做了贼,被人家抓到了,收容所里装不下,就被那市里的警察用警车押着送回到了槐树乡”。“穷”像是一种获罪,要被押送到城市接受“救赎”,又因无法有效自救而被城市警察押送回乡下,来去之间都无法躲过被押送的命运。不管城与乡,椿树村人都无从更无意掌握自己的命运,进城与返乡都是茫然而非自愿的,是迫于强势文化和强势政权所逼,因此是“人治”与“现代化”合谋的结果。柳乡长代表着槐树村的最高权威,他对“人民”的影响如影随行。就整个文本而言,“柳乡长”已不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一种符号,表征着权力;而槐花作为树立起的“模范”,也不再是单个的女性形象,而是乡民的集体指称,即作品中柳乡长口中的“人民”。
可以说,椿树村人“进城”完全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被当权者驱赶进城市的,是在权力宰制下的迎合之举。在某种程度阎连科是继承了鲁迅传统——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文化上的批判。但这还只是阎连科审视权力的一个层面,再细读,会发现整个文本呈现出一个反讽式的叙述,甚至一个可怖的民间文化场。
二 权力宰制下的狂欢化叙事
文化转型时期,往往显出狂欢化特点。狂欢广场的语言,是大众语言,与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相对立。官方语言带有典雅、庄重、严肃、僵化、封闭的特点。狂欢广场的语言则多为方言、俚语、俗语、日常口语,显得粗俗,甚至“肮脏”,有亲昵之感。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语言通常表现为“戏谑隐喻”和“冷静反讽”。《柳乡长》中,作者深味狂欢化语言的妙处,巧选叙述视点,运用隐喻和反讽,使叙述语言呈现寓言性。通过这种狂欢化的叙事,水到渠成地解密了民间文化如何消解、嘲弄了主流政治,以及民间生存法则是如何建立的。
作品以讲故事式的引语开场:
乡长这人哟,屌儿哩,说好着去县上向新来的县委书记汇报乡里的工作呢,可是,可是到了半途却又冷猛地打道了,折身返着了,说为了全乡人民哟,我不能丢下工作去拜见一个县委书记去,要拜呢,也该去拜我那柏树乡的人民哩。
去拜哪个人民呢?
去拜了椿树村叫槐花的姑娘了。
槐花是干啥儿哩?
原是在九都市里做鸡儿那种营生呢。
这是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开始。这里是以旁观者的眼睛来观察人物的行动,明显的言意悖反预示了作者态度。而这位柳乡长为什么放着新上司不见,要去拜访“人民”呢?是他真的更在乎“人民”?文本语言上他是一副为民做主的表相,在县委书记找他时,甚至显摆地说:“让他等着吧,看他敢不敢把我这乡长给撤掉。”随情节的展开,他的用意也逐渐暴露。当书记的车驶近槐树村时,“他撒腿跑了起来,因着是冬日,穿得厚,日又暖,几步下来他就一满脸的大汗了,气喘吁吁了,为了不使那汗落下来,为了能满脸大汗地迎着新书记,为了能让新任县委书记和他一块返回到椿树村里看一看,使椿树村成为新任县委书记下乡检查的第一个村,柳乡长跑着跑着就在一块平地上兜着圈子了,不停脚也不往前去了。”这里,一个前倨后恭的弄权者形象跃然纸上。例如,他在“人民”面前大加赞扬槐花的“榜样事迹”,背着人却向亲手立的“碑”吐痰等处均可见出,柳乡长谙熟为官之道,权力在握,他知道如何增加政治资本,他熟知民间社会的生存法则。这种法则的根,深深植于历史中,广泛地存在于民间文化中。
柳乡长把青年男女骗到城市后,威胁道:“若谁敢一转眼就买票回到村里去,那就不光是罚款了,是要和计划生育超生一样待着的。”对从看守所放出的村民,同样呵斥道:“做了贼我不罚你们,可二年内你们几个必须在村里办出几个小工厂,要办不出几个厂,再被押回来我就让你们在全乡戴着高帽子游街去。”此类在主流话语体制之内具有正当性、合法化的言语经由权力的挟持,遂变为一种工具或者手段,用于维护当权者的话语权与权威性。至于当权者的指令正当与否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达到目的。而乡村里的“人民”也都心知肚明进城的“槐花们”是如何实现对城市资本的“掠夺”,却都心照不宣地享受着“掠夺”而来的“文明”,甚至在看到槐花家装点得那般奢华时,发出:“让我认槐花做干娘我都愿意哩,让我们全村男的都做她干儿子,女的都做她干闺女,我这村长都保准答应哩”的感慨。
作品中有诸多主流政权体系内的语言,即官方的话语方式。柳乡长准备开会给槐花立碑,“说他要当着全乡各个村干部的脸面儿——啥儿村长呀、支书呀、民兵营长呀、妇女主任呀、经委主任呀,一老全儿所有的村干部的脸面儿,给槐花姑娘树上一块碑,要号召全乡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开展一场向槐花学习的运动哩。”柳乡长在会上表扬在城市做“鸡儿”的槐花:“她不光把自己的妹妹从椿树村里带了出去了,还把同村、邻村的好多小伙、姑娘带了出去了。一帮一,一对儿富;十帮十,一片儿富——这就是我们要走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呢,就是我们日常间说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哩。像槐花这样的人,你们说不给她立碑给谁立碑呢?”诸如此类,常常出现在主流政治话语里的大言夸夸之词,被反讽式的揶揄消解得支离破碎。
作者要表达的是一种反讽性的题旨,要揭示的是在权力的宰制下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换之所以艰难的缘由,以及在这种文化转型过程中主流价值体系的尴尬与民间文化场中的顽疾。如此的主题和情调,限定了作者必然选择一个能够巧妙地宣示这一主题、包蕴这种情调的视点。这个视点不可能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柳乡长,因其奉行(表面上奉行)着主流文化价值且身属要揭露的民间文化场域,如果以他为视点展开叙述,难免流于浅露直白的控诉与怨怼。这样,为表现柳乡长(们)阳奉阴违地玩弄权力,及民间文化的顽疾,就需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文本外叙述者的身份讲述这个故事,而聚焦点则是柳乡长。
文本中的叙述就是立足这一旁观的视点进行的,但作品中的叙述视点并不是始终不变的。随着叙述的推进,外在于文本的叙述者视点与文本的聚焦点有重合分离的变换和流动。作品中,柳乡长向槐花的碑“吐痰”时,叙述者视点游移,不知不觉中过渡到从人物的视角进行描述。作品结尾处柳乡长与槐花对望时,叙事的视点也移入文本中的人物,叙述焦点与视点出现了重合。
叙述视点的变换,使文本表层和文本深意呈现相互对立。如果没有这种对比,就只有单一视境,就无法产生多重视境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反讽意味。表层话语体系与内在情感机制在同时延进时也在反向互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图就无法得以实现。
《柳乡长》文本中,故事情节基本是一种概括性的转述,且有效运用视点的转换,使文本出现分裂和复义性,也使作品充满寓言性,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多重意味的寓言意象在语言的形象与抽象之间呈现张力。Allegery,中文译作“寓言”,也可译为“讽喻”。“寓言”中的“讽”主要是“反讽”的运用。“喻”即是“隐喻”,“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物之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2]在《柳乡长》中,作者数次运用了隐喻,隐喻的作用往往与作品的寓言性紧密相连,但这里毋宁说它点化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彰显文本的分裂与复义性。其例一:当柳乡长用骗的方式把椿树村的青年男女运到九都市,随即每个人发了一张想咋填就咋填的“盖有乡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就“头也不扭地回了他的三百里外的柏树乡”,扔下“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的“人民”;后来给槐花立碑时,再次交代“能干的发给他们十张二十张村委会的空白介绍信,不能干的给他们发三张五张也就行了呢”,说必要时“乡里党委的介绍信空白着也可以发给那些有能耐的男女哩”。这里的“空白介绍信”出自“乡里、党委”,它所代表的是绝对权威以及绝对权力的支持和庇护,至于受庇护者拿着““空白介绍信”做什么事,全然放任自流,如此一来就戏谑地消解了这一权威信物的合理合法性,但也确证了另类民间生存法则的合法。其例二:柳乡长到市里公安局领一群“精赤条条,裸了身子”的槐树村姑娘时,一个警察走过来在柳乡长面前“恶恶地吐了一口痰”;而柳乡长在给槐花立了碑之后,忽然也“朝那碑前吐了一口痰,就像三年前他去九都市里领那些脱了衣裳的姑娘时,那警察在他面前吐了一口恶痰一模样”。前者如果隐喻着身处都市强势文化中的人对进城为娼的弱势人群的鄙夷不屑,后者就在文本深意与文本修辞上荡开精彩一笔。就文本深意来说,柳乡长人前卖力吆喝“学习槐花好榜样”,人后尽显鄙夷唾弃之态,可见不管是都市强势文化还是乡土强势政权都对“男盗女娼”式的行为不屑,表面上却不遗余力地夸赞,这种分裂说明深为民间文化侵染的柳乡长深谙民间生活的潜规则,深知权力能使龌龊的生存法则合法化。其例三:给槐花立的“碑”,究其“立碑”的缘由,表层看是因槐花“能干”,她带领村里的姑娘“致富”,发扬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还准备给村里修路,这样的人还不给她立碑吗?可人人心里都明白她是靠什么“致富”的,却都响应“学习槐花好榜样”的号召。再者,“立碑”意味着纪念,纪念的对象也许早已不是槐花,而是民间的生存法则,一种摒弃是非的生之道。
通过对作品中的反讽式语言、视点转换、寓言意象的分析,可以感知文本充满戏谑的隐喻与冷静的反讽,以一种狂欢化的叙事,指示了民间文化的顽疾,也嘲弄了主流政治的虚假。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民间文化与陈思和所谓民间有许多相似性。就陈思和所谓民间来说,内涵有三:(一)它是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相对的自由活泼形式;(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既然包纳五花八门的小传统,它是菁华与糟粕的综合,也必须拒绝单一价值判断。①转引自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8 页。
这一民间文化思想个中深藏危害性,是作者内心的隐忧,因为它以主流文化价值为掩护,不断渗透到生活中。作者似乎要说:当代民间文化之恶在强权政治有意无意地关照下,无孔不入地侵入生活,且左右逢源。②王尧《为信仰写作》,文中援引阎连科的话:“真实不存在于生活,只存在于写作者的内心。现实主义,不会来源于生活,只会来源于一些人的内心。”(《当代文学评论》2007年第2 期)。更为可怖的是民间生长的这朵“恶之花”是在主流政权的宰制下肆意生长,其中的暧昧性耐人寻味。
小说的最后,“槐花脸上的羞红淡去了,恢复了她的白嫩白润了,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柳乡长,像看一个自家不太熟的哥。柳乡长呢,也那么静静地望着这槐花,像望着一位自家不太熟的妹,望着望着呢,槐花在柳乡长眼前便有些模糊了,漂亮得成了真的莲花,真的牡丹了。”这段文字似乎留有一抹温情,作者煞有介事的语言背后是否还保留着物伤其类的同情与怜悯,隐忍着连骨伤筋的痛楚?
当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被简单化为对强势文化的机械模仿,当“男盗女娼”式的疯狂之举在强势政权的宰制下变得理直气壮,当现代主流社会暗藏欺诈与诡计,当民间文化中的顽疾如鬼魅般挥之不去,“乡下人进城”这一当下中国最为壮观的社会化运动将以何种面目收场,是乡村最终完成文明的自我“救赎”?还是在追求城市文明的道路上悲壮的沦陷?作者以他独异的姿态和言说方式发出了质疑。
[1]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2]〔英〕特伦斯·霍克斯.论隐喻[M].高丙中,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1.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