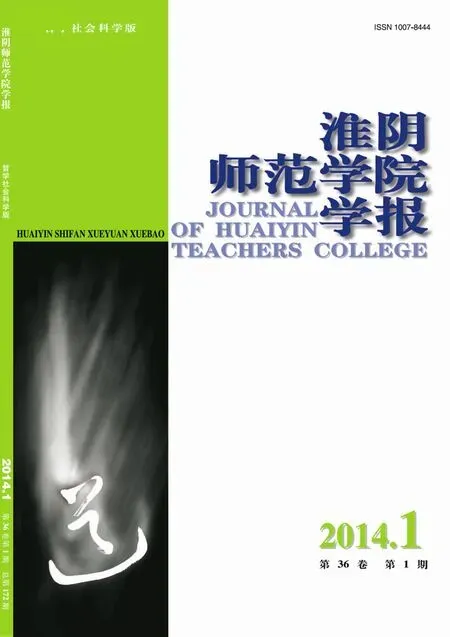“此身虽异性长存”
——古代小说中的转世主题
万晴川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中国古代关于鬼魂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佛教三世说融合。佛教认为,除今生外,人还有前生、后世,合称“三世”。《宝积经》解释道:“三世,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云何过去世?若法生已灭,是名过去世。云何未来世?若法未生未起,是名未来世。云何现在世?若法生已未灭,是名现在世。”[1]佛教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在没有获得解脱之前,都必须依循因果规律在“三生”和“六道”中轮回。其依据实际上是灵魂不死的学说,一个生命死后,灵魂则可以发生迁移,按照因果报应的规律重新投胎,这就是转世。转世重生取决于因缘和业力,“欲知过去因者,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者,见其现在因”[2]。“因”是种因,为能生;“果”是结果,为所生。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前世的善恶业是现世的苦乐之因,现世的苦乐是前世的善恶业报,现世的善恶业又是来世的苦乐之因,来世的苦乐是现世的善恶业报。生命如此因果循环,生死无穷,永远无法逃脱。释慧远《三报论》解释道:“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3]善业是清净法,不善业是染污法。以善恶诸业为因,就能招致善恶不同的果报。世俗世界的一切万法,都依照善恶之业而显现出来,得到了善恶果报的众生,又会在新的生命活动中重新造作业因,招致新的果报,依业而生,依业流转。只有修行成佛,才能跳脱轮回之苦。因此,佛教讲“转世”是为了说明因果,让众生明了因果实相,从而避恶趋善,并最终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
佛本生即描述佛祖的前世故事,呈三段式结构模式:缘起,即交待佛说前生故事的地点及缘由;前生故事;对应,即把前生故事中的人物与缘起部分中的人物对应起来。这一模式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转世叙事有重大影响。
佛教“转世”观念与中国人重生恶死的心理深相契合,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之说打破了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人生观念,开拓和丰富了人们的想象,使人们对人生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一、“转世”的表现方式
在早期古代小说中,“转世”的观念主要用来表现如下几种感情:
(一)解释亲情。在早期志怪小说中,“转世”的描写,既宣扬轮回、报应的佛教思想,又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如《冥祥记》中“向靖”条:
晋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吴兴郡丧数岁女。女始病时,弄小刀子,母夺取不与,伤母手。丧后一年,母又产一女,女年四岁,谓母曰:“前时刀子何在?”母曰:“无也。”女曰:“昔争刀子,故伤母手,云何无耶?”母甚惊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犹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录之。”靖曰:“可更觅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择。”女见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儿许。”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审其先身。
向靖《宋史》有传,小说以向靖女能记起并认识前世玩弄的小刀子作为叙述线索,证明她是前女转世。小说又写道,在丧女之后,向妻“痛念前女”,以至不忍看到她生前喜爱的玩物。这篇小说显然是以转世说来缓解父母的丧子之痛。
又如《冥祥记》中“羊祜”条:
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晋名臣,声冠区夏。年五岁时,尝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环。乳母曰:“汝本无此,于何取耶?”祜曰:“昔于东垣边弄之,落桑树中。”乳母曰:“汝可自觅。”祜曰:“此非先宅,儿不知处。”后因出门游望,迳而东行。乳母随之。至李氏家,乃入至东垣树下,探得小环。李氏惊怅曰:“吾子昔有此环,常爱弄之。七岁暴亡。亡后不知环处。此亡儿之物也,云何持去?”祜持环走。李氏遂问之。乳母既说祜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祜,还为其儿。里中解喻,然后得止。祜年长,常患头风。医欲攻治。祜曰:“吾生三日时,头首北户,觉风吹顶,意其患之,但不能语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祜后为荆州都督,镇襄阳,经给武当寺殊余精舍。或问其故,祜默然。后因忏悔,叙说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诸罪,赖造此寺,故获申济,所以使供养之情偏殷勤重也。
羊祜五岁时,竟然还记得前世幼时游玩时丢失的指环,并在桑树中找到了它。又记得前世有罪,今生造佛寺供养赎罪。这些行为都无法用常理来解说,故说成是李氏子转世。李氏在得知羊祜是其亡子转世后,悲喜交集,并试图要回羊祜做自己的儿子,虽没有成功,但至少可以帮助她缓解失去儿子的痛苦心情。
(二)解释友情。
如《冥祥记》中“王练”条:
晋王练,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玟,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梵沙门,每瞻玟风釆,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玟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之奇珍锒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梵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玟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云。
王玟与梵僧原为好友,梵僧因为倾慕王玟,死后托生为其子。作者通过描写王练一系列神奇的能力来证明是梵僧转世:幼时无师自通懂外语,认识许多异国珍宝名物,天性亲近梵僧。这些小说,都是通过人物外部令人费解的举动而轻率地得出转世的结论,并未深入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最有名的是“三生石”的故事。唐袁郊《甘泽谣》中“圆观”写李源与洛阳惠林寺僧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生讥诮,如此三十年:
二公一旦约游蜀川,抵青城峨眉,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岀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岀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浦,维舟山下,见妇人数人,锦裆负罂而汲。圆观望见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上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恐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其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公当访临。若相顾一笑,即某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符。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岀家财,厚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有治命。后十二年秋八月,直指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縁未尽,但愿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逺,尚闻歌声。词切韵髙,莫知所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一年亡。
作者将李源和圆观的友谊植入两世的轮回之中,表现了真挚不渝的友情。重点不再是宣扬因果报应,而是突出人类情感的绵延永恒。李源与圆观之间那种超越时空的感情,借“转世”的形式得到了最充分、最动人的表现[4]。
(三)解释爱情。唐代以后,由于佛教的世俗化及文学化等原因,佛教的转世思想在小说文本中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果报应、求解脱的出世色彩大大淡化,代之以浓重的人间世俗情感的色彩。小说不但以转世“观念”演绎人类的亲情和友情,还有生死不渝的爱情。
如《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写元末赵源在南宋奸相贾似道旧宅旁遇到一绿衣女子,两人相爱。后来赵源得知绿衣女子是女鬼,生前是贾似道的侍儿,因与贾似道的男仆相恋而被赐死。赵源即男仆转世,二人阴阳相隔,再续人鬼情缘。故事中的人鬼相爱,是因为“夙缘未尽”,前世不能圆满的情爱在转世后得到了补偿。现实的动荡使饱受痛苦的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此生不能相聚,便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佛教的转世思想符合了人们绝望中对来世的企望,于是就借佛教的转世观念,来演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的愿望。这就使佛教用来明因果、求解脱的转世思想反而成了表达人间情感的一种手段。这些作品中,轮回转世成了情感得以延续的凭借。岁月流转,生死无情,幽明殊途,然而这一切都阻隔不了人间真挚的情感,正如绿衣人所说“地老天荒,此情不泯”。这种超越时空的感情,借“转世”的形式得到了最充分、最动人的表现。又如《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喻世明言》第4卷)中的阮三在与官家小姐陈玉兰幽会时莫名猝死,在故事结尾,作者向读者解释道:阮三之死不过是为还却前缘夙债,今生注定与玉兰相遇。玉兰前世是个扬州名妓,阮三是金陵人,到扬州访亲,与玉兰相处情厚,许诺一年之后再来,娶她为妻。及至归家,因惧怕父亲,不敢禀知,别成姻眷,使玉兰终朝悬望,郁郁而死。但两人情缘未断,故今生闲云庵私会,是完前生冤债,阮三身死,是偿玉兰前生之命。《石点头》卷九《玉箫女再世玉环缘》写京兆韦皋乃孔明转世,幼聘张延赏秀才之女芳淑为婚,后延赏官至西川节度使,迎韦皋到官衙完婚。因志趣不投,韦皋受到张延赏的冷遇,愤而出走,至江夏姜使君家,教授其子荆宝,爱上荆宝乳母之女玉箫。后韦皋父母来信催归,韦皋临行赠玉环一枚而别,玉箫誓言等他七年。韦皋走后,因发奋功名,致爽玉箫七年之约,玉箫绝食而死。韦皋发迹后,得知玉箫已死,礼忏虔诚,为玉箫大做法事,感动阎罗天子,令玉箫鬼魂托生,十二年后,再为韦皋侍妾,重续前缘。在这个故事中,作者通过转世观念,构建韦皋与玉箫矢志不渝的爱情故事,以补偿在人世间未能遂愿的情憾。
(四)解说两人才貌相似的现象。
如殷芸《小说》(《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七)中写张衡死时,蔡邕母怀孕,两人才貌很相似,时人说蔡邕是张衡之后身。牛僧儒《玄怪录》中“顾总”条,写梁吏顾总因昏戆无能,常为县令鞭扑,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遇王粲、徐干鬼魂,告知他是建安刘桢转世,并给他读刘桢集,顾总立即“明悟”,“觉藻思泉涌”。小说结尾,顾总以刘桢集示县宰,当县宰“见桢卒后诗”时,即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宾礼待之”。这篇小说以顾总与王粲、徐干鬼魂相遇为线索,形成小说情节的基本架构。同时,以“亡灵忆往”的方式,穿插王粲、刘桢在冥中坤明国的情事,将现实时空(梁代县吏顾总的环境)与历史时空(汉末曹操邺下)及虚拟时空(冥中坤明国)三者纽结在一起,构思奇妙。
(五)解释某些历史现象。古代小说还常常借用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形态。中国传统天命观的形而上理论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来说明王朝的更替。
如《三国演义》开始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就是基于此类天道循环观。佛教中也有世界循环论。小乘佛教认为物质世界有成、住、坏、空四劫。每一劫中都有二十中劫,总共为八十中劫,合为一大劫。佛教的这一世界循环论与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表面相似,但有根本区别。“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是以一种不可知论的面目出现。天道渺茫人难知,但天道始终在运行,故而盛衰转移、苦乐交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世界模式中,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某一众生的生活质量,都取决于他本人的业力。当世界进入灾难时期,此世界的众生普遍受苦,但那些不受苦报的众生就不进入此世界。佛教关于统治者个人别业与众生共业关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看法,即统治者的个人别业与众生共业相应。个人是得福报还是苦报,最终由他自己决定;而一个地区或国家是盛是衰,则由其中居民的共同业力决定。在佛教的历史因果观中,没有上帝,没有天命,导致国运兴衰、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别业和众生的共业。
佛教的历史因果观,提供了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正义观的形而上理论基础,对古代小说产生影响,形成了历史因果报应类小说。传统天命观强调有德者得天下,同样,佛教的个人别业观也强调行大善者受大福报,而在人世间,最大的福报就是能成为君王,这是历史题材小说能采纳佛教以个人别业为基础的历史因果观的根本原因。
宋代讲史《新编五代史平话》对从汉到三国的历史作了因果报应的诠释。话本开头写道:刘邦杀害功臣韩信、彭越、陈稀。三人抱屈衔冤,诉于天帝。天帝怜其无辜,令三人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日后瓜分汉家天下。此后,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明代冯梦龙《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喻世明言》第31卷)皆从此因果报应故事有所发展,几乎把全部三国时的重要人物都说成是汉初人物的转世,三国故事只是他们恩恩怨怨的继续演绎。《隋唐演义》以转世说为全书的骨架,在小说结尾借仙人张果之口点明:孔升真人在太极宫中听讲时,因与蕊珠宫女相视而笑,很不严肃,被谪堕凡尘,入隋官为朱贵儿,再转世为大唐天子唐明皇;蕊珠宫女前世托生为隋宫侯夫人,再转世为唐明皇之宠妃梅妃;而隋炀帝乃是终南山中一老鼠精转生,再转世则为杨贵妃。这种安排看似荒诞,但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兴趣。
对于梁武帝因崇佛而亡国之事,早就出现了用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来解释的小说。最早在唐代笔记《朝野佥载》中,就写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而夺其位,东昏侯死不甘心,转生为侯景,后率军攻破建业,囚禁武帝,使其饿死,并诛杀萧氏梁弟,略无孑遗。作者不仅以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来解释梁武帝亡国的原因,而且对当时的一些历史故实也作如是解,如作者解释梁武帝误杀磕头师之事,说前世小沙弥误杀一条曲蟮,磕头师是前世的小沙弥转世,曲蟮是梁武帝的前生,故今世梁武帝误杀磕头师。正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这个故事到明代冯梦龙的《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喻世明言》第37卷)中,更是踵事增华。《吴越王再世索江山》(《西湖二集》卷1)写钱俶归降赵宋后,吴越王钱镠英灵不泯,每欲问宋朝索还江山,后趁徽宗昏庸,转生为高宗,夺还江山。作者从外貌、生平行事、爱好、享年等方面进行对比,指出两者“恁地合拍”之处,以转世来解释南宋高宗时的许多历史现象。
总之,作者企图以明确的因果关系,将历史和人生化约为可以理解的模式。这种化约虽然满足了一部分读者的心理要求,但却并不符合事物的本身规律。因为实际上历史和人生总是充满各种无法确定、无法归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就能解释得了。因此,认识论上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六)解释因果报应。当然,在古代小说中,转世观念最为普遍的还是用来演绎因果报应故事。
作者通过转世的方式来说明因果,旨在劝善戒恶,唤起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如《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警世通言》第22卷)中写宋敦见一位老憎坐化于路旁,于是尽其所有买棺葬僧。老僧为报宋敦之恩,投胎为宋敦之子宋小官,后来当宋小官遭遇危难时,又遇到圣僧相救,最终逢凶化吉。这类故事告诉人们:前世积德,后世沾惠。另有一类小说,则写前世造孽,后世遭殃。如《续玄怪录·张高》篇(《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六)叙述一头驴子因前世欠长安张高二万钱未还,故今生转世为驴子供张高驱使。二十年后,张高死,驴子便拒绝为其子张和服务,并开口说话:“汝父当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驴子要求将自己卖给王胡子,以偿还所欠张高的最后一缗半钱。张和果然把驴子卖给了王胡,得钱一缗半,而驴子竟死,王不得骑。作者以一头驴子的前世、今生诠释业报轮回思想。又如《原化记·戴文》(《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四)讲述戴文种下恶业,死后堕入畜生道,来生变为牛供人驱使。
(七)转世修行。有的人因为品行有亏,抱憾而死,转世后继续修行,以赎前衍。如《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第29卷)和《明悟禅师赶五戒》(《喻世明言》第30卷)中的玉通禅师,本是修行高僧,只因一时受到美色的诱惑而破戒,受到业报,来世转生为妓女,继续修行,历经磨炼,最终修成正果。这些高僧并非有意犯戒,只是受到诱惑,一时把持不住,因此作者给予他们赎罪的机会。
二、“转世”观念与小说结构
在许多明清小说中,转世故事既是结构形式,又是情节内容,很难将两者具体区分开来,但在小说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转世观念更多的是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并成为小说结构的一种常见的模式。有的偏重于写今生,转世报应只是简单揭出,如《金瓶梅》的内容,主要描写西门庆今世作恶的故事,西门庆后世转生为孝哥,得高僧点破,出家为西门庆赎罪之事,只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有的侧重于来世,如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写西门因为前世作恶,受到一连串的轮回报应的故事。《后水浒传》叙述宋江、卢俊义等三十六条梁山好汉转世为杨么、王魔等三十六家草莽英雄在洞庭揭竿而起之前的苦难历程。有的叙述人物的两世故事,如《醒世姻缘传》由狄希陈的两世恶姻缘构成:前世晃源、计氏及珍哥,今世狄希陈、薛素姐与童寄姐,最后得高僧点化。只是相对于后世来说,前世的内容稍简。虽然这样的结构形式难免会使作品笼罩上一层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但小说主要表现的是现实生活,是人物的七情六欲和真实的生命历程。相比之下,转世故事中原有的迷信因果成份被淡化了,留下的主要是转世的结构框架。总之,按照佛教因果报应的律约,前世的故事对后世的故事具有某种暗示或预叙的作用。
明清通俗小说中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利用转世故事做小说的楔子,其功能或为整部小说的引子,或为解释故事发生的因由。转世投胎、谪降历劫等情节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广阔的时空架构,扩大了叙事的容量和自由度,并提供了结构故事情节的内在机制。如《水浒传》以“误走妖魔”的故事作为楔子,将梁山一百零八将说成是天罡地煞转世。《说岳全传》开头说,因宋徽宗不敬天地,玉帝大怒,遂令赤须龙下界,降生女真国为金兀术,扰乱宋室江山。而如来佛怕无人能制服赤须龙,便派护法神大鹏金翅明王下凡,名为岳飞,来保卫宋室江山。大鹏金翅鸟在如来说法时,啄死女土蝠,又将铁背虬王左眼啄伤,虬龙后投胎秦氏,即为秦桧;女土蝠投胎王氏,嫁给秦桧。夫妻俩专门残害忠良,以报前仇。这样,宋金的民族之争、岳飞与秦桧、王氏的忠奸之争,都被解释为宿世的因果报应。作者拾取佛、道二教的某些素材,对岳飞精忠报国和围绕着抗金斗争的忠奸斗争,进行了一种神话性的先期阐释,从而为其后大奸大忠、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提供了一个带预言性的“元故事”[5]。《红楼梦》开头的“还泪故事”,也是对后来宝黛爱情故事的神话诠释。
总之,这些小说多借用“转世”作为结构的枢纽,往往是情节发展的关键转捩点。
如何揭出人物的转世关系?如果由小说作者或说书人直接指出,对读者或听者来说,就缺乏可信度。因此,由可以洞察三世的高僧点明转世的真相,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有的则通过做梦的方式点明。如《冥祥记》中“陈秀远”篇写陈秀远少信三宝,年过耳顺,因欲知自己从何而来,祈梦感通。梦中见一妇人对他说:你的前身就是我,因以花供养佛故,得转世为男身。又指着一白头老妪说:她又是我的前身。言毕而去。古代中国是个男权社会,作为父母来说,希望生下男子传宗接代,延续宗嗣;作为女性来说,希望来世生为男子,改变被压迫的地位。这个故事就以转生说,吸引女性信佛修行。这类写法在《聊斋志异》中常见,如“蒋太史”、“邵士梅”、“四十千”、“拆楼人”、“珠儿”、“汪可受”、“李檀斯”等篇。在梦幻中,出生的生理作用被抽掉了,婴儿并不是受孕的直接结果;受孕只是母亲为接受和生出那个已经存在的灵魂做准备。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古代人认为,为了使一个状态产生变化,首先必须破坏原有的现状,由现状的破坏而产生和引导出另一个新的状态,因此对古代人而
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达到再生的过渡,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常见的是灵魂转生的信仰,死去的灵魂转化为人、动物或者植物而使原来的生命得以继续。”[6]这是转世观念产生的文化渊源。对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明清作家来说,选择以“转世”来演绎爱情、历史等各种故事,既可以看做是他们为了适应读者世俗化审美趣味而做出的叙事策略的调整,也可理解为他们试图对历史偶像和现实人生进行新的解读。其次,佛教中的转世轮回观念被普遍地引进明清小说结构的局面,既对形成具有我国古典特色的小说叙事模式起了促进的作用,同时又为转变和打破这一模式起了阻碍的作用。以相关佛教观念为构架的小说,虽然在世俗化的阅读背景下体现出了其在叙事策略上的优点,但一旦变成一种程序化、凝固化的叙事模式,就变得呆板并阻碍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艺术形式的变化虽然相对内容来讲有其一定的稳定性,但它的生命力仍在于不断创新。只有到了近现代,随着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和传统小说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才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引进佛教观念的结构模式也逐渐为小说家所舍弃。
[1] 宝积经[M]//乾隆大藏经:第19册.台北:传正有限公司,1997:47.
[2] 因果经[M]//民间宝卷:第十一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227.
[3] 释慧远.三报论[M]//僧佑.弘明集:卷一.刘立夫,胡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100.
[4] 孙逊.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J].文学遗产,1997(4).
[5]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6]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