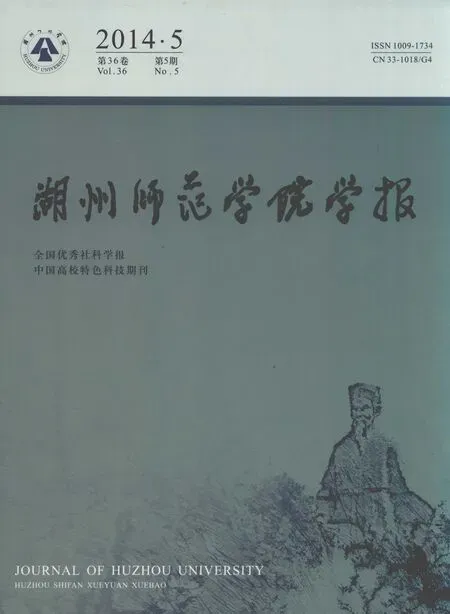论老舍小说的生育叙事*
郭 聪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论老舍小说的生育叙事*
郭 聪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之一,老舍与一些男作家一样,关注到了女性的“生育”问题,但在叙事上与女作家直面生育之苦不同,他们不关注生育场面的描写。以“生育”为切入点,可以挖掘老舍复杂的文化、性别意识,回应其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同时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把握可以给予作家老舍更为客观、立体的评价。
老舍小说;生育叙事;文化启蒙;现实关怀;理想生育观
所谓生育叙事,在现代文学文本中,既指涉及女性生产的“生育”书写,即对生育场面及生育现象(包括顺产、难产、流产及堕胎、不孕、非婚生等)的描述,又包括对生育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文化、现实问题及生育主体(男性与女性)的关注,还可以涵盖透过文本所反映的作家的生育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中,已有部分女作家从生育角度出发,直面女性的生育之苦。作家通过大量生育场面的描写,观照着女性的生命本体存在,饱含着鲜明的性别意识。①如:萧红的《王阿嫂的死》《生死场》《弃儿》,白朗的《四年间》《女性的刑罚》,左蒂的《女难》,凌淑华的《小刘》《中秋晚》等。然而,对女性生育过程的正面、深入描写,在中国现代男作家笔下并不多见,女性自身的生育之痛往往被一笔带过。但他们并没有全然忽视生育现象,而往往是从男性视阈书写女性,通过难产、流产、堕胎、典妻生子、生儿育女前后主人公的变化等相关生育叙事,来完成启蒙任务。《家》中的瑞珏、《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死水微澜》中的顾二奶奶、《倪焕之》中的金佩璋、《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最后的幸福》中的美瑛等均是此类叙事作品中的代表人物。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之一,对生育现象同样有所关注。其小说《骆驼祥子》《鼓书艺人》《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抱孙》《生灭》《一筒炮台烟》等作品中皆有与生育相关的叙述,并呈现较为丰富的内涵。
一、生育现象背后:别具一格的文化启蒙
新时期以来,学者们摆脱政治视角,以文化视角还原老舍在现代文学中的文化面目。他一方面继承思想启蒙“文化批判”、“改造国民性”的题旨;但另一方面,其创作倾向与主流性启蒙文化观存在明显差异,并不被鲁迅、茅盾等启蒙中坚人物所认同。因此,老舍作为肩负文化启蒙任务的一份子,有他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在其生育叙事中有所体现。其文化启蒙的价值在于:老舍没有导向主流启蒙主义文化那种非中即西、非古即今的单向度价值取向,也没有决绝地与传统文化、历史全然割裂,而是表现出“结构双面关注”[1],文化批判中有反思,文化认同中不失焦虑,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启蒙特色。
(一)反思传统文化习俗
《骆驼祥子》《抱孙》通过产妇难产而死的相关叙述,既批判了那些利用迷信催产、恪守旧文化习俗等人物的盲目、愚昧,揭露封建旧习对其执迷者的戕害,又有对身处新旧、中西文化之间的小市民无知、迷茫状态的反思。而在《正红旗下》《四世同堂》等文本中则将“洗三”、“办酒”等生育习俗视为不可抹去的文化烙印,表现出深切的文化认同与深刻的文化焦虑。综合上述两方面,呈现出老舍与文化启蒙主流有所不同的思想倾向。
《骆驼祥子》中的虎妞与《抱孙》中的儿媳皆死于难产,导致逆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孕妇孕期胡吃海塞,疏于运动致使胎儿过大。《抱孙》中则通过对孕妇各样食物的精细描写,来完成辛辣地揭示与讽刺。生产时,两人也都把收生婆接生作为首选。当意识到胎儿仍不能顺产,虎妞自己决定请来了“虾蟆大仙”并以荒谬的迷信手段催生,致使难产而死。《抱孙》中则经过一番争论,最终选择了去医院。但由于王老太对西医的强烈质疑与无知,以及对“洗三”习俗的顽固恪守,终酿成媳孙两失的悲剧。两篇小说隐含作者皆以嘲讽、戏谑的喜剧口吻揭示了固执于传统旧习的恶果,批判了传统小市民中落后的文化现实,显露出较为明显的“国民性”批判意向。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迷信导致难产至死引发的批判,《家》中瑞珏之死(“血光之灾”)与虎妞不同,巴金更多指向封建家庭“孝”文化与家长制罪恶的谴责,是对礼教而非封建习俗的批判,与五四主流吻合;而《抱孙》中的“家长制”则主要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传统文化观念,作家的批判单纯指向执迷于旧习、旧传统观念的愚昧者,而非礼教痼疾。此外,抱孙悲喜剧的上演,隐含作者并非无动于衷,“男大夫?男医生当接生婆?”、“这些孩子都是掏出来的吧?”[2](P96,第七卷)王老太这一系列的问号,真实地表现了小市民在新旧、中西文化之间的迷茫、惶恐。可见,作家在批评之余有着文化反思意识。
实际上,老舍对《抱孙》中王老太的批判,其实质并非文化习俗本身,而是她的愚昧与固执。他对传统文化习俗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这一点可以在《正红旗下》中得到佐证。作品也提及 “洗三”生育习俗,作家不但没有批评,反而以温情的方式呈现出来。来看下面一段关于“洗三”典礼的叙述:
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3](P246)
“洗三”是“我”的“历史”,隐含作者以温情脉脉且不失幽默的回忆方式详细描述了整个“洗三庆典”,除了“洗三典礼”,“我”的“出生日”、“满月宴”的礼仪习俗也描绘得惟妙惟肖,显然作家十分怀念并尊重这些文化习俗。《四世同堂》也提到金三爷在战争年代仍为外孙办三天和满月,虽有小市民讲面子、求体面的一面,但作者并没有否认这种文化传统,而把它看作是北平文化的一部分。可见,老舍不但认同这些传统习俗,而且将其看成是一种融于历史血液且不可抹去的文化烙印,因此面对西方文明浪潮,老舍表现出深深的文化忧虑。这又与文化启蒙主流思想强调的与传统全然割裂的倾向有所不同。
(二)中西医价值判断
老舍关于“生育”的小说中,涉及就医问题时,他明确肯定了西医的科学性、准确性,但并未因此就导向对中医的否定,而是保持不温不火的中立态度。在生育叙事外的文本中,老舍也未否定过中医的价值。这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中坚人物那种绝对肯定西医、否定中医的文化态度迥然不同。这样,老舍再次与主流启蒙思想相疏离。
《抱孙》中的儿媳妇最终到医院生产,隐含作者透过王老太的质疑与无知,反衬出西医的科学性。《鼓书艺人》中方宝庆在秀莲生产之前建议她到医院检查:“宝庆懂得医学常识,跟她说,检查一下,对孩子有好处。”[2](P220,第六卷)尽管整部小说只有此处提及科学就医的问题,同样可体会隐含作者借宝庆之口传达了对西医的肯定态度。而《生灭》中夫妇二人为了确定梅是否再次怀孕,首先去中医孟老头儿那检查,得到欢喜的结果,可是到了西医那则检查出梅确实有了孕,对西医的检查结果,虽然女主人公此处以问句表达心中的猜疑,但看后文的发展,梅从一喜转为一忧可知,隐含作者默认了西医的准确性。
可贵的是,作品中作家肯定西医科学性的同时,却并未导向对中医的否定,而是保持不温不火的中立态度。如:《生灭》中并没有指责中医的误诊。在生育叙事之外的文本中,老舍也未否定过中医的价值。《四世同堂》中给受伤的钱先生看病,瑞宣主张看西医,李四爷请来中医,最终虽是西医看好的病,却也没批评中医文化。这就与作为启蒙中坚人物鲁迅迥然不同。在《父亲的病》中,隐含作者尖锐地讽刺了曾给父亲看病的两位医术不高明且漫天要价、故弄玄虚、戕害病人的两位中医代表。可见,鲁迅对中医持有绝对的否定态度以及强烈的厌憎感。相对于鲁迅,老舍对中医的态度则相当温和,没有轻易地进行价值判断。而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又可折射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态度。这样,老舍再次背离文化启蒙的主流轨道。
老舍与“五四”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本文不能详细论述。不过,在相关生育叙事的文本中可见端倪:一方面,作为“五四”运动的旁观者,他以强有力的文化批判坚持和继承了“五四”精神;另一方面,他的文化启蒙又与“五四”并不完全一致。老舍的文化批判更多指向于对落后的文化习俗的批判而非礼教的批判。此外,批评之余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认同与焦虑,没有导向与传统的全然决裂,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启蒙特色。
二、关注生育主体:理性的现实关怀
与《伤逝》《倪焕之》《寒夜》等现代文学作品一样,《生灭》《一筒炮台烟》关注到了青年知识分子结婚后的经济问题。老舍笔下,严峻的经济问题因妻子有孕一事铺展开来。与前三部作品提出问题但以无解的悲剧收尾不同,老舍为处在矛盾中的人物提出了解决方案:面对现实,解决经济问题,以生存为先。作家对生育主体给予高度关注:一方面明确了男性不但要勇于承担个人小家庭的重担,还要有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面对被残酷现实所累的美好女性(不只是知识女性),作家能够抛开世俗的道德评判,站在男性合理立场关怀、理解将为人母的她们,守护其主体存在。可惜,由于自身复杂的性别意识,尤其是对女性深层的心理恐惧,导致对“恶女”形象关怀不足,存在某些价值缺陷。不过从整体来看,生育叙事的小说中对生育主体的关注,所展现出老舍富有理性关怀、可贵的现实主义品格。
(一)明确男性责任
在散文《婆婆话》《我的几个房东》中,老舍指出了家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老舍不但敏锐地提出了复杂的现实问题,并且在现实困境中给出了些许明智的策略,即生存为先,生产在后。在他看来,爱情与婚姻不同,婚姻(家庭)要求人的行为更加理智,只有奠定殷实的经济基础,方可谈及家庭与孩子。因此,《生灭》中秀华的怀孕让曾满怀理想的阚进一认识到了经济问题的严峻;《一筒炮台烟》里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文与梅为了更好地生存,选择了堕胎。
此外,在老舍的观念中,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男性。如在散文《有了孩子以后》中,作家在享受孩子给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感受到男性所肩负的重大责任。而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婚姻、家庭负责,也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所以,《生灭》中的文要对自己爱的行为负责,就必须残忍地除掉“甜蜜的负担”;《一筒炮台烟》中的阚进一在结尾呼出:“咱们的儿女必要生得干净!生得干净!”[2](P90,第八卷)他不再把婚姻当儿戏,开始为秀华生产考虑,还要肩负起社会责任,拒绝获取不义之财。且不论文章艺术价值的高低,隐含作者确乎借阚进一之口表明了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折射出老舍的家国理想和现实主义品格。
(二)女性观照的得与失
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老舍抛开世俗的眼光,理性地站在男性合理立场庇护美好女性的生命存在,体认那些将为人母的女性价值,反对把女性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从而守护了女性主体意识。遗憾的是,源于老舍对女性主体性深层的心理恐惧[4],谈及“生育”,仍对其笔下的“恶女”、“泼妇”形象仍然关怀不足。作家一味地丑化这类形象,掩盖了她们的合理声音,造成其艺术价值和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
老舍笔下,丈夫对怀孕的妻子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尊重与呵护。《一筒炮台烟》中曾一度对婚姻满不在乎,抱有理想主义的阚进一对秀华有孕后的体态、容貌的改变持深切的理解与关怀态度:“他服侍她,安慰她……她现在正受着一种苦刑”。[2](P84-85,第八卷)这明显与《倪焕之》中倪焕之对金佩璋嫌弃、憎恶的态度不同。《我这一辈子》中纵然 “我的妻”背叛了“我”,“我”对将为人母的“我的妻”表现出相当的欣赏与呵护:“她有了孕,作了母亲,她更好看了……世界上还有比怀孕的少妇更可怜,年轻的母亲更可爱的吗?”[5](P273)隐含作者借将为人父的丈夫之口,表达了对女性生育之苦的关怀与理解,同时肯定了女性生儿育女的价值。尤为可贵的是,他摒除世俗的道德评价,给予经受现实困苦的美好女性们温存的关爱与宽容。《鼓书艺人》中被丈夫抛弃的方秀莲未婚先孕,作者并没有用道德的眼光审视指责秀莲,而是通过父亲方宝庆宽广、深厚的父爱表达了对她的同情与关爱;《生灭》中,对于妻子梅的再次怀孕,丈夫文常常自省自责不理性的施爱行为,而最终梅毅然选择堕胎,隐含作者没有用人伦道德评价这一行为,而是站在了尊重、理解女性的立场上,并主张成熟男性理应主动为“爱”负责。
老舍尊重女性生育价值的同时,反对把女性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传统生育观。《柳屯的》中,因不能完成传宗接代任务而被夏家欺凌的夏嫂,得到 “我”的竭力帮助,最终含笑死去。隐含作者怜悯夏大嫂的处境,控诉了男权社会中因女性不能传宗接代而遭虐待的丑陋现象。这与以传统观念品鉴女性的林语堂等人的生育观念截然不同。《京华烟云》中,不能生育的牛素云无法进入曾家族谱,而为曾襟亚生儿育女的丫鬟银屏却被写入族谱。可见,老舍站在了更高处,颇具现代性与进步性。
然而,很可惜,老舍对美好女性的宽容与观照却没有分给文本中的“恶女”、“泼妇”。首先,《骆驼祥子》中对待虎妞难产之死,隐含作者并未体现出逝者已去的悲伤,而是借此完成祥子的“又一落”;除了在情爱方面对虎妞不公,①参见: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张丽丽:《从虎妞形象塑造看老舍创作的男权意识》,《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文本也没有挖掘虎妞之死的深层原因:虎妞无母,缺乏母爱以及母亲对女儿在生育方面的教导。但作家并没有点明其母爱及母性教育的缺失,只是看到父亲对虎妞扭曲、变态性格的影响。不但对虎妞关怀不够,也有为祥子开脱之嫌。再看《柳屯的》中的“柳屯儿”,作家不再给予她和夏大嫂一样的怜悯,她钳制夏家人甚至整个村,是个极其泼辣、令人生厌的形象,我们很难燃起对这一可怕的泼妇形象的同情。笔者以为,“柳屯的”这一形象的塑造存在严重缺陷:该形象的产生是基于作者内心深处对女性的恐惧心理之上,因此从“柳屯的”一出场就展现出她惊人的“神通广大”。殊不知,“柳屯的”也是被娶来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受害者,到了夏家她同样失去了自由,隐含作者丝毫没有体会她的合理诉求,陷入了以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刻意丑化女性的性别偏见之中。因此,老舍对其笔下的“恶女”、“泼妇”形象作为生育主体的观照有失偏颇。
三、关怀理想的生育观:为国家而生产
抗战时期,老舍义不容辞地奔赴前线。“国家至上”成为他此期间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最突出的思想主题。涉及生育问题时,与前文体现的理性生育观有所不同,明显表明女性要“为国家而生产”的理想生育观念。因此,这些小说中承担生育任务的女性沦为作家宣传爱国思想的工具,致使女性形象单一化、符号化,小说也因此陷入了概念化写作的泥潭。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又与一直怀有强烈国家意识的老舍,在此期间持一颗诚心狂热地追赶时代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从而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
(一)“国家至上”的爱国生育理想
全民抗战爆发后,老舍擎起“国家至上”的大旗,以唤起整个国民的爱国意识。基于崇高的爱国理想,“国家至上”的核心思想同样渗透到此期间有关生育叙事的文本中,老舍为此提出“为国家而生产”的理想生育观。
1938年3月15日,老舍曾在给陶亢德的一封书信中强调国难期间男女都是兵,不属于彼此,而属于国家。小说《四世同堂》《蜕》以及话剧《大地龙蛇》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意识,而话剧《国家至上》这一标题,便凝结了“老舍一以贯之的社会理想”,成为他“抗日战争期间戮力追求的精神要义”[6](P303)。所以,此期间老舍以铿锵的笔调奋力宣传爱国主义的作品中几乎只有国家,没有个人。这样,一来谈及“生育”的文本不多;二来老舍把生育问题与国家联系起来,提出了“为国家而生产”的理想生育观。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如阚进一明确指出要为国家生子:“一个人必须为国家生小孩,养小孩,教育小孩。”[2](P85,第八卷)另外,当生育之事与国家大业发生矛盾时,“为国家而生产”的理想生育观则演化为“为国家而放弃生产”。《兄妹从军》中纵然家中老人盼媳妇秀兰“早生娃娃”,但听到丈夫与妹妹商议奔赴前线之事,秀兰则主动放弃传宗接代的使命,不但能够理解丈夫为国赴义的壮举,还甘愿侍奉老人。显然,秀兰这一形象满载作家“国家至上”的爱国生育理想。无论是“为国家而生产”还是“为国家而放弃生产”的理想生育观,都是为了完成老舍“国家至上”的爱国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它是建构在其政治理想上的一种空想,因此导致这部分创作丧失个性与现代理性,走向概念化写作的误区。
(二)追赶时代的概念化写作
抗战时期老舍小说中有关生育叙事的文本,大都是其爱国理想的宣传品。实际上,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老舍牺牲了创作个性,一味地追赶时代大潮,导致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均比较单一、苍白,尤其是女性形象更缺乏丰富性,艺术价值不高。在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价值作出客观评定之余,还须看到,一向疏离政治的老舍在抗战之时投身政治,成为时代的宠儿,他确是怀着一个真诚的心,勤勤恳恳地实践其贯穿始终的家国理想,而非刻意逢迎时代的伪善之作。倘若有“迎合”之嫌,又须看到老舍内心的矛盾与无奈的苦痛。认清这一问题,需从他的身份、个性出发体会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首先,为了宣传爱国理想,老舍简单地将其笔下的女性划分为好坏两个极端,仅就《四世同堂》而言,这种区分已很明显:文本中的“好”女人,往往是积极投身或配合国家危亡大业的那些女性,如:钱少奶奶、韵梅、高第,等等;“坏”女性则与“国家”背道而驰,不是汉奸就是堕落的浪荡女子,而且一旦贴上“坏”的标签便一坏到底,无一人得善终。如“泼妇”大赤包、胖菊子、招弟。她们贪婪、丑陋、自私,是社会的蠹虫,日本人的走狗,简直可恶得无可救药。再看所谓的“好”女人,一旦涉及抗战,便无主体性可言,从漠然的国家意识到坚定抗敌的思想转变,这一指向是老舍爱国宣传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已。这样该类小说就彻底走向了概念化写作,叙事手段并不高明。
有几个问题值得追问:老舍这些概念化的创作是否是以功利为目的的逢迎之作?答案是否定的。1937年11月老舍初到汉口以后,在抗战各个阶段的各类创作都坚守“文艺为抗战效力”的观念。在《写家们联合起来》《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等文本叙述中都可见老舍积极为抗战效力,绝非个人功利主义,并且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为民族战争服务,势必会大大削弱文艺本身的价值。但是,正是出于“国家至上”的真诚的爱国理想,他只能先做国家的捍卫者,暂且牺牲文艺的理想与价值。那么,为何一向疏离政治的老舍在抗战期间突然主动参与,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解释该问题,需要认识到老舍的特殊身份。他出生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和剧烈社会动荡的旗人家庭,满清王朝的没落带给旗人群体的衰落,对敏感的老舍产生巨大精神和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被时代遗弃的自卑意识。“五四”给了老舍“一个新的心灵,一双新的眼睛”,但是压抑、自卑的民族心理只是略有缓解,内心的“子民心态”(古世仓、吴小美语)始终没有彻底转变。到了抗战,老舍受到了当局者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认可,担任抗战文协负责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勇士,自卑的民族心态也逐渐被自信取代。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舍心态发生转变,时代越是消解了他压抑的民族心理,他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便愈加紧密,到抗战时,他已成为整个时代的追随者与歌颂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育”是一个价值的窗口,它蕴含着对女性、传统,甚至是家国的态度与思考。通过“生育”叙事,我们可以于细微之处了解并体认一个立体多面的老舍。
[1]王昉.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J].文学评论,2009(1).
[2]老舍.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舒雨.老舍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4]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J].南京大学学报,2005(6).
[5]现代小说经典丛书——老舍[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6]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On the Birth Narrative in Lao She’s Novels
GUO Cong
(School of Humanities,Beijing Language&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ao She,like some other male writers,paid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n women’s“kid-bearing”.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direct narration of the pain and efforts during the bearing process,he seldom described about the“bearing scene”.Based on the narration of kid-bearing in Lao She’s fictions,we could excavate his complex cultural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d to his relation to the era and politics.Only in this way could we give him a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Lao she’s fictions;the narration of kid-bearing;cultural enlightenment;reality concern;ideal procreation conception
I246
:A
:1009-1734(2014)05-0048-05
[责任编辑陈义报]
2014-02-24
郭聪,在读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