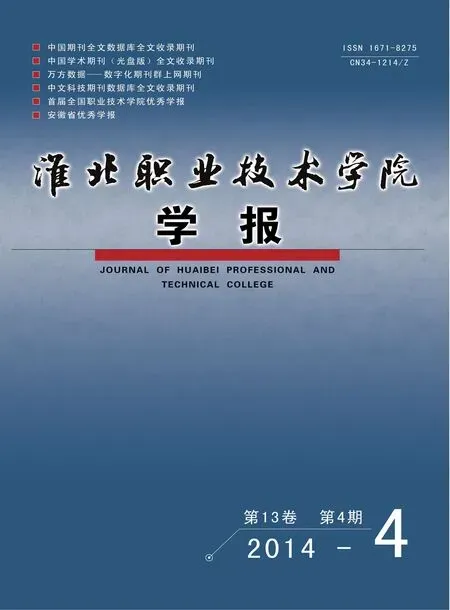扬州梦与长安梦
——论杜牧入幕扬州时期的复杂心态
陈红艳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扬州梦与长安梦
——论杜牧入幕扬州时期的复杂心态
陈红艳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杜牧是晚唐重要诗人。他曾入幕扬州,扬州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他惯有的心态产生摩擦与融合:身处扬州时,虽然享受着扬州的繁华与风流,但仍无法摆脱强势文化影响的焦虑;离开扬州后,却因“长安梦”的失落,常回忆起扬州的美好,以调适其严肃人生下的压力。
扬州梦;杜牧;心态;强势文化
杜牧是晚唐时期重要的诗人,他入幕为官多年,离开生活了二十几年的长安,辗转多个城市,从最初的洪州、宣州,接着到扬州,再而重回长安、洛阳,随后再寓宣州。空间的移动多少都对诗人的创作和心理感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城市都在杜牧的人生旅程中留下了不同的烙印。这期间,杜牧在回顾其入幕生活时,感叹“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可见扬州的回忆在杜牧入幕历程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的。而且,扬州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他惯有的文人心态产生摩擦与融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研究杜牧在扬州时的心态对整体把握杜牧其人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从中折射出当时的都市繁华与文人士子心态的关系。
一、强势文化影响下的焦虑
杜牧入扬州幕的时间并不算长,“(大和七年)四月,沈传师内召为吏部侍郎。杜牧应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1]145,大和九年,杜牧“转真监察御史,赴长安供职”[1]151,如此算来,杜牧入幕扬州大概两三年。而在入扬州幕前,杜牧与扬州已有联系,杜牧与牛僧孺早已认识,而在杜牧入扬州幕前已去过扬州,“(大和七年)春,奉沈传师命至扬州聘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往来于润州”[1]144。由此可知,杜牧在赴扬州幕前,便已经对扬州稍有了解。
《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篇对杜牧入幕扬州时的生活有所叙述:“唐中书舍人,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席。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轻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麓,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2]2151杜牧来到扬州这个繁华的胜地,生活过得逍遥自在,这样的生活与杜牧的性情是非常契合的。而且杜牧诗中如“才子风流咏晚霞,倚楼吟住日初斜。”[3]1373也透露出他在扬州时的风流自在,但从上述文段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杜牧面对着牛僧孺的告诫,他本能地予以否认、拒绝,何以致使杜牧言行不一?
(一)中晚唐时期的扬州
“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2]2151扬州虽不是唐代的京都,但绝对是当时繁华的都会。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也有记录:“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4]122便利的交通成就了扬州的繁荣,同时随着唐代具体国情的不同,扬州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初盛唐时期的扬州,在文人士子心中,多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游玩胜地,或是“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的散心地。时移世易,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代国运的转变,中晚唐扬州的地位也越发显得重要。
首先,安史之乱后,扬州成为政府财政命脉的咽喉。“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5]677,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尤为严重,北方大多数地区的赋税来源基本断绝,国家所需的财物,大多都是倚仗于江淮地区,“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3]1068,而扬州是江南地区的重镇。“节度使为军三万五千人,居中统制二处,一千里,三十八城,护天下饷道,为诸道府军事最重。”[3]755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彰显出扬州在中晚唐时期的重要性。
其次,由于扬州事关国家的财政,淮南节度使的人选也是十分关键的,因此,扬州也成为了众重臣的集居地。“然倚海堑江、淮,深津横冈,备受艰险,自艰难已来,未尝受兵,故命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3]755曾在扬州担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有:高适韦元甫、杜佑、牛僧孺、李德裕……戴伟华师《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有关淮南节度使的考证较为详尽。[6]此外,由于扬州是重臣的集居地,必定也会引来众多文人士子们的入幕,随之扬州的文化地位也相应提高。
因此,“邈若仙境”的扬州,借着它繁荣的经济、政治、便畅的交通吸引来自各地的文人士子,而“疏野放荡”的杜牧则是其中一个。然而,“文化的强弱区往往是政治中心及其直接辐射区域”[7]161,即便扬州此时的经济、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唐代的一国之都还是长安。扬州在文人士子心中仍然只是通向心中梦想地的匆匆一站而已。而长安,依然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二)杜牧印象中的扬州
杜牧是扬州的一位过客,同样的,扬州也只是杜牧生命中短暂的一程。身处扬州的杜牧对扬州的印象到底如何呢?杜牧在入幕扬州时曾写过《扬州三首》:
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投。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
秋风放萤苑,春草斗鸡台。金络擎雕去,鸾环拾翠来。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处处皆华表,淮王奈却回。
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柂轴诚为壮,豪华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3]287-288
杜牧诗文的研究中,对其抒情主体,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者着重其风流多情的“才子”形象;一者着重其正气凛然的“儒者”形象。在《扬州三首》中,杜牧展示出他作为风流才子对扬州繁荣似锦的喜爱与享受,而扬州的繁荣与享受在作为儒者的他看来,则成为一种罪恶。相比较而言,儒者形象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在杜牧的诗中,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贯穿了他对扬州最真实的印象: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杜牧印象中的扬州更多的是过去的扬州,隋朝的扬州。杜牧在扬州所写的诗文中,他多次有意或无意间涉及到隋韩时的人与物。如:
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却笑邱墟隋炀帝,破家亡国为谁人?《隋苑》
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隋宫春》[3]1432、1464
隋炀帝在扬州的风流韵事深入人心,寓于了扬州特定的浪漫风月色彩,同时,隋炀帝在扬州的狂欢如今也只是枉然。与隋炀帝有着千丝万缕的隋堤、隋宫、隋柳在杜牧特定的时代成为隋朝亡国的意象,如李商隐《隋宫》。此外,李山甫、罗隐、秦韬玉、吴融、翁承赞、江为等诗人也有类似题材的诗歌,都是借隋代的事物咏史怀古,抒发兴亡之感。这与诗人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因为相比较初盛唐的诗人而言,初盛唐时期书写扬州与隋朝相关人和事的诗歌非常少,明显的只有王泠然的《汴堤柳》,但王泠然是开元五年的进士,生活在唐代上升时期,诗中断然不会抒发朝代的兴亡之感。中晚唐的诗人们有的经历了唐代由盛而衰的体验,有的无缘盛唐的繁华,对过去的繁荣强盛只能想象与追叹,而扬州特定的历史文化正迎合了他们的文人心态。杜牧是那个时代的一员,在审视扬州时多少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虽然现实中的杜牧对扬州的繁荣乐在其中,充分展现其风流才子的一面,但杜牧在诗中还是无意识地秉持着儒者的风貌,对扬州的风流寓于批判。与其说杜牧对扬州风流的批判,不如说是杜牧对隋朝、隋炀帝的批判,或者是每个朝代晚期时自然而然的兴亡之感。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杜牧常处于长安强势文化区的角度来俯视扬州。在杜牧入幕扬州期间,他曾给卢弘止写过书信,信中透露出杜牧当时在扬州的心态与想法,《牧陪昭应卢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罢府,罢府周岁,公宰昭应,牧在淮南糜职,叙旧成二十二韵,用以投寄》:
燕雁下扬州,凉风柳陌愁。可怜千里梦,还是一年秋。
宛水环朱槛,章江敞碧流。谬陪吾益友,祗事我贤侯。
印组萦光马,锋铓看解牛。井闾安乐易,冠盖惬依投。
政简稀开阁,功成每运筹。送春经野坞,迟日上高楼。
玉裂歌声断,霞飘舞带收。泥情斜拂印,别脸小低头。
日晚花枝烂,釭凝粉彩稠。未曾孤酩酊,剩肯只淹留。
重德俄征宠,诸生苦宦游。分途之绝国,洒泪拜行辀。
聚散真漂梗,光阴极转邮。铭心徒历历,屈指尽悠悠。
君作烹鲜用,谁膺仄席求。卷怀能愤悱,卒岁且优游。
去矣时难遇,沽哉价莫酬。满枝为鼓吹,衷甲避戈矛。
隋帝宫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此总云浮。[3]1435
卢郎中,即曾与杜牧在沈传师幕中就职的卢弘止,而这是杜牧离开沈传师幕一年后与卢弘止的通信,诗中杜牧也不乏怀念过去与卢弘止共事的日子,但诗中开篇一个“愁”字,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暗示着即便身处更加繁荣的扬州,内心还是愁苦。“可怜千里梦,还是一年秋”,“可怜”应为可惜、辜负之意,“千里梦”可理解为“长安梦”,所谓“长安梦”,指回归强势文化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杜牧出身于名门望族,虽然年幼时便家道中落,但他从小便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邦济世的思想,抱有“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理想。而长安是唐代的强势文化区,即便是在藩镇割据的中晚唐时期,在众多文人士子心中,长安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杜牧不远千里来到宣州、扬州,希望通过入幕这一途径进入仕途,回归长安,从而实现自己的“长安梦”。然而,“还是一年秋”,一年过去了,从洪州、宣州,到现在的扬州,虽然扬州更繁荣、安逸,但其性质是一样,依然是远离强势文化区——长安。杜牧不禁感叹“去矣时难遇,沽哉价莫酬”,透露出杜牧即便身处繁华美景中,仍无法摆脱源自强势文化区的莫名压力。
基于那个时代与个人的因素,即便杜牧身处充满狂欢的扬州,也无法摆脱强势文化影响的焦虑。扬州能满足杜牧物质上的欢愉,却填补不了他精神上的空虚。
二、严肃人生下的自我调适
扬州对于杜牧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消逝,反而,距离抹去了扬州的灯红酒绿,留给了杜牧温情的小美好,调适他在严肃人生下的压力。
杜牧“(大和九年)拜真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结束了扬州的入幕,杜牧回归到强势文化区。这符合当时文人“进士——入幕——仕途”的期待轨迹,这也有利于他“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宏伟抱负,但身处强势文化区的杜牧常回忆起扬州的生活。《本事诗·高逸》记载: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巵,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后又题诗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8]17-18
“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如今杜牧集的版本多为“十年一觉扬州梦”,到底是“三年”还是“十年”呢?
此诗是收录在《樊川文集》的外编,这诗最早见于唐孟棨《本事诗》,为“三年一觉扬州梦”,同为“三年”版本的,还有宋初《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篇,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所编纂《说郛》。从杜牧在扬州入幕的时间来看,“三年”比“十年”更符合客观现实。然而,从情理上看,“十年”也未尝不可。“十年”并未指杜牧实际入幕扬州的时间,而是杜牧的心理时间,强调他对“扬州梦”的留恋,“十年一觉”正如《南柯一梦》一般,虽然黄粱一梦短暂,但已历经人生种种,犹如度过一生,更能反映出杜牧对扬州生活的念念不忘。
俞陛云《诗境浅说(附续编)》认为此诗诗眼当为“薄倖”二字[9]124,我却认为诗眼应为“扬州梦”。与“扬州梦”相对的是“长安梦”,根据《唐才子传校笺》卷六引《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等文,杜牧在大和九年至开成元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因此,杜牧写此诗时是身处洛阳——强势文化区。回归政治文化中心本应心里得到满足的,但杜牧反而沉醉过去在扬州的日子。期间,杜牧曾给扬州的韩绰判官寄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3]426诗中透露出杜牧对扬州浓浓的怀念。对“扬州梦”的怀念,意味着“长安梦”的缺失。大和九年正是杜牧回到长安那年,朝廷发生了“甘露之变”,对当时文人士子们政治热情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杜牧在《李甘诗》中曾表达出他经历“甘露之变”后的心态:“其冬二凶败,涣汗开汤罟。贤者须丧亡,谗人尚堆堵。予于后四年,谏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于时一裨补。拜章岂艰难,胆薄多忧惧。如何牛斗气,竟作炎荒土。题此涕滋笔,以代投湘赋。”[3]77由此可以推想,“甘露之变”时,杜牧身心所受到的压力之大。在强势文化区中实现不了自己的“长安梦”,唯有寄托于“扬州梦”,他透过扬州梦的追忆消融了长安梦的不得志,从而达到自我精神境界的平衡。
“扬州梦”,除了扬州的风花雪月外,还意味着杜牧在强势文化区中的迷茫感与失落感。在杜牧心中“扬州”已经不单纯是繁华城市的地标,同时,也从过去隋朝充满罪恶的迷楼,蜕变成属于他自己美好回忆的记忆城。
三、结语
杜牧对于扬州,并不是单纯的沉醉与享受。扬州的繁荣让杜牧暂时消融人生中的不如意,换言之,他只是用这样的轻描淡写来掩盖心中沉重的伤痛。这不仅仅是中晚唐士大夫的人生艺术,更多是他们悲剧人生的艺术表现。
[1] 缪钺.杜牧年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 杜牧.樊川文集校注[M].何锡光,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
[4] 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孟棨.本事诗[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9] 俞陛云.诗境浅说:附续稿[M].上海:上海书店,1984.
责任编辑:张彩云
I206.2
A
1671-8275(2014)04-0049-03
2014-05-21
陈红艳(1989-),女,广东台山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