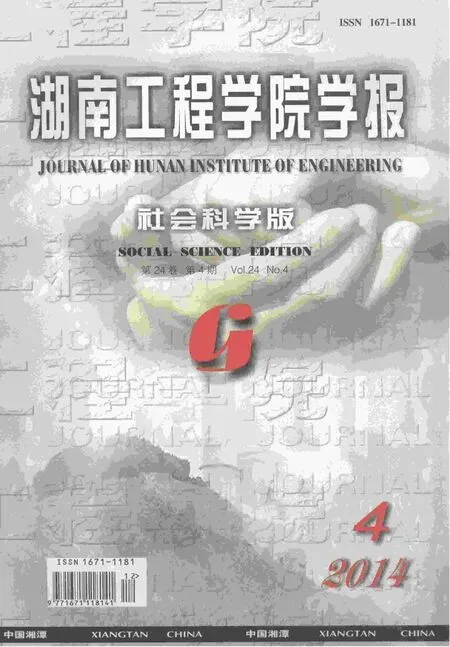扩大民间交往,推进东亚合作——新功能主义理论对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启示
陈 宇
(兰州商学院 陇桥学院,甘肃 兰州730101)
一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新功能主义理论
(一)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关于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是在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理论吸取了联邦主义理论的一些内容,与功能主义的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对于欧洲一体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功能主义理论。其理论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奈,菲力浦·施密特,厄恩斯特·哈斯等人。与功能主义理论一样,新功能主义也非常重视功能部门之间的合作,然而所不同的是,对于区域化合作的动力方面,新功能主义认为,不仅社会因素是区域合作的动力,超国家机构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因素主要是指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民众之间的多层次交流,而超国家机构主要是政治精英自主地推动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在双方力量的作用下,推进地区之间的融合和一体化的进程。
新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外溢,这一概念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功能性外溢,其二是指政治性外溢。所谓的功能性外溢就是指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一定功能部门的合作会溢出到另一个部门或者领域的合作,并且会将越来越多的部门与领域结合进来,由此逐步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所谓的政治性溢出就是指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会逐步有政治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合作。越来越会有超国家因素的合作,进而会逐渐推进这种超国家机构的产生,由此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厄恩斯特·哈斯(Ernest Haas)将其描述为:“最初由一个领域进行一体化决策外溢到新的功能领域。”[1]另一个新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ity),在外溢的过程中,一体化进程中的各国主权被越来越多地共享,而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将会在一体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随着超国家共同体逐渐地发挥作用,民众也会越来越多地增加对它的认同,从而逐渐发生效忠转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超国家的机构并非国家主权的替代物,而是与各成员国政府共享主权。欧洲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从1951年建立的的欧洲煤钢联营到现如今的欧盟,都体现了新功能主义的解释力度和指导作用。本文试图就新功能主义在欧洲一体化历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东亚的合作进行一定的对比,然后就东亚的合作提出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二)新功能主义要求的区域合作层次
新功能主义要求的合作是从两个层次推进的,一个是精英高层层面,另外一个是民众层面,欧洲的合作正好体现了这一理论的解释性,然而,相对于欧洲的合作,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有着自己的特征,总体来看,亚洲的合作在政治和精英层面的问题很多,难于进行,而在民众和社会层面,则有很大的前景。
二 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超国家层面阻力分析
欧盟目前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从欧洲煤钢联营开始,到欧盟的形成及欧洲统一货币的发行和欧洲议会的建立,欧洲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上的合作逐渐加大和深入。现在的欧盟正在经济上高度一体化的基础上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力图建立完全的经济政治上的联盟。
相比较而言,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就非常的困难。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东亚的区域合作涵盖了东亚的中国、韩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区域合作的机制中,目前有东盟以及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10+1和10+3等机制。比较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东亚的区域化进程虽然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逐渐进行,但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及全球化本身推进过程中的动力因素,东亚这一区域在经济一体化上或许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但在政府层面上,政治的一体化则极少可能到达像今天欧盟国家所达到的程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体化进程的外界压力
西欧当初设立煤钢联营以及后来欧共体的形成和欧盟的建立,一个重大的推进作用就是外界的压力。冷战时期这一压力主要来自外界的安全压力,具体主要是指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西欧各国的安全压力。当时的西欧各国,为了自身的制度安全,都有相互加强合作的要求和需要。这为欧洲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另一压力来自于内部,历史上的欧洲战争不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沉痛的记忆,为了以后欧洲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同时也考虑到对抗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战后的法德两国,在美国的推动下,[2]以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方式走上了民族和解之路。自70年代及冷战以来,欧洲联合的外界压力渐渐开始源自于经济上与日美竞争的压力。为了增强本国经济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欧洲各国的联合在经济上日渐加深。冷战后,欧洲各国联合的外界动力就主要的来自于日美的经济竞争压力。欧盟走到今天这一步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外界压力使然的结果。
东亚合作的外界压力并不如欧盟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大,而现在东亚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在欧盟和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压力下,东亚各国的合作主要是进行经济上的合作,这种合作可以更好地配置东亚区域的资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东亚各国的竞争力。然而这一进程是与全球化的要求相一致的,受全球化发展的决定和制约,不能主观硬性地强制推进,必须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要求逐步推进。现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至于东亚政治上的合作与一致,现在看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要看最终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要求了。
(二)各国之间的制度与文化差异问题
西欧各国的文化共同源自于希腊和罗马文化。西欧各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信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并不大,欧洲历史上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及其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及地理上的无阻隔使得欧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因此,早在18世纪伏尔泰就提出:欧洲各国应该建立欧洲联盟。
而东亚各国则差异巨大。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早在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了 “脱亚入欧”的方针,到现在仍从整体上自诩为一个西方国家。中国虽然改革开放30年,但社会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与东亚其他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东盟近几十年在发展速度,文明程度上日益提高,但与日本及中国等在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均存在差异,且与东盟的后加入国家越南、柬埔寨等亦存在差异。在中日韩的文化差异中,日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深远,而韩国文化则具标榜其独立性,东南亚各国,如马拉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地区的文化庞杂,除了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也是在历史上受到西方文化最早影响的亚洲国家。[3]由于在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宗教文化,国家的大小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一体化进程则要求各国在这些方面的一致性。这使得东亚各国在政治上要获得一体化是极其困难的。
(三)东亚各国之间的现实矛盾
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领土争端。东亚地区有包括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4]目前,在东亚各国中,中国、韩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争端,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领土争端,中国和菲律宾、越南之间存在南海问题争端,朝鲜半岛核问题争端,中国的台湾问题,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背后都有美国的巨大影响,美国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些问题复杂化,加剧了这些问题的解决难度。基于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问题解决的困难性,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东亚地区的政治和进一步的各项合作。
(四)区域战争意识的影响
欧盟的合作,固然有外界压力以及文化认同等诸多影响,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欧洲国家对于战争有一种普遍渴望避免的心态。正是此心态推动了法德这两个欧洲国家间的合作,才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获得了核心动力。欧洲国家自早期的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战争就始终未间断过,除了自19世纪初维也纳体系建立后的一百年时间,欧洲历史上爆发的战争数不胜数。尤其是法德这两个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大国,几乎与每一次的欧洲大战都有关系。而且彼此之间的战争与冤仇不断,围绕阿尔萨斯及萨尔区的争夺一直都在进行。本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欧洲战场,更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法德作为参战的双方,在谁也压不倒谁的状况下,双方的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和解,才会对双方都最为有利。由此,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双方最终达成民族谅解,走上了民族和解之路。
东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东亚的两个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就开始了连绵不绝的仇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给中国人民的伤害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得以平复的。而现今,日本政界不断有人出来发表否认侵略的言论,更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对二次大战的态度上,到现在为止许多日本人还不认为是中国打败的日本,是美国打败的他们。而在日本民众中间存在着大量的日本民族优越于亚洲其他民族的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和解。民众之间的不和解极大地阻碍了东亚区域之间政府层面的合作。
在日本民族和亚洲其他民族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日本人的种族优越心态及在历史上对亚洲的侵略,这一创痕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这还很难说,并且战争在促进亚洲的和解上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上是与欧洲联合也是有所不同的。欧洲联合可以说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选择的唯一道路,而亚洲由于各国的意识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层,也就是为避免战争爆发的心理准备还不充分。因此,东亚各国的统一观念是欠缺的。这样的看法乍一看或许有些极端,但人类的品性或许就是这样,欧洲的联合确实有对于战争恐惧的意识在其中起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亚洲则缺乏这样的一种意识,这在未来势必会阻碍东亚的一体化进程。
由此我们通过对照欧盟和东亚的合作的经验可以看出,未来东亚在经济上更为紧密的合作是非常必要和可能的,但在政治上出现欧盟一体化那样的趋势,在目前看来,还未看到这一可能出现。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由于外界的和历史的与现实的矛盾,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推进国家间政治层面的和精英层面的合作难度比较大。即便是有政治精英人士认识到东亚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也会因为上述的历史和现存的矛盾,导致各国民众之间对抗意识的加强,使得东亚国家间的政治合作遇到阻力。由于全球化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东亚的合作,有其必然的趋势。所以加强东亚的合作,符合历史潮流和规律,由此,找到东亚各国之间合作的突破口,对于东亚未来合作的发展,对于东亚各国未来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加强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民众交往关系的重要意义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东亚的合作是必然的趋势,而在阻碍东亚合作关系的发展中,主要是历史积累的矛盾和东亚的共同意识的欠缺,阻碍着东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东亚的合作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很多人也提出了东亚加强合作多种方式,但这些方式大多注重的是从官方角度来推进合作,即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来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而对于加强东亚地区民间的合作,似乎重视不够。本文力图通过说明加强东亚地区民间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东亚的区域化进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全球化进程一部分,其进程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东亚区域化进程目前发展较为迅速,但总体来看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对东亚区域化的进程势必产生很大阻碍作用,这中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东亚区域内,各国在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考虑到东亚各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国民的贫富水平及国家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及相互了解就显得对东亚区域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东亚各国之间民众的交往,有助于消除各国民众之间的误解和隔阂,这对培养民族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为东亚的区域化进程奠定一定的基础
东亚各国在历史上矛盾很多,这使民众之间的隔阂很大。在东亚的区域合作关系发展中,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钓鱼岛的领土争端问题。历史问题在中日两个民族间的关系发展中,目前来看处于重要的地位,从实质上来说,战争的责任其实应该由发动战争的反动统治阶级来承担,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则亦是战争的受害者,发展中日之间民众的相互了解以及消除相互的误解对于认清历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领土争端背后的关键因素还是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历史问题解决了,钓鱼岛问题自然就有了谈判解决的平台。另外还有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信任问题,而影响这一因素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问题。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在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差异,很多东盟国家的居民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与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这对于东盟各国与中国发展双边合作关系有很大的阻碍作用。所以有必要加强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活动,权威不一定来自于政府,而可以出自社会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甚至私营机构,这些第三方的权力也可以得到承认,并实际地发挥作用。[5]
(二)加强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有助于东亚区域共同意识的培养和建立
东亚的共同意识其一致性远小于欧盟,东亚各国在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有生产力作用的结果,也有东亚各国交往的限制及外来殖民主义行为影响的因素。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民间往来,对于加强东亚各国居民间的一致性,培养各国居民的共同意识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为东亚一体化进程奠定良好的基础。建立各国之间的非政治性的合作是一种良好的民众沟通方式。非政治性机制的作用不仅在于协调国家间经济社会交往面临的大量实际性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深化,还有利于扩大参与和支持区域化的精英群体,构建各国对于东亚区域注意的“共识”。[6]
(三)加强东亚各国间的民众交往有助于各国间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
各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增多,会增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也就会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创造机会。东亚各国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资源配置上也互有优势,民众之间的往来增多了,相互的认同增强了,就会为经济联系创造条件,从而可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从而不仅可以促进本国和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推动东亚的区域化的推进进程。
(四)加强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适应了全球化的进程,各国均可获益
东亚的区域化进程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加强各国民众间的交往,有助于推进区域化的进程,而区域化进程可以增强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其国家的竞争力和生存力,可以使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均获益。加强各国间的民众交往适应了区域化的进程,从而会使各国获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举动。在加强东亚民众的交往方式上,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首先,增强各国间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这里的非政府组织有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类的,这样可以促进东亚地区的非政府层面在这些方面的的各种联系。其次,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东亚各国民众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东亚有类似的文化,加强东亚间的文化和人员交流,可以促进东亚地区共同意识的提高。第三,为促进东亚各国间的人员往来创造条件,比如对于各国人员往来的签证和旅游等提供各种便利。
四 对中国来说,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民间的交往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和东亚搞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发展与东亚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既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也可以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中增强对抗来自美国以及欧洲的竞争压力。(2)发展了东亚关系,对于中国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以美国为首建立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这使东亚各国在历史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敌对和隔阂心态。在改革开放30年后,现在中国虽然在与东盟各国的相互了解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历史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加上中国和东南亚个别国家有南海领土争端,使得东南亚各国依然对中国存在一定的猜疑心态。而中国的崛起,对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也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东亚各国现在仍然对中国的发展并不完全放心,盛传一时的 “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表现。新世纪之初担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极独霸世界格局体系,继任的奥巴马政府虽然在对外政策中改变了单边主义行为,但是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格局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及中国的巨大潜在力量使得中美之间在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存在许多可变的因素。中国要想处理好中美关系,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要,可以增强与美国对话的能力。
因此,中国有必要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发展与东亚各国之间的民间往来对于消除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的误解和隔阂,增强双方的理解、谅解和信任,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有着突出的重要意义。以经济为动力形成的区域组织,从实践上看,它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内发生作用,它还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协调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提供帮助。[6]
鉴于和东亚各国发展关系的重要性,由此我们有必要在加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上下很大的力气。东亚各国发展民间交往的形式有许多种:加强民众之间的经贸往来关系,政府可以为此创造条件;加强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往来,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消除相互对对方的不正确的看法和态度;创造各种民间团体的相互往来的机会,搞好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此活动达到一定的程度,对于消除民众之间的相互误解,不至于因为一两件事情而对整个民族产生误解的现象发生会有很好的作用;鼓励东亚各国之间旅游业的发展,人员的交流可以促进相互的了解和民众间感情的联系,对促进民族间信任的建立有很大的好处。
总之,加强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间的民众交往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
[1]Brenst B.hass.International intergrate: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1,24(4).:372.
[2]李东屹.东亚区域化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J].外交评论,2010(2):84.
[3]王作成.试论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的构建[J].沈阳大学学报,2002(2):69.
[4]于海洋.东亚区域化的进展[J].东南亚研究,2010(1):61.
[5]李东屹.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4):73.
[6]王淑红.东亚区域化的必要性和制约性因素分析[J].美中经济评论,2005(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