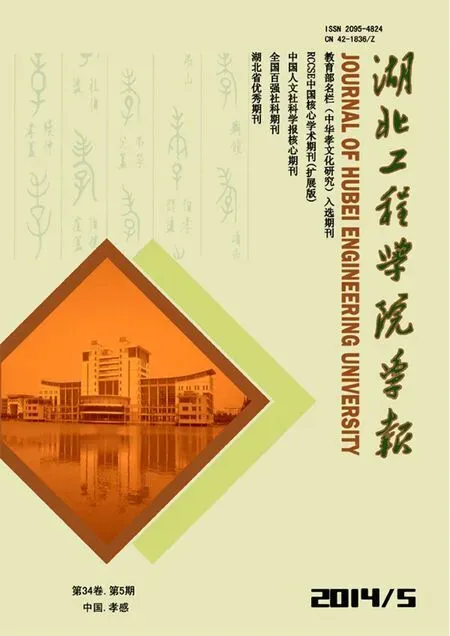网络犯罪中若干问题的界定
——对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思考
张立鹏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网络犯罪中若干问题的界定
——对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思考
张立鹏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9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这一司法解释满足了当下打击网络犯罪的需要,同时也给网络犯罪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此《解释》也引发了社会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本文是对《解释》条文规定进行的思考,主要涉及网络犯罪的概念、利用网络实施犯罪行为的入罪标准两个大的部分。在前一部分,主要是分析网络犯罪概念广义论和狭义论,并得出《解释》支持狭义论的结论。在后一部分,主要是分析《解释》对入罪标准的界定的意义以及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网络犯罪;界定;言论自由;管辖权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网络在全世界得到迅速普及,并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近日“秦火火”等一批网络水军的落马又一次警醒了世人,网络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网络犯罪也随之而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9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规范司法机关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刑事案件时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文就该解释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对网络犯罪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对网络犯罪的概念的界定
与“青少年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一样,网络犯罪并不是法定概念,不是刑法中单独规定的罪名,它是犯罪学上对一种类型犯罪的统称。对于网络犯罪,我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网络犯罪这一词语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网络犯罪是一种运用网络技术进行的综合多方面的犯罪,故对其进行有效界定不是一件易事。
就网络犯罪概念的界定而言,有学者提出“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两层概念。[1]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计算机是使用因特网这一介质、工具,由于因特网与计算机的使用在一定意义上已属一体,计算机是使用网络的前提,计算机犯罪的外延应该大于网络犯罪,网络犯罪应当包括在计算机犯罪之中,计算机犯罪显然是属于较高层次的概念。所以,对于网络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就首先要弄清楚计算机犯罪的涵义,这样才能了解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之间的差异及相互关系。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特网的使用必须通过计算机这一介质,但是,反过来,计算机犯罪的行为也必须借助于因特网,因此,在犯罪层面,计算机与网络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分别进行定义,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若不存在互联网犯罪的话,那么所谓的单独的计算机犯罪也就不会成立。
目前我国学界对网络犯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广义的网络犯罪概念一般被界定为以因特网为中介,以计算机为工具或者仅仅以计算机系统安全为侵害对象(对实体计算机终端设备的打砸行为除外)而实施的违反刑法,危害社会,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依据广义说,网络犯罪既包括现行刑法中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也包括利用网络实施的盗窃、诈骗、赌博等传统意义上的违法犯罪行为。网络犯罪按照这种观点应概括为: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攻击对象或利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为工具而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2]狭义的网络犯罪概念是指利用计算机操作所实施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盗取内存数据及破坏其他网络终端程序。[3]相对于广义的网络犯罪概念,狭义的网络犯罪概念少了第二层含义,即不包括利用计算机实施的传统犯罪。狭义论者认为,网络犯罪时,计算机和网络本身既是必需的犯罪工具,同时也是犯罪的对象。
广义说的网络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的犯罪:第一类以计算机本身为犯罪对象,例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第二类是以计算机为犯罪工具的犯罪,这类犯罪是高科技与传统犯罪的有机结合,例如,利用计算机系统危害国家安全、窃取国家机密的犯罪;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经济犯罪,比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利用计算机系统毁坏他人的名誉和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犯罪等。
而狭义论者认为,网络犯罪仅仅包括具有网络独特性质的犯罪。广义的网络犯罪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第一,虽然利用网络这个工具实施传统犯罪与传统方法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其行为仍应以传统罪名定罪,其根本性质没有变化。第二,以犯罪的方法作为划分一类罪的依据,这不符合以犯罪客体作为划分不同类别犯罪的理论。若是以犯罪方法作为划分犯罪性质的基础,那么,任何罪名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犯罪,因为几乎所有的传统犯罪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实施。第三,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网络犯罪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刑法第 287 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 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可以看出,刑法典认为以计算机为犯罪工具所实施的各类传统犯罪仍被认定为传统犯罪。持狭义说的学者还从最初的立法原意来论证其合理性。我国对网络犯罪最早进行定义的机关是公安部修改刑法领导小组,在其所颁布的《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罪方案》中,对网络犯罪概念界定的重点即在于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我国现行刑法第285条、第286条规定计算机犯罪,根据这两条规定,网络犯罪行为被认定为通过计算机非法操作来实施,其犯罪侵犯的法益也是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并且,这种对于网络犯罪的规定方式,意味着网络犯罪是法定的,唯有符合法定的条件,才属于网络犯罪的范畴。
持广义论者认为,将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纳入刑法学研究的领域的刑事一体化思想,是近年来学者所倡导的,也是刑法学研究的大趋势,认为刑法学研究应多加关注犯罪学中的研究方法、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问题等多方面,这样才能使得刑法学研究更能指导并应用于实践。[4]因而,对于网络犯罪一特殊的犯罪形式,应该将其进行多方面考量,涵盖各个方面,这样才能深入地了解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之策。其认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犯罪方法上,还体现在危害结果、实施方式以及案件司法管辖权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不同体现了网络犯罪的独特性,所以应将利用互联网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进行归类总结,整合为一类犯罪,在此基础上,再合理组织对此类犯罪的处罚。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广义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此决议虽然没有明确网络犯罪的具体概念,但是将以计算机系统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和利用互联网实施的传统犯罪都认定为网络犯罪。
广义说存在合理性,但是狭义说能更好地与传统的犯罪分类进行衔接。传统上,我国刑法学对犯罪类型的划分依据为同类客体、次同类客体。[5]狭义论者依据犯罪的本质属性, 将计算机犯罪限定为利用计算机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就遵循了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国外的立法也有很多采用狭义论,例如,1986年美联邦颁布的第一部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法案《计算机诈欺与滥用法案》明确6种行为构成网络犯罪。
笔者认为,网络犯罪的概念应采用狭义说。主要原因有:第一,这符合传统的犯罪分类方式,在实践中有利于被法律人所掌握运用。例如,某犯罪嫌疑人利用网络实施了诈骗犯罪,法官完全可以按照传统的方法判断这一“新型”案件。第二,狭义说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狭义说将以计算机系统为犯罪对象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分别交给传统的罪名研究,这有利于网络犯罪研究的细化,也更有针对性。第三,有利于立法及法律的适用,在立法方面,立法机关不可能将网络犯罪统一并进行细化规定,但是可以将利用网络这一方法解释到传统的犯罪当中,既可以解决网络犯罪问题,也可简化立法。在法律适用方面,虽然法官造法在我国未得到承认,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法官的主动性,法官完全可以对利用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进行判断,所以,我们没必要将网络犯罪的概念扩大化。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解释》,第一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一)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根据该规定,利用网络实施的诽谤行为仍应定为传统的“诽谤罪”,之后的几条规定都有类似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的导向是支持狭义说的。
二、网络行为入罪标准及其完善
2013年9月9日两高发布的《解释》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一些网络行为出入罪的标准。《解释》很细致地规定了一些网络行为入罪的条件,这为规制网络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在这个《解释》之前的立法中,乃至于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很少有涉及网络行为的出入罪问题,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刑法典只是规定了以计算机安全系统为侵害对象的网络犯罪,却对利用网络实施其他传统犯罪的行为没有进行界定;第二,网络行为本身及其产生的影响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难确定其危害性,也很难量化研究。
1.两高《解释》确定网络行为出入罪标准的意义。第一,这一标准的确定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这一标准的确立就像确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数额五万元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原来的不确定的东西进行量化,确定了入罪的标准。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带来一些危害。“熊猫烧香”烧毁了多少人的数据;*熊猫烧香是一种经过多次变种的“蠕虫病毒”变种,2006年10月16日由25岁的中国湖北武汉新洲区人李俊编写,2007年1月初肆虐网络,它主要通过下载的档案传染,对计算机程序、系统破坏严重。也有利用网络实施传统犯罪的例子,近来的“秦火火”、“薛蛮子”无不挑战着这个社会的秩序。网络谣言危害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需要依法打击。为此,在法律上完善打击网络谣言的相关规定至为重要。第二,这一标准的确定是保护普通大众权利的需要。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一个个体拥有很大的权利的话,那么别人的权利往往就容易受到侵害。[6]网络水军“秦火火”不仅编造、虚构事实攻击红十字会组织及杨澜(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及企业家),还捏造事实攻击道德模范雷锋,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更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网民的行为没有规制。所以,规制网络行为对保护普通大众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这一标准的制定也能防止普通公众不受非法追究责任。对刑法的司法解释,应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特别在目前打击网络谣言的大背景下,刑法谦抑、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重要。在一批兴风作浪的“网络大谣”落马的同时,另一种倾向也值得关注——个别基层司法机关执法不当,将网友的可以理解的失误,也当成恶意造谣进行了严厉打击。所以,将网络行为的入罪标准明确化,这也是对不当执法的一种限制,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
2.虽然两高作出《解释》有很深刻的意义,但是仍有很多有关网络行为犯罪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关于网络行为入罪标准确定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两高《解释》的第二条上,该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此处的转发500次或者浏览5000次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不可否认,这给网络诽谤入罪提供了一个标准,笔者也相信两高是在大量的调研之后才选择了如上量化标准,但是笔者认为,转发的次数及浏览的次数只能反应其中一部分社会影响,无法全部容纳所有的情况,比如,一个明星利用自己的微博等网络交流工具转发肯定比一个普通人转发影响大。明星转发后的影响可以用浏览次数来进行计算,但是,有很多信息是不点击就可以看到的。就像是普通网站上的广告,虽然他人没有点击该广告,但是人们潜意识当中已经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第二,有关网络行为证据的保存问题。关于电子证据的获得及证明力等问题,学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是仍没有得出很好的结论。一方面,电子数据的易损性决定了其极易灭失,犯罪分子只要有相应的网络知识就可以修改甚至销毁证据。同时,网络中数据信息的高速流转也可能使电子数据被覆盖;另一方面,网络海量的存储性也提高了电子数据获取的难度。[7]例如,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涉案电子数据集中在网站、网络空间、音视频文件、银行账户记录等方面,涉案证据数量多,公安机关需要对几个 T 的电子数据进行筛选、取证,检察机关也需要对其逐一进行审查。 同时,涉嫌网络犯罪的嫌疑人可在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隐匿,所以还需要远程监控、IP 地址追踪等技术手段对其进行锁定,办理网络犯罪案件比办理普通案件需要付出更大的警力和财力。既然电子证据难以收集、保存,那么仅仅根据转发或点击次数作为入罪或出罪的标准,是否严谨?令人费解。
第三,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如何保证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不被侵害仍需要明确。立法者在制定一部法律之前应将所有的可能性进行考虑,这样方能使制定出的法律既能满足现实所需,又不会被有关机关所滥用。在《解释》公布后,出现了很多打击网络犯罪错打的情形。前边笔者也提到,在目前中国打击网络谣言的大背景下,刑法谦抑、实事求是的精神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反腐的关键阶段,网络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给大众说错话的空间。动辄得咎,让互联网失去活力,舆论丧失监督能力,绝不是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的目的;相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让违法者寸步难行,让守法者畅所欲言,这样才是互联网法治的目的。所以,在贯彻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时,应体现宽严相济、不枉不纵、刑罚适当的法治精神,严格区别恶意造谣和错误表达,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保障公民的言论空间。
第四,网络行为犯罪管辖权的问题。网络行为犯罪具有很强的辐射性,[8]其涉及的范围不仅跨地域,甚至还跨国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各个国家或享有独立刑事诉讼权的行政区之间的司法管辖权的冲突。根据传统属地管辖原则,犯罪行为地或结果产生地都有权管辖,这就会间接产生一个法律冲突的问题。例如,赌博行为在A国是合法的,在B国为犯罪行为,这时,对跨国赌博行为人的行为怎么定性就产生了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两高发布的《解释》显然没有解决网络犯罪管辖权这一问题。
3.完善网络行为入罪标准及有关问题的建议。第一,进一步细化网络行为入罪的操作程序。笔者认为,此次两高联合发布的《解释》是一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司法解释。它明确了网络行为入罪的一些标准,并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之后肯定会有诸多的解释,甚至相关法律要参照它,所以就应予以完善,使其承担起标杆作用。按照《解释》第一条所给的标准,如果把握过松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把握过严又有可能干涉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应将有关条文进一步细化,达到现实的可操作性。笔者建议,对于在网络上诽谤他人的行为,应确立从网络行为受众这一角度切入的基本理念。一个网络行为一旦做出,其产生的影响主要通过受众数量来进行衡量。例如,某人发表一个诬陷他人的言论,经过多人转发,这时候就应该考虑经过转发后看到这一言论的人数多少,综合衡量其影响。解决网络诽谤的最好方法是从源头上限制,而不是单纯在事后“堵嘴”。所以,笔者建议,通过规定网络管理者的刑法责任督促网络管理者行使自己的监督权,避免网络管理者为了利益而放任网民的行为,进而实现网络行为的社会自制,而不是单纯的由国家事后处理。我国有关的法律已经规定了网站在不法网络行为中的法律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合理界定网站在网络犯罪行为中的刑法责任。网络行为主观上的故意是最难界定的,可能作出诬陷言论的人会说“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开个玩笑,他们当真了”或者类似的辩护。依据刚才所说的网络受众的角度,笔者认为前述情况仍构成犯罪,因为,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受众的想法,而不是言者的态度。
第二,通过法律以及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电子证据难题。科技带来的问题应该由科技进步来解决,但是,在科技尚不能解决其产生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法律不仅要满足眼下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在科技没成熟的情况下解决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当然,这需要成熟的理论以及完善的立法技术来支撑。[6]82与传统的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在取得、保全以及证明其真实性上有很大不同。在刑事诉讼法中虽然电子证据被归类到视听资料,但是与视听资料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鉴于电子证据的特点以及诉讼的便利性,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法律应对电子证据的获取及其证明效力进行明确规定,简化电子证据获取难及保存难的问题。例如,在普通犯罪中我们可以简化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可以同意个人的取证。在复杂案件中,应由专门的机构取证,并对个人取得或专门机构取得的电子证据程序的合法性、关联性质证并认定其效力。在技术层面,各网络管理者之间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并对网民影响力进行有效的评价。例如,应将关注者更多的明星的微博*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等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的影响力评定得高一些。
第三,明确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目前我国推进法治的情况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益发显得重要。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网络逐渐普及的情况下,言论自由权利得到更大程度行使。例如,网络反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次两高发布的《解释》最令人关注的是其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的影响。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强调,网民进行网络检举,“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两高考虑到了该《解释》对网民言论自由的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谁会一直关注新闻发言人所说的话。所以,应将这种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思想予以明文规定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体现在法律条文中,这样才更能体现立法者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视。就公众言论自由的保护,笔者认为应通过司法的透明化来实现。实行审判的公开公正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于网络行为犯罪,我们更应该在相关网站上及时的公布案件信息及通报案件的进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实现公民对网络案件监督,另一方面也用现实的案例来对公民进行网络普法宣传。总之,打击谣言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网络话语权、网络监督权,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第四,对于网络犯罪管辖问题,有的学者将几种管辖方式都进行了分析。[9]笔者比较赞同陈结淼先生所提出的区分网络犯罪的国内管辖权与国际管辖权的原则。首先,在主权意识强烈的当下,国际管辖牵涉到国际法,其只能通过主权国家签订国际条约来实现。而国际条约的内容,完全可以商定。对纯国内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适用现行的地域管辖理论,借鉴民事案件的管辖权规则, 以网络犯罪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服务器所在地、网络作案所侵入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或显示犯罪结果信息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网络犯罪管辖权的复杂就在于其国际管辖上的复杂,所以,解决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
三、结语
两高联合作出的《解释》是对网络犯罪规定的一个推进,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通过分析《解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网络犯罪的概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网络犯罪,以及非“典型”利用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行为。此解释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对于某些网络行为入罪标准的界定,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它为国家有效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提供了依据,也是受到非法打击群众维护自己权利的“护身符”。怎样既能打击日趋猖獗的网络犯罪,又能很好的保护好公民的言论自由及其他的网络权利的行使?这个问题是对此解释现实操作性的一个考验,也是对整个司法系统的一个考验。虽然《解释》解决了有关网络犯罪的疑难问题,但是除了文中提到的电子证据、网络管辖的问题,网络犯罪还有诸多问题待我们继续研究、解决。比如,《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有关情形控告方怎么提出证据的问题、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例如网络游戏中的“装备”)等。
[1] 卓翔.网络犯罪若干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04.
[2] 陈开瑜.计算机犯罪定义之我见[J].现代法学,1992(5):44-47.
[3] 赵秉志,于志远.论计算机犯罪的定义[J].现代法学,1998(5):8.
[4] 陈兴良.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犯罪学研究[J].中国法学,1999(6):113-115.
[5] 刘守芬,孙晓芳.论网络犯罪[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4.
[6]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21.
[7] 邵禹,张验军.网络案件引发的思考——以大连地区审查逮捕的网络犯罪案件为例[J].中国检察官,2013(5):32-33.
[8] 刘守芬,孙晓芳 .论网络犯罪[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4.
[9] 陈结淼.关于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立法的思考[J].现代法学,2008(3):92.
(责任编辑:胡先砚)
How to Define Some Conceptions about Cyber Crime: Reflections onInterpretation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 s Procuratorate and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Zhang Lipeng
(ShandongUniversityLawSchool,JiNan,Shandong250010,China)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s released 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abouttheCasesofImplementationofFraudCrimeorSimilarCasesbyUsingtheInternet(the following will refer to it asInterpretation). This judicialInterpretation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Cyber crime, and can be used as the direction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Cyber crime. Nevertheless,Interpretationhas also brought about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is papers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s in theInterpretation, discusses about the conception of Cyber crime and the criteria for Cyber crime. In other words, it analyzes the generalized theory and the specific theory of Cyber crime, and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Interpretationsupports the latter. In addition,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riteria for Cyber crime and the releva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criteria. Key Words:Cyber crime; define; freedom of speech; jurisdiction
2014-06-10
张立鹏(1989- ),男,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D924.399
A
2095-4824(2014)05-01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