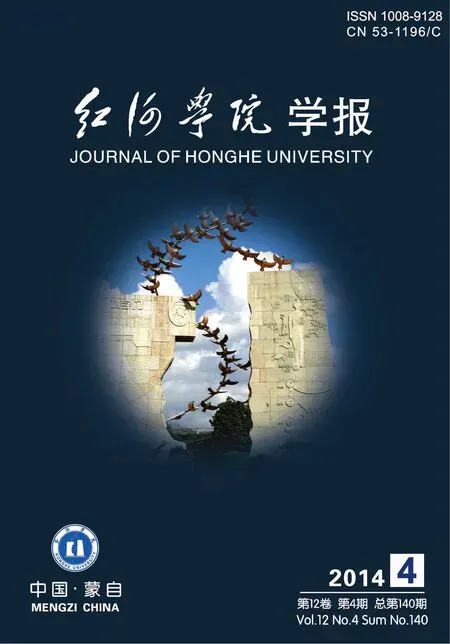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兴观群怨”说二解
聂家伟,苗鸿满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500)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兴观群怨”说二解
聂家伟,苗鸿满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500)
对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历来解释不一,且有相当出入。本文从《论语》的文本出发,结合《论语》中的相关言论以及其他相关典籍,从一种接受视角来解释“兴观群怨”。文章着重分析了“怨”字,认为“兴观群怨”在教化论之下体现出了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的层次;其在实用论之下,则体现出一种从内向外又回到内的“净化”作用。
“兴观群怨”;论语;孔子;教化论;实用论;“净化”
“兴观群怨”来自《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中的第九章:“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历代以来,许多文人学士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进行界定。“兴”,西汉孔安国认为是“引譬连类”[1]16,宋朝朱熹认为是“感发志意”[2]179;“观”,郑玄认为是“观风俗之盛衰”[1]16,朱熹解释为“考见得失”[2]179,黄侃义疏说是“诗有诸国之风,风俗盛衰,可以观览而知之也”[3]1552;“群”,孔安国认为是“群居相切磋”[1]16之意,朱熹认为是“和而不流”[2]179的意思;黄侃认为是“诗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也”[3]1552;“怨”,孔安国认为是“怨刺上政”[1]16,朱熹解释为“怨而不怒”[2]179,黄侃认为是“诗可以怨刺讽谏之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3]1552。从上面所举的几种解释可以看出,尽管这些文人学士的出发点有某一些共同性,比如都在强调诗的教化,但是,他们的解释却并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对“怨”的解释。
不仅如此,就是当代的一些文人,在对这几句话的解释上,也表现出了不小的分歧。
杨伯峻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诗?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力,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呢,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远呢,可以用来侍奉君上;而且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4]183”
夏传才教授在《古文论译释》一书中是这样翻译的:“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诗呢?诗有修身感化的作用,有认识现实的作用。有互相沟通思想的作用,有批评讽刺的作用。近呢,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呢,可以用来侍奉君王,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字。[5]23”
以上分歧似乎正应和了现代接受美学所讲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思,这些解释都是文人学士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阐释的,不同的人就有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不是就没有一种比较更加接近孔子这句话的原意的解释呢?
一 “兴观群怨”说的接受视角
接受美学是一种以读者(接受者)为中心,围绕读者与文本对话这一焦点展开研究维度的文学批评方法。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和阅读的再创造性。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居于整个文学过程的中心,是实现文学审美价值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说,没有读者的阅读,没有读者将文本具体化,那么久没有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6]347”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耀斯也认为,作品总是为读者而作,未被阅读的作品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阅读过程才能将之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接受美学者曾言:“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6]341”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置于接受美学的视角之下,我们发现其与接受美学中审美经验的基本结构:创造、感受、净化中的“感受”、“净化”有共通之处。秉承接受美学中解释和再解释以求新、满足变化现实需要的思想,用接受美学视角来讨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兴观群怨”说是可行的。
刘若愚先生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要我们注意“兴观群怨”之前的那句“小子何莫学夫诗”。因为很明显,孔子是在教导学生,强调诗对学诗的人的功用,从这一句出发,“我们可以认定孔子是从读者的观点,不是从诗人的观点,来论诗的”[7]234-235。从一个读者(接受者)的角度来看诗,那么,说诗可以“引譬联类”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显然是说诗人作诗的一种表现方式:类比;而“观”,则表示诗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至于“群”,刘若愚先生认为联系到前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十三章)的话,则可以看出群则是指“作为社交成就的优雅谈吐”[7]236;而对于“怨”,刘若愚先生则认为“怨刺上政”这样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从读者观点到诗人观点的突然转变”[7]236,并且认为孔子很可能是说“一个人可以藉着‘吟咏’适当的诗句而消除怨情”[7]236,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
无独有偶,叶朗先生在其《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也表达了与刘先生几乎相同的看法。叶朗认为虽然孔子说到“兴”,但是这个“兴”不是“赋”“比”“兴”的“兴”,因为“赋”“比”“兴”的“兴”是就诗的创作而言的,而孔子所说的“兴”,则是就诗的欣赏而言的。对于“观”,叶朗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诗歌的欣赏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二是认为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志向(“诗以言志”)和诵诗的人的志趣(“观志”)。至于“群”,叶朗在结合了孔安国和朱熹的解释后,认为“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情感,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8]51。谈到“怨”时,叶朗认为是说诗歌“可以引起欣赏者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态度”[8]51。
尽管叶朗在对诗句的具体解释上和刘若愚先生还是有一定出入,但是,两者都认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都是从读者接受的视角去说诗的功能的。
但是,孔子为什么要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呢?这句话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是一种从诗的功用来讲的纯教化的理论,还是一种从读者视角来讲的纯实用理论?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包含在内。
二 纯教化的“兴观群怨”说
从以上分析的接受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这句话是在强调诗对接受者的教化作用。
无论是谁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将“兴”理解为诗歌的一种感发性能,即激发人们的兴味,将“观”视为诗歌的一种认识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将“群”理解为通过咏诗以达到社交目的进而达到合群目的,这种解释应该是恰当的。但是对于“怨”的解释,我们则要作一思考。
正如上文所言,如果将“怨”解释为“怨刺上政”,那么,孔子就从一个读者视角转向到了作者视角,因为诗“怨刺上政”,显然是作者(创作主体)的工作。但是能不能将“怨”字理解为读者借诗来表达“怨刺上政”的意见呢?笔者认为,这显然也是讲得通的。
从对“兴”“观”“群”三者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可以感发人们的意志(“兴”),诗歌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事物(“观”),诗歌可以使人们达到社交目的(“群”),这是诗歌的教化功能的三个层次:“兴”(感发意志),这种功能是在人的内心完成的;“观”(认识事物),这种功能是在人自身完成的;“群”(社交与合群),这种功能是在人与人这样的小群体之间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内心——人本身——人与人之间(群体),这呈现一个从内向外扩展的趋势,那么,作为第四层次的“怨”字,则必然走得更远,它指向一个更大范围的群体——社会。这里的“怨”字就是指对社会不平种种的批判,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奴隶半奴隶社会,社会的种种不平现象又多是上层统治者的统治造成的,所以将“怨”字理解为读者借诗“怨刺上政”应该也是可行的。
《诗经》中许多诗人用诗来表达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如《魏风•葛屦》中“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小雅•节南山》中“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不过正如上文所言,这些例子都是诗人自己作诗来“怨刺上政”,并不是读者的参与。虽然在孔子时代,“赋诗言志、引诗证事之风由高峰开始回落”[9]75,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古代典籍里,却记载着不少这种风气。《左传》中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之会中就是赋诗言志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垂陇之会: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奔奔》。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闻,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10]105”子展赋《草虫》,以赵孟为君子,表达对赵孟的仰慕,所以赵孟推托说“不足以当之”;而伯有赋《鹑之奔奔》,原诗是卫人讽刺其君上荒淫的,伯有在这里表达了对郑伯的不满,赵孟觉得在这种场合赋这样的诗不合适,所以说“非使人之所得闻也”,但是伯有借诗来讽刺郑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出,借赋已有的诗来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将“怨”理解为读者借赋已有的诗来“怨刺上政”的说法是可行且恰当的。此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赋诗者(接受者)是因为其心境或者情感指向与诗中所表达的意思相符即产生共鸣,故借诗纾解内心的愤懑,也就是耀斯所说“让观察者在独自的心灵解放中获得纯粹的个人满足。[11]116”满足纾愤的需要。
如果将“兴观群怨”后面那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话考虑进来,则更可以看出孔子说这整句话的一个层次了。“迩”,是近的意思。也就是说,诗对读者的功能或作用是一个从近到远的走向。这就更加证明前文所理解的内心——人本身——群体——社会这四个层次的正确性了,因为内心,人本身,我们可以视为“迩”;群体,社会,则可以视为“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这四个层次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只有诗感发了人的意志,人才能认识事物,从而进行社交活动,达到合群目的,并进而对更广大的社会种种不平进行批判或“怨刺上政”。所以,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所起的功能作用是从内到外、由近及远的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三 纯实用的“兴观群怨”说
当我们再次考察以上这种从内到外、由近及远的诗教功能时,我们发现,当我们把“怨”字理解为读者借赋已有的诗来“怨刺上政”的说法并不能完全视为孔子真正的意思。因为,整部《论语》中,每次孔子谈到“诗”时,他都不是以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来对诗进行文学性的解读的。
在《八佾篇第三》中,当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时,孔子答道:“绘事后素。”当子夏对于老师的回答进一步发挥为“礼后乎”时,孔子给予了子夏很好的评价:“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可以看出,孔子对弟子的问题并没有真正从诗本身去解读,他完全是断章取义,为他自己的教学所用。从这种断章取义可以看出孔子在解读诗时是采取的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
在《子路篇第十三》中,他的这种实用观表现得更加明显:“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认为,纵然读诗读得多,但是不能做好政务,不能借诗来谈判应酬,那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在教育他儿子伯鱼(即孔鲤)时,他也表现出那种实用目的。他问儿子学诗没有,当儿子回答说没有,他便说道:“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第十六》)。杨伯峻先生将这句话译为:“不学诗就不会说话。[4]177”杨先生当然是理解这句诗的意思的,不过考虑到译文要通行的原因,并没有对该句话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学诗,就不能懂得一些辞令,就不能对答。孔子将《诗经》视为一种外交辞令的词典,实用主义的观点也就更加明显了。
当把“兴”、“观”、“群”三者分别理解为激发意志、帮助认识事物、帮助达到社交和合群目的,这些功能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把“怨”字理解为读者借赋诗来“怨刺上政”则可以看出对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诗歌激发意志、帮助认识事物、帮助达到社交和合群目的,这些都给一个读者以切身的益处,而“怨刺上政”则不能;固然这种“怨刺上政”的声音能够传达到统治者的耳朵中,但是统治者是否会反馈,反馈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很难预计的,并且这些反馈都是很滞后的,并不能及时地给讽咏的读者带来好处。
那么,这里的“怨”字就应当是刘若愚先生那种理解了:一个人可以借吟咏适当的诗句而消除心中的愤愤怨情。这种解释是讲得通的,因为当我们阅读了一篇美好的文章时,我们烦乱的心绪就会平静下来,这正说明阅读的这一个重要作用。当然,如果这样理解,这就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给悲剧下定义时,就谈到悲剧的净化作用:“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别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2]19”这里的“陶冶”可以翻译为“净化”或“宣泄”。很显然,这句话说明了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净化”,而不是人们所讲的“引起怜悯和恐惧”。罗念生先生以为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所持守的“中庸之道”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须求适中,情感须求适度”[12]118。亚里士多德在其《尼科马科斯伦理学》中这样说道:“……那么美德也必善于求适中。我所指的是道德上的美德,因为种种美德与情感及行动有关,而情感有过强、过弱与适度之分。例如恐惧、勇敢、欲望、忿怒、怜悯以及快感、痛苦,有太强太弱之分,而太强太弱都不好;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动机下、在适当的方式下所发生的情感,才是适度的最好的情感,这种情感即是美德。[12]118-119”
孔子同样讲究中庸之道,他强调“过犹不及”(《先进篇第十一》),讲 “温柔敦厚”之道,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正是孔子所说的“怨”。
而接受美学的领军人物耀斯是这样界定“净化”的:“对由演说或者诗歌激起的情感的享受,这种享受在听众或者观众身上造成信仰的变化和思想的解放。[11]112”即它能够能改变并解放听众和观众的心灵。显然,从这种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个“怨”字照样是对接受而言的。不过,很可以看出,耀斯的解释将我们的视角延伸到对“观”的解释上了,读诗人即耀斯所说“听众”或“观众”在阅读(观外)之后内心生发“感受”并反观自身(观内),自审、自省,发现自己言行举止等不当则改之,以达到提高自身修养——净化的作用。他在谈到“感受”的历史变迁时说:“爱德蒙•伯克和卢梭是使感受从美的传统准则中解放出来的先驱。此后,感受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把自然体验为风景,使观察者在风景与他的灵魂交流中发现真正的自我。”[11]95这样,在“观”(认识事物)的基础上,我们与外界一切达成共鸣,从而与外界化为一体,达到合群的目的,最后在这些基础上,在外界与灵魂的沟通过程中,终于得到净化,从而发现真正的自我。可以看出,二者都强调审视外界事物对反观自身(灵魂)的重要作用——净化。
“观”与“怨”是紧密联系的。读者通过读诗(观),有所感——产生共鸣,“受到演讲者诗歌激励”[11]39,借诗纾解内心不平与怨愤,从而产生泄愤之乐,达到净化心灵的作用,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怨”。
当然,当我们把“怨”字与“净化”等同时,我们发现孔子说这句话的另一个层次了:从人的内心到人自身,再到人与人之间的群体,最后又回到人的内心,也就是内心——自身——群体——内心。当然,开始是激发内心的意志,是一种冲动的情感,是孔子所说的“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太强”,而最后是在内心净化情感,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这四个层次,始终没有离开人自身,从内心到内心,可以看出孔子的一种人本主义关怀,更加可以看出其实用的目的。
结语
接受美学的理论让我们明白,作品的意义及审美价值都是在读者(接受者)的阅读和欣赏中实现的,只有通过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来更新其意义,才能使曾经是权威的文本满足变化的现实需要。
纯教化的“兴观群怨”说结合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将兴观群怨解释为诗的四种功能;纯实用的“兴观群怨”说将其解释为对读者有益的四种实用目的。我们应该看到,前者忽视了孔子在整部《论语》中解读诗时的那种实用观点,而后者则忽视了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的视角。也就是说,这两种解释都可能不完全是孔子的意思,但是,当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则会发现这两种解读新颖别致且又合理之处。笔者从文本出发,以一种接受视角来解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这只是一种尝试,但没有达到深度,而至于更深入的分析,则只有以待来者了。
[1]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55.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96.
[3]黄怀信,孔立德,周海生.论语汇校集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512-1530.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09.
[5]夏传才.古文论译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4.
[6]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41-354.
[7]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1-334.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98.
[9]马银琴.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J].文学评论,2004, 5:71-80.
[10]傅道彬.“诗可以观”——春秋时代的观诗风尚及诗学意义[J].文学评论,2004,5:102-115.
[11]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1-150.
[12]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134.
[责任编辑姜仁达]
Two Interpretations of “To Inspire, Observe, Company, Grieve” in the View of Reception
NIE Jia-wei,MIAO Hong-m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500,China)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s for Confucius’ “To Inspire, Observe, Company, Griev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To Inspire, Observe, Company, Grieve” from one receptive view according to the text of "The Analects", combined with some words in “The Analects” and other relevant books. The paper, focusing on analysis of the word--“Grieve”, interprets that “To Inspire, Observe, Company, Grieve” show some gradations which is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 from the near to the far from didactic view; show a function of “catharsis”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 and then back to the inside from practical theory.
“To Inspire, Observe, Company, Grieve”;The Analects;Confucius; didactic view;practical theory;“catharsis”
I0
:A
:1008-9128(2014)04-0078-04
2013-10-01
聂家伟,男,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