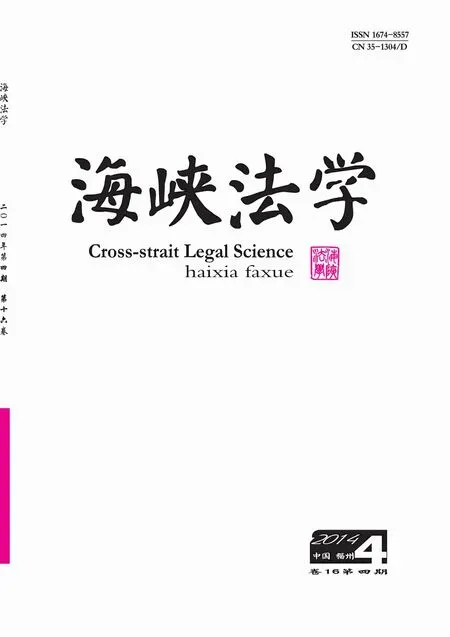论刑法的标签化及其克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面对大量的信息越发觉得无从选择,而“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有力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的网络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我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①[美]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7页。当陷入这样的困惑时,价值迷茫的个体只得通过标签来确定自己的选择方向和选择对象,而这已经影响了刑法的功能选择和价值取向,从而赋予刑法某种属性。
一、刑法标签化问题的提出:刑法标签化的不可避免
标签(label)概念源于基督教教主帽子上的一根布带,是权力的象征和标识。当经过商品标识的演化,标签被人们用来标志目标的分类,从而成为便于人们查找和定位目标的工具。这样,标签文化逐步得以形成。在标签文化中,人们运用互贴标签的手段给自己或者他人比较快速和明确的社会定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标签文化因具有快速定位的功能而被运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使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便捷地找出自己或者他人的社会定位,进而便于快速做出价值判断和方向选择。
在标签文化下,刑法也会成为标签化的工具,即社会利用刑法而将犯罪人与非犯罪人区分开来,并将犯罪人定位在社会的特定位置。这便造就了标签文化下的刑法。对犯罪人通过贴标签的形式予以评价并由此确定犯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这种做法,也为犯罪标签理论所支持。
犯罪标签是“社会对犯罪人刻意区别(与正常的社会人)导致犯罪人角色的定型。”①刘朝阳:《从犯罪标签理论的角度看刑法第100条的规定》,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第84页。同时,犯罪标签也是社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借助刑法评价而使得戴罪之身带有明显的社会标识。显然,犯罪标签引导着社会舆论将犯罪人排斥在正常社会生活范围与社会价值之外,其体现是某人在犯罪之后,社会舆论会对其加以各种批评,甚至全盘否定其个人品德和个人价值。犯罪标签是刑法标签化的一种外在体现或不可或缺的附属产品。
如果说社会是刑法“永远走不出的背景”②利子平、石聚航:《刑法社会化初论》,载《南昌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56页。,则刑法也永远是存在着刑法的社会的评价标杆。由于刑法毕竟是社会的刑法而刑法评价毕竟是社会评价,故通过定罪量刑而挂出来的犯罪标签便永远是刑法实施的一种副产品。因此,刑法的标签化是刑法的一种“宿命”。那么,作为刑法“宿命”的刑法的标签化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二、刑法标签化的恶果与真相:评价混同与义务强加否定个体价值
刑法的标签化是通过对犯罪人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予以确定其身份。那么,刑法的标签化带来了什么呢?其真相又是什么呢?
(一)刑法标签化的恶果:对个人价值的过度否定
刑法对人的评价功能是通过肯定或者否定其行为来实现的,但是这种评价本应仅限于法律方面。然而,在刑法将对犯罪人的评价功能标签化之后,社会舆论便将刑法赋予犯罪人的评价转化为对犯罪人评价的主要内容,并将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发生前的个人价值或是个人品格也牵扯进去。于是,刑法的犯罪标签便将该犯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在社会群体中的品格皆予以固定。之所以如此,乃因为社会无法于短时间内给予该犯罪人确定的社会位置以及恰当的评价。不可避免地,社会在借用刑法的标签评价时,又引入道德评价。这就造成某人在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之后,其个人价值及个人品格容易被社会全面否定。
通常来说,当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被刑法处罚后,该犯罪人的犯罪标签应该被及时去除,从而获得社会的原谅。但是,因为犯罪人曾经被贴过犯罪标签,同时该犯罪标签又“及时”被社会道德评价体系认可并且确定下来,故其作为“异类个体”会一直被归于“犯罪人”的行列,并且因为该犯罪标签的持续影响而致其在社会中在很长时间之内被处于固定的位置,并且因为社会道德评价系统中欠缺标签退出机制,最终导致其一直无法以正常人的角色融入社会,正是因为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中标签退出机制的欠缺,刑法标签化的克制方显得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现实情况是,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在欠缺标签退出机制的同时,刑法却在强化着犯罪标签。例如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该条规定的是前科报告制度,并明目张胆地贴起了犯罪标签。这可视为刑法维护自身已有标签化功能的典型体现。
在刑法贴出犯罪标签之时,其并未对犯罪标签的退出机制加以规定。囿于该机制的欠缺,刑法在贴出犯罪标签的同时又不断地强化其自身犯罪标签化的功能。由此,刑法在维护其犯罪标签功能的同时,也是在维护和巩固自身评价机制与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的一种“联盟”,以造成刑法评价与社会道德评价互相影响之局面。刑法对犯罪标签予以肯定的过程,即是刑法与其谦抑性相背离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不或多或少侵犯他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互相忍耐他人的侵犯。”③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如果说刑法一直存在并且保有犯罪标签化的本能倾向,那么刑法是在不断通过限制人的自由、固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之手段,以达到消灭犯罪之目的。
刑法对犯罪标签化持续肯定与强化的过程,也是刑法持续否定个人价值的过程,而配合该过程的是社会道德对个人评价的长期化与稳定化。在犯罪人被贴上犯罪标签之后,其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之前所有的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都会被社会道德否定,即便是改造后的犯罪人,且暂不谈论改造结果,他都将无法抹去犯罪标签。该犯罪人因为犯罪标签的存在无法重新融入社会,因为犯罪标签的存在强化了犯罪人与社会其他个体之间的区别,而被改造之后的犯罪人之个人价值,也会被社会利用犯罪标签予以否定。这表明刑法在贴出犯罪标签之后,社会利用该犯罪标签实现了对个人价值的全面否定,并且社会利用该标签持续排斥改造后的犯罪人。因为犯罪标签的存在,犯罪人始终无法与社会道德的要求达成一致而成为“异类”,以致成为社会的“弃儿”。改造之后的犯罪人因为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个人价值无法在社会中得以再次实现,该人将可能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由此可见,刑法充当了社会道德的“帮凶”的角色。
(二)刑法标签化的真相:与社会评价“为伍”且变相强加义务
当刑法对标签文化和犯罪标签持肯定态度时,可能并未考虑到犯罪标签对社会价值和社会道德观念的负面作用。当犯罪标签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以及社会道德评价的范围时,其给予犯罪人的迅速定位便被社会道德迅速吸收,而这符合标签文化中社会对人快速定位和道德对人快速评价之特性。同时,这种快速作用也是刑法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肯定与确认,也是对社会道德评价的肯定与维护。由于在标签文化中,社会和道德需要快速鉴别个人的社会地位,而法律的评价又是现成的假借,故刑法的犯罪标签化与标签文化中的社会价值与道德系统有所“暗合”。因而,在刑法进行犯罪标签化的同时,也是刑法对社会标签文化的肯定。刑法的犯罪标签化,是刑法对社会道德借用犯罪标签对某人进行鉴别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导致了社会道德在借用犯罪标签对某人进行评价时,刑法处于不作为状态。这导致某人在犯罪之后,因为犯罪标签的存在而被社会边缘化。同时,刑法对标签社会的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念的认同,使得社会道德观念对个体的排斥也当然地被认同。这便造成了犯罪人在重新回归社会时丧失了刑法的支持。
标签文化利用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对刑法实现不间断的导向与改造。在刑法通过自身的标签化肯定标签文化以及标签文化下社会对个人定位的方法之时,社会也通过运用犯罪标签肯定和衬托出刑法犯罪标签化的意义,但是刑法的评价功能在社会中的体现常常被这种运用歪曲,即社会利用犯罪标签对个人的定位,只是将刑法在社会中的作用局限于犯罪标签。社会运用犯罪标签对个人予以评价又反作用于刑法,即刑法为了维护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持续地肯定自身犯罪标签化的功能倾向,而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刑法被社会不断“浸泡”的同时逐步迷失了自身,从而被“标签社会”完全或彻底“绑架”,并成为社会道德评价卖力的“工具”。于是,我们看到刑法被社会不断改造的同时,刑法的评价也逐步与道德评价混同。刑法在标签文化中进行犯罪标签化的同时,其本该独立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式逐步与社会道德评价迈向混同。犯罪标签化不但否定了犯罪人实行犯罪行为之前的个人价值,也否定了改造之后犯罪人的价值。这种对人之价值的否定与道德对人之评价是一样的,即道德观念中的人是不可以有瑕疵的。这种本质上的“暗合”,使得他人在评价犯罪人的时候,对自己适用的评价的属性无法有效辨认,而进行评价的人对刑法评价功能与道德评价功能会出现认知错觉甚至混同。而混同的结果是刑法逐渐失去自身的独立评价体系与独立的评价功能,从而逐步沦为社会道德评价的“借具”。当刑法评价体系与社会道德评价体系趋同乃至混同,社会道德在对个人进行评价的时候便“绑架”了刑法,并以刑法评价之名行社会道德评价之实。
刑法评价功能逐步迈上标签化道路之时,便意味着刑法评价逐步偏离其初衷,而刑法的应然价值也被逐步改变。学者指出:“刑法的价值是奠基于保护公民自由基础上保护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统一。”①陈世伟:《刑法信仰的根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3页。但在标签文化中,刑法评价功能的标签化,最终实现的是刑法对个体社会境遇的定位。然而,对个人社会定位的功能本该由社会评价个人参与社会活动所体现之价值来实现,即社会通过个人在社会中体现的价值予以相应的定位。但是,刑法评价功能的标签化却是将社会评价纳入自己的麾下,从而导致社会评价与刑法评价同步且混同,最终使得刑法评价与社会评价产生了价值选择的迷茫甚至迷失。
刑法评价功能的逐步标签化抑制甚至否定了个人的正常欲求。对于个人的正常欲求,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指出:“国民的欲求是一种抽象化的观念。立法者最终只能站在平均的国民立场上来推测这种欲求。刑法应当在其与国民的欲求的关系上回忆起近代刑法学的精神,即刑法是国民自主规范的成果;应当重新考虑把制定刑法的基础与国民的欲求联系起来;而且,还应当重新认识到国民的欲求的基础中有人的赤裸裸的欲求在活动。”②[日]西原春夫著:《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3页。刑法评价功能的标签化,使得个人不得不考虑到犯罪标签的负面作用,进而压抑自己的欲求避免个人被贴上犯罪标签,以屈从于刑法评价功能的标签化以及与之“为伍”的社会评价。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中个人的定位无法被正视,而个人的价值无法通过正当欲求的实现得以彰显,最终个人价值在刑法评价的标签化之下变得迷茫,以至于迷失。
由于标签化的刑法压制了个人的欲求,故社会通过给个人设定过多的义务以配合刑法的需要。又当个人被设定过多的义务时,其欲求的被压制便进一步加大而变得越发不可奢求。在个人被强加更多的义务之后,刑法评价标签的外延便被标签内含的义务扩张了,而义务的扩张便是权利的限缩。易言之,刑法评价标签外延的扩张伴随着义务的强加。如果我们对刑法评价标签化外延的扩张作一剖析,便会发现标签文化下的社会评价体系对于义务强加是肯定的,同时社会也利用标签化的罪名评价个人,以肯定刑法评价标签化外延的扩张。基于社会的肯定,包括通过立法活动,刑法也进一步肯定了社会评价体系的标签化。在标签化的评价体系之下,个人的义务在不断增加,而增加的义务让个人自由越来越少。这样,刑法自身逐步被纳入标签文化的大潮,进而被标签文化同化,以至于缺少了独立精神的刑法成为标签文化的“附庸”。于是,刑法的独立性逐步丧失,而刑法也终将演变成标签文化中的“刑法标签”。
三、刑法标签化克制的价值之途:尊崇个体价值,塑造刑法信仰
学者指出:“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是在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遵循或诉诸法律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③朱苏力:《法律如何被信仰——<法律与宗教>读后》,载许章润主编:《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刑法信仰化的过程是刑法融入社会观念的过程。在当下的标签文化中,刑法被标签文化异化为社会道德对社会成员评价的标签,这便造成了刑法难以被信仰,因为犯罪标签化能够满足并表达社会成员参与评价和定位社会个体的外在需求,但无法反映并满足社会个体的情感寄托和内在需求。犯罪标签化的刑法忽视个人内在正当欲求以满足社会个体的外在评价需求,甚至是为了满足标签文化而“自我阉割”,使刑法在偏离被信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刑法信仰化需要刑法尊崇社会个体的价值,避免贬抑社会个体的正当欲求。如果说满足社会需要是刑法成为社会信仰的必须,那么尊重个人价值则是刑法成为社会信仰的基石。学者指出:“法律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意义,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④卓泽渊著:《法律价值》,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刑法要成为社会信仰,不能仅仅满足个体以及社会在标签文化下对个人定位的欲望,更需要满足个体及社会对刑法的内在精神以及内在价值的追求。那么,刑法需要尊重主体即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不能运用犯罪标签予以完全否定。刑法需要从尊重主体的角度出发,引导社会观念对个人的评价,避免因为刑法自身之缺陷误导社会观念。同时,刑法需要避免因为自身的缺陷导致对个人正常欲求无法满足之情形。此乃刑法信仰的必由之路。但在标签文化中,由于受标签文化评价体系和社会道德评价体系的双重约束,个人的自由空间颇为局促或逼仄。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刑法未将保障个人自由作为首要任务,那么个人的自由空间将会被通过标签化评价和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所增设的义务压缩得无限小,从而刑法信仰之目标也只会变得遥遥无期。
对于需要被信仰的刑法,从保护个人自由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刑法需要实现自身价值的多元化,避免陷入标签化的窠臼而成为标签文化的附庸。诚如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刑法学界看来,刑法最为重要的价值不外两个,即一是保障人权;二是保卫社会。”①陈世伟:《刑法信仰的根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7页。对于保障人权而言,刑法至少应先避免成为伤害个人的工具。在标签文化中,评价个人的标签来自于标签文化所掌握的工具,该工具包括道德和法律。但是,刑法的立法过程只会是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和妥协。在刑法成为信仰的道路上,刑法需要重视个人的利益,避免为迎合国家之要求、适应社会之需要而忽视个人之利益,因为个人的利益始终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和被评判的位置,个人利益容易在标签文化中经常被忽视、被侵蚀,而导致的结果是个人对刑法难以信任和难以信仰。当刑法信仰化的过程缺少个体基础,则刑法社会信仰便难以“汇聚而成”。那么,刑法评价应避免以个人某一方面的价值评判该人的整体价值和避免以刑法评价代替对个体的终身社会评价。易言之,只有摒除标签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的影响,刑法才能实现自身独立、公正的评价功能,从而塑造刑法信仰。
囿于个人需要服从社会需要这一特征,标签文化中的个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个人的价值难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得到尊崇,甚至为了满足社会利益和价值的需要,个人的价值可以被放弃。基于该社会氛围和文化思维,社会价值则是刑法关注的重点,而我们很难在刑法中寻觅个人价值的踪影。于是,刑法现代文明的特征被大打折扣。而在标签文化下,刑法若要尊崇个人价值,首要的是避免刑法中出现过多的个人法律义务。我们知道,标签文化为了满足达到在社会中快速定位个人的目的,会给个人强加更多的社会义务。在该文化影响下,刑法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而迎合社会文化的需要,以使自身在社会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刑法会给个人增加标签义务,例如刑法的前科报告制度之规定。但是,这样的义务规定让本属于标签文化的软规定变成了硬规定,因为标签文化中个人的义务可以分为软义务和硬义务,而社会通过刑法强加给个人的义务属于硬义务。于是,这样的规定便将个体的权利泯灭在标签文化中。因此,刑法需要通过自身规定肯定个人价值,乃至尊崇个人价值。这样,个人价值才可以在标签文化中得到尊重。刑法尊崇个人价值意味着尊重个体权利,应避免为了限定个体权利而规定更多的义务。易言之,个人权利需要得到刑法的扩张,而个人义务也需要得到刑法的限缩。刑法需要通过减少或限制标签对个人权利的限制而实现尊崇个人价值的目标,避免个人陷入标签义务的重围。只有这样,刑法才能避免个人价值被标签文化抹杀;也只有这样,刑法才有可能逐步被信仰。
避免个人被强加过多的义务意味着刑法需要注重个体的正当欲求和满足个体的正当需要。学者指出:“法律之主体的信仰对象,必须反映主体的情感寄托和内心需求,尤其法律调整对象的普遍性决定了法律要从整体上记载、反映并保障主体需求。”②谢晖著:《法律信仰的基础与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由此,标签文化下刑法务必充分考虑到个体的价值需求,以避免刑法彻底成为社会评价的“借具”。如果在标签文化下的刑法充分尊崇个体正当的价值需求,则刑法才能保有其评价功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才能结出刑法信仰之果。
四、刑法标签化问题的余论:刑法谦抑性中的制度补救
学者指出,“对于犯罪而言,刑法是一种有力的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不是决定的的手段,因为要完全消灭犯罪就必须消灭犯罪产生的原因。”①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可见,标签文化中的刑法干涉本属于社会评价的内容,故刑法只能慎重地、谦逊地适用于必要的范围。这是由刑法的谦抑性决定的。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在参与社会评价活动时应该恪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涉及到社会对个人的评价时,刑法应该退居其次。那么,刑法需要将属于社会道德评价的内容予以归位,坚守自身独立的评价特征。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在评价个人时应该充分地体现自身的宽容情怀,因为每个人触犯刑法规定是由各种原因综合造成的。然而,我们却看见刑法在利用标签评价个人之时,将犯罪原因归咎于犯罪人自身,从而将犯罪人的个人价值全方位抹杀。如果刑法对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如此对待,对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如此评价,那么就与刑法保障自由的目标相去甚远,也与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大相径庭。因此,在谦抑性原则指引下的刑法评价不应该全面否认个人的价值,而是应该在否定个人犯罪行为的同时,也肯定犯罪人的个人价值,以最终确保刑法评价本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唯有如此,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才能充分实现。
那么,在刑法谦抑性之中,作为对刑法标签化克制的,便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两个具体的制度举措: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综观各国的立法规定,前科消灭是指当曾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便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罪刑记录的制度②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而复权制度,是指对被宣告资格刑的犯罪人,当其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审判机关提前恢复其被剥夺的权利或资格的制度③同上,第716页。。前科是一个人不光彩的历史记录,一个人会因此而丧失某种资格或社会信誉。永远地保留前科意味着一个人因“一失足”甚至是事出有因的失足而永远地承受实际上的惩罚和心灵上的煎熬,这是不人道的。而前科消灭制度,就是要保证有前科者不至于永远承受实际上的惩罚和巨大的精神负担,从而合乎人道主义。前科消灭制度还为消除社会对有前科者的歧视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其不会因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在我国,虽然政策上坚决反对歧视曾经犯过罪的人,并强调各级组织要给曾经犯有罪行的人提供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和条件,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那种嫌弃、歧视曾经犯过罪的人的习惯势力还是很大的④同上,第713~714页。。可见,前科消灭制度至少能够事后性地和一定程度地消解刑法标签的负面影响。同样,复权制度也能够事后性地和一定程度地消解刑法标签的负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复权制度在消解刑法标签的负面影响上似乎呈现出更加积极的色彩。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则本文不便赘述。
正如本文开头指出,标签化是刑法的“宿命”,而刑法标签化的克制意味着我们应作出一种努力,而努力的目标是避免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在此“宿命”之中被“毙命”。如果说刑法标签化的克制是很困难的,则说明刑法标签化的克制是极有意义的。我们总认为刑法的价值求索之路艰辛而漫长。那么,刑法标签化的不可避免和必要克制之间的悖论,则是个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