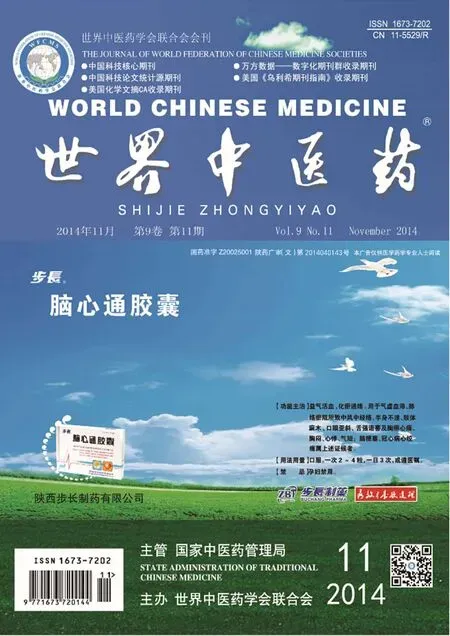经典的注释立场与话语特色:“志注”中“血气之生始出入”探讨
杨 峰朱 玲
(1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理论与方法学重点研究室,北京,100700;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100700)
经典的注释立场与话语特色:“志注”中“血气之生始出入”探讨
杨 峰1朱 玲2
(1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理论与方法学重点研究室,北京,100700;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100700)
张志聪对于气血理论的独特认知与表述,与针灸理论内容关联密切,尤其在有关血气出入路径的论述中,经脉、络脉、五输穴等理论内容得以丰富,彰显出作者自身深刻的理论思考,形成了“志注”颇具特色的注释话语,反映了其《黄帝内经》注释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立场,在诸位注家中颇为瞩目。气血理论性质颇为特殊,既是中医基础理论的范畴之一,同时也与针灸、经络理论密不可分,特别是气血出入体内与体外、脉内与脉外、体表与经脉、脏腑与体表的路径,纷繁复杂。在中医理论体系、针灸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中,对气血理论的内涵如何认识,及在针灸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中气血理论如何定位、表述,张志聪的相关认识或许可以提供借鉴与启示。以注释话语特色研究为切入点,可较好地把握注家的理论立场,总结其注释特质,有助于深入发掘与阐释注家的学术思想内涵,揭示其丰富的理论认识,由此可呈现针灸理论在注释中是如何传承、接受、理解的。对于针灸理论传承研究而言,这是值得关注的视角。
针灸理论;黄帝内经;经络;气血理论;注释
清代著名医家张志聪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注家中颇有特色且较为重要的一位,汇集同学及弟子,开集体注经之先河,先后著成《黄帝内经素问集注》[1]《黄帝内经灵枢集注》[2],影响深远。笔者在原著阅读中注意到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即《素问集注》《灵枢集注》的注文(以下简称“志注”)中大量出现与“血气”有关的论述(其具体话语表述又多与经络相勾连),内容涉及疾病、针刺治疗、经络、腧穴、脏腑等诸多方面,反映出张志聪对于“血气”形成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认识。换言之,“血气”相关论述在“志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内经》其他重要注家,如杨上善、王冰、马莳、张介宾等,在其注释中并未发现如此显著的特点。因此,对“志注”中的“血气”相关论述,实有专门探讨之必要。
“志注”中与血气密切连用的话语,有“逆顺出入”“逆顺之行”“出入之会”“外内出入”“循行”“生始出入”等,其义基本一致,尤以“生始出入”最为显著,共34次,且其他重要注本中未出现。可见,此话语在张志聪关于血气的认识与表述中极其重要(“志注”中有多次强调之辞)。本文拟以“血气之生始出入”为中心梳理张志聪对于血气的系统认识,探讨在此过程中彰显的其对于针灸理论相关内容的理解,以期阐明特色注释话语及其反映的注释立场。
1 血气之“生始”
《内经》中,“血气”“气血”并见,其义基本相同,“志注”中亦如此,但“血气”之使用多于“气血”。关于“血气”的生成,《内经》中已有论述。如: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灵枢·玉版》)“志注”秉承了经典所明确规定的这种理论认识,且更为丰富。
血气之“生始”与先天之肾(足少阴)、后天之脾胃(足阳明、足太阴)关系密切。且两者之用语亦有细微差别,言及肾(先天)者,多为“始、本、根、原”等,言及脾胃(后天、水谷)者,多为“生、出”。如:“此言经脉之血气,资生于胃,而资始于肾也。”(《灵枢集注·口问》)“营卫血气,皆本于先天后天生始之血气以资益。”(《灵枢集注·逆顺肥瘦》)“上节论经脉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阴肾。”(《素问集注·刺疟》)这种用字上的差别,也反映出先天与后天在血气“生始”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
脾胃虽为后天,但与血气的关系有所区别。如:“夫气血发原于肾,生于胃而输于脾。”(《素问集注·玉机真藏论》)“荣卫气血,始于足少阴肾,生于足阳明胃,输于足太阴脾。”(《素问集注·藏气法时论》)“十二经脉,荣卫血气,皆阳明胃气之所资生,足太阴之所输转。”(《素问集注·太阴阳明论》)可见,胃侧重于生发,脾侧重于转输。
心、肺与血气亦有关。如:“夫血脉始于足少阴肾,生于足阳明胃,主于手少阴心,输于足太阴脾。”(《素问集注·通评虚实论》)“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之血气,始于足少阴肾,生于足阳明胃,主于手少阴心,朝于手太阴肺。”(《灵枢集注·邪气脏腑病形》)心主血脉,肺朝百脉,脉中运行血气等,俱乃经典之义。但经典中并未明言血脉即是血气,张志聪基于对经典理论的相关理解,通过在概念上将血气与(血)脉互换、互用,如“上节论经脉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阴肾”(《素问集注·刺疟》),实现了血气与相关脏腑的紧密关联(直接关联,无需体会言外之意)。由此亦体现出,血气在张志聪的注释立场或话语体系中地位非常重要,因为相比于(血)脉为有形,血气则为无形,且在张志聪的认识中,血气在某种程度上隐含(血)脉的意味,但又摆脱了其有形之羁绊,故其解释或运用的范围更为宽广,最终形成了张志聪特有的对于经典文本的本质或终极理解。
“志注”中血气的分布极为广泛,与血气连用的词语较多,诸如“荣(营)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十二经脉”“阴阳”“脉外皮肤”“脏腑”“形中”等。实际上,这种分布《内经》中即以“出入”的话语表述,“志注”以经典为依据,且进一步丰富其内涵。
2 血气之“出入”
“血气、神气、正气、脉、经别”与“出入”之连用在《内经》中俱见,但关于“出入”之路径并无详言。《内经》中关于(血)脉行的逆顺出入论述颇多,如《灵枢·经脉》《灵枢·逆顺肥瘦》等。“脉为血之府”,血气之出入与脉自然关联密切,但又不等同于经络之行,尤其是“志注”所论较为复杂。
2.1 血气“出入”的基本原则为“循环” 如:“夫阴阳气血,外内左右,交相贯通。”(《素问集注·阴阳应象大论》)“盖人之血气,外络于形身,内属于藏府,外内出入,交相贯通。”(《素问集注·脉要精微论》)“夫上下左右之脉交相应者,血气之循环也。”(《素问集注·三部九候论》)
早在《内经》中,循环已是经络、营卫运行的特点,如“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灵枢·经水》)“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灵枢·营卫生会》“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灵枢·动输》)“志注”中,血气之“出入”也承继了此点。循环是基本原则,但正如上文分析所言血气分布于身体各处,若要循环,先要实现相互之间的联系(体内与体外、脉内与脉外),即“贯通”。
2.2 血气“出入”应天道四时 如:“四时阴阳,自有经常。血气循行,各有调理。”(《素问集注·经脉别论》)“盖人秉天地之气所生,阴阳血气,参合天地之道,运行无息。”(《灵枢集注·九针十二原》)
关于此点,《素问·八正神明论》已有相关论述,如“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张志聪显然是承继了经典理论的表述。
2.3 血气“出入”的主要路径
2.3.1 脉内脉外的交通路径 如:“夫经脉之血,从经而脉,脉而络,络而孙。脉外之血,从皮肤而转注于孙脉,从孙络而入于经俞。此脉内脉外之血气,互相交通者也。”(《素问集注·调经论》)“然脉内之血气,从络脉而渗灌于脉外。脉外之气血,从络脉而流注于脉中,外内出入相通也。”(《灵枢集注·九针十二原》)“阴阳相随,外内相贯,谓脉内之血气,出于脉外,脉外之气血,贯于脉中,阴阳相随,外内出入。”(《灵枢集注·卫气》)。可见,孙络是脉内脉外血气相互交通的重要节点,脉内之血气可从孙络而渗灌于脉外皮肤,脉外之血气亦可从皮肤经由孙络而入于脉内。以上类似表述,可见于《素问·缪刺论》《素问·皮部论》《灵枢·百病始生》等篇论虚邪入客人体、逐步入侵的过程,如“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素问·缪刺论》)经文所论只限于外邪入客,其次序是由外入里。另外,关于经脉、络脉、孙脉的关系,《灵枢·逆顺肥瘦》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志注”在经文相关表述的基础上,将原本邪客之路径扩展到解释血气出入,且衍生为脉内脉外血气出入的两种路径。
2.3.2 五脏与体表的交通路径 如:“五藏之血气,从大络而出于孙脉,从孙脉而出于肤表。表阳之气,从孙络而入于大络,从大络而注于经俞。此外内交通血气之径路也。”(《素问集注·调经论》)可见,此处所论脏腑与体表的血气出入,在本质上与上述脉内脉外血气之交通,并无二致,均以孙络为重要媒介,只是此处更为强调脉内血气之来源即五脏。
2.3.3 肤表与经脉的贯通路径 如:“血气之生于阳明也,当知血气乃胃腑水谷之精,有行于皮肤之外者,有行于经脉之内者,外内贯通,环转不息。”(《灵枢集注·邪气脏腑病形》)。血气从胃阳明而生,其分布之途径有两个,即内外之分。其一、行于经脉之内,此点较易理解。其二,行于皮肤之外,其具体路径为,“渗出于胃外之孙脉络脉,溢于胃之大络,转注于脏腑之经隧,外出于孙络皮肤。”(《灵枢集注·百病始生》)但这仅仅说明了从胃阳明而出的血气分为两支,那么这两支血气之间如何实现“贯通”?如下所述:“肤表之气血,从五脏之大络,而出于皮肤分肉之外,复从手足之指井而流于荥,注于输,行于经,而与经脉中之血气,相合于肘膝之间。此人合天地阴阳,环转出入之大道也。”(《灵枢集注·玉版》)。据上可知,实际上无论哪种交通路径,其交接点都在于体表孙络。这也与《内经》中所规定的手足阴阳经脉都在肢体末端交接的规律一样,只是张志聪以血气为话语形式将之系统论述。
2.3.4 脉外血气出入之路径 脉中运行气血,乃《内经》之旨,系共识,并无多少可论之处。但《内经》之中,对于脉外之血气的论述并无太多论述,基本围绕“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对此,“志注”有批判,如“阴阳之道,通变无穷,千古而下,皆碍于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之句,而不会通于全经,以致圣经大义,蒙昧久矣。”(《灵枢集注·营卫生会》)张志聪有关血气的论述之中,对于脉外血气尤为重视。如:“是脉外之气血,一从经隧而出于孙络皮肤,一随三膲出气以温肌肉,变化而赤,是所出之道路有两歧也。其入于经也,一从指井而流于经荥,一从皮肤而入于络脉,是所入之道路有两歧也。”(《灵枢集注·经脉》)此句详论脉外血气所出入之路径各二。
2.4 血气“出入”的复杂性 正因为血气分布于体内外,无所不到,且彼此贯通,形成循环,故其“出入”之路径极为复杂,不易认识,“志注”中对此常有慨叹。如:“营卫血气,虽皆生于胃腑水谷之精,然外内出入之道路不一,学者非潜心玩索,不易得也。”(《灵枢集注·玉版》)“此篇论血气之生始出入,外内虚实,乃医学之大纲,学者宜细心体认。”(《素问集注·通评虚实论》)“经脉血气之生始出入,头绪纷纭,不易疏也。”“阴阳血气之离合出入,非熟读诸经,细心体会,不易悉也。”“曰阴阳相随,外内相贯,血气之生始出入,阴阳离合,头绪纷纭。学者当于全经内细心穷究,庶可以无惑矣。”“血气生始出入之道路多歧,若非潜心体会,反兴亡羊之叹。”
3 “血气”与针灸、经络理论的关联
尽管张志聪有关血气的论述涉及内容较为广泛,但因其与脉有天然之联系,故“志注”所论之血气,一则其本身内容多涉经络理论内容,二则多用于与针灸、经络理论相关内容的注释。如下详论。
3.1 “血气”与五输穴 “肤表之气血,从五脏之大络,而出于皮肤分肉之外,复从手足之指井而流于荥,注于输,行于经,而与经脉中之血气,相合于肘膝之间。”(《灵枢集注·玉版》)
“凡二十七脉之血气,出入于上下手足之间,所出为井,所流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此二十七气之所行,皆在于五腧。盖十二经脉之血气,本于五脏五行之所生。而脉外皮肤之气血,出于五脏之大络,流注于荥腧,而与脉内之血气,相合于肘膝之间。此论脏腑经脉之血气出入。”(《灵枢集注·九针十二原》)
“井者木上有水,乃淡渗皮肤之血。从井木而流于脉中,注于输,行于经,动而不居,行至于肘膝而与经脉中之血气相合者也。眉批:十二脏腑之脉,出于井者,非经脉之贯通,是以十二经脉,只论至肘膝而止。……肺出于少商者,谓脏腑之血气,从大络而注于孙络皮肤之间。肺脏所出之血气,从少商而合于手太阴之经也。……本篇论十二经脉之所出,从井而入于合,盖自外而内也。玉师曰:故只论五腧,而不及通体之经,大概过肘膝则为经脉之血气矣。”(《灵枢集注·本输》)
“夫曰所入为合者,谓脉外之气血,从井而流于脉中,至肘膝而与脉内之血气相合,故曰脉入为合。”(《灵枢集注·根结》)
“再按:十二经脉之始于手太阴肺,终于足厥阴肝,周而复始者,乃荣血之行于脉中也。十二经脉之皆出于井,流于荥,行于经,入于合者,乃皮肤之气血,流于脉中,而与经脉之血气,合于肘膝之间。”(《灵枢集注·经脉》)
张志聪认为,从井之合之血气,为脉外之血气、皮肤之血气,而非经脉之血气。至入于合,即肘膝处,则入于经脉之中,而为经脉之血气。究其原因,张志聪认为,井荥输经合五输穴系由脏腑而发出,如“肺出于少商者,谓脏腑之血气”,即系脏腑血气,然后“从大络而注于孙络皮肤之间”,直至肘膝才入于经脉之血气。由此体现的是,张志聪对于五输穴与脏腑、经脉关系的不同的认识。
3.2 “血气”与气街 “脉内之血气,从气街而出于脉外。脉外之气血,从井荥而流于脉中,出于气街。”(《灵枢集注·卫气》)
“此申明经脉之血气,从四街而出行于脉外。皮肤分肉之气血,从四末而入行于脉中。……此经脉中之血气,复从络脉之尽处,出于气街,而行于皮肤分肉之外也。”(《灵枢集注·动输》)
“气街者,气之径路。络绝则径通,乃经脉之血气,从此离绝,而出于脉外者也。”(《灵枢集注·卫气》)
据上可知,张志聪认为,气街是血气从络脉内而外出于皮肤分肉的中间地带。因此,“络绝”之时,血气可从气街而外出,从而实现血气的内外交通循环。
3.3 “血气”与络脉(孙络) 上文所论血气出入路径,尤其是体内外交通的路径中,已较多涉及络脉(孙络)。
“盖大络之血气,外出于皮肤,而与孙络相遇。是以脉外之卫,脉内之荣,相交通于孙络皮肤之间。”(《素问集注·气穴论》)
“是血气之从经脉而外溢于孙络,从孙络而充于皮肤,从皮肤而复内溢于肌中,从肌肉而著于骨髓,通于五藏。是脉气之散于脉外,而复内通于五藏也。”(《素问集注·四时刺逆从论》)
“胃腑所出之血气,别走于脉外者,注脏腑之大络,从大络而外渗于孙络皮肤。”(《灵枢集注·邪气脏腑病形》)
“盖形中之血气,出于胃腑水谷之精,渗出于胃外之孙脉络脉,溢于胃之大络,转注于脏腑之经隧,外出于孙络皮肤,[眉批:玉师曰:本经凡论针论症之中,当体认经脉血气之生始出入。]所以充肤热肉,渗皮毛濡筋骨者也。是以形中之邪,亦从外之孙络,传于内之孙络,留于肠胃之外而成积。故下文曰其着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拘积而止之。盖外内孙络之相通,是以外内之相应也。……孙络者,肠胃募原间之小络。盖胃腑所出之血气,渗出于胃外之小络,而转注于大络,从大络而出于孙络皮肤。”(《灵枢集注·百病始生》)
“通篇论经脉血气之生始出入。……按:此篇论血气出入于络脉之间,故篇名血络。”(《灵枢集注·血脉论》)
据《内经》可知,经脉行血气而营阴阳。络脉与血气之关连,所论甚少。上文已论脉外之血气是“志注”的重点,其主要路径则是以络脉为主,涉及络脉、脏腑之大络(即张志聪所认为的“经隧”)、孙络。张志聪还明确指出,孙络亦有内外之分,且内外孙络之间亦有沟通。“血气出入于络脉之间,故篇名血络”,亦为其证。
4 “血气之生始出入”形成的背景及其影响
“志注”中论及血气之时,多涉及“四时阴阳、日月星辰、参合天地之道、应天地运行之道”等,且举自然界之现象与血气类比。
如:“皮肤之气血,犹海之布云气于天下。经脉之血气,合经水之流贯于地中。”(《灵枢集注·卫气》)“其血气之流行升降出入,应天运之环转于上下四旁。……盖脉内之血气,应地气之上腾于天,脉外之气血,应天气之下流于地。”(《灵枢集注·论疾诊尺》)
因此,“志注”之中“血气之生始出入”诸多论述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天人相应”思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张志聪在经典注释中将这种观念认识上升为指导思想,化为其独特的注释或认知立场。而且,血气之出入与经络之行有着逻辑上必然的紧密关联,因而张志聪认为无论是天道、针道,还是血气之出入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即“盖针道与血气之流行,皆合天地之大道。”(《灵枢集注·邪客》)关于这一点,张志聪在《灵枢集注·序》中有明确表达。如:“故本经所论营卫血气之道路。经脉脏腑之贯通。天地岁时之所由法。音律风野之所由分。靡弗借其针而开导之。以明理之本始。而惠世之泽长矣。”“故本经曰人与天地相参,日月相应,而三才之道大备。”
另,张志聪有关血气的论述,在其《金匮要略注论》《伤寒论集注》《侣山堂类辨》等其他著作中亦有体现。据《金匮要略注论》《伤寒论集注》可知,张志聪明显持“六经气化”之论,这与“血气之生始出入”之论在思想背景上有某种共同基础。
5 借针明理:注释立场与话语特色
《内经》很多涉及针灸内容之处,张志聪多从血气之理论之,且反复论述,不厌其详,显示出与其他注家的显著差别。究其原因,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张志聪认为,“血气之生始出入”之理是“全经之总纲”(《灵枢集注·官能》)“医学之根本”(《素问集注·气穴论》),学者应当努力学习、体会,否则难以理解经旨。因为,在张志聪看来,经旨并非如其经文文字表面所表述的那样(多言针灸内容),其背后隐藏深意,应当“于针刺之外,细体认其义”(《灵枢集注·血脉论》)“学者当于《针经》,乃本经针刺诸篇,用心参究”(《素问集注·调经论》)。故张志聪对于马莳之注释有所批评,如“马氏又专言针而昧理”(《灵枢集注·序》)“马氏随文顺句,惟曰此病在某经,而有刺之之法,此病系某证,而有刺之之法,反将至理蒙昧,使天下后世藐忽圣经久矣”(《灵枢集注·热病》),明确提出“当于针中求理,勿以至理反因针而昧之”(《灵枢集注·周痹》)“以理会针,因针悟症”(《灵枢集注·序》)。
可见,针后隐藏之理才是张志聪所最看重的。因此,张志聪极力挖掘、阐释论针、论症经文之后的“血气生始出入”之理,并在注释中一以贯之。换言之,张志聪注释的理论立场之中,“血气之生始出入”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内经》的注释历史来看,通注《内经》的注家,一般不会仅仅随文而注,会更多地从文本甚或全书的角度去总体衡量、评价。换言之,注释时尽管是面对有时甚至是有不一致的文本,但注家心中或潜意识中还是会秉持某种较为稳定的基本理论认识的立场、观点、模式或框架,并且在经典注释中一以贯之。基于或围绕这个立场,在具体的注释中便会产生或较多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注文表述形式(某种论述理路、理念、相同的字词),因而就产生了一些颇具个人注家特色的注释话语(在比较诸家注文之时,可以很明显地体察到)。而且在中国传统诠释学中,这种情况颇为常见,比如朱子以“理”、陆九渊王阳明以“心”等解释儒家经典思想。
对于注释立场的关注是以往经典理论研究中较为忽视之处,基于注释立场,可以从更高的层面或新的视域去整体把握、理解相应的注释,解读具体注释背后所隐含的理论立场,而不止于于具体注释之语的评判与考量,从而加深对于注家学术思想的认识,有利于经典理论学术内涵的梳理与深层次的理解。
[1]清·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清·张志聪.黄帝内经灵枢集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2014-07-22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Position of Annotation in Classics and Discourse Features:Study on Zhang Zhicong's Annotations about the Outlet and Entry Path of Blood and Qi
Yang Feng1,Zhu Ling2
(1 Chinese Acupuncture Research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 theory and method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 acupuncture andmoxibustion key research laboratory,Beijing 100700,China;2 China in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Beijing 100700,China)
Unique 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ory of qiand blood of Zhang Zhico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y of th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His description about the outletand entry path ofblood and qienriches the theory ofmeridians,collaterals and five shu point,which reflects an characteristic position in Neijing annotations.The nature of qi and blood theory is rather special,which is not only the category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CM,but also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eridian theory,especially in the paths between in vivo and vitro,between in pulse inside and outside,between in body surface and meridians,between in zang-fu viscera and the body surface.Zhang Zhicong's annotations should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pression of qiand blood theory and the location i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ory system of frame structure.The discourse features in annota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may better grasp the position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notators,which is helpful to study and interpret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of the annotators,appear the inheritance,accept,understand acupuncture theory in annotations.It is noteworthy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n inheritance of acupuncture theory.
Acupuncture theory;Neijing;Meridian and collateral;Theory of qi and blood;Annotation
R221
A
10.3969/j.issn.1673-7202.2014.11.017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课题(编号:2013CB532006)
杨峰(1980—),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针灸理论、文献、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