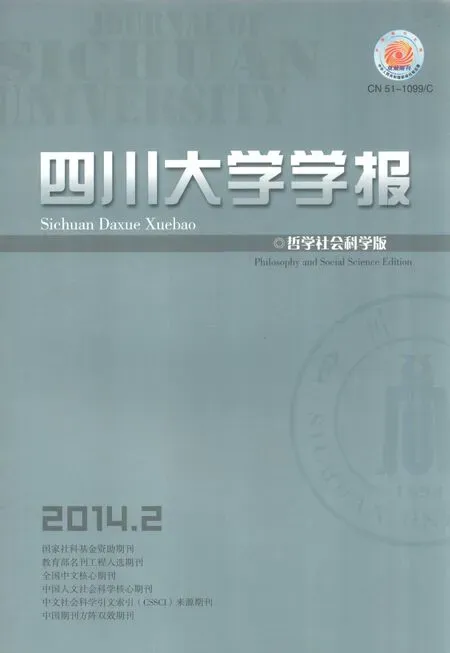语言即当下经验——论奥尔森的语言观
刘朝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院,广东深圳 518055)
在传统的语言观中,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中国古人所谓的“文以载道”,指的就是语言是“道”或意义的载体,相比“道”而言,语言位居其次,所以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说“得意忘言”,孔子说“吾欲无言”。在西方,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近代的笛卡尔,思想家们都持某种形式的语言工具论,即认为语言是反映世界或人的一面镜子。持语言是反映世界的工具之观点者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亚氏认为语言的形成过程是:事物引起人的经历,然后人根据此经历发声以表达该经历,最后用文字记录表达经历的声音。在此过程中,主体被动地接受客体的影响,而语言也只是客体的附属物或表达工具。持语言是反映人的主观意识的工具之观点者以笛卡尔为代表。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在此原则下,语言只是反映“我思”的工具。在现代西方,英美分析哲学语言观认为,世界由语言所决定,语言构建了世界也构建了我们的自我。①英美分析哲学是一种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该流派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务。德国阐释学派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实质。阐释学的代表之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②Martin Heidegger,“Letter on Humanism,”in Hazard Adams& Leroy Searle,eds.,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third edi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p.1053.另一代表伽达默尔则指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606页。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由此可见,随着西方哲学的演进,语言观实现了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而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独占鳌头,其领军人物德里达推出了以书写论为核心的解构主义语言观,以“延异”和“踪迹”等理念颠覆了传统的话语/书写的二元对立,认为语言充斥着差异和不在场意义的踪迹,“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是其基本特征。④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141.但是后现代主义诗人、美国当代投射派诗歌的领袖查尔斯·奥尔森 (Charles Olson,1910-1970)却似乎并不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而是强调语言是当下的行为或即刻经验。他在《人类宇宙》中写道:“谁能把语言从行动中抽离出来呢?”①Charles Olson,“Human Universe,”in Ralph Maud,ed.,A Charles Olson Reader,Manchester:Carcanet Press Limited,2005,p.113.凯瑟琳·R·斯廷普森 (Catharine R.Stimpson)在《查尔斯·奥尔森:初步映像》一文中指出,“奥尔森对语言的信任使他有别于众多后现代主义者”,对他而言,语言“既不是一张网络,也不是蒙住眼睛的眼罩,而是‘最值得自豪的’人类行为之一”。②Catharine R.Stimpson,“Charles Olson:Preliminary Images,”Boundary 2,Vol.2,No.1/2,Charles Olson:Essays,Reminiscences,Reviews,Autumn,1973-Winter,1974,p.154.奥尔森的语言观到底有何内涵?这些涵义是否契合他所在的理论语境?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奥尔森的语言观
奥尔森于1951年发表了《人类宇宙》一文。在此之前,他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考察玛雅文化中的象形文字诗歌,长达半年。奥尔森认为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了解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人类宇宙》就是基于这段经历。该文写就后,奥尔森对朋友说:“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文化定位,确定了我信仰的主体与实质。”文章开篇就说:“人类宇宙和另一个宇宙一样,都是可以发现、可以定义的。”至于如何去“发现”、去“定义”另外一个宇宙,奥尔森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检查”“语言目前的状况”,那么目前语言到底为何种状况呢?据奥尔森所言,自古希腊时期开始的“逻各斯或论说已将其抽象性植入我们的语言概念和语言使用中”,“以至于语言的另一功能,言说,似乎急需恢复自身的地位”。③本段引文参见 Olson,“Human Universe,”pp.112,113.语言的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我们仍处于“论说的宇宙”中,我们避开自己的直觉,要么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通过逻辑与分类去创造一个宇宙或世界,要么像柏拉图一样,从理念世界寻找现实的依托。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语言都成为了脱离实际经验或当下行为的存在。
奥尔森要恢复“言说”在语言中的地位,就是要使语言回归到经验中本来的位置。罗伯特·克里利 (Robert Creeley)在评介奥尔森时曾提到:“奥尔森执意要做的是:使语言像其他行为一样,恰当地回归到经验中本来的位置。”④Robert Creeley,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obert Creeley,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24.较早提出“语言”和“言说”区别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索氏认为语言是集体的、概括的、有限的、静态的系统或知识;言说是个人的、具体的、无限的、动态的现象。我们认为,言说的具体性、无限性和动态性使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不受先验模式的控制,而与经验直接相关,既远离了逻辑与分类,又能具体动态地再现经验。这也许正是奥尔森想恢复语言中言说地位的原因。为了恢复“言说”的地位,奥尔森一方面声讨希腊人发明的逻辑与分类以及理念世界,认为它们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严重妨碍了人们的行动。另一方面,他通过恢复语言中的“呼吸”,使语言成为即刻经验的再现。
奥尔森之所以强调呼吸的重要性,是因为“呼吸是人类作为动物所具备的特殊资格”,“声音是人类从呼吸延伸而来的”。当然动物也发出声音,只不过这些声音没有形成系统的语言。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语言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最明显的标志,所以奥尔森说“语言是人类最值得自豪的行为之一”。语言中若有了“呼吸”,就会有动感和生命,即使是跨越时空,语言仍会活脱地再现说话者的气息,仿佛他仍然在场。在《投射诗》一文中,奥尔森开篇就写道:“而今1950年的诗歌,如果要向前进,具有实质性价值,我认为必须牢牢把握某些呼吸的规则和可能性,即把创作时的呼吸及听到的声音放进诗歌里。”他认为“呼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使语言所有的言说力量返回其中(言说是诗歌的‘实体’,是诗歌能量的秘诀)”。他在此文中还提到,“呼吸有双重含义”。尽管他并未明确指出其两重含义是什么,但他说道:“自从打字机出现之后,有一个好处尚未完全被发现或利用。……正是打字机的优势,其刻板性及间隔的精准性,使得诗人能够确切地表示他想要的呼吸,停顿,甚至音节的悬留,或短语各部分的并置。诗人第一次像音乐家一样,有了五线谱和小节线,第一次能够记录他所听到的自己的言说,而不必用传统的韵律,并由此来表示他希望读者如何有声或无声地去读他的诗歌。”①本段引文参见 Olson,“Projective Verse,”in Maud,ed.,A Charles Olson Reader,pp.48,39,44,45-46.奥尔森在这里不仅提到了呼吸的双重含义:“气息”和“停顿”,而且指出应该借助“打字机的优势”来表示“呼吸”。这样一来,读者无论“有声”还是“无声”地读诗,都能体会诗人创作时个人的、具体的、动态的言说,体会到诗人当时的即刻经验。这样,呼吸就恢复了“言说”的力量。
奥尔森恢复语言中“言说”的力量之用意,是恢复“最无意”、“最不逻辑”的自然自发的语言,从而使语言不偏不倚地回归经验。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自然自发的语言的再现却要凭借近乎教条的技巧,奥尔森在《投射诗》中作了详细说明:“如果一个当代诗人留下的间隔的长度与前面的词组一样长,他的意思是空白处的呼吸与词组等时。如果他在行末悬留一个单词或音节 (这主要是卡明斯的做法),它的意思是停顿的时间——那一丁点的悬留时间——就是眼睛移到下一行要花的时间。如果他想要的停顿短得刚好把单词分开,而他又不想用逗号——逗号是意义的中断而不是诗行的发音,他就用打字机已有的一个符号,请理解他。”这里列举了两个技巧:一是用间隔 (行内或跨行)的长度来表示停顿的长度,二是用斜线“/”分隔符而不用逗号表示行内很短的停顿。接下来他还指明了另一技巧:利用打字机的空格符呈现参差的左边页边,这样排列出来的诗行不是传统的齐头式,而是层层推进的楼梯式,用以表示“意义和呼吸的推进”。②本段引文参见 Olson,“Projective Verse,”pp.42,46.
除了通过再现“呼吸”来恢复言说的地位外,奥尔森还借助单边括弧 “(”来表示言说中或说话时思绪自然地向前流动。约翰·奥斯伯恩 (John Osborne)论及奥尔森的这一技巧时提到:开放的单边括弧 “(”在口语和思考中很常见,但在书面语中却很少见,因为在口语中,暂时离题的闲话结果往往没有再回到原来的主题,而是喧宾夺主地取而代之。③John Osborne,“Black Mountain and Projective Verse,”in Neil Roberts,ed.,A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Poet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1,p.171.
总之,奥尔森认为,“呼吸”是语言最重要的言说力量,有了呼吸的语言是当下的行为,是人类行动中的直接体验,是没有被逻各斯抽象思维污染的人类经验。奥尔森强调语言是当下经验,是修复思维和行动 (或经验)之间以及符号与意义之间的破裂的一种尝试。他在《人类宇宙》中提到:作为即刻行为的语言和作为关于即刻行为的思考的语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等同于即刻经验,而后者是关于即刻经验的思考,后于即刻经验生成。前者中只有直接体验,而后者已经过思维的整合。直接体验不来自想,而来自人的本体感觉,即其在《本体感觉》中所说的“身体内部通过自身组织的运动而产生的感觉”或“终端器官位于肌肉、肌腱、关节的感觉”,④Olson,“Proprioception,”in Donald Allen & Warren Tallman,eds.,The Poetics of the New American Poetry,New York:Grove Press,Inc.,1973,p.182.或者用拉尔夫·莫德 (Ralph Maud)的话来说,它“既来自心脏,又来自横隔膜”;作为即刻行为的语言是自然自发的,奥尔森认为这样的语言“像树木一样纯净,因为它源自自然之手”,⑤Olson,“Projective Verse,”pp.39,47.他通过强调语言是当下经验,使得诗歌语言摆脱传统格律的限制,从而诗歌的节奏就是自然的呼吸节奏。因为诗歌语言是诗人当下的经验,所以诗歌的内容不必再是旧式的阳春白雪,只要是诗人体验到的事物,哪怕是下里巴人的事物,都可以入诗。
二、奥尔森语言观的理论语境
奥尔森以学者型诗人著称,他的阅读面非常广,对语言学、哲学、历史、地理和考古学等都有涉猎。在诗学传统上,奥尔森承认继承了庞德-威廉斯传统,且认为自己的诗学发展并超越了这一传统。然而有的评论家并不认同此观点。例如:马乔里·G·帕洛夫 (Marjorie G.Perloff)就认为,奥尔森的诗学相对于庞德和威廉斯的诗学来说,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帕洛夫在《奥尔森与“低下的”前辈:重读〈投射诗〉》一文中,详细对比了奥尔森和庞德以及奥尔森和威廉斯关于诗学的言论,指出他只不过是把这两位前辈的说法变换了措辞而已。①Marjorie G.Perloff,“Charles Olson and the‘Inferior’Predecessors:‘Projective Verse’Revisited,”ELH,Vol.40,No.2,Summer 1973,pp.285-306.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奥尔森的诗学不仅来自这些前辈,还低于他们。当然这些只是一面之辞。奥尔森在世时就对这些观点进行过强有力的驳斥,他的立场得到了许多批评家拥趸的支持。其中之一是罗伯特·温·霍尔伯格 (Robert von Hallberg)。他在1974年发表的《奥尔森与庞德和威廉斯的关系》写道:“很少有人关注奥尔森、庞德和威廉斯之间的区别,所以某位庞德支持者轻率地认为奥尔森的诗学几乎完全来自而且绝对低于庞德。任何一个对美国诗歌过去六七十年的历程以及未来的方向感兴趣的人,都有可能对这种鼠目寸光地将他们混为一谈的做法感到失望。实际上,奥尔森与庞德和威廉斯的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理清这些关系有助于理解三个诗人,尤其是他们的长诗。”②Robert von Hallberg,“Olson's Relation to Pound and Williams,”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5,No.1,Winter 1974,p.15.从霍尔伯格的这席话中可以看出,奥尔森与庞德、威廉斯之间存在区别,并且奥尔森同样对“美国诗歌过去六七十年的历程以及未来的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奥尔森与此两位前辈的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奥尔森受到了二人的影响。在语言观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都要求语言直接呈现经验,都反对求助于陈旧的故纸堆的语言,都致力于清除自苏格拉底以来附加在语言之上的种种形而上的意义,都主张诗歌语言的节奏不应受传统韵律的限制。因为奥尔森是后辈,而且他推崇庞德和威廉斯的诗学,所以这些相似的方面可以归结为奥尔森对庞德和威廉斯语言观的传承,也可以说是奥尔森语言观的诗学语境。
奥尔森语言是当下经验的观点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观有相同之处。尽管有学者已经考证,“在西方文学史上有一个现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维特根斯坦的作品——尤其是哲学著作——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视觉艺术家和诗人产生过广泛而普遍的影响,并给他们带来了创作上的灵感”,③林玉鹏:《日常语言与当代西方诗学:〈维特根斯坦的梯子: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奇特〉》,聂珍钊等编:《玛乔瑞·帕洛夫的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诗歌与诗学解读》,《世界文学研究论坛》2011年9月专号,第127页。但奥尔森直接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奥尔森发表《人类宇宙》时,维氏的《哲学研究》尚未出版,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奥尔森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对于语言的看法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认为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实质区别,都强调语言使用的即兴性,都拒绝以语言的世界取代现象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奥尔森在《马克西姆斯诗篇》中也写了一句异曲同工的话:“没有等级,没有终极……只有/大家头颅上的眼睛,/从那往外看。”⑤Charles Olson,The Maximus Poems,New York:Jargon/Corinth Books,1960,p.29.“想”即思考,思考意味着逻辑和分类,意味着去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去寻求一种解释,从而产生“等级”和“终极”。在想的过程中,事物的命运只有两种:一种是找到了解释,一种是找不到解释。在前者中,事物最后等同于其解释,而在后者中,事物往往被当作无意义的东西而摒弃。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事物本身都被搁置了。而“看”则意味着回到事物本身,直面事物本来的样子,不受逻辑的限制,体验事物的千变万化。奥尔森和维特根斯坦的“看”并不是强调视觉,而是强调实际体验。这种看不是柏拉图式的在情境之外或之上看,亦即西方传统的形而上的看,而是身临其境、情随境迁地看,就像克里利所说的司机开车时看前面的道路那样看,视野时时刻刻在变化,司机不关心以前和以后看到的一切,只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同时采取相应的行动。总之,奥尔森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试图使语言从形而上回归到实际经验。对他们来说都只有语言的使用,没有超出直接经验的元语言。
奥尔森的语言观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也非常相似。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即人的存在,是人在世界之内经验和体验世界之内的东西。海德格尔为了展示存在本来的样子,审视了始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经过考证他发现,逻各斯最初的意义是“言谈”,在古希腊文化向拉丁文化的转换过程中,人们把古希腊的“人是被赋予逻各斯的动物”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①Heidegger,“Letter on Humanism,”pp.1053,1056.这一翻译导致了理性的无限扩张,逻各斯越来越远离其最初“言谈”的本义,而成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等的代名词。奥尔森在《人类宇宙》中指出,人类宇宙和另一个宇宙一样,是“可以发现”、“可以定义”的,而要发现或定义人类宇宙,关键在于语言;在他看来,自古希腊开始,语言已经被逻各斯或抽象概念所侵蚀,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经验,所以他说:“我们在界定和表达经验时没有找到遵循和坚持经验本来面目的方法。换言之,我们没有找到停留在人类宇宙的方法,或避免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被引入到分裂的现实的方法。”②Olson,“Human Universe,”pp.112,114.为了发现或定义人类宇宙,奥尔森强调要恢复语言中言说的地位,使语言成为即刻的经验。可见,奥尔森和海德格尔都坚持让事物如其所是,都试图恢复逻各斯言说或言谈的原初意义。关于奥尔森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相似之处,威廉·V·斯潘诺斯 (William V.Spanos)已有论证。他在《查尔斯·奥尔森与消极能力:一种现象学的诠释》一文中指出,奥尔森对济慈的“消极能力”的解释有着“鲜明的当代性”,与后现代现象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去中心的认识论关注”非常相似,他认为,对海德格尔和奥尔森来说,“‘后现代’思维的根本任务是揭示被遮蔽了的逻各斯的原始意义”。③William V.Spanos,“Charles Olson and Negative Capability:A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21,No.1,Winter 1980,pp.39,46.
奥尔森的语言观虽然与维特根斯坦以及海德格尔有相似之处,他们之间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奥尔森是美国诗人兼历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则是德国哲学家。奥尔森从不讳言自己的影响源,但在他的文字中却找不到这两个哲学家的名字。然而,他们的相似却并非偶然,同处西方当代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他们遭遇了相同的形而上学的传统,他们对传统语言观中过度膨胀的理性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发起了相似的挑战。奥尔森和这两位哲学家之间虽没有相互影响,却有相似的语言观。奥尔森和另外一位哲学家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之间的关系却是另外一回事。据罗伯特·温·霍尔伯格考证,奥尔森于1955年春天第一次阅读了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这本书是他的藏书中评注最多的书本之一,从书中的旁注可以看出,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他仍然在读这本书”。④Robert von Hallberg,“Olson,Whitehead and the Objectivists,”Boundary 2,Vol.2,No.1/2,Charles Olson:Essays,Reminiscences,Reviews,Autumn,1973-Winter,1974,p.86.奥尔森1956年在黑山学院作了关于怀特海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后来被编辑出版为《特别的历史观》(The Special View of History)。这些都足以证明奥尔森受到了怀特海的影响。那么奥尔森的语言观到底受到了怀特海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怀特海的理论体系中,每个实体 (actual entity)或实际情形 (actual occasion)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实体都相互关联,关联的方式是“感悟”(prehension):一个实体要么积极地要么消极地感悟另一实体。如果是积极的感悟,它就传播了自己,从而延伸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是消极的感悟,它就会决定不在另一个实体的能量中构建自身。尽管实体之间相互关联,每一个实体却总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它自己决定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地感受其他实体。这一自我生成的过程不可复制,因为时间和空间不可复制。怀特海对实体的描述或定义被奥尔森挪用到了对语言的描述中。他认为语言也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其感知的对象共同存在于不可复制的时空或场域中,语言是这个不可复制的时空中每个点上的经验。正因如此,他认为投射诗人在作诗的过程中“应该设法记录下耳朵所闻和呼吸的压力”。⑤Olson,“Projective Verse,”p.41.这样的语言是由即刻经验汇聚而成的过程。
奥尔森的语言观还回响着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艺术即经验”之观点。该观点是杜威的论著《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的中心论点,也是他实用主义哲学的生动体现。他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式的抽象分析或推理,大力提倡对纷繁复杂却又真实可触的实在现象的关注。奥尔森在其作品中没有提到过杜威,乔治·F·巴特里克 (George F.Butterick)和拉尔夫·莫德两位学者考察了奥尔森阅读过的文献,对他的影响源做了详细的探寻,但他们没有发现奥尔森的影响源中有杜威。后来研究奥尔森的学者大多以他本人的言论以及巴特里克和莫德的文献为依据,不去追究奥尔森到底有没有受到杜威的影响。然而,凡事皆有例外。和奥尔森同时代、且同为投射派诗人的罗伯特·邓肯 (Robert Duncan)在论及奥尔森《马克西姆斯诗篇》的诗学时,却提到了杜威对奥尔森的影响:“约翰·杜威在《艺术即经验》指出了‘艺术成品 (雕像,绘画,凡此种种)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他还写道:‘秩序、节奏和平衡只是意味着对经验重要的能量在发挥最佳作用。’我要提爱默生和杜威,以说明美国哲学中已有《马克西姆斯诗篇》的预示或预兆。”①Robert Duncan,Fictive Certainties,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5,p.68.邓肯言下之意是,奥尔森的《马克思姆斯诗篇》受到了爱默生和杜威的本土哲学的影响。无独有偶,另一位名叫斯蒂芬·弗莱德曼 (Stephen Fredman)的学者也对奥尔森美学中的杜威背景进行了探究。事实上,奥尔森担任校长的黑山学院就是以杜威的教育思想为指导而创建的。对青年时代的奥尔森来说,接受杜威思想可谓是顺理成章之事。正如弗莱德曼所言,“对于一个在政治、教育和美学方面有大众化和实用主义品味的年轻人来说,受到杜威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②Stephen Fredman,“Art as Experience:A Deweyan Background to Charles Olson's Esthetics,”Journal of Philosophy:A Cross Disciplinary Inquiry,Sept.22,2010.杜威认为,“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存在于个人化的经验中,才不仅潜在地,而且是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件艺术品”。③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Penguin Group(USA)Inc.,1934,p.108.也就是说,“个人化的经验”才是艺术品生成的关键。与此相似,奥尔森也认为,个人化的经验是诗歌创作的关键。诗人在创作时,“每时每刻,必须行动,并意识到某些正在涌现的要仔细视察的能量”。④Olson,“Projective Verse,”p.40.在这样的创作中,诗人只留心当下经验,而不去反思或推理。诗人的语言就是当下或即刻的经验。
从上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奥尔森的语言观与其所在的理论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为何斯廷普森却说“奥尔森对语言的信任使他有别于众多后现代主义者”呢?对比一下后现代主义典型代表德里达的语言观就可以回答该问题。同为后现代主义者,奥尔森和德里达都否认形而上的主体的存在,都试图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都青睐流变性、差异和运动。但是德里达对语言的态度是质疑而非信任。在《论书写学》中,德里达通过解构口语/书写这一传统的二元对立,对语言符号、词语以及书写的传统价值定位进行了全面的质疑;他认为,西方人自柏拉图到索绪尔,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者,他们信守语言是以声音或话语为代表的,在他们看来,话语比文字离思想更近,话语能够最为直接、清楚、透明、真实地表现思想,而实际上,“书写发生在言语之前、之内”,⑤Derrida,Of Grammatology,p.313.即书写的无声音、无意识、无中心、无序等是口语的前提或增补成分,口语或声音在发出之时就受到了书写的增补(supplement)作用的影响,语音中心主义者所想象的口语的意义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一开始便被书写所瓦解,充斥着差异和非此在意义的踪迹。总之,在德里达看来,不管是口语还是文字,语言符号既不是实体,也不具有此在性,语言是包含差异的嬉戏,其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确定的。
与德里达相反,奥尔森对语言更多的是信任,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奥尔森竭力恢复语言中言语的力量,使语言回归直接经验。回归到直接经验的语言必定是值得信任的,因为不必去追问其意义确定与否,其价值就在于它是“‘最值得自豪的’人类行为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奥尔森致力于恢复语言中言说的地位,就认为他是一个语音中心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奥尔森恢复言说地位与德里达推翻口语/书写中口语的权威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处。德里达认为,口语产生之前和产生的过程中,已经受到了无声音、无意识、无中心和无序等广义的书写的影响。奥尔森则强调,言说来自人的直接经验,是未经逻辑或分类等手段整合过的语言。德里达和奥尔森通过不同的方式做了同一件事: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奥尔森把语言等同于直接经验,又把直接经验植根于人的本体感觉。由此看来,他对语言的信任说到底是对人的信任,或者更具体点说,是对人的肌体的信任。奥尔森说过,生命的信息与活力都来自他自身的身体,“身体就是他的答案”。①Olson,“Resistance,”in Maud,ed.,A Charles Olson Reader,p.4.其次,对于奥尔森来说,语言中的词语具有实体性。他在《马克西姆斯诗篇》中写道:“物体之外不可能存在名称/行动之外不可能存在动词。”②Olson,The Maximus Poems,p.6.名称与物体对应,动词与行动对应,每一个词都源于经验,而且还能启动新的经验。在《舞者的符号表》(A Syllabary for a Dancer)一文中,奥尔森甚至把文字符号和舞者的动作类比:“符号,不管是在语言中,还是在舞蹈中,都是那股表述的力量,总在自身之内保持着……重要性足以赢得名称的物体的神话。符号的运动 (动词的动作,或舞蹈中肢体的活动)本身包含着人类可能有的——或人类看到其他事物可能有的——所有意愿。”③转引自 Stimpson,“Charles Olson,”pp.154-155.奥尔森通过类比文字与舞蹈动作,指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它们都是“表述的力量”,表述的是人类自身或人类从其他事物中看到的所有可能的意愿。
至此,我们已经回答了文章开头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奥尔森认为语言是当下经验,为了使语言回归经验,他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将语言沦为逻辑、分类等形而上思维的工具的做法,强调“呼吸”对语言的重要性,提倡借用打字机的优势来恢复书面语中的“呼吸”。奥尔森的语言观在诗学传统上和庞德、威廉斯的观点一脉相承,同时也和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怀特海以及杜威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奥尔森的观点和他所在的理论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奥尔森的语言观与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德里达的观点不尽相同。他对语言的信任明显不同于德里达对语言的质疑。也许正因为德里达的观点在后现代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所以斯廷普森说“奥尔森对语言的信任使他有别于众多后现代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奥尔森反对概念化抽象化的语言,认为语言应该像玛雅象形文字那样就是经验本身,但在诗歌实践中,他的语言却给读者晦涩难懂的印象。他和他的投射诗友克里利认为,写作就是一次次发现之旅。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活跃的思维注定了他的发现有着与众不同的广度和深度,如此看来,他那深奥晦涩的语言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