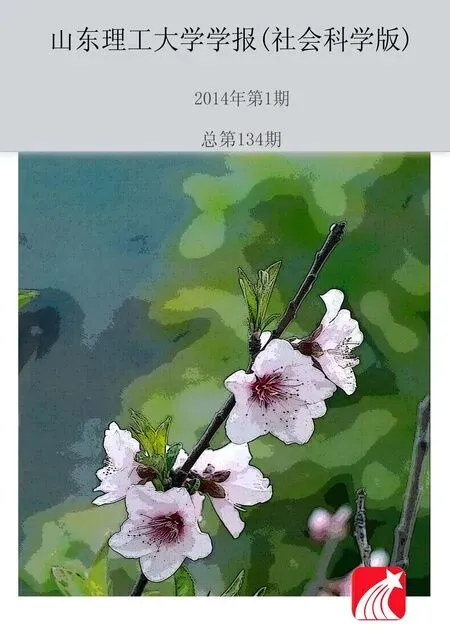李清照与狄金森爱情诗比较研究
胡竞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600)
李清照(1084~1151),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其词在清新之风中流露真情实感,在委婉含蓄中抒情达意。其众多诗词千古流传。艾米丽·狄金森(1830~1886),美国19世纪传奇女诗人。一生创作诗篇1789首,生前默默无闻,仅发表10首诗作,现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富于睿智,擅长用新奇的比喻及各个领域的词汇。爱情、死亡、永生都是其诗歌的重要主题。
二人生平截然不同,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迥然相异,但二人生活中都遭遇坎坷挫折、他人的不解与孤独。李清照出身于南宋末年条件优越的官宦之家,幼时家庭学术氛围浓郁,培养了其独特的文学气质。狄金森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一个名门望族,从小受到正统的宗教教育。与李清照幼年活泼美好宽松的生活氛围不同,狄金森的青少年时代平静而单调,很少外出,旅行过一次。截然不同的早期生活经历促成了两人的早期诗歌风格。李清照前期诗风清新自然,透露出活泼开心的少女情怀。而狄金森早期作品风格传统,感情自然。
李清照嫁给赵明诚后曾有过一年多平静美好的爱情生活,之后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改嫁被骗等多种生活波折,使其词风发生了相应变化,有对夫君思念及国破家亡的悲哀及自身气节的体现。与李清照的幸福婚姻生活不同,狄金森一生未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闭门谢客。然而,过着隐居生活的狄金森作品颇丰,诗歌充满活力与激情。
尽管两人生活经历不同,历史背景不同,但诗歌这个艺术形式把两人联系在一起。同是女子表达爱意,两人的风格各不相同,意象选取也不同,但表达的意境有相通之处。本文试图从风格和意象及女性意识的角度对两人作品对比讨论。
一、含蓄直白显文风
所谓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它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特征。李清照的文风委婉含蓄,表达爱意多用其他事物指代,反应相思之愁情浓意更浓。而狄金森的诗歌大胆直白,直抒胸臆,感情浓烈火热。
例如李清照的《点绛唇·寂寞深闺》: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1]70
在这首借伤春写离别怨恨的词中,作者表达相思之苦离别之愁,没有直接说“我想你”,而是借“春去”、“催花雨”、“草”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伤春、伤别,千缕愁苦浓在一起。“望断归来路”,体现出作者对丈夫的思念。
狄金森则在表达对爱的期待和相思之情时,直白炽热。例如《如果你能在秋季来到》最后两节写到:“如果确知,聚会在生命——/你的和我的生命,结束时——/我愿意把生命抛弃——/如同抛弃一片果皮——/但是现在难以确知/相隔还有多长时日——/这状况刺痛我有如妖蜂/秘而不宣,是那毒刺。”[2]177诗人大胆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思念之情:我想你如针蛰之痛!直接并带着火热的情感,浓烈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狄金森的比喻形象生动,让人感同身受。
又如李清照的《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下阙写到:“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红”。[1]14作者思念自己的丈夫,用“梦断”、“醒时”来对比,含蓄地刻画了思念的心理,从侧面烘托愁苦情思。全文不写相思一字,却把浓浓的相思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再看狄金森,她在表达爱意时毫无掩饰。她的《我一直在爱》写到:“我将永远爱下去/也可以向你论证/爱就是生命/生命有不朽的特征。”[2]189作者用生命来比较爱情,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爱上自己的心上人,这种爱是不朽的,是超脱生与死的。作为未婚女子,这么大胆直白表达爱意,大胆出位,使读者深深感受到狄金森浓浓的爱意。
两位诗人同样是表达相思和爱意,却带来了不同的韵味。含蓄与直白对比明显。耐人寻味的是,两位诗人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正是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反。李清照曾有过幸福的婚姻,当丈夫不在身边时,是有资格大胆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相思之情的。但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只能含蓄而露之。而狄金森终身未嫁,自己喜欢的人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跟自己在一起,按世俗的观点,不应该也没有机会大胆直白地透露自己的爱意,但狄金森突破了世俗的观点,反应出自己的女性意识和对爱情追逐的权利。由此可见,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诗人表达爱意的方式虽不同,但两位诗人对爱人的相思之情、爱慕之情是一致的,形式不同,时代不同,但感情相同,因而可引起读者共鸣。
二、意象表征存差异
意象:“意”就是意念,“象”就是物象。有一个想法后,把所要表达的情感用物象呈现出来。意象并不神秘,作者头脑中一瞬间的想法,借助某事物表现出来,读者通过阅读能体会作者的含义并感知其中的美感。罗良功教授关于意象的一段描述为:“意象是诗歌意义的灵魂。所谓意象是指灌注了一定思想感情的形象,即用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来表现人们在理智、情感方面的经验。它具体可感,但又不是表象;它能够显示本质,但又不是概念;它是感情与理性、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形象。诗歌中的以形象化的语言来暗示,又引领读者从感觉世界走向情感与理性交织的世界。”[3]73
对于李清照和狄金森来说,诗歌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在选取意象上,与其说选取,不如说信手拈来,诗歌是他们最自然的感情流露,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成为他们表达情感的手段。由于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二人在选取意象及表达方式上风格各异。
(一)李清照的词中常见意象分析
纵观李清照的诗词,花这个意象出现频率极高。多以花自比,表现自己高雅、率直、傲岸品格以及对崇高气节的敬佩。当花的这个意象与特定的时间、季节、气候、心境等联系在一起时,李清照的心理活动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例如,描述少女情怀的《点绛唇》:“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1]83一句花瘦,赋予花以生机,形象生动,体现作者轻松愉悦的心情。却把青梅嗅,以此动作做掩护,把一个怀春少女想见客人时的娇羞神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又如《如梦令》中:“误入藕花深处”,区区几字勾勒出在碧绿的荷叶中,小姑娘划船的情景,活灵活现。这蓬勃的荷花映衬了少女时代李清照轻松愉悦的心情。婚后的李清照,独守空闺,花的意象复杂起来,从单纯的自然景物,变成李清照形象的写照。这时她多用“残花”,如“泪融残花”、“梅萼插残枝”、“红藕相残”、“梅花鬓上残”。[4]晚年,李清照遭到诸多不幸,丈夫去世,国家战乱,生活流离失所。这时她用“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又谁堪摘”反映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黄花,可以代表曾经的幸福生活,如今已飘落满地无人采摘,这花的形象变得沉甸甸的。最知名的《醉花阴》中“人比黄花瘦”,李清照以黄花自比,黄昏时分,自己一人借酒消愁,愁更愁。透过此处黄花的意象,我们看到了温柔贤惠的妻子,看到了思念丈夫的怨妇,看到了心底充满惆怅的老妇人的内心。这婉转的语言饱含深情,文字朴素,感情却浓烈。在封建时代,李清照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她的这种才气和勇气令人惊叹。
李清照的人生经历,由花这个意象明显地反应出来。从乐观开朗的美少女,到独守空房的怨妇,再到国破家亡的寡孀,花的意象处处可寻、耐人寻味。由此可见,在反映李清照漫漫人生路途的各个阶段中,花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意象。
(二)狄金森诗歌意象分析
与李清照诗歌意象不同,狄金森的诗歌意象灵活多样,她不断变换意象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其爱情诗中,她以自然的意象作为媒介表达自己的爱情诉求。例如大海、小河、船等。她的《但愿我是,你的夏季》写到:“请采撷我吧——秋牡丹——/你的花——/永远是你的!”[2]67以夏季、秋牡丹这些简单的意象为媒介,把自己比作一朵秋牡丹,永远为她的爱人开放,[5]浅显易懂,很容易让读者与她产生共鸣。在《我的河在向你奔来》中,诗人用了“河流”、“大海”这两个意象,分别暗语自己和爱人。表面上看是写大自然的大海宽广包容,实际是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诗人心中爱人像大海,而她是河流,最终目的是奔向大海与爱人相拥,融为一体。诗人渴望爱情,希望得到心上人的接纳。《暴风雨夜,暴风雨夜》中诗人用了“大海”和“船”这两个意象,又一次把爱人比作大海,自己为船。在爱人的怀中有了方向,不需要罗盘和海图,最终希望自己停泊在爱人的水域。这些反映诗人炽热情感的自然意象在狄金森的爱情诗中比比皆是。
此外,狄金对森意象的选取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性,让人意想不到却感觉恰当表达了主题。例如她的《“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希望’是个有羽毛的东西——/它栖息在灵魂里——/唱没有歌词的歌曲——/永远,不会停息——。”[2]15狄金森用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小鸟”这个意象,把“希望”这个抽象形象反映出来,充满想象力。“栖息在灵魂里”形象生动,有独特创意,又让读者深刻领会到作者用意。“永远不会停息”一句使读者深刻感受到狄金森对希望抱有的执着态度,对爱情“永不言弃”的炽热情感。
通过李清照和狄金森诗歌意象比较,可以看出,李清照诗歌意象选取相对狭窄,多取日常生活之物,并用白描手法,以独特的文字表达构建奇绝不凡的千古名句。在封建社会,女子地位受限,活动范围也多局限于家庭之中。李清照虽然相对于其他普通女子经历丰富,例如青少年时经常出游,之后逃亡,改嫁等,但一生中接触更多的仍是日常生活之物品。信手拈来的生活之物,自然之物,尤其是花儿最能反应出诗人的心境。而奇特的构句和搭配更突显诗人独特的才华。狄金森一生多寡居,活着时默默无闻,生活中甚至有些自闭,因此,狄金森诗歌意象选取充满着想象力,其选取材料极其丰富,在其巧妙营造下,看似不着边际的事物构成狄金森诗歌中独特的意象。例如前文的妖蜂、河流、小鸟等。狄金森采用意象传递自己的情感,她的意象多发人深思。
由此可见,意象的选取同样与时代背景相关,与个人经历喜好相关。虽然两位诗人选取的意象不同,但都同样传递作者的情感,都留下千古绝句。
三、女性意识有共鸣
在李清照和狄金森的爱情诗中,多首诗句反应了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这体现了两位诗人的自我意识。在两人各自的生活背景下,当时社会均是以男性为主导,爱情诗歌多是男权支配下的爱情诗歌,通常忽视女性对爱情的表达。即使有女性对爱情的表达,也是从男性意识的角度来描写。两位女诗人均突破了这种束缚,超越了时代,反映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例如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在表达相思愁苦的同时,反应出女性不再是一个没有思想情欲的附属配角,而是可以把“愁苦”和“对未来的向往”传递给丈夫的富有情感的独立角色,这在当时封建社会下,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表露。[6]狄金森的诗歌中自我意识体现得更明显。例如狄金森的诗歌《爱,先于生命》中写到:“爱,先于生命,后于死亡,是创造的起点,是世界的原型。”诗人表达了爱情高于生命、爱情永恒这一思想,这是对男权社会中男人认为爱情是男性规则下的游戏的挑战,也摆脱了爱是婚姻附属品的理念。[6]充分反映了女性对爱的独立的认识和女性在爱情中的自我意识。
除了彰显自我意识之外,李清照和狄金森的诗歌中还体现了女性的叛逆意识。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年代,女性对情爱的正常渴求被压抑被剥夺,然而两位女诗人均以其反叛的个性,大胆挑战这一传统。例如李清照的《丑奴儿》“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7]这首诗在当时可谓是一语石破天惊。诗歌大胆反映了女性对性爱的追求:“穿上粉红色的透明睡衣,雪白肌肤隐约可见,一阵阵幽香散发出来,含情脉脉对夫君说:今晚竹席应该很凉快!”夫妻之间谈情说爱本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封建年代,这首诗被人骂称“不知廉耻、荒淫放肆”,在封建社会众多有文采的大家闺秀中,像李清照这样大胆地表达自己对爱的追求是独一无二的。这首诗大胆放肆的背后,恰恰反映了李清照大胆叛逆、挑战传统的气魄。再看狄金森的《暴风雨夜,暴风雨夜》:“啊,海!但愿我能,今夜,泊在你的水域!”[2]73诗人暗示想和自己心上人在一起的想法,直白表达了自己对情爱的向往。在此,诗人强烈地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大胆反抗,表明女性也是有情感需要的独立个体。此句直抒胸臆,大胆直白,打开了女性自我禁锢的枷锁,表达了挑战男权社会的叛逆意识。
两人诗歌的女性意识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体现自我意识、叛逆意识的爱情作品是两人对当时社会男权意识的抨击,也是诗歌领域情感的升华。之所以两人诗歌中女性意识如此强烈,均与二人早期生活相关。正如前文所述,李清照生活在有良好文学修养的家庭,早年宽松富裕的生活极少压抑她的自由,这对她后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空间。狄金森也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并曾进入女子学校学习,这些都奠定了她良好的文学修养。同时狄金森生活的年代,受到了爱默生倡导的“自立、自主的个人”思想的影响。虽然没有渗透到女性世界,但狄金森却以自己的独立和反叛,独居未嫁的生活方式向当时社会抗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彰显女性自我意识的优秀作品。
四、结语
通过对比李清照和狄金森两个人的爱情诗作,可以发现,尽管两个人选取的意象不同,词风不同,但表达的心境有共同之处,女性对爱情的赞美和渴望是相通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致的,她们都用自己独特的女性情怀,细腻的内心去感受爱情,同时在她们的作品中彰显了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大胆叛逆、渴求爱情的女性意识,为女性诗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1]王仲闻. 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美]艾米莉·狄金森.狄金森抒情诗选[M].江枫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3]罗良功.英诗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张彩霞,宋世勇.论李清照词花意象[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5]林丽.从李清照和艾米莉的诗歌意象看不同的爱情观[J].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8,(1).
[6]米丽娜.艾米莉·狄金森和李清照爱情诗的女性意识比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7]袁志成.从闺内吟咏到闺外结社——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突围之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