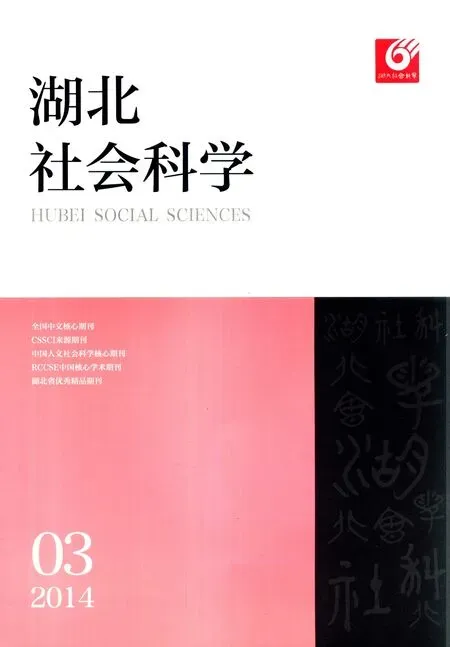从形离到神合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极相通中中华文化精神的寻绎
薛晓芳
(韶关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韶关 512005)
·人文视野·历史·文化
从形离到神合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极相通中中华文化精神的寻绎
薛晓芳
(韶关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韶关 512005)
在同一历史语境中诞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由于其“形”的分离,使得它们之间相互对立,但是二者又是近代社会变动和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孪生体和伴生物,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明显地可透视到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深沉气韵,这种“神”的契合,使得二者互相针砭又互相启发,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景观。在二者非此即彼极性思维的隔膜中,寻绎它们内在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情怀,可消弭其不可调和的交锋与冲突,以此实现二者公平的文化思维表述与传播。
形离与神合;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中华文化精神
中国现代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相互冲撞,由于其“形”的分离,导致它们之间呈现出互相对峙的尖锐形态。但是二者又是近代社会变动和进步过程中的孪生体和伴生物,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明显地可透视到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深沉气韵,这种“神”的契合,使得二者互相针砭又互相启发。我们亟待在中华文化精神“花果飘零”之际,在这二者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中,寻绎它们内在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情怀,这有助于二者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对方,从而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
一、“形”离:无法规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发端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晚清,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并至、东方与西方文化危机的并存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生存环境,可以说,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1](p129-136)五四时期,民族存亡危机将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推至极点,中西文化论争的跌宕起伏使得文化保守主义蔚为大观,形成一个高峰。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文化保守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断得到拓展,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新儒家。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晚于保守主义三、四十年,19、20世纪之交,当戊戌时代曾经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革局面猝然崩塌时,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由此全盘拉开了序幕。五四前后,对固有文明的重读和对西方文化的择别成为这一时期有识之士担负的双重历史使命,这一时期文化激进主义再次吹响了“激”战的号角,并一路引吭高歌,抢占思想领域的鳌头。20世纪3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对固有文化发动全方位、广角度的冲击,从而达到了高峰。
纵观在同一历史语境中诞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虽然都是在近代中国面临文化走向孰去孰从的历史性课题时,所必然作出的回应和选择,但是二者相互对立,势同水火,可谓冰炭不同炉。“保守者对激进主义横加指责,或者避而远之,认为无论其是否设立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目标,用全盘反对传统的激进方式去实现是大有问题的,最后只会把精华丢弃而存留糟粕。而对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者总是怒其不争,批评其守着旧传统的筐子而不愿进步,要是果真如此并长此以往,当今中国还依旧在缠辫子裹小脚的时代!”[2](p23-27)它们之间的相互对峙有时是以潜对话的方式存在着,有时是以鲜明对垒的方式进行着。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文化保守主义深恐国人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此激发民族自信心。所以,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来讲,主要偏重于对约束性美德的持守和对传统遗产的敬奉,认为传统理应成为被守护和世代相承的连续性巨链,它重视的是文化变迁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而文化激进主义是在当时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现实国情下,在强敌环伺中对于如何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采取了对传统文化强劲的否弃态势。因此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于对本国文化痼疾的针砭,对民族文化封闭性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文化优长之处的阐释和认同,它重视的是文化变迁中民族文化的创新。由于“形”态的差异,它们之间的互相针砭一度演绎出文化思潮纷争迭起、异彩频呈的文化景观。就像吴宓曾讲:“此二种运动方向相反如寒来与暑往,形迹上似此推彼倒,相互破坏。”[3]或许正因为如此,上世纪初那场此起彼伏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论争至今仍令学界念念不忘,让人不仅欣赏保守主义者的勇气与信念,同样也敬重激进主义者的学识与锐气。
二、“神”合:不可或缺的一对孪生体与伴生物
从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形”态来看,二者各有分歧,文化保守主义念念不忘自身存在的根基,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传承下来的民族智慧,而文化激进主义则更期望通过西化举措,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指明方向。尽管“形”态的各异导致二者颉颃互不相容,但是在同一历史语境中诞生的矛盾体,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又是历史进程中一对不可或缺的孪生体与伴生物,正如许纪霖指出:“激进与保守表面上看似乎是势不两立,水火难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在深层具有共通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4](p72)所以,尽管双方论争十分激烈,但隐藏在“形”态分离表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意识却是十分强烈而一致。它们“共通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也使得二者的“神”态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
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继承性来看,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登场亮相的,在内外忧患交相煎迫时,表现出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性的自觉,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及所属国家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与忠诚,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综观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它们提出的各种主张,就其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而且虽然文化保守主义认同维护传统,文化激进主义主张西化或者全盘西化,但是由于它们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因此二者又都面临着相同“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来说,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传统文化左右不逢源的困境,才为其植根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大多怀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以光大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5](p51-55)它们坚守中国文化的道统,它们的保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与坚持,还是对过去传统理念和价值的珍视与偏爱。在持守“传统”方面,文化激进主义曾一度与“反动”齐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遮蔽了人们深入认识其文化内蕴的视野,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确实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反动,但是即便是最激进的反动也没有能够真正取消它在意识层里对传统的承担。从戊戌到辛亥,从辛亥再到五四,激进主义的浪潮的确是一波高过一波,然而在惊涛骇浪之间,不管激进主义怎样反传统,它们的潜意识里还与传统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相通的思维模式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正如余英时所论述的“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传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6](p346-347)所以,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神”态的契合,使得二者互相针砭却又互相启发,形成了独特的张力。历史也正是借助两者的砥砺而曲折前进,不断地延伸着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纪发展的脉络。
三、从“形”离到“神”合
每个民族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生息繁衍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使整个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同,形成了一种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从中华文化精神的角度爬梳与厘析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可以看出二者“形”态分离,各有分歧、矛盾,但是看待任何一种思潮,我们均要放在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放在本国厚重沉实的文化精神中去寻绎。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明显地可透视到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深沉气韵,这种“神”的契合,不断地软化着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硬性边界,使得二者在中华文化精神浸润下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景观。
(一)“和合”文化精神——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渐进与归依。
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总是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程思远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中华和合文化”。“和合”文化精神注重和谐、推崇和谐,这种重和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即使在最难堪的“船坚炮利”的非理性非常态的语境中,也不断地通过“释中”、“会西”来彰显其内在的文化价值。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就是肇始于这一非理性非常态的语境中,它们都在当时现实国情的刺激下,对中国文化出路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并作出了积极回应。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尽管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鼎立抗衡,但是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中西取舍”、一味复古或全盘西化的单向度思路,而倾向于“中西融合”、综合创新的立场。如早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就反复表达中西融合的思想,他多次主张要“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7]就连最激进的胡适也强调:“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8]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赞成要维持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它们在吸纳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得不遗余力,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9]面对中西文化冲突,张东荪也提出了“化冲突而为调和”的中西文化观,他在《思想自由与文化》中指出:“我们所应努力的不在顺着自然的趋势以助长一方,推倒他方,乃只在于设法各得相当的安排,互有界限,不出范围,化冲突而为调和。”[10]
文化保守主义从诠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入手,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拥有异常广阔雄厚的民众基础,特别是它们对“融化新知”和合文化精神的不懈追求,使得它们仍然在今天还保持着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激进主义更多地只是破坏和扫除“儒家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特别是它对“昌明国粹”和合文化精神的温情和敬意,不仅是对崇洋媚外文化心理的有力抨击,而且对于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也是深刻的批判和合理的矫正。因此,从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发展看,“和合”文化精神对于二者打破自闭状态,实现双方的吸纳、互补与融合,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以人为本”文化精神——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共通与旨归。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的思想观念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向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这一文化精神指的是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根本,关注人,肯定人,尊重人,强调人性发展。它推崇人追求生命之完善、道德之自觉、人伦之和谐,是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伦理精神和人生价值观念。这一文化精神几千年来以其特有的智慧,烛照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创造,同时也始终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一以贯之的致思路线。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工业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它显示出了对人生命价值的认同、回归与捍卫,如唐君毅曾十分精辟地总结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人文精神,是“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煞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11]它还揭露了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冲击下,人忽略了对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的修养,因而以倡导道德情操、精神修养、人伦道德见长的儒家思想也就成了其可利用的资源宝库,譬如梁启超希望从东方的学问道德中找到高尚美满的人生观,以处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梁漱溟也提出以孔家“生”的人生哲学、“刚”的人生态度来指导人生,来救治理性主义控制下人精神的疲敝、人际关系的淡漠。文化激进主义,从表象来看似乎是与传统血脉的主动割裂,但是其对理想人格的认同和高扬则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有着深广忧患意识的文化激进主义,所激发出的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救亡图存”思想,本身就是“以人为本”所衍生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德情怀的体现,这些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尽管在不同时代内涵有所不同,但几乎都构成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共同情态。特别是在激情高昂的新文化运动时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巨子们高擎着个性解放、个人独立的大旗,对导致个人意识泯灭的传统道德观展开了批判,他们对“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呐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追求,这些都无不弥漫着“以人为本”文化精神的气息。
文化保守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它们认为要保守、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就要关注人格修养、精神自由,它们所积极倡导的道德情怀、精神修养,已经为其发展裹上了真善美部分;文化激进主义也从关注中国命运及其特殊历史处境出发,期望通过自由心性的充实与理想人格的追求,达到救人、救世、救国的三重目的。现如今,拂去历史的尘埃,抛去那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语境,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阐扬的有关人生、生命安顿、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方面越来越“趋同”,这种“趋同”已经越过了时空的限制,成为二者思维嫁接的契合点。
[1]郑大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05,(2).
[2]于毓蓝.刍议中国的激进与保守思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3]吴宓.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J].学衡,(65).
[4]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5]任晓兰.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评祈[J].贵州社会科学,2009,(4).
[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胡适.先秦名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9]粱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0]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Ⅲ[J].文史月刊,1 卷10期.
[11]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责任编辑 王京
G02
A
1003-8477(2014)03-0103-04
薛晓芳(1973—),女,韶关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硕士。
2013年度韶关市社科规划立项课题“网络文化对韶关市青少年德育工作的影响与对策研究”(G2013006)阶段性成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基金课题“广东省生态发展区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挖掘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GD10XMK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