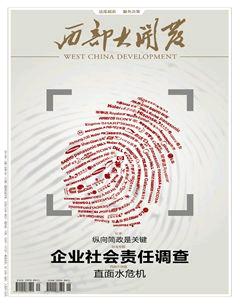南涧跳菜 天上舞蹈
许文舟


在南涧县无量山任何一个彝族村寨,对客人的尊敬,不仅体现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上,他们边上菜边跳舞,而成为敬重宾客的最高礼仪。在冬樱花盛开的季节,我有幸欣赏到南涧跳菜的醉人风采。
八仙桌沿两侧一溜摆开,宾客围坐三方,中间留出一条跳菜通道。神性的大锣连响三声,那是跳菜宴音乐织成的帷幕;芦笙细声柔气,仿佛是冬樱花无处倾吐的诉说;小三弦轻快活泼,演绎成涧溪欢喜的激情;而吹叶高亢,似乎向天上的神发出邀请。穿着美丽的彝族姑娘环佩叮当,轻歌曼舞,而壮实的彝族小伙唱着“呜哇哩——噻噻”的高腔。
随着“总理”引导,参加跳菜的高手齐刷刷地亮相,他们反穿羊皮,古铜色的肌肤,笑起来就包不住白生生的门牙了。跳菜者完全来自民间,来自生产劳作的好手,盖瓦酒每家每户都有跳菜的高人,随便点哪个出场,都不会怯场。发型显然精心处理过,留长发的扎成马尾,短发的有点“锅盖”,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理的发型,怎么成了跳菜者标杆一样的符号?
拱揖拜厨,一招一式虔诚而庄重,这时的舞者一脸认真,清香燃点,气氛就有所不同。不用化妆,阳光给这些男人涂脂抹粉,工具就是双手,托举的黑漆溜金的木盘,浸淫着民间的油腻,光亮的外表下有些通透。从厨房里递出来,内装8碗菜,然后轻轻放到跳菜者头上。“呜—噻噻”的吆喝声中,只见顶托盘的光头汉子双手拱揖,迎着客人出现。脚步忽高忽低,让人立马想到看上去寻常却有功力无边的少林扫地僧。怎么突然想到《天龙八部》来呢?也许,那些头顶盘子送菜的男人就是传说中武功高人的绝情隐士吧。另一个头顶和双臂各撑一菜盘的汉子仿佛从灵鹫宫出来,一脸神秘,襄中一定揣了绝杀的秘笈,否则断然不会让两盘满满当当的菜轻松地落到身上。合着古朴纯厚的民乐协奏曲,脸上时而滑稽风趣,时而神秘莫测,歪来复去的舞步,简直就是连少林众高僧也丝毫没看出破绽。时而,他们像鹰一样展翅,时而,他们如鱼一样浅游,菜盘宛若装上了吸顶的利器,紧紧吸在舞者头上。两位手舞毛巾的搭档,则怪态百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为其保驾护航的男士,则如天山童姥,也绝非等闲之辈。据说那位顶菜的高手失手,看上去陪衬的舞者,他们会准确地抓住落下来的菜盘,一样扭动腰身,客人丝毫不会看出破绽。
心悬了起来。那是刚出炉的高汤,那是才从锅里捞出的热菜,轻轻一落,就是跳菜者头上的高山。客人们惊叹着,为他们暗自担心,并且随着跳的幅度的加大而加大。那其实该是一种功夫吧,我想,如果没有功夫,仅仅顶一个空盘也困难重重,何况还要加那么多菜在上面,似乎我的担心显得多余,跳菜者忽急忽缓的舞步,丝毫没让一滴汤水落下来。二十四个菜盘稳稳地落到八仙桌上,刹那间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
正暗暗叫绝时,只见一位头顶托盘内装12碗菜,口中衔着两柄铜勺,勺上各置一碗菜,双臂各叠5碗菜的“空手叠塔”顶极高手合着鼓乐声上场。这样的跳菜实在不多见了,如果把无量山写得神乎其神的金大侠见了,一定会在他的武功秘笈里放上这一招功夫。那一起一落、摇来晃去的舞姿使众宾客为之捏一把汗,生怕盘翻菜撒而不敢出气。只见表演者从容自如,重叠在他臂、口、头上的24碗菜却随着他的舞姿位置变换而稳稳当当,同样是一滴汤汁也不曾溅落出来。表演者臂、肘、手、口、头功齐用,开张整合,缓急有序,让你在“天人合一”之中见美、见奇、见情,自然又让我想到慕容复与萧峰。
据野风所撰《定边纪事》记载:“跳菜”艺术源自彝族“原始宗教—古道教”文化,曾是原始母系社会时期狩猎与战庆活动过程中的进奉行为。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原始跳菜仍保持着强大生命力而在唐代民间大放异彩,并随南诏第二代君王——蒙逻晟炎进京“奉珍耍杂”之机(约公元679年),以其独特的光头、羊披、托盘、大耳环四大特色和几人重叠的杂技表演亮点而博得了武则天的赞赏。融会人与事、亲与仇、友与敌、古与今、美与丑、生活与生命、平凡与伟大的道教原则。“南涧跳菜”盛行于唐代,承传埋没于民间,发掘发展于当今。经文化艺术工作者研究和发掘整理,现在比较有名的跳菜节目有《跳菜情源》、《火恋彝乡》、《十二兽神舞》、《彝族打歌》、《哑神之舞》等。
跳菜表演者,通常都穿着彝族节日盛装,也可根据舞蹈节目的需要适度夸张,但又不失“土而美”的本色。演出采用“揉、狂、猛”递进的艺术手法,融传统“跳菜”、“十二兽神舞”、“打歌”、“哑神之舞”等为一体,体现了“彝乡歌韵、涧水狂情、气贯长虹”的核心内涵。“跳菜”音乐始终保留彝族“自吹自唱”的风格,并把南涧近几年来音乐创作成果中最有影响、观众最为熟悉、传播最为广泛的优美曲调融入其中,使之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亲和力、感染力。跳菜的舞蹈不仅有轻松自如的抒情性动律,也有刚劲猛烈的彝族气质性动律,集典型性、民族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馀说,云在青霄水在瓶……没有千辛万苦,上不了跳菜的舞台,看似简单的一招一式,其实浸淫着多少汗水啊!尽管它不是一种功夫,却也像修道一样,需要经年修炼参悟的。跳菜的魅力,在于他扎根民间,草根性质的舞蹈,简约而丰富,高贵而素朴。作为观众,内心一直以为看似欢快的舞蹈带给身心的将是无尽的愉悦,实际的情况是,有人一边看一边想陷入沉思,有人一边看一边落下感叹。
南涧跳菜除了一只鼓,没有筝音细碎,琴瑟相闻,除了一双手,也没有另外的道具。盘中盛满生活的美味,脚下踏起满天的尘灰,这就是美!演员们清一色男人,没有姿质如兰色淡气清的小女子,闷萧音孔,也不是兰花手操弄,就是这样的粗犷,引得长空水泻一掌风流。
跳菜结束时,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个舞头,但我用了许多掏心的话,还是没能打开他的话头。他是想我笔下词不达意吗?将狐妖的意味强加于落地生根的跳菜,然后添一些佐料,让原本的民间文化活动,硬生水袖与眉眼,污染了固有的美,原来飞花碎玉的质地。
这么多年,南涧跳菜从现实的婚丧喜事现场,转向舞台,那可是押了资本的赌,看上去转身华丽,实际上让南涧跳菜的原生态意味顿失。舞台灯火再明,也不及无量山间的若明若间的火把通透,一点火星也会让一出戏有曲径通幽的理由。我戴着嘉宾证去看跳菜,那一定是坐在包席上的位置,你看不出跳菜的凌厉与迅猛,跳菜者无所顾忌的展示,相反,让这样的跳菜置于民间,不比丝弦上挪动莲步浅笑低颦的女子夺人眼目。因此舞台上的跳菜多少有点孤芳自赏的苦涩。
握手是有的,这是作为嘉宾能与跳菜的演员最直接的问候,关节突出、青筋毕露的手伸过来,我得赶紧握住,我想让这双手回到无量山间,省得他们跟在事先设计好的套路上,任由人摆布。
(作者为云南省作协会员、临沧市作协理事,出版散文集《在城里遥望故乡》《云南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