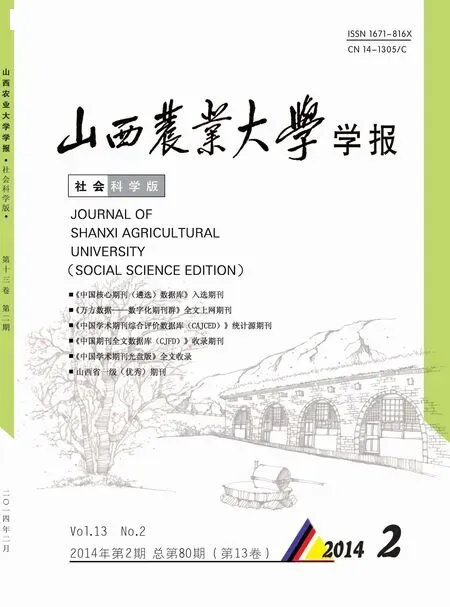论接受美学翻译观
李庆明,于莎莎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论接受美学翻译观
李庆明,于莎莎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从接受美学视角审视翻译作为一个完整动态过程所显示的特征,一位成功的译者需重视读者的 “期待视野”,并以极大的跳跃性,附以文本以未定性,创设 “召唤性”结构,以待读者再度挖潜。而后使译文如镜中之像,相中之色,言有尽而意无穷。将接受美学引入翻译领域,无疑为翻译活动规律的界说规约了一个较为合理的 “解读空间”与逻辑起点。
接受美学;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翻译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基于现象学和阐释学理论,以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创立了接受美学,认为传统文艺史家将作品视为超时代的自足客观存在,众多传统文论只从文学总体活动的单一维度出发,即以作家为中心的外部研究抑或以作品为中心的内部研究。此种研究范式往往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动态持续性特质,将“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的总体过程分割为静态封闭、相对独立的不同领域,阻隔了读者与作品间的联系交流。接受美学将文学研究的方向从传统的以 “作者——文本关系”为中心转移到以 “文本——读者关系”为中心,突破了传统文论单纯注重作品文本研究与作家心灵研究的片面性,使文学研究趋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一种研究文本接受的读者反应论。
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原文、译者、译文、读者构成的接受与建构的动态过程。以接受美学视角看翻译客体,译文文本不可能将原文相关的阐释、想象、意义完全再现,对等的缺失让译文读者与文本对话,而作为原作接受者的译者兼有原文二度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故而,翻译实为一种感受文本空白与再现空白的过程。将接受美学引入翻译领域,从文本的多层次结构意向性审视翻译作为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显示的特征,无疑为翻译活动规律的界说规约了一个较为合理的逻辑起点与 “解读空间”。
一、关照译文读者的 “期待视野”
纵观翻译研究历史,其重心经历了由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的转移过程。接受美学认为作品并非与读者无关的非意向性客体,在 “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读者也绝非单纯的被动接受者,相反,读者是整个活动的能动主体,其积极地介入与参与译本、译者与之形成辩证的对话关系。事实上,作品的阅读过程是读者与文本间的对话与交流。正是由于读者阅读过程的参与,作品得以进入无限的接受活动链中,文本中隐藏的没有标明的预设编码被予以不同的释义,作品意义由此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审美经验之中。故而,接受不再是被动的反映,而是作品意义和审美功能的积极建构。
(一)“期待视野”的平衡机制
任何翻译总体活动中,作品的接受过程必然涉及主、客体两极。读者 “审美视野”未介入之前,本文只是充满未定性的多层面图示结构,即作品的 “一极”——接受客体。读者与本文间的对话与交流,使本文未完成的图示结构得以具化,构成作品的 “另一极”即接受主体。作为接受主体的接受者建构其 “期待视野”的过程是心理图示中 “同化”与 “顺应”两种机能彼此更迭的过程,亦是接受者与作品相互交流、 “双向”互动的过程。
1.作品客体主体化
“期待视野”作为 “读者中心论”的根本理念,是接受美学鼻祖之一Jauss基本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所谓 “期待视野”是指 “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期待,这种期待有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可能的限度”。[1]即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活动前都处于一种先在理解结构与知识框架状态下,对作品都具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包括既有的语言习惯、背景知识、兴趣爱好以及审美经验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对作品的期待与要求,并在接受活动中具化为一种潜在的惯性期待。这种心理上的定向期待在接受主体的阅读过程中发挥着求同排异的潜在作用。符合读者思维定势的文本,进入读者审美视野;相反,不符合者被拒之门外。基于期待视野而对作品进行审视求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作品客体的主体化。
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定向期待,已然内化为一种心理上的积淀:作为一种稳定的、惰性习惯倾向,读者会不经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按照既定期待视野审视作品,作出合乎旧视野的选择。因此,审美经验视野一定时期内是内质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一成不变或直线累积的过程。文学作品将读者导入特定体验,在阅读过程中激发、实现抑或改变、重新定位其期待视野,即作品激发接受者的一系列意识活动,这些意识活动的组合被用来解释新阅读的内容,由此而形成的文本意义进而改变最初的 “期待视野”,因此,读者在阅读新内容的同时其实亦在阅读过往,期待视野进而成为一种习惯性扩张与延伸。
2.读者主体对象化
读者主体对象化作为接受主体心理图示上的一种叛逆倾向,是 “期待视野”异化机制的结果。对于公式化的文学作品,读者难免产生审美疲劳,此时,在求新求变的惯常心理倾向诱导下,接受主体便会打破惯常心理模式,突破既定视界的束缚,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客体中与过往经验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改变意味着革新,期待指向的受挫,审美距离 (“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 ‘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2])的存在,必然会令接受者感到暂时不适,但只要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在一定距离内,正面失望亦会峰回路转,激发读者探寻欲望,进而不断重塑期待视野。对于作品而言,其在被大众所接受过程中由冷到热以及由热到冷便不足为奇,姚斯认为 “文学作品并非是一个对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足客体,也不是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本质的纪念碑。文学作品像一部乐谱,要求演奏者将其变成流动的音乐。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拥有现实的生命”。[3]而作品生命的维度又在于每部作品的本质特征,历史纵深感强、解读空间大的精品文本便能在无限延伸的接受链条上,展现其更为 “广阔”的潜在意义;于读者而言,期待视野由此成为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过程,艺术生产与接受相互作用,真正实现了读者介入的作者、作品、读者的互动交流。
(二)审美距离若即若离的度
上述有关读者 “期待视野”平衡机制的论述表明,“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接受对象——文本的选择,即读者具有选择译作的主动权。如若将读者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审美距离设为“1”,可以将读者基于期待视野对文本的态度大致划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1)审美距离=0→审美疲劳→排斥文本→期待视野静止
(2)0<审美距离≤1→中性→接受文本→正面失望的期待视野更新形成
(3)0<审美距离≤1→正面失望→接受文本→期待视野更新形成
(4)审美距离>1→正面失望→排斥文本→期待视野静止
因此,要使文本为读者所接受,在审美距离允许的范围内文本至少应在某方面带来比读者的认识和生活经验更为丰富的东西。翻译过程亦是如此,若译作完全基于特设的隐含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只能见到我们 “已知熟悉”的东西,那么它固然能够使接受主体得到熟识美,却也只止于此,且会让读者兴趣尽失,译作也因此 “空洞无物”;再者,若译文读者读到熟悉的领域依然兴趣盎然,也是因为译文为读者呈现了未知的陌生,引导了一个不熟悉的新方向。因此,当 《竹枝词》中 “道是无情却有情”被许渊冲依据传统英诗规范,并选取了译语民族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意译为"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这样地道的英文时,部分读者虽然给予肯定,但也不乏负面评价:"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的出现令某些读者联想到"as…as the day is long",可谓是“陈词滥调”及“庸俗的摇滚歌词”。再如,傅东华先生所翻译的 《飘》大量采用归化法,将主人公Scarlett O.Hara译为“郝思嘉”,以 “蝶姐”、“阿毛”、“方老太太”指称原著中的一系列人物,这无疑给读者一种古怪的感觉,放佛这已不是那个发生在美国南方的传情故事,而是一个在黑头发、黄皮肤间的展开的剧情与此相反,当翻译家Jacques Dars直面差别,正确把握译作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以超出当地读者期待中的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视野,将《水浒传》中 “天子”、 “张天师”大胆地译为“天之子”和 “天之师”,而非传统地归化为 “皇帝”、“道教之师”时,其译作反而得到译评家的肯定,受到法国读者欢迎。因此,译作若想引起译语读者的兴趣,就必须拉开自己与读者审美期待间的距离。
如若译者过分拉大译作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效果亦会过犹不及。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心系民族命运的士大夫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学说的重要性,但 “吾闻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传统思想仍深深植根于国人潜意识中。因此,要介绍西学,就要求译者正确把握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尽力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注重对原文思想精髓的传播。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 《域外小说集》重点介绍了东欧及北欧弱小民族作品,以期借此引起遭受列强压迫的国人共鸣,挽救民族于生死危亡,但该译文在出版10年后仅售出20余本。在直译之风盛行的 “五四时期”,当时的中国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带有欧化风格的 《域外小说集》在其特定的历史传统中似乎并不合时宜。读者对译文的要求 “不外乎两种,一是至少要看得懂,二是要读了有所得”。[4]所谓 “看得懂”即译作要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而 “有所得”指的是译作还应存在审美距离。《域外小说集》虽然满足了当时读者渴望进步文学的公共需求,但却忽视了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采用了过于欧化的语言,使译文过于生涩。读者阅读起来都困难重重,又如何期待接受主体读有所得呢?
与鲁迅和周作人的译文相比,处于同一时期的林纾的译文 《黑奴吁天录》大受民众欢迎,尽管其译文常有随意删节、评点之类的讹错,但林纾充分关照当时中国读者特定的期待视野,“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5]在译本的序、跋及例言中译者故意弱化原著中基督教的价值观,转而以 “另一种意识形态——中国传统道德观所涵盖的道德”[6]代之,为此,林纾在译本例言中写道:“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去其原文稍繁琐者。”[6]由此可见在林纾看来,晚清时期中国普通读者对基督教思想相对陌生,长篇累牍的宗教思想宣扬显然不适于一成不变地译为中文,翻之,反而弱化读者阅读兴趣。显然,译者考虑到了当时读者的 “期待视野”。再看一例,译文《黑奴吁天录》的原著中夜娃的父亲圣格来,在夜娃死后对死亡有如下一番思考:
"DEATH!""Strange that there should be such a word,"he said,"and such a thing,and we ever forget it;that one should be living,warm and beautiful,full of hopes,desire and wants,one day,and the next be gone,utterly gone,and forever."[7]
林纾将其译为:
“吾躯命尚健,何为遽死。凡人恋生,常不自计其死。今吾自省健硕,未届中年,竟如是乎?”[7]
原著这段话将思考焦点落于 “死”,强调生死仅一步之遥,死是一种不可违、不可预测的事物,而林纾译文将重心偏向 “生”,流露出对现实生命的关注,对 “生”的眷恋。显然译者关照了译语读者 “活在当下”的期待视野,反映了中国传统 “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观。
由此看来,于译者而言,任何翻译文本的定位、语言的斟酌、策略的采用,都应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读者意识应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中,只有突出特定历史阶段读者 “期待视野”的中心地位,将审美距离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准确把握二度创作的度,进而使原文、读者、译文三者辩证统一的译作,才能称之为成功的翻译。
二、译文文本意义的 “具化”
文本作为审美创造主体对象化和语符化的一种体现,其与生俱来的文学性特质在接受活动介入之前只是隐藏在文本结构中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并由此形成召唤性结构,以待读者的审美参与。由此看来,传统文论将文本意义视为绝对静止、自足客体的存在事物已然走入了认识上的误区。文本并无终极意义,不同接受者审美、阅读过程的参与势必赋予文本意义以多元、无限、动态性特质。
(一)文本意义的 “未定性”
接受美学另一代表人物伊瑟尔教授沿袭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致力于用现象学分析文本结构内部阅读反应机制,借解释读者反应批评以及叙事理论开拓接受美学之路。他认为接受活动文本作为一种接受前提,其各构件是以语符形式呈线性排列,读者介入阅读过程必然使各构件有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间隔,因此文本本身存在 “召唤结构”,即具有某种隐含意义的 “未定性”。否定和空白是未定性的两个基本结构。否定意味着“阅读过程中轴上的动力空白”,[8]其激发读者冲破前意向,想象对象的含蓄,“逼迫”读者在习惯性倾向与新发现间作出选择;空白是指文本通过已实写的部分向读者提示的、未明确写出或未写的部分,当读者的想象被激发,视点和图式联为一体,空白便不复存在。未定性存在三重含义,第一层是指诸如双关、词类活用、意识流、时空交错等艺术形式上的技巧与手法,注重文本层面实与虚、确定与未定的形态;第二层倾向于一种调节功能的意义,即通过未定性引导读者在运动中对最终意味的具化与实现;作为体现审美本质意义的第三层含义,在艺术技巧与调节功能基础上,建构了一种超越性本质意义,达到了审美意境,体现了掌握世界方式的艺术性基本特征。
文本中描述现象与现实中事物确切关系的缺失对读者发出了无言邀请,促使有着主体意识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文本的意义空白,联接文本连贯的 “暂时中断”,不断重构 “格式塔”,使未定性被意义所替代,创作意识进而被具化转为接受意识,文学作品由此真正进入存在。正如伊瑟尔教授所说 “空白作为一个空无的位置,它们自身一无所有。也由于这个 ‘空无’,它们在开始交流时才成为活跃的动力”。[9]
(二)关照性叛逆下 “召唤性结构”的创设
伊瑟尔认为:“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其想象去填补文本中的所谓空白,也就是说,在一个文本中存在着悬而未决或尚未提到的东西需要填补”。[10]由于文本无法自发地响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提问和指示,只能通过未定性或构成性空白等不同形式的召唤结构,在信息载体中留下暗示,以此作为与接受主体对话的前提,神明里透出幽深,呼唤读者合作,引导其建立语境。译者的 “关照性叛逆”[11]即基于读者 “期待视野”的二度创作过程,尤其应注意把握原文中 “虚实隐显”的神韵,并基于此遴选最佳的翻译策略使其在译文中得以重现,实现原作生命力的延续,构建译本的美学价值。试看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 “吊着羊角大灯”的两种不同译法:
杨译:"big horn lanterns hanging above."(vol.2.p.608)
霍译:"great horn lanterns."(vol.3.p.500)
羊角大灯,俗称明角灯,“是用羊角加溶解剂水煮成为胶质,再浇入模具,冷却后成为半透明的球形灯罩,灯罩上彩绘花纹,或贴剪纸花纹,再配以蜡烛座和提梁而成羊角灯”。[12]对此,两位译者都未作出任何解释和增译。对于不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译语读者来说,这无疑是阅读上的挑战,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张艺谋导演的影片 《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西方广为流传,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视野也因此逐步改变,潜意识里对中国灯笼有所认识。但译本中“great horn lanterns”这个意象与读者既有的 “前理解”不符,这种间接性、模糊性以及跳跃性令译语读者头脑中既定的期待惯性被打破,使异文化读者会感觉些许陌生及暂时不适,但时过境迁,译本由此而产生的特殊张力便会对译文读者产生特有的感染力,触发其想象活动,从而构建全新的图示关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读者在建构文本过程中实现价值、享受愉悦,体味 “未定性”的独臻妙境。
又如苏轼的诗作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13]
许渊冲将其英译为:
Red Flowers Fade
Red flowers fade,green apricots appear still small,
When swallows pass
Over blue water that surrounds the garden wall.
Most willow catkins have been blown away,alas!
But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grows no sweet grass.
Without the wall there is a path,within a swing.
A passer-by
Hears a fair maiden's laughter in the garden ring.
The ringing laughter fades to silence by and by;
For the enchantress the enchanted can only sigh.[13]
初读 《蝶恋花》似觉只云风月,无关国事,再读便觉一种深沉的悲哀与无奈。诗作写于诗人被贬惠州期间,“绿水人家绕”、“墙里佳人笑”看似繁花似锦、风花雪月,实为人生空漠、世事成空,只能随缘自适,任运自在。
许渊冲在其译文中将上阕中 “残红”、 “青杏”以及 “绿水”此类意象分别译为 “Red flowers”、“green apricots”、“blue water”。此译法故意切断视觉意象的流动质感,将意象的静止状态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以连贯性的 “暂时中断”勾起读者无限想象,为意境注入了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意识,并将其融会贯通,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清淡浅雅的静态美色调跃然纸上。对“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的翻译处理更显高明,“without”和“within”两个虚词的使用与原作只写佳人笑,而将佳人的娇容与姿态全部隐藏的隐显手法大同小异,既运用了头韵的手法,又增加了空间概念感,以 “象”之外的 “空、虚、气”释意境之根与魂,以 “隐”拓“显”,让读者的想象也随行人驰骋万里。此译法与诗人对意境的诠释不谋而合,可谓 “译气不译字”间再现原文的 “语近情遥”。而对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中 “声渐消”的翻译则更为巧妙,“fades to silence by and by”意境何其空远,丝丝入扣、铢两悉称的翻译在若远若近、若即若离间令读者渐觉 “声音”远去,暗香浮动。
总之,译作的意义是由原作者与译者共同创造的。在保证语言翻译准确的同时,译者须充分重视 “留白”的意味,将原作的独臻妙境在译文中以 “召唤性结构”的形式加以展现,以便留给读者较大的玩味空间。
三、译者面临的两次 “视野融合”
翻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而非一个由译者建构将原文在译文中再现的简单直线型过程。翻译理想化恰恰忽视了译者与读者在解读原作本文过程中的能动参与作用。在翻译的整个运行过程中,译者必然面临两次 “视野融合”,而这两次“视野融合”都强调了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最终话语体系形成中的中心性地位:首先,译者将其自身 “期待视野”与源语本文进行交流,达成第一次 “视野融合”;其次,译者预设虚拟现时译文读者,预测其与译文的对话与交流,形成 “期待视野”的第二次融合。因此,译文最终意义的呈现源于作品本身以及接受者所赋予的意义总和。
事实上,译作的源语文本来源于本文与译者解读相互作用后,于译者头脑产生的一个近似于本文的虚拟文本,而非本文。这一虚拟文本并非译者完全受动本文产生,而是译者包含创造因素的、积极的建设性理解行为之后,二度创作的结果。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把自己也写进去,留下一定位置给灵感、直觉、推敲等艺术思维方式,但建设性的构建活动并不等同于译者的纯心理主观随意行为。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只能使接受活动脱离本文,而使翻译成为译者的独自话语。因此,本文意向的指示性与归约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对译者自由创作的制约作用。本文的制约性与接受的能动性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因此,为了使本文与源语文本最大限度近似,就必须确保译者自身与源语交流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达到第一次 “视野融合”。
翻译的出发点与指归都是读者,即译者心中特设的特定文化知识、交际需要和希求的作品本文的终端接受者。因此,即便现时读者的阅读反应过程在翻译活动结束之后才得以真正介入,也并不意味着译者无需考虑译文读者,相反,译者仍需兼顾译文与译文读者间的关系,即在翻译过程中就面对预设现时读者,考虑其审美趣味与接受水平。译文读者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国别、年龄、性别、职业、经历等都可能成为影响他们阅读接受译文的因素,且 “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也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要求”。[14]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提前预测现时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实际的翻译运作机制中,译者俨然已将自身设为译文读者中的一员,凭借自身特殊的读者身份,不断模拟译文与预设隐形读者间的交流与对话,进而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唤起处于特定历史阶段读者大体相同的反应,使译文与译文读者的 “期待视野”达到第二次融合。
四、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颇具现代意识的一种全新理论,接受美学否认文本的无客体指向性,赋予读者以阐释优先权,认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构建在读者审美经验之上,惟有读者阅读过程的介入文本的存在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接受美学翻译观强调文本的开放性以及阐释的不惟一性,承认每一位读者的释义权利与才能,突出作为读者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出翻译乃是以读者为中心,以译者为主导的本文与译者、译文与译文读者间的对话交流、视野融合之主张。将接受美学引入翻译研究领域,无疑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范式革命,将翻译模式从 “原作→译作”间的简单对等转为“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间的多方互动。对读者而言,读者的参照地位得以确认;对译者而言,将译者由翻译的 “奴隶”解放为翻译真真正正的 “操盘手”,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寻找到相互容纳的切合点,以期达到阅读中最佳审美效果的质的临界点,更好地服务于译文读者。对译文而言,文本意义在与读者、译者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之中得以具化,译文亦由此如镜中之像,相中之色,言有尽而意无穷。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9.
[2]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9-31.
[3]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4.
[4]吴娜.“期待视野”与翻译中的注释[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08.
[5]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5.
[6]张佩瑶.从话语的角度重读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J].中国翻译,2003,24(2):15-20.
[7]魏家海.文学翻译的操纵性与主体性[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2):115.
[8]伊瑟尔著.鑫惠敏译.阅读行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273.
[9]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第1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35.
[10]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09-310.
[11]孙致礼.翻译与叛逆[J].中国翻译,2001,22(4):21.
[12]邓云乡.红楼识小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30-31.
[13]戴玉霞.飞鸿踏雪泥 诗风慕禅意——从接受美学视角看苏轼诗词翻译中禅境的再现[J].外语教学,2011,32(5):108.
[14]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
(编辑:佘小宁)
Anakysis on Transk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ve Aesthetics
LI Qing-ming,YU Sha-sh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Shaanxi 710054,China)
The final aim of translation is the reception of the reader.The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is attempted by the translator so as to impel the reader's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 and his dynamic searching for its implied meaning.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in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Reception Aesthetics perspective,thus providing a reasonable reading room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ranslation.
Reception Aesthetics;Horizon of expectations;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Translation
H059
A
1671-816X(2014)02-0179-06
2013-10-13
李庆明 (1963-),男 (汉),湖北黄冈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