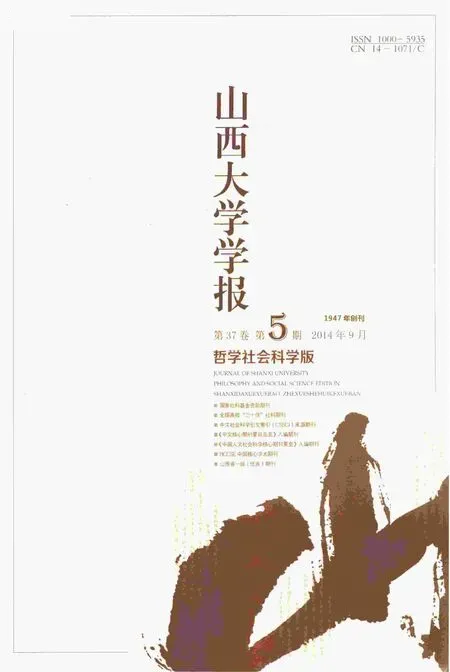“光学一致性”与科学视觉表象的客观性——关于摄影技术史的一项科学编史学考察
刘 兵,宋金榜
(1.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2.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
一 引言
科学活动具有社会性、传承性和积累性,科学家只有将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过程、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表达出来,才可能与他人进行交流,才有可能接受科学共同体的检验并纳入知识积累体系。表达的形式可以是语言文字的,也可以视觉图像的。科学家通过绘画、版画、制图、图表、符号、摄影、录像、电影、模型以及实物标本等非语言文字的视觉方式进行的表达被称为视觉科学表象(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science),其中二维静态的视觉科学表象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科学图像。
科学图像对事物的观察和记录功能往往是文字所不能代替的。特别是17世纪时在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建设宏大的“自然档案”的理想激励下,科学图像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尤其是对于博物学、解剖学这样的观察和描述性学科来说,将研究对象以图像形式细致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对于建设“自然档案”显得特别有意义。
科学图像的记录功能要求图像必须具有写实性,即图像与其所表达的对象必须从视觉上保持一致。中国古代画家将这种写实性称为“应物象形”,而西方学者称之为“光学一致性”(optical consistency)。写实表象技术的发展史就是追求光学一致性的历史。从原始的勾线填色到文艺复兴艺术的透视画法,再到暗箱和明箱等绘画辅助工具的使用,使得光学一致性的达成越来越容易。而19世纪摄影技术的发明则完全摆脱了画家的参与,使得没有艺术背景的人(包括科学家)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制作具有高度光学一致性的图像,摄影技术因而成为人类历史上写实表象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在科学史上,摄影技术出现之后迅速以其没有人工干预的“机械性”引起19世纪科学家的高度兴趣和极端崇信,一度掀起使用照相机制作各种科学图集的热潮,这些图集被称为“观察科学的圣典”。但是摄影技术的“机械性”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特别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构主义学者更是对摄影技术的“机械性”进行了细致的“解构”,提出摄影和绘画一样渗透着摄影师或科学家的理论,而主观需要和审美情趣对摄影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科学史家也发现,摄影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绘画在科学中的运用,他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摄影本身对于表达科学概念的功能的缺失。
本文从科学编史学角度出发,对摄影技术出现之后的19世纪科学家、20世纪的建构主义学者以及科学史家在摄影史研究中对摄影所持的不同态度及其研究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把握摄影史的发展变化和其中对摄影技术看法的变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摄影技术运用于科学视觉表象的优势与不足。
二 从写实绘画到摄影技术
不管是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还是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的《阿尔诺芬尼的婚礼》,从形象和光影效果上对事物真实而细致入微的描绘都会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美的享受。绘画与其描绘对象的光学一致性对于科学来说更加重要。所谓光学一致性,就是指画面中所描绘物体的每个点,从相对位置、亮度、颜色等方面都和人眼所观察到的物体本身的点一一对应。这样,绘画就准确地记录了人眼所观察到物体的形象,人们观看绘画就能真切地感知到物体本来的样子。
绘画是画家用画笔把眼睛观察到的物体的形象描绘在画纸(或者画布)上,因此从物体本身的形象到画纸上的形象之间要经过画家双眼、大脑和手、笔的一连串转换过程。经过这些过程的转换,最终的绘画结果和物体本身的形象相比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真。高明的画家能更逼真地描绘出物体的形象,而平庸的画家则难以准确地“应物象形”。
15世纪早期欧洲兴起的透视画法第一次为绘画的光学一致性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透视画法的基本原理就是画家用一只位置固定的眼睛通过一个窗口去观察窗口后面的物体,将人眼所观察到的物体在窗口中投影的相对位置准确地复制在另一个“窗口”——画纸上,从而达到准确描绘物体的目的。[1]透视画法将观察者的眼睛固定下来,绘画过程中省去了大脑的转换过程,因而在写实绘画技术史上取得了重大进步。
公元前400多年,中国的墨子就观察到小孔成像现象。如果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将物体的形象直接投射到画纸上,然后用画笔将物体在画纸上所成的像描绘下来,这样就省去画家双眼和大脑的转换,就有可能比透视画法更准确地进行描绘。暗箱(camera obscura)就是基于这一原理发明出来的。暗箱是一面开有一个小孔的密封箱,箱外景物透过小孔,在黑暗的箱内壁上就形成了上下颠倒且两边相反的像。画家先用铅笔勾勒出成像的轮廓,然后再进行着色,即可得到一幅非常逼真的绘画。1807年,英国画家奥拉斯顿(W.H.Wollaston)又发明了更为简便易用的明箱(camera lucida)。明箱的关键部件是一个棱镜,画家通过棱镜向下观看,可以同时看到下面的画纸和前面物体通过棱镜的反射所成的像,而物体所成的像刚好就在下面画纸的位置上,这样画家就可以直接在画纸上将物体的成像描绘下来。[2]
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暗箱和明箱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虽然利用暗箱或明箱绘制的作品一度使真正的画家感到一丝威胁,但这种绘画方式仍然离不开绘画者的手法和笔墨,因此并不能达到完全准确描绘事物的目的。如果能有一种物质或者技术,可以直接将物体在暗箱中所成的像记录下来(明箱在画纸上所成的像是虚像,因此无法直接记录),那么“绘画”的过程将不仅不再需要画家双眼、大脑的转换,甚至也无须画家的手法和笔墨的参与,因此就应该能够更为准确地描绘物体的形状。这一想法导致了摄影技术的发明,而暗箱也被公认为是照相机的前身。
对于摄影技术的发明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动记录光学成像的物质和方法。1825年,法国人约瑟夫·尼塞费尔·尼埃普斯(Joseph Nicephoce Niepce,1765-1833)用朱迪亚沥青做感光材料,使用“日光刻蚀法”拍摄了人类历史上有确切年代可查的第一张照片《牵马的孩子》,但是他的方法要经历数小时的曝光,而且成像模糊,因此实用性较差。1837年,法国人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1787-1851)创立了“达盖尔摄影术”(Daguerretype,亦称银版摄影法)。达盖尔摄影术以铜板为载体,以光敏银层为感光材料,曝光时间仅需15-30分钟,而且成像品质优良,[3]8达盖尔因此被公认为摄影技术的发明人。达盖尔摄影术的诞生,掀开了利用“自然之笔”——光线获取图像的新篇章。
从写实绘画到摄影技术的发展史,是一部逐步将主观因素排除于“绘画”过程的历史。随着主观因素的逐步排除,绘画的光学一致性越来越容易实现。发展到摄影技术,主观因素被最大限度地排除出去,“绘画”过程完全通过“自然之笔”——光线来实现,使得其光学一致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自然之笔”:19世纪科学家对摄影技术的极端推崇
摄影技术以其操作过程的机械性,为科学图像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带来了无限期望,更迎合了培根思想影响下的观察科学积累知识的需要。对于观察科学来说,“科学家必须杜绝将自己的愿望、预期、概括、审美,甚至日常语言强加于自然的影像。由于人类自我约束的能力在衰减,因此必须由机器来取而代之。”[4]摄影技术恰恰满足了这种需要。“碘化银纸照相法”的发明者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 -1877)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摄影师之一,他在1844年出版的《自然之笔》(Pencil of Nature)一书中把摄影描写成“自然物体描绘它们自己的过程,而不需要艺术家的画笔的帮助”[5]。人们都深信,由于摄影是利用化学方法将物体发射或反射的自然光线通过镜头在底片上所成的像记录下来,整个过程都是通过自然过程实现的,也就摆脱了画家的技能、好恶等主观因素可能带来的偏差,因此能完全客观、真实地描绘物体。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传播科学系主任、教授吕克·保韦尔斯(Luc Pauwels)也指出,和手工表象方式相比,对于摄影来说,“人眼直接观察可见的物体或现象可以被照相机这样的表象设备捕获,并产生以时间统一、空间连续为特征的详细表象,这会产生某种‘中立’,因为所有的元素和细节都是被平等对待的”。[6]所谓时间统一,是指摄影是在瞬间完成的,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对对象完备的描绘结果,而不是将对象不同时刻的状态进行综合的结果。所谓空间连续,是指凡是对象进入镜头的发光点,都会依据既定的投影关系在底片(或者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上形成一个像点,发光点和像点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摄影师在按动快门的瞬间无法改变这种对应关系,摄影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机械的”、“中立的”乃至“客观的”表象方式。而手工表象不具有时间统一性(因为绘画过程不可能在瞬间完成),也不具有准确的空间连续性(因为绘画需要画家的参与)。因此,摄影发明以后不久,迅速得到科学家们的信赖,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让自然为其自身说话”成为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新科学的口号,并激起采用了照相机制作确保不受人类干预的鸟类、化石、人体、基本粒子、花卉图像的图集,即“观察科学的圣典”的狂热。[3]81
这种狂热的确在知识的积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人们对摄影技术的过度迷信。德国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博物馆馆长、生物学和哲学教授、自然科学史讲师奥拉夫·布赖德巴赫(Olaf Breidbach)在其《微观世界的描绘:19世纪科学显微摄影中对客观性的申明》中详细研究了19世纪的科学家对摄影这种图像生产方式的过度痴迷与信赖。显微摄影是摄影技术在科学中的最早应用之一,第一本有显微照片插图的专著于1845年出版。到了1860年,解剖学家已经出版了大量介绍显微摄影技术的书籍。从布赖德巴赫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把显微摄影技术看作是一个记录显微分析的、不受观察者主观干扰的重要方法。显微照片被一些作者认为是对微观世界彻底的、可靠的替代,而不是人工生产的制品,他们甚至试图利用这些显微照片代替标本本身来研究微观世界。当时显微镜的放大极限是2 000倍,为了获得更大的放大倍率,当时的科学家采用了这样的方法:首先制作一张某一真实标本的显微照片,然后把这张显微照片作为标本放到显微镜下再次放大,从而制作第二张放大倍率更大的照片,这样第二张照片可以达到8 000甚至30 000倍的放大率。这些科学家利用照片代替标本以实现二次放大,是因为他们的确认为这些“照片可以提供微观世界结构的精确信息”,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方式还将向我们提供照片成像的颗粒以及光学负片的其他物理属性的“信息”。[7]
摄影被认为是自然物体描绘它们自己的过程,而不需要艺术家的画笔的帮助,因此可以杜绝画家将自己的愿望、预期、概括、审美甚至日常语言强加于自然的影像。但是19世纪的科学家对摄影技术也存在着过度迷信,甚至将照片代替研究对象本身的现象。
四 “人工干预”:建构主义学者对摄影技术“机械性”的解构
19世纪的人们有些过于沉醉于摄影带来的惊喜,片面夸大了摄影的“客观”和“真实”。虽然摄影师对摄影的干预方式不如绘画那样自由和多样,但是摄影也无法完全摆脱主体的干预。从摄影发明之后不久,便开始有学者反思摄影的“机械性”。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1924-1967)更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学说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下,建构主义学者更是热衷于发现科学家的理论背景在摄影过程中的渗透方式,揭示主体对摄影进行干预的途径,从而对摄影技术的“机械性”进行解构。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可以将摄影渗透主体理论的方式以及主体对摄影进行干预的途径分为以下几种:
1.摄影器材及其设置。照相机本身以及镜头、滤镜的选择,照相机光圈、焦距、快门速度、白平衡等参数的设定以及摄影模式、对焦模式、测光模式的选择,相机底片大小及其感光度,相纸的选择以及冲印技术的运用,自然光线以及闪光灯的布设等等,都为摄影师干预摄影提供了可能性。
2.对象选择。对拍摄对象的选择直接渗透着科学家的理论背景和学术观念。假如一个植物学家信奉林奈分类体系,他在拍摄植物的时候就会特别关注植物的花而很可能忽略其他器官,因为林奈分类体系是以植物的性器官——花为分类依据的;而一个信奉自然分类系统的植物学家必定关注植物的全部器官,因为它们都是自然分类系统的分类依据。
3.背景选择。背景的选择也能体现出科学家的理论倾向。比如,林奈分类体系对动物的分类更强调其形态学特征,因此信奉林奈分类体系的动物学家拍摄动物时就有可能不会特别关注动物所处的环境,甚至会有意使动物脱离特定的环境;而有的动物学家则强调动物的生活习性及栖息地特征也应成为动物的分类依据,他们拍摄动物时便会更注意将动物置于特征性的环境中。
4.视角控制。由于照相机的底片是平面的,这就决定了摄影和透视画法一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边缘拉伸形变,广角镜头产生的形变尤其明显,这种形变就是透视形变。而人眼的视网膜是球面的,不会产生这种形变,这就决定了摄影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记录人眼所观察到的效果。人像摄影师使用广角镜头拍摄美女,可以使其双腿显得更为修长,就是利用了广角镜头的透视形变。在科学研究中,透视形变也很早就被科学家有意识地利用。19世纪时考古学家、建筑师和制图师沃辛顿·乔治·史密斯(Worthington George Smith)在利用明箱绘制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标本时,就曾通过将明箱更加靠近眼眶,以使得眉骨显得更大,而其他部分包括前额则被缩小[8]。较小的前额代表着较小的大脑容量,这样就佐证了他所支持的赫胥黎所提出的尼安德特人是一种“最古老的人种”的理论。
5.美学考量。摄影师的摄影技术、摄影风格、艺术修养和审美兴趣,以及拍摄需要、对拍摄对象的认知和个人好恶,都将对拍摄结果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伊丽莎白 A.凯斯勒(Elizabeth A.Kessler)曾经参与观察了哈勃后续计划(Hubble Heritage Project,又直译作哈勃遗产项目)的天文学家对M51号星云的哈勃望远镜照片的选择和处理的详细过程。通过观察她认为,哈勃太空望远镜所拍摄的照片对换取官方支持和公众热情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图像并不是依赖其科学内容,而是依赖其惊奇和震撼的美学效果来激发公众的兴趣和热情的,因此天文学家在选择和处理照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种程度的美学价值判断。比如,为了显示光强度的精细差别以看到对象的更多的结构和细节,天文学家们调整了数据中的测光范围,减少了图像中所包含的亮度的范围并强化在该范围内的光强度数值的差别,而在此选择范围之外的数据则被忽略或者降低饱和度。图像还被进一步修正以提高清晰度,宇宙射线痕迹被去除,望远镜或者探测器的其他一些设备因素比如坏像素带来的暗点以及过度曝光区域等也被去除。为了创造一幅完美的图片,尽管天文学家和图像处理者如此细致打磨,但是他们却保留了一项设备不良因素带来的影响——衍射芒(看上去像是从明亮星体发出的尖细的光线)。这虽然是光线在望远镜内部形成的不理想的效果,但是因为它们很符合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形象,成为重要的美学元素得以保留。[9]
6.作品解读。摄影的解读离不开主体的参与,解读过程无法避免主体的理论背景、兴趣、意愿等主观因素的干预。其实,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观察渗透理论的研究中,对于“观察陈述”中主观因素的存在和影响,已经是一个接近于常识性的知识了,但当这种学说专门地用于对摄影技术带来的用于科学研究的视觉图像的分析时,仍然会突出地展示出其冲击力。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艺术与文化系伯尼克·帕斯威尔(Bernike Pasveer)曾经观察研究了临床医生制作和解读X射线照片的过程。他发现,对X射线照片中阴影的临床意义的判断是一个复杂、费时而又充满着主观解释的过程,它有赖于从他人、传统医学以及其他诊断方式(触诊、叩诊、听诊、对尸体的解剖等)获得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对其他X射线图像的对比研究。[10]
因此,不管是科学摄影还是艺术摄影,都无法完全摆脱摄影者的干预和主观的表达。对于科学摄影而言,科学家的理论背景更是渗透于整个摄影过程,包括摄影器材的选择及其设置,拍摄对象的选择及其背景的处理,摄影手法的运用,最终照片的解读等。
五 “功能缺失”:科学史家对摄影技术科学表象功能的反思
普林尼曾断言绘画不可能成为传递真正的普遍知识的工具,因为它们总是和有形物体的偶然特质相关。[11]135如果普林尼能够活到今天,他会发现这种说法更适合于摄影。
摄影期许不受人为决断干扰的,以时间统一、空间连续为特征的客观图像,但这也恰恰造成了传递“真正的普遍知识”的功能缺失。摄影的时间统一性使得单张摄影作品通常无法表达事物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摄影的空间连续性使得科学家无法像绘画那样对视野中的对象进行取舍、强调或重组。因此,摄影是一种包含着完备的原始信息的“原始图像”,是对具体的特定事物的表象结果,而不是对一类对象共同属性的抽象,因此无法传递或者再现“物理对象的本质”,即科学概念和规律。
绘画则可以通过选择、忽略、分离、组合、强化、淡化、色彩运用甚至加注文字等手段,抽象出同类对象的一般特征然后描绘出来,从而表达和传递物理对象的本质。比如在解剖学中,绘画可以淡化、模糊甚至忽略次要组织,从而简化复杂的解剖学信息;可以将不同的元素综合到一幅绘画中,从而描绘更完整的解剖学概念;可以加上箭头,来表示血液流动的动态路径;可以用红色线条表示动脉、蓝色线条表示静脉、白色线条表示神经,从而更好地揭示机体的解剖学本质;等等。[12]
科学史家在研究摄影技术应用的历史时也发现,虽然摄影技术出现之初迅速引起科学家们的广泛兴趣,也出现了一些使用摄影作品的科学画册,但这种热情很快冷却,更多的科学家仍然倾向于继续采用绘画来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莎拉·德·瑞克(Sarah de Rijcke)关于19世纪神经解剖学图像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873年,在摄影技术发明30多年后,第一本包含有照片的神经解剖学图集,朱勒·伯纳德·路易斯(Jules Bernard Luys)的《中枢神经摄影图集》才出版,此后摄影在神经解剖学中的应用仍然相当少见。《中枢神经摄影图集》是作者此前《对大脑系统结构、功能和疾病的研究》一书的修订和补充,其中最大的改变是照片的使用。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了在这本图集使用照片的真正目的:“在这本书(指《对大脑系统结构、功能和疾病的研究》)出版后,我看到有些知名人士(对他们我完全发自内心地给予敬重)对我当初精心制作的表达了我对神经中枢的理解的绘图产生了怀疑,而且听说他们还怀疑这些绘图是否的的确确真实地反映了我所看到的,甚至怀疑我是否以我自己的双眼亲自看到过,或者怀疑我这个极度专注的作者的过度想象是否影响到了我之所见。”“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把我自己完全清除,通过用光线的作用来替代我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既客观又可信的关于我第一部作品中的插图的解剖学细节图像,以此来有效回应对我第一部作品的批评。”[13]通过使用照相机,路易斯成功地证明了此前科学行为的合法性。但是有趣的是,作者为了充分阐释照片不太清晰的解剖学内涵,所有的照片都在下一页配上了一幅说明性的版画。
莎拉·德·瑞克还研究了显微摄影领域的领军人物圣地亚哥·拉蒙·卡哈(Santiago Ramony Cajal)作为狂热的业余摄影家,为什么更倾向于使用绘画而不是他所独创的显微照片。在一本关于神经组织摄影的专著中,卡哈提到只有当神经组织切片非常平整而且非常薄(1-10微米之间)的情况下,照片的效果才能和较好的绘图的效果相提并论。但是当使用较厚的组织学切片的时候,神经解剖学家通过显微镜观察时就不得不频繁地变换焦距,不得不对大量的不同光平面进行整合。而照片不可能表达多个焦平面中观察到的重要细节,同时隐去那些不重要的细节。而绘画却可以“像地图一样刻意指明穿越陌生地带的道路……大脑的特征能够通过颜色或交叉影线的综合运用来得到突显,而其他无关信息则通过阴影淡化或者省略消失在背景中……这对于摄影来说是极端困难的。”[14]
恩斯特·海克尔认为,插图不仅是对所看到的事物观察的结果,也应该是对事物的解释。摄影“时间统一、空间连续”的特征决定了摄影用于科学概念和规律表达的功能缺失,这是造成19世纪摄影技术发明之后,科学家仍然倾向于继续采用绘画来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绘画可以通过选择、忽略、分离、组合、强化、淡化、色彩运用甚至加注文字等手段,描绘出同类对象的一般特征,因而相对于摄影而言,在表达科学概念和规律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六 结论
图像对事物的观察和记录功能往往是文字所不能代替的。图像要用于科学研究中的观察和记录,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光学一致性。从写实绘画到摄影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光学一致性的历史。当时的人们认为,将主观因素排除于“绘画”过程而以自然过程来取代,是提高光学一致性的重要途径。对于摄影技术而言,主观因素被最大限度地排除,“绘画”过程完全通过自然过程来实现,使得其光学一致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摄影被认为是自然物体描绘它们自己的过程,而不需要艺术家的画笔的帮助,因此可以杜绝画家将自己的愿望、预期、概括、审美等强加于图像。摄影因而受到19世纪科学家的高度信赖,并被广泛运用于制作各种科学摄影集,“让自然为其自身说话”成为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的新科学客观性的口号。
但在后来,科学史家及相关的研究者们发现,摄影“时间统一、空间连续”的特征决定了摄影用于科学概念和规律表达的功能缺失。这是造成19世纪摄影技术发明之后,许多科学家仍然倾向于继续采用绘画来表达他们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而绘画可以通过选择、忽略、分离、组合、强化、淡化、色彩运用甚至加注文字等手段来描绘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因而在表达科学概念和规律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在科学史家对摄影技术史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他们自身对摄影图片以视觉方式所表达的对象“客观性”的这些认识的变化,其实与科学哲学中著名的“观察渗透理论”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意,都是对观察陈述的客观性的新认识。只不过,在对摄影技术的利用中,因为更多不依赖于人的技术手段得以发展的缘故,而使这种传统中被设想的客观性的假象更加隐蔽而已。
不过,在现实中,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是很顽固的,再加上对于新的技术手段的崇拜,在当代还出现了对于所谓图像时代的到来的片面认识、欢呼和追捧。从科学界对图像的利用,到现代化教育中对视觉图像手段的过分热衷,再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有图有真相”这样的看法的信奉,恰恰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的实例。因而,重温摄影技术史中所体现的人们对于基于“光学一致性”而带来的客观性的信念及其在后来的变化,依然是有着重要的启发性意义的。
[1]Svetlana Alpers.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43.
[2]John Galloway.Seeing the invisible:photography in science[J].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1992,42(4):330.
[3]李文芳.世界摄影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4]Lorraine Daston,Peter Galison.The image of objectivity[J].Representations,1992(40):81.
[5]转引自 Sarah de Rijcke.Light tries the expert eye:the introduction of photography in nineteenth-century macroscopic neuroanatom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2008,17(3):349.
[6]Luc Pauwels.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visual 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 in knowledge building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s.Luc Pauwels(ed.).Visual cultures of science: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 in knowledge building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M].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6:7.
[7]Olaf Breidbach.Representation of the microcosm:yhe claim for objectivity in 19th century scientific microphotograph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2002,35(2):232 -233.
[8]David Van Reybrouck.Imaging and imagining the Neanderthal:the role of technical drawings in archaeology[J].Antiquity,1998,72(275):59.
[9]Elizabeth A.Kessler.Resolving the nebulae:the science and art of representing M51[J].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2007,38(2):485 -488.
[10]Bernike Pasveer.Representing or mediating: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X -ray images in medicine.Luc Pauwels(ed.).Visual cultures of science: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 in knowledge building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M].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6:57.
[11]Raz Chen - Morris.From emblems to diagrams:Kepler’s new pictorial language of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M].Renaissance Quarterly,2009:57 -62.
[12]Ann Thomas.Beauty of another order:photography in science[M].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24.
[13]转引自 Sarah de Rijcke.Light tries the expert eye:the introduction of photography in nineteenth-century macroscopic neuroanatom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2008,17(3):356 -357.
[14]Sarah de Rijcke.Light tries the expert eye:the introduction of photography in nineteenth-century macroscopic neuroanatomy[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2008,17(3):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