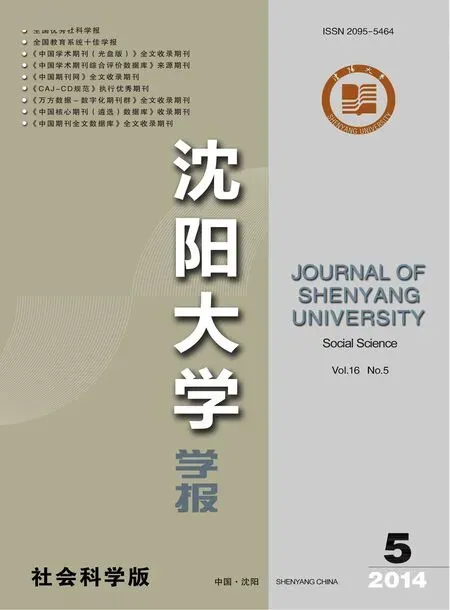民间情结中的帝王记忆
——辽西蒙古贞民间传说与康熙
齐 海 英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民间情结中的帝王记忆
——辽西蒙古贞民间传说与康熙
齐 海 英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关注并探讨了辽西蒙古贞民间存在的大量关于康熙皇帝私访当地的传说。论证这些传说并非是在客观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康熙,而是借助想象化、民间化的康熙形象寄托和传达广大民众渴慕明君、纾困解难、知恩图报、崇佛向善等生存情结。认为蒙古贞民间传说因康熙这一形象符号的介入而获得更好的传承效果。
蒙古贞; 民间传说; 康熙; 民间情结
一、 康熙与蒙古贞及蒙古贞民间传说
满族统治集团在入关之前便与蒙古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沟通与交往。仅以婚姻来看,就可看出双方交往的密切程度。“从太祖努尔哈赤起,经太宗、世祖共3朝,都实行了皇帝聘蒙古族后妃与满洲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大臣的双向通婚的交换形式。太祖纳蒙古族后妃1人,公主下嫁蒙古王公3人;太宗纳蒙古族后妃7人,公主下嫁蒙古王公12人;世祖纳蒙古族后妃5人,公主下嫁蒙古王公1人。圣祖、世宗、高宗3朝,开始实行了满洲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单向通婚形式,中止了皇帝纳蒙古族后妃的通婚。圣祖公主7人下嫁蒙古王公,世宗公主3人下嫁蒙古王公,高宗公主3人下嫁蒙古王公,……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百年上下满蒙贵族通婚习俗发展时期,上行下效,在满族臣民中满蒙通婚结亲成为广泛实行的婚俗。”[1]
满族在入关之前,与蒙古族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明朝,这使双方很自然地结成了利益攸关的同盟关系。满族入关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满族与蒙古族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产生矛盾是必不可免的。此时清朝统治集团需要运用更为有效的策略去调和与蒙古族的关系,以达到笼络蒙古族,巩固自己统治根基的目的。康熙称帝时期正是确立中央集权统治的最关键时期,因而与蒙古族的关系尤其成为关乎统治根基的重要问题。康熙在此方面有很多的作为和建树,经他的努力,满蒙关系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从他的三次东巡便可看到。康熙十年(1671)经直隶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出山海关,再经兴城、北镇、黑山等地抵盛京(沈阳),又经铁岭等地至吉林境而返,是为第一次东巡。第二次东巡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大体沿袭第一次路线,只是此次由盛京向北行程更远,抵达现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第三次东巡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此次东巡路线不同于前两次,走的是北线,经密云,出古北口,越长城,出口外,再经承德奔蒙古族地区,经翁牛特、敖汉、奈曼、科尔沁,再转南,途经拖而惠、乌楚滚,后又转向吉林,远达松花江流域,然后由吉林回盛京,经南线返北京。此次东巡途经更多蒙古族聚集地区,可以看出康熙笼络安抚蒙古族的用心。
蒙古贞地区(辽宁阜蒙县)有数量众多的关于康熙东巡私访的民间传说。笔者曾对已出版的,和自身近期民间采风获得的蒙古贞民间传说作过统计,关于康熙私访蒙古贞的民间传说不下几十篇,而且民间还有未被发现的遗存传说。
然而从现有康熙东巡的历史遗存资料来看,康熙东巡关乎蒙古贞的记载鲜见,这自然让人们对康熙是否曾亲历蒙古贞存有疑问。但蒙古贞民间既然有众多的关于康熙私访的传说,不能是空穴来风,人们基本可以认定康熙东巡曾到过蒙古贞。此结论也有历史的支撑依据:日本人园田一龟著《清朝皇帝东巡の研究》(大和书院,1944)中提及康熙东巡曾到于喇嘛寺(今阜新阜蒙县于寺镇)。同时还看到,有关历史资料岁记载的三次东巡驻跸地中的北镇、黑山等地与蒙古贞西南部接壤,奈曼、科尔沁等地与蒙古贞北部接壤,这是造成康熙能够私访蒙古贞的客观地理条件。但如曾多次亲历为何鲜见记载?疑问依然存在。《清帝东巡》一书中对康熙帝第三次东巡驻跸地问题有如下的解说:“而第三次东巡,因取道蒙古,驻跸处所达五六十处,即途中就用去五六十天,跨越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往返行程数千里。沿途驻跸处所除一些较大州县外,较小的偏远去处,特别是蒙古族牧区今已不可考。”[2]此解说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上述所存疑问。
由此可见,康熙东巡曾亲临蒙古贞南、北部一些地区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史实。
二、 民间情结与康熙
在传统观念中,“历史”与“传说”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概念。“历史”要力求还原化的真实,所叙人与事能够为不同的史料所证明。而“传说”则无需他者的证明,不仅如此,不见经传的虚构恰恰是它的特权。
虽然传说不是史学家所首肯的历史,但它却是民众历史意识与观念的形象化、真实化的反映。“按照历史人类学的观点,重要的不是历史叙述的对象,更是史料建构的过程。对同一宗事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关键在于哪一套历史叙述成为主流,强势的声音怎样压抑了其他声音。传说实际上是民间群体通过自己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地方历史,却被正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家们拒之于历史的门外。问题并不在于传说运用了夸张、虚构,是‘文学’的,而是传说提供了现实生活必要的历史记忆,这才是最重要的。”[3]传说是口传的历史,先民对于本族群历史的记忆以及现实所引发的一些生存愿望等都成为民间传说虚构性、文学性话语真实的内在蕴涵,换言之,即表现了一种意义层面上的真实,民间传说所口传的历史亦可称之为“意义的历史”,也即是民众话语所蕴涵带有民间立场的,“集体无意识”化的历史观念。
清代曾先后有六位帝王东巡,但到过蒙古贞地域的或许只有康熙帝一人。康熙皇帝是在清朝强盛过程中起到重大历史贡献的帝王,同时他在广大民众中也有较好的口碑。清朝及康熙帝在历史上与异族的东蒙有着密切的,诸如婚姻、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联,因此,蒙古贞地区便存留下了大量关于康熙帝的民间记忆与印象。这种记忆与印象或许也以一定的客观史实为基础,但此些许的史实却在蒙古贞民间场域中获得了想象化、理想化和现实化的发酵,形成了极富民间口传化之虚构、传奇色彩的叙事形态。这些民间口传叙事的接受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借此还原一个史实化的帝王形象,而最主要的是体味和解读蕴涵于其中的,与蒙古贞地区广大民众生存密切相关的历史观念与情结等。基于此认识和考虑,下面试图从“意义历史”角度对蒙古贞地区流传的康熙传说作探讨和分析。
1.渴慕明君情结与康熙
民众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模式与理想模式。对于中国古代民众而言,明君情结、清官情结与豪侠情结编织出了他们心目之中憧憬与渴盼的理想社会与生存境界。何谓“明君情结”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生逢圣明君主当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明君可遇不可求,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史,称得起明君的帝王寥寥可数,明君出现的概率实在是太低。正因如此,民众对明君的期盼与渴求便更强烈。康熙在清朝十二帝中可以算是一位较为圣明的君主,创立了一些值得颂扬的历史业绩,在后世民众心目中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便挥发成了民众口头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说。
蒙古贞民间传说中出现的康熙几乎全为“微服私访”者形象。而历史上所记载的康熙东巡每次都是随从众多,队伍庞大,场面神圣威严。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康熙在漫漫行程中偶有去官方形式化的考察民情之举,但此举即便存在,也为偶然个例。因为康熙本人便不赞成“微服私访”。据《清圣祖实录》卷271载: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庚申,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朕尝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据此可知,有关康熙及其他帝王微服私访的传说大多出于民众的想象性口头创造,是对圣明及亲民等帝王理想人格的追慕与呼唤!蒙古贞流传的关于康熙传说也不例外。蒙古贞民间流传着一个《王大山的传说》[4]142,叙述的是康熙把女儿嫁给蒙古贞王子为妻,不想在出嫁的路上,一夜之间掉光了头发,她无颜见王子,便吞金而死。陪嫁的宫女冒充公主与王子成亲。后来康熙下旨命公主回京城省亲,假公主不敢回京城,便写信推脱说有些蒙古贞人想造反,自己帮助王子平息后再回去省亲。康熙看到信,不明真相,便决定到蒙古贞私访,一来看女儿,二来体察民情。于是第二天康熙就扮做道人,带了一个武艺高强的随从,各自骑着毛驴去了蒙古贞。在蒙古贞,通过与路遇的一个庄稼汉的开怀闲聊,了解了蒙古贞地区的民心、民情。
此故事情节中已将康熙完全民间化了,其所为、所言与真实的帝王角色相去甚远,但这种身份与社会角色的想象化变易却存在着真实的情感基础——民众心目中的“明君亲民”情结。
2.纾困解难情结与康熙
在过去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天灾人祸等造就了广大民众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广大民众为了生存,罹受了太多的坎坷、困苦和艰难。这种生存困境很多时候依靠民众自身的努力或抗争是很难获得改变或解脱的,于是,广大民众便幻想出现神奇的人物或力量,施展超现实的威力为他们化解或消除生存的困境和苦难,他们渴盼“纾困解难”者的出现,他们在这种“情结”中获得了艰难前行的生存勇气。
辽西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古代大凌河流域水量充沛、低山丘陵植被覆盖率高,具有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辽金以来,随着历代统治者对大凌河流域掠夺性垦殖的加剧,遂使这里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伴随着滥伐林木、毁林开荒与超量放牧,大凌河流域的草甸被破坏,水位继续下降。辽西蒙古贞属于内陆地区,干旱程度相对要严重一些。此不利的自然条件对于农牧兼具的蒙古贞民众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对“水”及其他自然生存条件的渴求与珍视成为蒙古贞民众心之所系的重要问题。这样,在蒙古贞便出现了很多与“水”相关的民间传说,康熙在此类传说中常常担当起了“纾困解难”者的角色。
《乌乐吉图宝力格的传说》[5]40叙述康熙从热河经朝阳,微服私访到蒙古贞石门子(现阜蒙县七家子乡境内),三伏天里口渴难耐,却难寻滴水。康熙情急恼怒之下,举起龙头拐杖狠狠地朝干涸的河套戳去,意想不到的是,随着龙头拐杖的提起,从戳出的沙洞里“咕嘟、咕嘟”地喷涌出泉水来,而且这泉水越涌越旺,顺河道蔓延开去。康熙应村民之请,为此泉取名为“乌乐吉图宝力格”(汉语为“吉祥泉”)。此泉无论天多旱,地多干,从不干涸,造福于当地民众。另一则民间传说《淌泉子的由来》[5]130也与前则传说相似,叙述康熙皇帝在蒙古贞骆驼山麓以马棒戳地戳出山泉而解救民众受干旱之苦的神奇故事。
康熙“纾困解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笔者近期在蒙古贞采风时采录到一则传说,叙述康熙私访到阜蒙县大五家子,看到一面山坡上百姓在深秋的早晨收割庄稼,庄稼已结了厚厚的寒冷的霜花,穿得破烂的父老乡亲收割庄稼时双手冻得发麻,不时地跺脚搓手。康熙见此场景,顿生怜悯之心,不禁脱口说道:“从今以后,此地再也不会下霜了。”结果,这面山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下过霜。
类似的传说在蒙古贞还有不少,在想象化虚构化的民间话语中,康熙游走于蒙古贞的山乡僻壤,成为解除民瘼,关心民生的“救世主”形象。
3.知恩图报情结与康熙
西汉刘向在《说苑·复恩》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报恩的历史典故和故事,以印证“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的命题,“知恩图报”说便源出于此。
“知恩图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沉淀凝聚成全民族共同信奉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尤其在普通民众层面,更成为待人处世,营造和谐、友善人际关系的道德规约和准则。
在蒙古贞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知恩图报”也是一个常在的主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恩报情结在神采飞扬的口传叙事情境中获得代代传承。康熙的形象也出现在此类口传叙事情境中,成为寄托蒙古贞民众恩报之情结意绪的符号意象。
《康熙与穷朋友》[4]34中扮算命先生私访的康熙想借宿于员外家,遭拒。为难之时,员外家长工将康熙领至破败的家中住宿,不仅如此,长工还让媳妇把家中仅有的打鸣的公鸡杀了,又打来好酒,尽他们所能,热情地款待了康熙,感激之下,康熙与长工结拜为兄弟。临别时,康熙将自己的住址写在纸条上,送给长工,邀他去京城家里串门儿。几年后,长工想起京城大哥,去京城寻找,才知这大哥是康熙皇帝。康熙留长工兄弟在宫中住了三个月。三个月后,当他回到自家时,惊呆了:破败的房子被漂亮的大瓦房取代,院里车马齐备,煞是气派。听媳妇介绍,才知这一切是皇帝大哥所为。再如《良官营子》[4]138叙述了蒙古贞一位村妇以猪耳朵和粘面做的“凉馍馍”招待康熙,令康熙感动,后来康熙应村妇之请,为村庄修桥报恩的故事。
知恩图报类传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恰恰在于民间存在着许多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的现象。广大民众以此类知恩图报的传说表达着对友善、良心的呼唤。蒙古贞一些知恩图报类传说中的报恩者是康熙等帝王形象,这和平民与平民之间的恩怨相报纠葛似有一些不同的意蕴,“知恩图报”情结中似乎还含有借助某种势力(康熙等帝王便是这种“势力”的象征符号),改变自身窘迫生存境遇的发迹情结,但这也无可厚非,向往与追求更优越的物质生存条件是人们正当的权利,况且父老乡亲所憧憬的只是温饱无虞的平淡生活。
4.崇佛向善情结与康熙
蒙古贞地区历史地与佛教(藏传黄教)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元朝时期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又称黄教,就已传入阜新地区。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大力扶持蒙古贞地区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佛教的思想和观念在蒙古贞地区可谓深入人心,成为与蒙古族民众生存密切相关的“崇佛”情结。到清朝末年,阜新全境有喇嘛庙360座,仅清朝皇帝康熙和道光亲题匾额的寺庙就有4处,康熙题匾的为瑞应寺(佛寺)、佑安寺(于喇嘛寺),道光题匾的为普安寺(海棠山)和吉庆寺(塔子沟)。其中瑞应寺(蒙语称葛根苏木,汉译佛寺),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诏拨国帑扩建,于1704年竣工,康熙帝亲书牌匾额“瑞应寺”,是阜新地区,乃至东部蒙古地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在辽西蒙古贞流传着很多关于瑞应寺及佑安寺的传说,而其中大多与康熙皇帝有关。如关于瑞应寺由来,据整理出版和笔者近期田野采风获得的民间故事传说,便有多种口传版本:康熙为报宝乐喇嘛救命之恩而建寺说;康熙寻父报恩建寺说;康熙寻金龙(金香)玉玺报恩建寺说;天鹅衔石选址建寺说;瑞鹰衔泥佛选址建寺说,等等。神奇的建寺传说,不一而足。这些关于建寺由来的传说中的主角大多是康熙皇帝,这既是对清王朝扶持蒙古贞佛教活动的民间化传播,也是借帝王之声名以壮藏传佛教之神圣。
不仅一些佛寺的由来与康熙皇帝有关,而且一些佛教观念的民间传承也因康熙的想象化在场而添神奇感。《双眼井的传说》[4]103叙述康熙私访瑞应寺时,将活佛献上的金碗圣水连同被风吹落的两粒柏树籽泼于柏树下,然后扬长而去。后活佛派小喇嘛追赶康熙等人,探问究竟。小喇嘛回来告诉活佛,康熙嘱咐找到两粒柏树籽,会有好处。活佛在树下细心寻找柏树籽,未见。又派人在树下挖了七七四十九天,未见树籽,却挖出了喷涌的一眼泉水,水中又现二蛟龙。活佛又派人急追康熙皇帝,未果。后得知,康熙离开瑞应寺路过蒙古贞王府时将一条幅交给王爷,命他五十天后交给瑞应寺来的人。活佛派小喇嘛从王府取回条幅,上书:“佛门从此行慈善,双眼井水医百病。”于是活佛派人将泉眼砌成大井,留两个井口,取名“双眼井”,方圆几百里的百姓谁生了病,喝上一口井水,马上就好。
在此则传说中,佛教所主张的,并已内化为民众生存情结的悲悯众生、护生救苦的慈善思想,因康熙形象的介入,获得了更形象,更具感染力的民间传播效果。
三、 结 语
蒙古贞民间传说中出现的康熙形象是想象化、虚构化的,与历史上真实的康熙皇帝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民间传说存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民间传说也是一种历史,是民间情绪与情结所支配和建构的历史,这种口述着的活态历史从表达的内在意义角度说,更是原生态的,可能更贴近历史的真相。在蒙古贞民间传说中,康熙皇帝因其较高的民众威望度和与东蒙之间的诸多关联,成为民众口头叙事经常念及的主角形象,但如果从这些民间传说的深层意蕴角度看,康熙皇帝的形象只是寄托和表现民众情结意绪的文化符号,民众借助于此极富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使飞扬在自己口头的口传叙事获得更强的可信度和社会传播力。
[1] 乌丙安. 论中国北方各民族的通婚习俗[J]. 民间文学论坛, 1994(3):9-18,58.
[2] 王佩环. 清帝东巡[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19.
[3] 万建中. 民间文学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81.
[4] 陈旗.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阜新市卷[M].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阜新市卷编委会, 1989:142-144,34-35,138-139,103-104.
[5] 柳绍才. 蒙古贞民间故事[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40-41,130.
【责任编辑田懋秀】
MemoryAboutEmperorinFolkEmotion——Some Folk Legends and Emperor Kangxi in Mengguzhen Region in West of Liaoning Province
QiHaiying
(College of Culture and Media,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1, China)
There are lots of folk legends about Emperor Kangxi got a private tour in Mengguzhen—the Mongolian region of the west part of Liaoning Province.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legends don’t restore a real Emperor Kangxi objectively, but with the help of imagination and plebification, convey some survival emotions of the public desire to have a wise emperor, who can resolve difficulties, be kindness and worship Buddha and so on. These folk legends of Mengguzhen get a better inheritance effect because of Emperor Kangxi’s image symbol.
Mengguzhen; folklore; Emperor Kangxi; folk emotions
2014-04-13
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2DMZ011)。
齐海英(1963-),男,辽宁阜新人,沈阳大学副教授。
2095-5464(2014)05-0699-05
I 276.3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