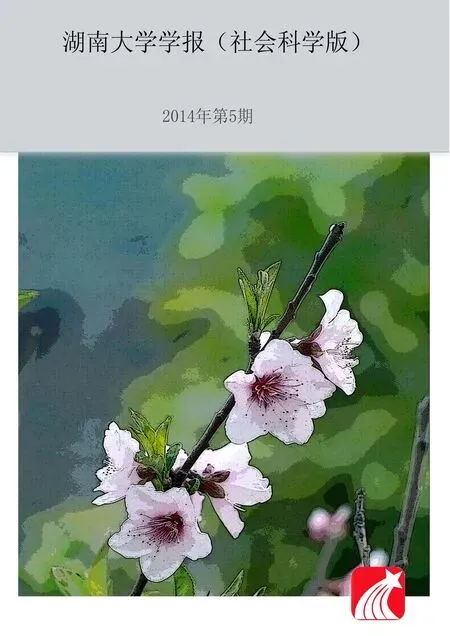论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论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
薛 泉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明代前期,散文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尊宋倾向,它与诗歌领域的宗唐倾向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当时复古文学的主流。这种倾向以经世致用为本,且主要聚焦于对欧阳修、苏轼、曾巩等人散文的推崇上。当然,尊宋倾向也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与流弊。无论如何,这一倾向对后来的唐宋派及其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明前期特定的政治环境、帝王之偏好、科举取士,以及文化渊源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促成了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正确把握这一倾向,有助于全面、客观体认明代文学及其发展轨迹。
尊宋倾向;政治环境;科举取士;文化渊源
一 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概观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称:“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何止明诗复古,明文亦然。可以说,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论者多侧重诗歌,又集中指向“宗唐抑宋”,而对复古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关注不够。正确把握这一倾向,对全面、客观认识明代文学及其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明前期散文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尊宋倾向,它与诗歌领域的宗唐倾向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当时复古文学的主流。明初,不少人尊崇宋文,主要是着眼宗经师古,旨在明道致用。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论文就露出这种倾向。其《苏平仲文集序》有曰:
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若文公之变化傀伟,文忠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
宋氏认为,秦汉以降,宋代散文成就为最,而苏轼、欧阳修、曾巩之文又为其翘楚。这一论断的得出,有其前提条件,那就是以载道、经世为本。其《白云稿序》云:“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这里的“道”,主要指儒家之道。《文原》即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非专指乎辞翰之文”。道学气息甚是浓郁。他推崇欧、苏之文,还因其近古、实用。《张侍讲翠屏集序》谓:“周、秦以前,固无庸议,下此唯汉为近古。”之后,一代不如一代,“至唐,韩愈氏始斥而返之”,故言“韩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汉之文也。”韩愈之文固然不错,但不能用于当世。至宋代欧阳修才开始弘扬、效法它,真正以之服务于政治。故宋濂又推论道:“欧阳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汉之文也。”原来,宋濂称许的欧、苏之文,自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宋代文章,而是秦汉古文之延续。尽管如此,客观上还是流露出一定的宗宋倾向。宋濂所尊崇的苏、欧等人之文,乃风格雄迈奔放、汪洋傀伟的醇雅之作,意在恢复古道,扭转其在《苏平仲文集序》所谓的“近世道漓气弱,文之不振已甚”之弊。其尊宋是以宗经明道为前提的,与韩、欧等古文家“文以明道”的观点,颇为一致。不过,他也意识到文体的时代差异性,《苏平仲文集序》即云:“古今之势不同,山川风气亦异,为文何异此。”因而,步趋如一地模仿古人,显然不现实,故师古文辞不必求似,师其意不师其辞方为上。否则,就会泥于古,此即其《答章秀才论诗书》所谓的“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不管怎样,宋濂已将散文复古对象溯至秦汉,可视为七子“文必秦汉”之先驱。朱右为文亦有以唐宋为宗的倾向。《文统》曰:“二氏(司马迁、班固)之文,遂足为后世之准程也。魏晋日流委靡,唐韩愈上窥姚姒,驰骋马班,本经参史,制为文章,追配古作。宋欧阳修又起而继之,文统于是乎有在其间。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轼,亦皆远追秦汉,羽翼韩、欧。”朱右尊宗宋文,因其能继承秦汉文统,《秦汉文衡序》云:“文莫古于《六经》,莫备于《史》、《汉》。《六经》蔑以尚矣,《史》、《汉》之文,庸非后世之准衡也。”为此,他还专门编纂唐宋文选本,以为文章典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白云稿》提要称:“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中,宋占其六,足见其宗宋意识之浓郁。宋濂的学生方孝孺,也以宗经明道为旨。其《览以德、用中二友和东坡喜雨之作》曰:“文章由来关政教,道德何曾问古今。”论文道学气浓烈不言而喻。由此出发,其论文反对宗唐抑宋,表现出宗宋的一面。《与赵伯钦》认为,“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尽过乎唐”,然“考道德之会通而揆其实”,则“宋为上”。宋文之中,他又颇重苏轼之文,《苏太史文集序》称:“苏子之于文,犹李白之于诗也,皆至于神者也。”在他看来,庄子、李白、苏轼的诗文皆非有意为之,故能达到出神入化之境,这主要是从艺术视角肯定三人之作。若按方氏《读朱子感兴诗》“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之论调,庄、李、苏三人之作当在否定之列,而此文却大加推许。可见,其论文又表现出一定的通脱性。正如论者所云:“这除了说明宗经明道之说不足以概括其文学的本质外,也可以看出方孝孺文学批评的灵活之处,当他不做道学语时,便能说出一些颇有价值的议论来。”[1](P50)
降及永乐、成化年间,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文人,尊宋倾向益趋鲜明,以至视欧阳修、曾巩等人的散文为创作圭臬。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即云:“杨(士奇)尚法,源出欧阳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杨士奇《东里全集》提要亦谓:其文“平正纡馀”,深得欧文之“仿佛”。“三杨”宗法欧、曾等人之文,心仪的是其可以鸣太平盛世的功能。正如董其昌《重刻王文庄公集序》所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所谓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鸣太平盛世与明道是密切相关的。杨士奇为胡俨《颐庵文选》所作序称:
文非深于道不行,道非深于经不明。古之圣人以道为体,故出言为经,而经者载道以植教也。周衰,圣人之教不行,文学之士各离经立说以为高。汉兴,文辞如司马子长、相如、班孟坚之徒,虽其雄材宏议,驰骋变化,往往不当于经。当是时,独董仲舒治经术,其言庶几发明圣人之道。至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曾子固,力于文词,能反求诸经,概得圣人之旨,遂为学者所宗。
韩、欧、曾之文所以“为学者所宗”,因其“能反求诸经,概得圣人之旨”,与宋濂之见略同。“三杨”师法韩、欧、曾,主要着眼“圣人之道”的发明,而不全以朝代先后为限,即“三杨”在尊宋的同时,也不废学唐。客观言之,“三杨”尊宋,师法欧、苏,较宋濂更注重其纪太平之盛(详后);其文风舂容详赡,和平典雅。
至成化、弘治间,李东阳等人对“三杨”台阁体褒扬有加。李东阳《呆斋刘先生集序》即称:“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实主文柄。乡郡之彦,每以属诸先生。文贞之文,亦所自择,世服其精。”其论文亦尚台阁体,如《倪文僖公集序》谓倪谦:“盖公之雄才绝识,学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达,卓然馆阁之体,非岩栖穴处者所能到也。”其论文亦与“三杨”一样,崇尚欧、苏。《春雨堂稿序》云:“韩、欧之文,亦可谓至矣。”《蜀山苏公祠堂记》亦云:“公之文章气节,天下莫不尊之。”李东阳之尊宋,也主要以实用为本,《叶文庄公集序》云:
夫欧之学,苏文忠公谓其学者,皆知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敢谏为忠,盖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
可见,李东阳所以尊欧、苏之文,欣赏的是其“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敢谏为忠”的政治功能。另外,李东阳同时代的人,也不乏学宋者。如:吴宽“平生学宗苏氏”[2](P1493),陆釴“后则专尚太白、六一间”[3](P38),王鏊文章“早学于苏”、“有唐宋遗风”[2](P1493)。
平心而论,明初至永乐、成化间,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主要以经世致用为本,道学气较浓。就推崇对象而言,主要聚焦于欧、苏、曾之文,反响甚大。正如黄佐《翰林记》卷十九《文体三变》所云:“国初,刘基、宋溓在馆阁,文字以韩、柳、欧、苏为宗准……永乐中,杨士奇独宗欧阳修,而气焰或不及,一时翕然从之。”
至明中叶,台阁体散文尊宋末流所造成的弊端,日渐暴露。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即批评道:“为欧文者,未得其纡馀,而先陷于缓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覼缕。”后来的四库馆臣斥责道:“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2](P1730)另外,明初以来,散文领域因长期以宋为宗,以致形成“操觚之士久奉宋为正朔,几不识汉、唐以前为何物”[4](P659)的局面。王国维曾有言:“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5](P70)一种文体如此,一种文风何尝不这样。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是以正徳、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2](P1730),他们倡言“文必秦汉”,意在改革文风,告诉时人,中国古代散文除宋文之外,尚有大量优秀先秦、两汉古文可继承、学习。至此,明代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一度步入低谷。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受共同经济基础、社会政治、时代背景等因素之影响,整个文学领域往往会产生共同的时代精神或主体旋律,各种文学样式、文学倾向自然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朝着历史既定的总方向发展。散文领域的宗宋倾向与诗坛上的尊唐倾向,皆为当时文学领域共同的时代精神或主体旋律的组成部分,它们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方所涉及的领域。故而,当时文坛上宗崇出现了三种基本倾向。其一,就某一人而言,宗唐与尊宋集于一身。客观地说,诗大抵以唐人为宗,文多尊宋。崔铣《胡氏集序》即谓杨士奇“诗法唐,文法欧。”其二,就散文领域而言,亦不同程度地受到宗唐倾向之浸润,宋濂、“三杨”之散文宗崇韩愈的一面,即是明证。宋濂、“三杨”散文尊宋,而不废学唐,虽可从宗经明道层面得到解释,但若再能从宗唐与尊宋两种倾向相互渗透的角度予以补充,答案似更圆满。不过,这种师法观是以文尊诗卑为前提的。杨士奇曾有言:“诗小技,不足为也。”[6](P4132)其三,诗坛以唐为宗的同时,也有反对的呼声。方孝孺论诗贵古而不贱今,其《观乐生诗集序》即称:“以古为高,以今为卑,随人为轻重,徇时为毁誉,不亦大惑矣乎!”他论诗取消古今尊卑的界限,只要便于“明道立政”、“发挥道德”,宗唐、尊宋皆可。故他多次强调尊宋的必要性,并对时人盲目宗唐提出批评,《谈诗》即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瞿佑编辑《鼓吹续音》更是宣称:“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7](P19)当然,这仅是主流诗学下的一股潜流,未能掀起多大波澜。
当然,也不容否认,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杨慎《文字之衰》称:“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持论虽显偏激,亦不无道理。既然“操觚之士久奉宋为正朔”,自然就难免以宋人之是为是。此举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为文抄录宋人策论,以牺牲散文的可读性、艺术性为代价,实不足取。
尽管如此,尊宋倾向对后来的唐宋派及其文学理论的形成,还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唐宋派文人为反对“文必秦汉”,倡导学习唐、宋散文,进而以宗法欧、曾为其法宝。《明史·文苑一》称:“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的确如此,王慎中《寄道原弟书八》即云:“学马迁莫如欧,学班固莫如曾。”唐顺之《答皇甫百泉郎中》云:“追思向日请教于兄,诗必唐,文必秦与汉云云者,则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为何语矣。”他对自已当年诗必唐、文必秦汉的倾向甚为后悔。李清馥《参政王遵岩先生慎中》亦云:“慎中学博才俊,自视亦高,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南丰。唐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王慎中、唐顺之皆为唐宋派的中坚,其言行当颇具代表性。
二 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的成因
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是由特定的时代政治环境、帝王的偏好、科举取士以及历史文化渊源等社会文化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促成的。揆其端绪,约略有如下数端。
其一,与当时特定的时代政治环境不可分。推翻元蒙统治后,为稳固统治,明代最高统治者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大肆杀戮异己;一方面又迫切需要恢复为被破坏的儒家伦理秩序。《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载,早在吴元年(1367),朱元璋即对臣下云:“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而“行教化”、“美习俗”,当务之急是“复衣冠如唐制”。同书卷三十又载,太祖元年,“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不仅如此,明太祖还直接倡导文章要明世务,美教化。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载:“(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与詹同论文章,上曰:‘古人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务。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忠义感激。近世文士,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为适应明初统治之需要,宋濂等一批开国文人承担起了以诗文创作“行教化”、“美习俗”之大任,大力提倡文道合一、宗经师古。以明经载道著称的欧、苏、曾之文,恰好能适应这一要求,自然易就成为其倡导与师法的选择对象。
燕王朱棣夺得帝位后,为巩固其统治,对不依附己的旧臣大开杀戒,无情打击,朝廷上下形成一片恐怖气氛。大臣动辄获罪,轻者杖脊,重者遭戮。方孝孺就因不愿为其撰写登基文而遭杀身之祸。杨士奇两次入狱,杨溥、黄淮曾度过十年大狱生活,若非成祖驾崩,其牢狱生涯或许依旧。杨荣虽无牢狱之灾,但不会不从同僚的不幸遭遇中吸取教训,调整处世方式。特别是方孝孺被杀,对明代士人震惊极大。李贽《续藏书》卷五就称:“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正直反遭屠戮,忠义难容于天下,士人不得不反思、调整个体行为,有人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格。为文趋向问题,当然也在其关注范畴之内。那位名不正言不顺的永乐大帝,迫切需要臣下为其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以弥补内心缺憾。据《明史·胡广传》载,胡广曾向成祖“献《圣孝瑞应颂》”,成祖“缀为佛曲,令宫中歌舞之。”基于此,台阁文人为文不约而同地趋向于歌颂功德与阐发圣人之道。苏、欧、曾等人的一些文章,在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自然容易成为他们借鉴的样本。
仁、宣之世,政治环境有所好转,一度紧张的君臣关系暂时得以改善;明代社会也进入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时期。《明史·杨士奇传》云:
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
此言虽有溢美之嫌,但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时局的好转的事实,恐怕不是明成祖时能有的。这客观上为歌舞昇平的台阁体散文创作提供了温床。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论贞观、开元文学时就说,“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而为治世之音”,流露出将文章与世运密切相连的意识,即太平盛世要有太平盛世时代的文章,他们崇尚欧、苏等人的散文,即与此有关。如果说明成祖时台阁文人歌功颂德多是出于封建淫威下的明哲保身,那么此时则是多源自于内心。明仁宗刚登基,就释放了身陷囹圄的杨溥、黄淮等人,委以重任,并“赐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8](P413)遭受如此的礼遇,又置身于王朝上升期,他们怎会不感激涕零,怎能不以歌颂昇平、润色伟业为己任!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即云:
仰惟国家列圣相承,图惟治化,以贻永久,吾辈忝与侍从,涵濡深恩,盖有年矣。今圣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职朔望休沐,聿循旧章。予数人者得遂其所适,是皆皇上之赐,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
杨溥亦持论如此。杨荣《登正阳门楼倡和诗序》载:“少保公(杨溥)曰:‘然吾辈叨逢盛时,得从容登览胜概,以舒其心目,可无纪述乎?’公遂赋二诗,予与诸公和之。诗成之明日,侍郎公又属予为之引,遂僣书此于首,俾观者知诗之作所以颂上之大功也。”这就表明,“三杨”等台阁文人已将歌颂昇平、“纪太平之盛”视为诗文重要的功能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欧、苏等人一些散文,在宗经明道的同时,可以鸣太平盛世,“三杨”等台阁文人以之为鉴,师法其文,自不待言。在他们的倡导下,天下文士“一时翕然从之”。
弘治时,宪宗朝紧张的君臣关系,又有所好转,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台阁体文人为之感动不已,以为是仁、宣之治重现,于是沿袭“三杨”之习,文法欧、曾,以鸣太平盛世。其《书赐游西苑诗卷后》即称:
君臣之际,亦重矣。盖必有天冠地履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后上下交而德业成。……我朝自皇祖以来,优礼儒硕,远超近代。凡一豫一游、一张一弛、严而泰、和而节者,皆于此卷见之。宣德之治,固有得于体貌之隆,信任之笃者,诚亿万世所当法也。东阳以后进菲才,备员左右,不能赞明良喜起之化,于此亦窃有感焉。
其二,帝王之偏好,起到不可替代的舆论导向作用。尊宋倾向所以集中指向欧阳修等人,与明仁宗的嗜好与提倡不无关系。仁宗位居东宫时,杨士奇就引导他研习江右先儒欧阳修文,使其逐渐热衷于欧文。杨士奇《滁州重建醉翁亭记》载:
我仁宗皇帝在东宫,览公奏议,爱重不已,有生不同时之叹,尝举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欧阳文忠有雍容醇厚气象。”既尽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
黄佐《翰林记》卷十九《评论诗文》记载此事更详赡:
(仁宗)尝与士奇言:欧阳文忠公之文,雍容醇厚,气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时之叹。且爱其谏疏明白切直,数举以厉君臣,遂命校正重刻以传,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时不过三、四人而止。恒谓士奇曰: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欧阳真无忝矣。
明仁宗称道“欧阳真无忝矣”,一是因欧阳修勤于政事,忠君爱民,可为臣子效法的对象;二是因欧文风格“明白切直”,又“有雍容醇厚气象”,足可以鸣太平盛世。故他下令校正重新刊刻,赐予知文朝臣各一部,以广其传。仁宗之子宣宗朱瞻基也很偏好欧文,其所作文辞不失典正和平气度。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朝廷上下逐渐形成文宗欧阳氏之风。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即谓:“于时文章尚宋庐陵氏,号‘台阁体’,举世向风。”黄佐《翰林记》亦言:“馆阁文字,自士奇以来,皆宗欧阳体。” 其三,科举取士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科考是明政府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文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特设科举,规定了科举取士的权威性与重要性。洪武十七年(1384),始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成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之废而不用。有明一代科考题目,专取于四书、五经,应试者须代圣人立言,行文“略仿宋经义”[6](P1693)。如此,宗经载道、经明行修的宋代古文为应试者所青睐,自然在情理之中。于是,以科举名世的欧、苏之文,长于论辩,特别是其明经载道、博通古今的策论,更是成为士子模仿的典范。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卷四曾指出:
近时俗学,皆尚三苏文字,不复知有唐文矣,况秦、汉乎?故不拘大小试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苏子口气。”或曰:“深得苏轼家法。”即中式矣!
此论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也大体上反映出当时的基本情形。衡文者以苏文为则,愈加刺激了求仕者对苏文的热衷。为应付科考,博取功名,他们为文以苏氏之文为准的,专心研习八股文。王世贞《苏长公外纪》亦云:“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而雌黄之类于公,不能无少挫,然使天下而有能尽四氏集者,万不得一也。”杨慎所谓举业者“抄宋人之策论”,亦有为此而发之意。如此以来,士子们的尊宋倾向非常浓烈,对宋代以前的优秀古文,或无暇顾及,或视而不见,以至形成不复知有唐文,无论秦汉的格局。就连《文选》这样著名选本,当时也少人知晓。田艺蘅《诗谈初编》云:“昔人言‘《文选》烂,秀才半’,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可作本领耳。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嗟乎!今之能学举子业者,即谓之秀才。至于《文选》,则生平未始闻知其名,况能烂其书,析其义乎?虽谓之蠢才,可也。”也就是说,科举取士在很大程度造成了明代散文与汉、唐散文的断层。从这一角度而言,七子派“文必先秦、两汉”的理论价值,愈发凸出。
其四,明人散文尊宋,有其历史渊源。至迟在南宋末年,已有人有意识地推尊本朝人诗文。刘克庄《本朝五七言绝句》引道:“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毋庸置疑,宋代古文水平整体高于唐代,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出自宋,便是力证。金代苏学北上,文学受苏轼的影响较大。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就称:“中州隔绝,困于戎马,多有得于苏轼之遗。”元好问《跋赵秉文和拟韦苏州》也称:“百年来,诗人多学坡、谷。”更有甚者,当时还出现了“仿苏才翁太甚”、或学黄庭坚而“模影剽窜”的情形。为扭转局面以及反对浮艳文风,贞祐南渡以后文坛虽然揭起了一股宗唐风气,但尊宋意识并未泯灭。如赵秉文主张师法韩愈、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儒之文,雷渊“诗杂坡谷,喜新奇”[9](P10)。元前期的文风,也多受苏、黄之影响。如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认为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轼之文,“皆以理为辞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为百世之师也”。刘因、王恽等人也主张师法宋文。元代中后期,宗唐与尊宋趋于合流,但尊宋一脉始终未绝。如苏天爵《题孟天暐拟古文后》有言:“三代以下,文之古者,莫韩、欧若也。”陈旅《元文类序》也称:“三代以降,惟汉、唐、宋之文为特盛。”当然,金元古文宗宋,多是以理学为观照视角。就整体而言,金、元人的尊宋,远没有宗唐势头强劲。一般而言,一种文学风气一旦形成,往往会延续一段时间。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就是此风续余与新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的产物。
这里还须特别指出,以上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明前期文坛上的尊宋倾向。
综上所述,明前期散文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尊宋倾向,与诗歌领域的宗唐倾向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当时复古文学的主流。这一倾向主要以经世致用为本,道学气较浓。就推崇对象而言,主要聚焦于欧、苏、曾之文。尊宋倾向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与流弊。无论如何,它对唐宋派及其文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影响深远。明前期特定的政治环境、帝王的偏好、科举取士,以及文化渊源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促成明前期散文领域的尊宋倾向。正确把握这一倾向,有助于全面、客观体认明代文学及其发展走向。
[1] 袁震宇, 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3] 李东阳. 李东阳集(第3卷)[M]. 长沙: 岳麓书社,1985.
[4] 张燮.书李献吉集后[A]. 明文海[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5]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6]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7] 周维德. 全明诗话[M]. 济南: 齐鲁书社,2005.
[8]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9] 刘祁. 归潜志[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On the Zunsong Tendency of the Prose Field in Early Ming Dynasty
XUE Qu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China)
In early Ming Dynasty, prose exist obvious zunsong tendency, with the poetry of zuntang orientation, working together to form the mainstream of Ming Dynasty ancient literature. This tendency is mainly served for politics, and mainly focused on Ou Yangxiu, Su Shi and Zeng Gong’s proses. Of course, the tendency to zunsong also showed a certain blindness and evils. The early Ming Dynasty specif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imperial preferenc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the source of culture and other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worship of song prose tendency. Really grasp this tendency, contribute to a comprehensive, objective recogni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Zunsong Tendenc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al origin
2013-11-10
薛 泉(1969—),男,山东莒南人, 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明文学与文化.
I106
A
1008—1763(2014)05—009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