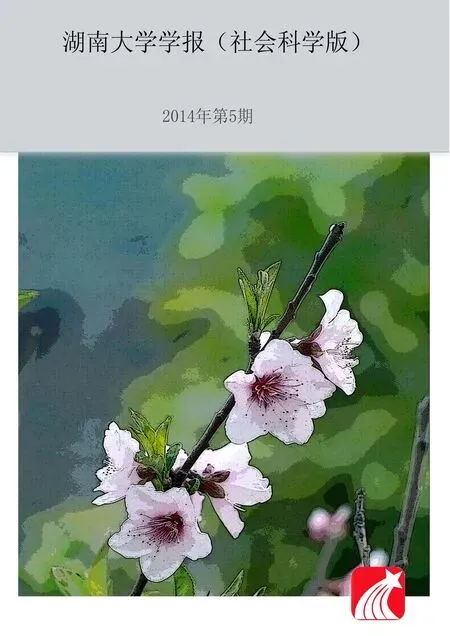从“整理国故”到“活的生命整体”
——略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李翔海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01)
从“整理国故”到“活的生命整体”
——略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李翔海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01)
从什么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之中是否还有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近代以来受到多方关注而又见仁见智的焦点问题。西化派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中西文化,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早就已经死亡的结论。文化保守主义者注重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坚心要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做见证,但也存在着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之组成部分的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论指明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明确肯定这一“文化生命整体”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从一个侧面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文化;整理国故;民族主体性;生命整体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中华文明不仅在器物与制度层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精神理念的层面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相对完备、思想特质颇为鲜明的民族文化系统,而且事实上成为传统东亚社会的主流思想,长期以来处于周边文化中的中心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古代中国文化还成为人类历史上与希腊、印度齐名的三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民族历史”阶段向“世界历史”阶段转进的过程中,随着西方列强用武力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在周边文化中的中心与主导地位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第一次面临到了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外来文化从器物到制度以至精神理念全幅层面的强烈冲击与严峻挑战。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社会与文化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面临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繁盛而衰微而复苏以致重新走向复兴的曲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从什么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之中是否还有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受到多方关注而又见仁见智的焦点问题。许多前辈与时贤均围绕这些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方克立教授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倡导和领导全国范围内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开始,现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就是其相关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先生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新进境。
一
与空间和时间构成了事物的基本存在方式相联系,民族性(即不同文化共同体在横向比较中亦即在空间向度中体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共同体的特质)和时代性(即与特定的发展演进阶段或过程亦即在时间向度中相联系的特征)一起共同构成了特定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且这种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处于自然的发展演进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无疑是有着原始的、内在的统一性的。但是,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以后,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所当具有的时代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这样,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本有的原始统一就仅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而处于后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就只能是走向分裂。换言之,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民族性就体现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非西方文化要想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就必须师法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伴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出现的是全球性的“西化”浪潮。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被迫走上了近现代化道路,从而在“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性张力。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正是由此各执一端,而成为直接的理论对立面。
西化派看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理论立场,就是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而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这在“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胡适教授那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在他看来:“我们的出发点只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77页。)因此,“我们承认各民族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第179页。)这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化都是走的同一条路,因而相互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大同小异”归根结底只是“迟速”、“先后”或曰发展程度的差异。这就在彻底抹煞了文化之民族性的同时,完全把各民族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主张“全盘西化”论最为彻底的陈序经教授则更为明确的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只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中国文化传统则只能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版。)。
应当说,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对于我们在一个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时代更为充分地了解、把握中国文化,特别是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比照之中更为清楚地见出中国哲学传统的自身不足之所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他们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对中华文化传统中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成分所施以的猛烈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廓清内涵空间之效。但是,西化派的内在局限也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由于西化派主要从时代性的维度来看待文化,中国文化传统被框限在“前现代”,成为归根结底已经不再对现实社会发生鲜活影响的“古董”。这在胡适的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胡适的眼中,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故”化,成为“死去”而没有自身生命力的“遗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对待身外之物那样,对之予以清理。惟其如此,要想“再造文明”,也就只有“全盘西化”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因此,“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1页。)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文化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进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就显然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二
如果说西化派最大的盲点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缺失,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则堪称鲜明地突出了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而可以看作是对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论述。这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集中体现。
其一是根本反对西化派专注于时代性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相关主张,着力突显了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对于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言,无论发生怎样的变革,都应当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如果一种文化变革是以丢弃文化的民族特质为前提的,那么,在经过了这种变革之后即使是实现了所谓的“现代化”,那也只能是事实上成为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因此,不同于西化派主张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明确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真正实现。为此必须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地吸纳外来文化。对此,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1年、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前期宣言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做了代表性的论述:“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
其二是针对一些西方汉学家以及中国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死亡”的观点,强调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有其强劲的生命活力。对此,发表于1958年,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先生共同撰写的、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后期宣言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做了代表性的论述。在现代新儒家看来,近百年来,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乃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逐渐洞开而引起的。此时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实来自对运入西方及在中国发现之中国文物之好奇心。例如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所发现之文物,所引起之所谓敦煌学之类。由此动机而研究中国美术考古,研究中国之西北地理,中国之边疆史,西域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以及辽金元史,研究古代金石甲骨之文字,以及中国之方言,中国文字与语言之特性等,数十年来中国及欧洲之汉学家,各有其不朽之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从中国文物所引起之好奇心,及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中国文物,以作研究材料之兴趣,并不是直接注目于中国这个活的民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精神之来源与发展之路向的。此种兴趣,与西方学者要考证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而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此诸文明之遗物之兴趣,在本质上并无分别”。而中国清学之方向,原是重文物材料之考证,直到民国,所谓新文化运动时整理国故之风,亦是以清代之治学方法为标准。由此,“中西学风,在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上,两相凑泊,而此类之汉学研究,即宛成为世界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之正宗。”(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页。)在这样的时代风潮的影响之下,“在许多西方人与中国人之心目中,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如斯宾格勒,即以中国文化到汉代已死。而中国五四运功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之学术文化,统一于‘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番,以便归档存案的。而百年来中国民主建国运动之着着失败,更似客观的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已经死亡。于是一切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7页。)
针对这种观点,现代新儒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在他们看来,西方汉学家与中国西化派以为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将中国文化与“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等而观之,“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的态度是完全错误因而应当彻底去除的。“我们亦不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医学家之解剖研究”。(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7页。)至于要问中国文化并非已经死亡的证据在哪里?这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就客观方面而言,像世界其他的一些民族文化一样,“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9页。)进而言之,“以文化历史之不断而论,只印度可与中国相比。但印度人以前—直冥心于宗教中之永恒世界,而缺历史之意识。故其文化历史虽长久,而不能真自觉其长久。中国则为文化历史长久,而又一向能自觉其长久之唯一的现存国家。”(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22页。)第二,就当下而言,以中国文化的现代传人自任的现代新儒家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依然“活着”的鲜活见证:“发表此文的我们,自知我们并未死亡。如果读者们是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你们亦没有死亡。如果我们同你们都是活的,而大家心目中同有中国文化,则中国文化便不能是死的。”(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7页。)中国文化进入近代以来虽然“正在生病”,但却不仅依然“活着”,而且有着强韧的内在生命力。
现代新儒家坚心要为中国文化依然“活着”做见证、着力突显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主张不仅对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而且对于在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华夏文化慧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的相关认识也有一个盲点,这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打成两橛,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偏狭的文化心态,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
如所周知,方克立教授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提出的“综合创新”论的响应者与探索者,“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方克立教授的热切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于如何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早在1988年,在提交新加坡“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首次提出“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参见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1990年,针对“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古今、中外文化之关系”的问题,方先生作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回答(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动态》1990年第3期。)。1996年,针对“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源’与‘流’之关系”的问题,方先生作出了“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的回答(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2006年,在致“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刘鄂培教授、朱汉民教授的信中,针对“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或三‘流’之关系”的问题,方先生首次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即“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在2010年回答《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记者提问时,方先生进一步对“马魂中体西用”论中“马魂”与“中体”的关系做出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的区分,深入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意义和关系中确实分别具有‘体’的优位性”的问题(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方克立教授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在在响应、阐释、深化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论的过程中提出。全面评析此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是从与本文主旨相关联的意义上,从一个侧面对其所关涉到的问题做出论述。方先生指出,所谓“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44页。)他强调指出,“我说的‘中学为体’,‘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已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47页。)这一论断中包含了认识中国文化的新进境。这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其一,明确肯定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由于在西化派看来,中国文化传统进入近现代就已经死亡,其相关努力是要通过输入西方现代文化而“再造文明”,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之间是横亘着历史性沟壑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内在的统一性。而由于现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僵固地持守夏夷之辨,在力图拒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亦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化归结为是中国文化的“歧出”,因而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也是打成两撅的。方先生的上述论断则鲜明地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共同构成了“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指出只有这样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这样的论断显然突破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藩篱,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新认识。
其二,明确肯定自古及今、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一论断明显是对西化派有关主张的拨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超越。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活着,但是由于他们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橛,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事实上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鲜活而充沛的表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明确肯定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了两者之间既是传承发展与变革转型的关系,又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生命精神。这就进一步畅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避免了由于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打成两橛而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难免窒塞不通的问题。
其三,既挺立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中,由于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挺立民族主体性与体现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关系成为一道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难题,不同思想流派往往在两者之间出现或倚重或偏忽的情况。“马魂中体西用”论则体现出了民族性与时代性并重的取向,既认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从而给中国文化以“体”的地位,又从时代性的高度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而为我所用。既突出了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方克立教授的上述工作可以看做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最新探索。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三星会聚”之地,这既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储备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如何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而谋求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是我们理当铭记的职责与使命。方先生相关论断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在“综合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可贵记录。
FromNationalCulturalHeritageSystemizationtoLivingVitalUnity——BriefViewoftheNewProgressonChineseCultureStudiesinRecentYears
LI Xiang-hai
(Marx's College of 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01)
How and from what perspective to regard Chinese culture, if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own inherent vitality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these have been focus issue concerned by many people since modern times. The Westernization regarde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y contemporaneity of culture, result the distin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summed up Chinese culture had already been dead. Cultural conservative insisted on the subjectivity of nat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hoped to witness the modern vit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y denied that Chinese modern culture is a part of the whole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Ma Hun Zhong Ti Xi Yong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are unified culture vital unity, and affirmed this unity still has living vitality today. This theory represented the New Progress on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ra.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ization; National Subjectivity; Vital Unity
2013-11-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56)
李翔海(1962—),男,湖北荆门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哲学、儒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B25
A
1008—1763(2014)05—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