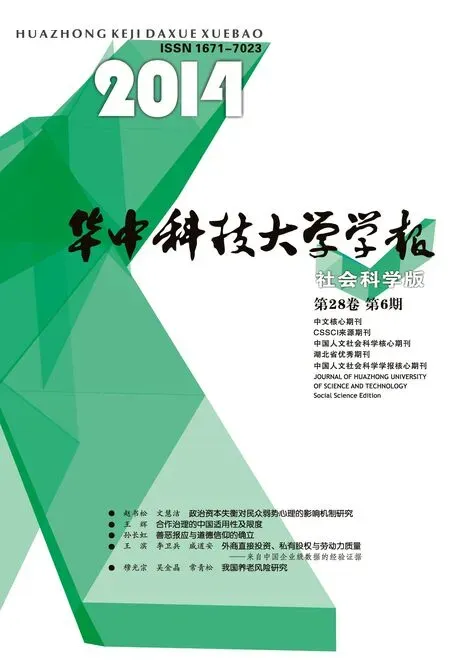重建的悖论:1920-1930年代知识女性职业价值观探析
马方方,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民元以降,致力于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知识分子,在猛烈抨击性别伦理秩序的同时,为女性就业大造舆论氛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她们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日益凸显,随即引发知识界的各种纷纭论见。20 世纪20 至30年代是论辩的集中呈现时期,在这论辩的过程中,知识女性的职业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解构传统的女性特征,以不出闺阁、专司家务的旧女性标志传统,而以有职业有独立意志的新女性象征未来,以此鼓励女性外出就业,这是主流的价值认同;二是对传统女性特征的复制和强化,强调女性在从业的同时对家庭的重要职责。两种倾向存在内在理路的根本分歧。笔者从社会调查入手,对悖论进行解释与分析。从知识女性自身的经验体认,我们鉴别辨认出她们对职业问题的基本价值认知,并希望以此进一步探视社会知识界对两性问题的理念与想象。
一、悖论的呈现:社会调查
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经济上的依附有悖于现代人格的更新与重塑,是女性应该摒弃的劣质,否则就不足以成为促进民族新生的力量。但是,仔细梳理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所标榜的原则与其实际行为并非完全合拍:尽管在不遗余力地呼唤女性就业,并视之为女性探求个体生命体验乃至国家民族解放的必然之势,但在现实选择中仍显现出女性走出家庭时无法摒除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固着。对高呼抹煞性别意义,强调个人独立价值的知识女性来说,这种矛盾无疑是一大反挫。
1.主流认识:女性就业乃必然之势
有学者称,“妇女解放的职业运动对20 世纪社会组织的影响不亚于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妇女的获得职业是女权运动的初步成功”[1]2-3,妇女职业问题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关注的焦点。启蒙思想家在晚清国力不振的探讨中,延伸出女子经济独立的策略性论述,并引发时人对女性就业的关注。民国以后,此论日盛。“五四新文化运动”揭橥女性独立自主人格理想的讨论,提出经济问题是妇女解放第一步的主张,并以参与社会的公共事业作为提高女性地位和扩张女权的最佳方式①以《妇女杂志》为例,在章锡琛和周建人等主持时期(从7 卷1 号到11 卷8 号),对妇女职业问题的探讨相对比较集中。据统计,这一时期该杂志发表的与“妇女职业”有关的文章数量,平均每期达到6.1 篇。在1924年第10 卷第6 号,以“职业问题号”为主题,对妇女职业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参见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湾大学文学院1996年,第154 页。。关于女子职业问题的种种论述,便是在这种时代思潮流变中进行的。
这种氛围也主导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职业价值观。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社会学者曾致力于广泛的社会调查,其中不乏关于对女性从业态度的调查。这些调查反映出知识女性对就业的普遍认同。梁议生在20 世纪20年代末对燕京大学女生的调查显示,60 名未婚女生中赞成婚后继续工作的有45 人,占75%,标举的理由包括“助社会进步”、“经济可以独立”、“提高妇女地位”、“有机会发展才识”等[2]65-66。周叔昭对燕大女生的另一份调查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他调查的45 名女生当中有43 人都认为“已婚妇除教养子女外应听其自由从事家外业务”,可见“‘女子主内’的思想在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中免不了要崩溃了!”[3]375-376陈利兰对全国200 名大中学校的女学生进行了调查,表示愿意婚后仍在社会上做事的共159人,占总数的79.5%。”[4]244
对于已婚女性是否应该从业这一点,男性知识分子的态度并无轩轾。楼兆馗对在京大学生的调查显示:118 名未婚男生当中,除4 人标明妻子无须有职业以及2 人认为应从于家事外,其他都认为女子应有职业[5]73-74。甘南引用10 个月的时间对全国各学校、机关的青年男性知识分子进行了调查,840 人当中,赞成妻子服务社会的共595 人,占全部人数的71%[6]170。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作为新观念的倡导者,他们的价值取向代表了社会的潮流,因而特别受到重视。这些调查证明,妇女参与经济生产或职业活动,乃是社会经济体制变迁无法遏阻的必然趋势。职业使女性在家庭之外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模塑新的角色,而且唤起了女性的自主意识,使她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萌生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要求,并通过职业生活改变自身的地位,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开启妇女解放之路。职是之故,摆脱传统束缚,在社会中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既是男性知识分子对新女性形象的一种理想化的构想,也成为大多数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对自身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划。
2.理想与现实:婚姻的现实障碍
尽管女性就业因代表着时代之方向而成为主流,但仔细梳理这些调查,不难发现婚姻在知识分子的女性就业观念中所彰显的意义。在葛家栋1928年对燕大男生的调查中,132 名未婚男生明确表示愿意配偶在婚后服务社会的有44 人,理家的36 人,服务社会兼理家的35 人,也就是说,尽管男生普遍认为女性外出就业已属必然,但至少53%的男生仍视理家为女性不可推卸的职责。在42 名已婚男生中,妻子受过教育的占总数的62.3%,但从对方职业来看,除2 人仍为在读学生外,理家的有34 人,占总数的81%(2 人未填)[7]42。楼兆馗对在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未婚男生绝大部分都认为女子应有职业,但在已婚的54 名男生中,妻子有15人无职业,18 人从于家事。由此可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未婚者多是怀着一种合乎时势的理想,但已婚者的事实却是婚后妻子不再工作[5]73-74、89。
社会学者甘南引的调查范围很广,既包括在读学生,也有各学校机关的工作人员。调查显示,在840 名男性当中,已婚、已订未婚、未订未婚这三种婚姻状态的男性赞成妻子服务社会的人数比例依次是59%、77%、82%。这实则代表了不同境遇下的不同感受,未婚的通常充满了理想憧憬,而已婚的则因家庭生活的现实不愿或认为妻子不能服务于社会[6]170。陈利兰对200 名女性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这三种婚姻状态的女性希望自己服务社会的比例分别是88%、83%、76%。对比甘南引的调查,女生对婚后就业的认同程度似更高于男生,但事实上,不管这些女生是否已婚,愿意出外做事的前提多是认为在理家和尽母职之外,或是没有小孩的情况下。陈利兰分析,“由此可知现在的女子心理,一面顾家事,一面愿服务社会。”[4]244。也就是说,知识女性是希望到社会上工作的,即使在结婚以后,但是要在尽其母职的基础之上。
这些调查当然并非巨细无遗的“全息”记录,包含了调查者个人选择的因素,但多角度、多侧面的调查统计,毕竟为我们探视更广阔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理奠定了基础,也为女性知识分子职业价值观念及行为的展现埋下深厚的根基,在知识分子的观念世界中,“就业”已然成为一个历史性的用以区分新旧女性的根本标准,但从理想规范的字面意义转移至实际生活的层面,即可体会女性的许多“现代”观念并非与传统简单地断裂,一腔豪情或踌躇满志,一旦诉诸婚姻家庭的现实,都难掩其内心的无奈与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回转,标示着知识女性对这一问题出现认知上的悖论。
二、悖论产生的语境: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虽然个人社会价值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观念在加强,但这些事实都没有从深层次上改变女性在家庭内部生活中的传统地位。职业对中国女性来说,便具备了成就与摒弃的双重意义:一方面,职业成为女性人生的转捩点,女性的社会参与,不仅证明她们能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同时对家庭、社会、经济也有贡献,以此突破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偏见,证明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另一方面,传统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加上女性自身内心深处对妻母职责的情感认同,又使她们时刻面临着社会与自我的双重道德拷问。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新女性无法完美地遂其所愿,“母职”因而再一次凸显。
1.职业女性的现实困境
女性从事职业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产物。处于分化和艰难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及其有限的容纳力,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对女性可提供的职位更是有限;加上社会习俗的影响,在求职和工作过程中,各部门歧视、限用女性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对职业女性的严峻考验。其中,最主要的困扰则是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女性的分身乏术是绝大多数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结婚生育对职业女性的影响是基于女性的自然心理和生理特征所无法解决的矛盾。任何一种文化都赋予女性作为母亲的根本性的职责,女性作为母亲的地位只可能历史性的再循环再延续,而不可能衰退消失[8]261。各种报刊杂志常出现关于女性职业问题的讨论,投书的女性一般为知识分子。通过她们的叙述可以发现,读过书的女性,更容易不满一般舆论加诸职业的负面意涵,但就业所引发的现实困惑以及人格冲突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①1924年《妇女杂志》进行过一次有关从业女性的征文活动,这次征文遍及各个行业,如教师、护士、女职员、女记者、女工等;三十年代初天津《大公报》的蒋逸霄女士也专门对天津各业女性进行了调查访谈。城市女性的职业生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中可进一步探析职业女性的职业价值观念。。女作家杨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我真是个矛盾百出的人:一方面那么爱孩子;一方面又厌烦孩子带给自己事业的阻力,因而讨厌孩子。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呵,请你长出两只强大温存的翅膀来吧!一只给你的孩子,使他们感到母亲的温暖;另一只献给祖国和人民。”[9]43当年曾为女高师四君子之一的程俊英,回想大学毕业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不禁感慨:“我每一个白天都是在课堂上和抚养五个孩子的家事中度过,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埋头批改学生的国文作业中溜走。”[10]68女作家谢冰莹当年也说过,婚姻与职业的矛盾“是女人感到最大、最深,而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她哀叹:“是女人自己不努力,不争气,不上进,还是家庭与社会的两种锁链把她们捆得太紧,使她们永远解脱不了,永远不能活动?”[11]20
美国社会学家J.罗斯·埃什尔曼说:“文化因素的力量在我们理解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社会化时占有压倒的优势。”[12]113他的这一论断为我们分析职业女性角色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指引了方向。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和潜在意识。在传统社会,理想的婚姻角色是与明确的性别分工连接在一起的,“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观念和与此相关的角色规范被广泛接受和赞许[13]182-183。民国以降,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职场,但却并未真正弱化儒家性别文化规定的关于男女角色分工的传统意义,女性以家事为首要之务在人们心目中视为理所当然。女性一旦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如果因职业而不能全力照料家庭,作为“女”人与生俱来的品性也会使她们产生自责与负罪感,于是这种强调女性以家庭为主要生活空间的定势思维,便自然主导多数妇女的行为规则。“前几年曾有好多女子,因为生理、心理都不容许她职业与家务兼顾,而视结婚为畏途,情愿过黯淡的独身生活;近年的倾向,则女子大都愿意牺牲职业而去实现家庭的美梦。”[14]19
2.解决路径:职业与家庭的调和
1927年《新女性》杂志曾针对“为妻为母与尽力社会及学问是否并行不悖”这个问题,以《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为题,向社会各界征稿。投稿的不乏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如费云鹤、周作人、孙伏园、沈雁冰、蔡孑民等,在22篇征文中,多数人的意见是这两种情形可以并行不悖。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启蒙知识分子曾积极倡导女子外出就业的意义,但并不意味他们认为女性应放弃家庭的职责[15]。
不少知识女性也以此自期。作为最早接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女性之一,北大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受西方早期女权主义运动影响至深。陈衡哲曾发表过多篇文章阐述她的女性立场,呼吁男女平等以及女性要追求人格的完善。但她对女性问题的阐述,更多是放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意义上来思考与解释。1927年,她发表了著名的《妇女与职业》一文,全面阐述了“女性应职业与家庭兼顾”的观点。陈衡哲认为,女子应该“同时发展天才和享乐人生”,一方面,她积极倡导女子教育,“使一般青年的女子,将来都可以有应付环境的能力,发展天才的机会和维持生命的职业”;另一方面,她强调“凡是靠了体力及智力所作的有目的和成绩的工作,都可以称为职业”,认为女子履行家庭职责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因此,衡量职业的标准并非报酬,家务是女子的职业,而且是已婚女子的基本职业:“假使一个女子在结婚后能把她的心思才力,都放在她的家庭里去,把整理家务,教育子女,作为她的终身事业”,那么,“即使她不直接地做生利的事业,她却不能不算是社会上的一个分利之人。她做的贡献虽比不上那少数出类拔萃的男子及女子,但至少总抵得过那大多数平庸无奇的男子对于社会的贡献了。”[16]60-72
著名女子社会活动家刘王立明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中国妇女运动》一书自序中她曾这样表达对丈夫刘湛恩先生的感激:“他不但知道男女在智力上是平等,并承认女子有她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在与男子同样的机会之下,能够创立伟业,服务人类。”正是丈夫的支持使自己得以有机会参加妇女运动。她曾创办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编辑女性刊物,成立女子生产合作社,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非常活跃,做到了“不负男女平等及职业解放的美名”。但她同时认为,女性从事职业并不意味着弱化家庭的责任,因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女性是家庭的柱石”,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攸关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妇女运动应避免空喊口号,“我们要返回我们的观念,重视已往的母职,认定已婚的女子最大的贡献是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国民”,另外,“职业有直接与间接的分别”,抚婴、治家要耗费女子许多精力,“这当然是一种间接的职业”。在刘王立明看来,结婚与职业并无必然冲突,因此女子兼负双重职责也是应有之义[17]4、127、142。
这种同“五四”反传统思潮大异其趣的思路显示出个性解放与现实环境互相牵制的矛盾与张力,也形成了职业与家庭之间并行不悖的一条弹性原则。在陈衡哲们的论述中,她们从家庭和社会的角度重新构建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为女性设计出一条融合“个性”与“女性”双重人格的发展道路,希望能在合乎时势与道德伦理之间取得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合理性。这样,知识分子高扬的职业目标的价值意义开始变得模糊,“职业”是扩展女性生存空间、重塑女性人格的重要资源,现在却面临价值的失落;“贤女淑德”本为告别传统而被大力鞭挞,现在反而彰显荣光。于是,知识女性关于职业的叙述与想象,一方面在文本中显现了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一方面却又在具体的语境中反观了传统。
不可否认,当时有少数杰出夫妇,夫妻两人都是社会精英,可成就职业女性双重角色兼顾的梦想,如社会学家任鸿隽与其妻陈衡哲,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与妻刘王立明,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杨堃与妻子中法大学教授张若明,语言学家赵元任与其医生太太杨步伟等。她们以自己特殊的经历建构起职业女性的理想生活,但多数男性知识分子,对妻子的职业,皆以能兼顾家庭为前提来看待,知识女性要处理好“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而且“女主内”的意识形式是建立在对女性平等独立的个体价值的否定之上,与现代价值观所宣扬的个人主义相矛盾,女性的家务劳动能得到多大程度的社会认同也是因人而异。正因为这样,陈衡哲们的呼吁显得乏力和有限。只是她们对女性职业问题的追问提示我们,从女性的自然/社会属性、家庭/社会角色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去关注职业女性的现实处境,当可为我们理解这种悖论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三、悖论的另一种解读:关注“主体”
妇女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培养和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人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18]89-90。以此而论,女性主体可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主选择生存空间,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从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来看,对女子就业将攸关个人是否能真正独立的确信使知识分子多以倡扬女子经济独立为目标,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寻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我主体感受是否被顾及?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往往让职业女性遭遇尴尬,作为已经觉醒的知识女性,冲突后的选择对“主体”而言是价值的找回还是失落?
仔细分析陈衡哲的女子职业价值观,似乎是从“个性”向“女性”的游移,然而这种游移其实却进一步彰显对女性本体的关怀。五四知识分子极力营造女性就业对其自身乃至民族国家意义的氛围,因此不乏一些女性顺时而动,一腔豪情壮志却未顾及自己的现实处境和感受。陈衡哲对此有冷静的分析,她认为职业的价值不在职业本身,而在于从事职业的态度,是否诚恳、快乐和觉得有意义。男女天赋各有不同,不能为邀声誉而从事违背天性的事业,要以自己内心的意愿而非社会的评价作为惟一指南,“‘做你所最愿做的,做你所最能做的’,是我对于一般女子的忠告”[16]60-72。关注女性“内心的意愿”是陈衡哲立论的基点。
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是热衷于社会生活的“新女性”,所以她很同情女性在社会上遭遇的种种束缚[19]。然而,在《新女性》杂志发起的“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的讨论中,与参与讨论的男性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学昭没有将社会需求放在第一位,而是更看重女性的主体意愿。她认为,“无论是为妻为母,还是攻究学问、改造社会,都不仅仅是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女性愿不愿意的问题:我们对于什么事情,不能以自己武断的主张,想到了为妻为母,便非个个女子都为妻为母不可,想到从事学问,便非个个都去从事学问不可,像驱赶一群鸡到埘里去的样子”,“这终究还是女子乐意与否的事”[15]35-39。“女性愿不愿意”是陈学昭关注的重心。
从这一点来看,冰心的态度也有关心女性“主体”的意义,她曾言,“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20]195。也就是说,冰心并不否认打倒怯懦依赖的“贤妻良母”,但不同意打倒能给丈夫孩子带来精神慰藉营造“爱”的家庭的“贤妻良母”。这一点和陈衡哲后来的解释也是一致的,陈衡哲认为绝大多数女子的健全生活,仍与家庭不能分开,但却与家庭的关系不同,“不曾解放的女子,只能为家庭的范围圈住,只能为她做一个奴才,而解放了的女子,却能跳出这个范围之外,又站到她的上面去,做一个指挥她的主人翁。”[21]12。这与胡适的以“自立”的精神补助“依赖”性质的“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22]。也就是说,“贤妻良母”这一形象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女性是否有“自立”的意识,是否能从对家庭的“依附”转向“主导”。
其实从“五四”启蒙思想家的论述来看,知识分子对女性“人”的价值的发掘,本是强调个人的“自立”精神。按照胡适对“自立”的解释,“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是“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都存一个‘自立’的心。”[22]作为“娜拉”形象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者,胡适对“娜拉”的诠释与期许,实际包括“救自己”与“负责任”两种层次,内对个人,外对社会,构成胡适对个人主义的理解。胡适藉娜拉的言行发出的呼吁,主要并非倡议大家“走”到家庭外并抛弃原有责任,而在于走出传统价值观,发展个人自觉与独立意识,因为他相信若未真正了解出走之意,只盲目跟随潮流,逃离家庭以摆脱束缚,不只未能解决问题,也将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负面结果[23]78。可惜的是,引入中国的“娜拉”,作为对“家庭”依附角色的背离,被赋予“社会”的独立责任,她们实践出走的激情,多胜过对个人主义真谛的理解及对现时处境的考虑。
胡适的解释为我们理解陈衡哲等知识女性的职业价值观提供进一步证明,关注女性,是要关注女性“主体”的感受。女性自我的确立,按照日本女权主义者水田宗子的观点,是女性先认识到自身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然后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形成“作为女性的人”的过程,即“女性—主体的人—作为女性的人”的过程[24]。但落到实处,很多女性对“我是人”的呐喊要求的是和男性平权的“人”的意义,而忽视了作为“女性的人”的存在。因此,倡扬职业固然代表着妇女解放的进路,这种意义自不待言,但在具体语境中,返回家庭也并非一定要贴上“旧思想”、“旧道德”的标签,对于妇女就业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应是妇女自己。正如有女性指出,“男子讨论女子问题,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点隔靴搔痒,必须女子自己去问自己,才能有切实的答案出来。”[25]如果女性认为职业能实现自己全部人生价值,她可以自觉自愿地履行职业角色,而如果认为家庭不仅是一个生存的空间,更是具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意义的空间,也可以倾力于妻母之职。由此来看,陈衡哲等知识女性的实践与言说,以其更深切关注女性的自我感受,而当具前瞻的意义。这与其说是一种悖论,毋宁说这种悖论是现代女性对启蒙导师他者构建的“定型化”的价值认同局限的思考与重建。
中国学者李小江曾言,“不仅不能做主人,而且不能做女人”[26]107,可谓对所谓“解放”的女子所面临尴尬的生动写照。如果一种角色规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如果一种行为模式是对人的自由的亵渎,那么这种规范和模式一定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类最高理想——个体的充分自由和价值的实现[27]186。笔者的研究表明,许多知识女性对“解放”的意义与感知并不具备必然的一致性,她们因“解放”而带来的焦虑和解决焦虑的方式,游离于时代主题之外,但却践履并诉说着自我生命更真实的体验。事实上不管是就业还是回家,如果能以女性主体的需要作为出发点,选择适合自我的理想路径,展示自我表达、自由抉择的女性意识,将会使我们跳出“出走—回归”这一截然对立的窠臼,置于具体的情境,不再执著于“男女平等”旗帜之下激昂的批判,多一些理解的同情,也许会让女性少一些身心异处割裂的痛苦,多一些自由呼吸的空间。
[1]张若:《已婚妇女的职业问题》,孙节译,载《家庭星期》1936年第17期。
[2]梁议生:《燕京大学60 女生之婚姻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周叔昭:《家庭问题的调查——与潘光旦先生的调查比较》,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陈利兰:《中国女子对于婚姻的态度之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楼兆馗:《婚姻调查》,载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葛家栋:《燕大男生对于婚姻态度之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田常晖、张峰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9]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10]郭汾阳:《女界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谢冰莹:《厨房与编辑室》,载《妇女月刊》1947年第4期。
[12](美)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潘允康、张文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
[13]王金玲:《女性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蔡慕晖:《职业与家务》,载《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7 号。
[15]《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编者按),载《新女性》1927年第2 卷第1期。
[16]陈衡哲:《妇女与职业》,载《现代评论》1927年第2周年纪念增刊。
[17]刘王立明:《快乐家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8]魏国英:《女性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陈学昭:《给男性》,载《新女性》1926年第12期。
[20]冰心:《我的母亲》,载《冰心全集》(3),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1]陈衡哲:《新生活与妇女解放》,载《妇女新生活月刊》1936年第6期。
[22]胡适:《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1918年第5 卷第3号。
[23]许慧琦:《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论述策略》,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2003年第10期。
[24](日)水田宗子著:《女性的自我与表现》(序),叶渭渠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5]张笑菱:《南洋漂泊的三年》,载《妇女杂志》1924年第6期。
[26]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以及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载邱仁宗、金一虹、王延光编:《中国妇女和女性主义思想》,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王周生:《关于性别的追问》,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