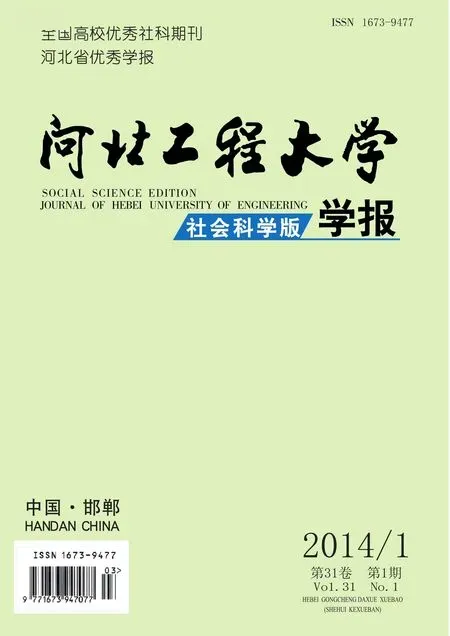检察官刑事拘留决定权之探索
胡滢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2000)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又称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遇有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所采取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1]
我国的刑事强制处分权主要集中于公安机关,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权力失衡,变革这样的局面成为必然。刑事拘留权作为其中涉及人身的较为严厉的一种措施,其决定权的归属应当综合司法实践、各个机关的职能以及权力制衡等因素,慎重考虑。
一、我国刑事拘留决定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事拘留决定权的现状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80条,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就人民检察院,在其直接侦查的案件中,对于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决定拘留。
(二)存在的问题
首先,刑事拘留属羁押性质的强制措施,对于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构成重大影响,其严厉程度仅次于逮捕,又被称为“非正式羁押”。然而,刑事拘留的审批机关是行政性公安机关,其审批程序也是行政性程序,其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与其程序上的保障不成正比。且我国公民在被适用刑事拘留后,获得救济的途径较少,无法要求事后审查或律师参与程序,其程序性辩护权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些都决定了刑事拘留的审批程序应当审慎而为,这是既是程序设计上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方面的要求。
其次,在我国,存在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配置过于集中,权力主体单一的严重现象,且公安机关通过相关的部门规章自我授权,变相扩大了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导致权力垄断现象严重,基本上排斥了其他国家机关在审前刑事强制处分中的权力。且由于警察权力垄断且决定程序的封闭性,缺乏客观公正的司法机构介入,为公民权利的侵害埋下了隐患。
最后,存在超范围问题、超期羁押的问题。超期羁押和超范围羁押的问题存在已久,有些案件在法定时间内无法收集充分的证据,办案人员基于治安管理压力而任意延长拘留期限、扩大拘留人员范围,归根结底都是公安机关权力过分集中所致。刑事拘留的申请主体、审批主体以及执行主体都是公安机关,即使申请、审批的层级不同,但在同一个机关的内部,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地审查。即便公安机关的审批人员能够做到客观公正,我们也不能将这样的需求寄希望于机构人员的自我克制。在制度的设计上即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实现权力的制衡,才是对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
二、关于司法令状制度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予以解决,其中主流的观点就是司法令状制度的引入。
(一)司法令状制度概述
所谓的令状主义,是在研究介绍国外刑事司法制度时对下面一种现象的归纳:在英美法系国家和现代的大陆法系国家,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或其他侦查人员)只有获得了法官签发的令状的许可,才有权力执行逮捕、搜查和扣押。[2]司法令状一般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
(1)司法令状的签发主体必须为中立的司法机关,这样的司法机关鉴于法官的独立、中立性地位而多设定为法官。即在侦查阶段,采取警察或检察官申请,法官决定的模式,没有法官的司法审查并决定,警察或检察官就不能执行行使强制处分。
(2)司法令状的签发必须基于“相当理由”的证据基础。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非基于相当理由,不得签发司法令状”,“相当理由”是司法令状签发的实质条件。而所谓的相当理由,没有统一的定论,有判决认为应依据具体的个案事实评估期相当性程度。[3]学者一般认为法院对“相当理由”的心证程度,比判决被告有罪“确定无疑”的程度低,但比“单纯怀疑”或“合理怀疑”的程度为高。
(3)令状的适用对象及范围必须具有特定性。强制措施的实施令状应写明其适用的具体人员、物品、场所范围以及执行人员、起止时限等,避免令状的执行主体拥有过大的裁量权,为其滥用权力提供可乘之机。[4]美国法院对令状特定性的解释是:令状的内容所达到的具体程度足以使执行令状的警察清楚他要搜查的地方和扣押的物品,即便是该警察事前并未接触过本案。[5]
(二)学者主张适用之理由
司法令状制度的适用,学者主要是从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和权力救济等几个方面来论述的:
1.权力制衡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若要保证权力的健康运行,除要求权力自身的节制外,最关键的在于权力之间的制衡。强制处分权的制衡就表现在只有法官能行使决定权,没有法官签发的司法令状,执行人员是不能实施强制措施的。当然,这样的制衡并不是单方面的,警察或检察官同样有制衡权,即没有执行人员的申请,法官不能主动签发司法令状。通过这样的制衡关系,警察或检察官与法官之间实现权力分配上的相互限制,最终保障被执行人的权益。
2.权力监督
司法令状的特定性为权力监督提供了可能。司法令状的内容要求写明其适用的具体情况,为执法人员的执行行为划定了界限,若存在超出司法令状所确定的范围,该执行行为即为违法。对于被执行人而言,司法令状的适用,使得他们对于被适用强制措施的原因、适用范围及自己享有的权利有较清晰的认识,也为权利救济提供了证据。概言之,作为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的依据,司法令状不仅能够帮助被执行人有效保全证据,而且有利于节制执法者的权力,防止权力被恣意滥用。
3、权利救济
就强制措施的实施者而言,令状本身就是法律授权的依据,是强制处分行为以及通过该行为所获得证据的形式合法性基础。即令状是执行者行为合法性的证据。而对于被执行者而言,针对执行人执行中存在的违法、侵权行为,可以依据令状申请法院进行事后审查。强制措施的令状及其申请材料可以反映强制措施的启动是否符合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要件,法官通过审查这些已有的书面材料和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并结合双方的控辩材料,可以判定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
三、检察机关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之正当性
刑事强制措施的令状制度是平衡国家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机制,它为二者之间的正面冲突增添了一道屏障。令状制度有助于监督、制约强制处分权的行使,为被干预者的权利救济提供依据,保障其免受无理强制措施的侵犯。
虽然司法令状制度在权力制衡和保障人权方面存在可借鉴之处,但最好的制度并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适合的。正如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玛什卡教授曾说的,“程序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移植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因此,在考虑移植某一外国规则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首先仔细考察在本国的制度背景中是否存在使此项外国规则有可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先决条件。”[6]因而主张将司法令状制度原封不动地引入我国,这是不切实际的。笔者主张由检察机关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
首先,就检察官的中立性问题而言,我国的检警关系与国外的检警关系不同。我国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相互之间互不隶属。具体而言,公安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而检察机关主要负责检察和提起公诉。虽然在某些情形下,检察机关会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主要是监督职能的行使,与国外由检察机关主导案件侦查的情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符合超然中立的决定机关的要求。
其次,从我国检察官的职能来看,我国的检察机关负担法律监督的职能,享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权。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监督活动的缺失,导致其监督权基本得不到行使,将刑事拘留的审批权交由检察机关来行使,有利于强化其监督职能。且检察机关的强制处分权的扩大与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并非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我国侦查阶段人权问题根本在于公安机关的权力过大。因此,将刑事拘留决定权交由检察机关来行使有利于制衡公安机关的权力,最终保障被执行人的权益。
再次,从法律传统的角度来看,英美法系的传统是并不信任检察官,而是充分信任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出:“任命品行良好的法官能够有效地阻止政府对个人的侵犯和压迫,它是确保稳定、公正执法的最佳手段,也是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必不可少的保障者。”[7]但在我国,司法并没有完全独立,且整体素质不高及司法腐败等问题存在,公众对法官的信任尚未建立,不具备社会威信基础,“在社会对法官抱有不信任的场合很难想象容许法官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合宪性审查。”欧洲人权法院解释《欧洲人权公约》认为判断官员中立性的三项具体标准:一是制度上独立于当事人和行政机关;二是程序上有义务对嫌疑人听审;三是实体上应充分考量有利于和不利于嫌疑人的各种因素。我国的检察官与法官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职业道德等,因此检察官在强制处分权的行使方面的操作可能与法官不遑多让。因此,将检察官中立性问题置于具体法律文化之中,结合当地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予以考量就会发现由检察官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是符合我国法律传统的。
最后,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实现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法官中立能够使得程序公正得到更好地体现,这也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司法要求法官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现实中难免受到各种观念影响。而司法令状是对已有证据的审查,若法官过早地接触相关案件的证据,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公正裁判的作出。
因此,依据我国的国情与法律实践,由检察院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具有可行性与正当性。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在刑事拘留决定权问题上,以司法令状制度为基础,对其进行适应我国国情的变革,将其决定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
有的学者忧虑检察官的部分行政性会导致其独立性上不如法官,其行政体系问题导致受上级影响的可能性大大提升,最终影响令状制度的适用目的,不利于对被执行人的权利保障。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国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公诉,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是否命令予以释放。”该权利公约中明确规定,若当事人认为其拘禁并不合法,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作为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当被执行人认为该执行行为存在违法,向法院提出审查申请可以作为事后救济的方法。
[1]谭世贵.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10.
[2]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21-131.
[3]Illionis V. Gates, 462 U.S.213(1983).
[4]杨雄.刑事强制措施中的令状制度研究——从美国法的角度切入[J].东疆学刊,2012(3):107-108.
[5]高峰.刑事侦查中的令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5.
[6][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
[7]林钰雄.检察官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