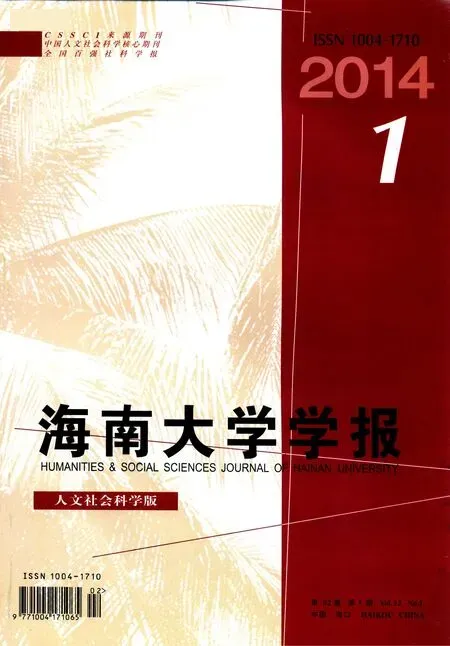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构
吴雪丽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文化寻根”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历史出场,一方面有以“文化反思”取代“伤痕”和“反思”文学的“政治反思”无法继续推进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也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作为作家群体中重要一支的“知青”作家远离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自我身份合法性的意义。“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因此绝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1]对于大多数具有“红卫兵”经历和“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经验的“寻根”作家来说,他们的写作也不可能是一种纯文学的诉求,其背后的文化政治逻辑和身份认同与建构都具有超越单纯的文学写作的意义。当“文革”成为被否定的历史,原来的评价机制和伦理结构瓦解,“知青”的社会角色本身已不再能提供道德评价的基础和理解自我的社会条件,寻找新的认同就成为这一写作群体和知识群体的现实问题,通过“寻根”,他们重构了“自我”的身份记忆和“群体”的身份认同。
一、知青记忆:乡土认同与游离
“我们是怎样成为现代的自己的?作为行动者,我们并不能通过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来呈现自我,而只能通过我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来表现我们自己。我们取舍事物的方式本身,决定了我们是谁。”[2]对于“寻根派”作家而言,他们是以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显影的,他们对待乡土世界的情感方式也表现出“寻根派”的群体记忆。如何确立“寻根”群体在80年代文坛上的身份,从他们的写作资源、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可以看到这一具有“知青”背景的乡土书写群体的精神姿态和身份记忆。
“寻根”作家几乎都有知青身份,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民间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和自身的生命体验,但他们从事写作时,已经离开乡村回到城市,“寻根”其实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的回望姿态,是一种源于“在地”的苦难、挣扎之后的文学表达。“寻根”作家大都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只是在生命的历程中被暂时抛出了既定的轨道,而在农村被流放的经历却成了他们以后从事文学写作的重要资源。从这样的视野看,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阿城等的文学书写其实都是以“他者”的目光对乡土的重新发现,这种“审视”、“发现”和“寻找”往往带有知识者的精英姿态和远离后的怀旧情怀。这和“五四”一代的乡土作家有根本的不同,鲁迅、许钦文、王鲁彦、蹇先艾们是来自乡土,作为乡土中国的叛子逆臣,作为现代都市的漂泊者、怀乡者、启蒙者去回望乡土,他们对都市文明的厌倦、对故土家园的深切怀想、对乡土蒙昧的深忧隐痛,都带有切身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个体生命经验。他们对乡土既怀念又痛恨的心态在五四时期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们是同时受乡土文明滋养和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一代人,因此,他们小说中的“乡土”和“寻根”小说中“乡土”也就承载了不同的意义和内涵。在“寻根”小说中,“乡土”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之地,是乡土中国的文化精华和文化劣根的所在地,是指向过去的文化原乡。但在“五四”作家那里,“乡土”是前现代沉滞、闭塞、愚昧的乡土,是传统中国的象征,是丞待被“启蒙”的乡土世界,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羁绊。
但“乡村”在有知青经历的“寻根派”作家的视野中又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不再是苦难和辛酸,而成为温情脉脉的乡村牧歌。清平湾流畅的河水、破老汉的信天游、放牛的日子、喂牛的夜晚在回忆的视野里,都弥漫着苦涩的温情。实际上,当史铁生告别贫瘠、荒凉的清平湾回到都市,对清平湾的记忆就成为一种在想象中的“怀旧”,怀旧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权力,“清平湾”的记忆成为史铁生个人生活中的一座纪念碑,依此他建立了“上山下乡”的人性记忆。面对乡土,史铁生没有现代的“启蒙”热望,而“乡土”反过来以它的淳朴和温爱重建了史铁生关于“知青生活”的个人记忆。“任何一种怀旧式的书写,都并非‘原画浮现’”,它“与其说是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3]。怀旧作为一种个人心灵的需求,它完成的不仅是在想象的空间中对自我灵魂的安放,同时,怀旧也是建构,那就是通过对过往生活的过滤掉苦难后的温情回忆,而完成对自我的“知青”经历的意义指认。因此,“寻根”小说对旧有岁月的追忆始终和个人记忆、历史的标识联系在一起,对于告别乡村回到城市的知青们而言,对“乡村”的温情书写,其实也是对自我的知青经历和知青身份的合法性的一种确认。当历史的反转证明了“知青”运动的无意义时,史铁生式的写作以对“乡村”的温情怀旧置换了对自我身份的深入反省,并有效地悬置了对知青“在地”的乡村经验的真实表达。
在“寻根”作家群体中,张承志也是重要的一个,在他的小说中,对“大地”、“人民”的体认是重要的叙事立场。对“人民”的认同,一方面彰显了“知青”来自“现代”都市的“他者”身份,另一方面对“乡村”和“人民”的认同也建构了他们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身份认同,其中暗含的民粹主义思想指明了自我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起点。自从19世纪中期出现的俄国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民粹主义思想传统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此后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人民”更是具有了独特的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特权话语。“人民”是民族解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力量,当任何个人一旦和“人民”产生冲突和矛盾,那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被国家意识形态放逐的对象。因此,当“伤痕”、“反思”文学的写作主体,也就是“右派”作家在被放逐后重新“归来”和知青作家在“上山下乡”后重新对历史发言时,“人民认同”就成为他们书写历史的一个基本基点,“由于‘人民话语’本身在现代中国所具有的无比神圣性和崇高而强烈的道义色彩,所以,无论是在他们‘受挫’之中,还是在‘受挫’之后,他们均都相当乐意地承认自己的人民认同。在‘新时期’以后,突出强调自己的人民认同,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所极力欢迎和表彰的。”[4]“知青作家”的人民认同在这样的逻辑上成为他们洗刷个人记忆,并把个人记忆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书写方式,“人民”话语所暗含的历史叙述的终极合法性,使知青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剥离了时代的荒谬和对“知青运动”的负面价值判断,从而获得了历史的体认。当张承志写下了“故乡,我的摇篮,我的爱情,我的母亲”(《黑骏马》)时,当他把白发额吉和索米亚指认为“草原母亲”时,他的“寻根”在“乡村——人民”的话语逻辑中,以“回到过去”的方式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并以“人民认同”重建了知青群体的身份皈依。
但在韩少功的“回望”视野中,“乡村”不再温暖美丽,“人民”也不再淳朴善良。韩少功笔下的“乡村”是怪诞的乡村,是遗落在历史深处的东方奇观。在《爸爸爸》中,谩骂、械斗、服毒、迁移成为族群的生存状态,原始的巫蛊横行、人神不分,鸡头寨成为一个乡村梦魇,是关于原初人类的生存寓言。“乡村”在韩少功的视野中延续的是自“五四”以来的启蒙情怀,他在“寻根”中发现的是“乡村”的沉滞、愚昧和“国民”的麻木、愚钝。对“乡村”和“原始初民”的文学想象,使韩少功这样的有过知青经历的“寻根”书写,成为对自我“知识精英”身份认同的追求。他带着对“楚文化”的期待而来,却发现了民族的“劣根性”,对“乡村”的怪诞和“民众”的顽劣的价值预设,使韩少功在“知青”和“精英”之间架起了一座“个体身份认同”的浮桥。他搁置了对曾经插队的“汨罗江”边真实的乡村书写,而是在隐喻的意义上重构了一个在现实中不存在的“鸡头寨”,寄予他“启蒙者”的文化热望。相对于史铁生、张承志对“土地”和“人民”的体认,韩少功以虚构意义上对“乡村”和“民众”的拒绝和批判,重建了他“启蒙者”的身份认同。
因此,在“寻根”小说中,“乡村”首先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写作资源出现的,“寻根派”对于“乡土”和“人民”的价值取向,也潜在地构建了他们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对自我的“乡村经验”的文学想象的不同,显示了“寻根派”自我认同的差异,“怀旧”、“认同”、“批判”、“启蒙”的不同姿态,映照的正是有知青经历的“寻根派”作家对曾经经历的生活和对自我定位的复杂性。
二、话语争夺:重获讲述权力
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作家主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和生活受挫,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在“新时期”他们成为“复出”和“归来”的一代,“50年代被‘放逐’的作家,在相当的时间里有一种‘弃民’的身份意识。”[5]194另一部分是“知青作家”,他们在“文革”时期经历了从“革命主体”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身份变化,在“新时期”身份的暧昧性使重建身份认同成为这一代写作者迫切的自我指认。这两代作家重要的差别在于:“‘复出’作家进入‘新时期’就意味着回归中心‘轨道’,回到‘目的地’,并获得‘文化英雄’的荣耀身份;而‘知青’一群在‘新时期’的身份、生活位置,却含糊不明而需要寻求和证明。”[5]194
“新时期”的到来,使原来的历史叙述发生倒置,“复出”作家重新获得了对历史的发言权。当王蒙和张贤亮们以“自省”或“忏悔”的姿态讲述“历史记忆”时,实际上作为“历史”的“受难者”和“承担者”的精英姿态,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个人的生活遭际、命运变迁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劫难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历史重新发生翻转,历史的“受难者”身份反向证明了他们对历史的责任和“讲述历史”的权力,“受难”成为一种“财富”,获得了历史道德和历史伦理的体认,成为进入新的“历史”和“现实”一种资本,并以鲜明的社会政治视角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叙事上的合法性。换言之,当“复出”作家们以“历史亲历者”和“历史叙述人”的身份讲述个人悲欢和历史遭际时,他们把属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换成了“民族记忆”和“人民记忆”,他们对“历史”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人民”和“民族”的名义置换了“自我”真实的历史承担,也就是以“民族”和“人民”共同的灾难叙事和道德优势放逐了对“自我”的深刻省察,并直接迎合了国家话语对“文革”的叙述。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拒绝反省”的方式进行的反省,是一种以“集体”的命名方式拒绝“自我”对历史承担的反省,是一种在重获“英雄身份”后却拒绝对“英雄历史”进行自省的身份表述。
和“复出”的“五七”族作家不同的是,“知青作家”对自我身份的重建和表述面临的是另外的困境。知青曾经是“革命小将”,是“文化革命”的主力,他们共同参与了“文化革命”并成为“革命”的主体,但当国家意识形态宣布了“文革”的“极端错误”时,“知青”作家如何面对自我的历史就成为他们重建身份认同的重要障碍。他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乡村生活经历,也成为他们面对新的现实时需要重新考量的历史。“红卫兵”在“新时期”成为一个“污名化”的历史名词,对于大多数有“红卫兵”的“革命”经历的“知青作家”而言,当历史证明“红卫兵”的革命历史的虚妄时,“知青身份”就充满了暧昧。“红卫兵”是一个在“文革”时期给亿万中国人造成终身伤痛的群体,“它不仅生命狼藉并且是‘文革’暴力的同义词”[6]。而从“红卫兵小将”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知青运动的终结,给这一代人最大的打击,不仅仅是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弃,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中,他们不仅成为了牺牲品,更可怕的是,他们成了在黑暗中长大的‘狼孩’”[7]。
那么,知青作家将如何重获对历史的发言权?当“复出”作家以“历史受难者”的姿态建构了他们的“文化英雄”身份时,“知青”作家显然无法讲述他们的“革命历史”,因此,在“新时期”“知青”们如何重获讲述历史的权力就成为新的“身份”定位必须逾越的一个巨大障碍。由启蒙的主体到被启蒙的对象,由“历史”的主体到“历史”的放逐者,他们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认同和身份意义,似乎退回历史、退回过往的乡土世界就成了惟一的选择。于是,知青作家走入曾经插队的乡村,走进被“放逐”的历史中,重新赋予“知青”生活以意义和价值。而作为叙事起点的则是一代人的青春、梦想和追求,回到过去成为对自我青春的证明。当知青历史被政治伦理证明为虚妄的时候,知青作家以在乡村的生命经验重建了“自我”的意义,因为“知青生活”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不能泯灭的个体生命际遇,正是通过赋予自我经历以意义,知青群体重新获得了进入历史的通道。
回到过去、回到乡村、回到自我的青春苦梦,知青作家一方面在怀旧中缓解历史压力下的焦虑和痛苦,另一方面通过对自我青春的证明重建“身份”的合法性。叶辛在回顾自己的知青生活时,满含深情地说:“我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业,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8]孔捷生在谈到《南方的岸》时也说:“怎能因为我们的些微奉献远抵不上十年浩劫的空前损失,便觉得毫无价值呢?”[9]而张承志更是对“知青记忆”充满了浪漫怀想,并对自我的“知青身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坚定认同,“无论我们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10]。但这种“辩护”与“重申”在为一代人重新寻求身份合法性的同时,其实遮蔽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和精神境遇的反省。那就是当每一个个体都以“自我”存在的意义而剥离荒谬的历史时,其实也剥离了个体对历史的承担。如果所有过往的“历史”都是被掏空了个体经验的空洞的“能指”,那么,“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也将成为无意义的虚妄的名词。因此,知青作家通过对自我经验的彰显而试图重获对历史的讲述权力时,实际上已失去了历史叙述的丰富性,而这种没有“历史感”的自我也将是一个个悬浮在空中凌空高蹈的“自我”。
总之,“知青”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为了重获讲述历史的权力,并有效地参与“新时期”国家话语的构建,对“自我”、“历史”都进行了有效的剥离。但是作为亲身经历并参与了“文革”的一代人,他们如何讲述“自我”和如何讲述“历史”都面临新的困境。如果说对于“复出”的作家而言,“文革”是他们“受难”的历史,那么,对于“知青”而言,“文革”既构成了他们青春的证言同时也解构了青春的意义。“上山下乡”的岁月是一段被“流放”的经历同时也是“个体”悲怆和苦难的历史,在历史伦理和个体伦理之间,“知青”的身份认同遭遇了难以弥合的裂隙。那么,对于80年代以及此后的“知青”写作和“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而言,他们如何正视自身的“革命历史”?他们如何重获历史讲述的权力?他们如何在更深入“反思”的意义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意义话语?这不仅是“知青”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样是也是作为“历史”的“受难者”的“复出”作家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精英姿态:重建启蒙主体
20世纪80年代被定位为一个“启蒙”的时代,从政治启蒙到文化启蒙,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话语上达成了“新时期共识”。而当“知青”群体通过对“自我”的“被欺骗”、“被流放”的“苦难”经历的书写而有效剥离了与“文革”的“暴力”历史的关系时,他们不仅重获了对历史和现实发言的权力,而且,在同是历史的“受难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他们又和“复出”的“五七”族作家一样建构了历史“启蒙者”的自我定位。“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神话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一样都具有‘虚构性’。”[11]“知青”作家和“复出”的“五七”族作家在对历史“虚构”和“想象”的逻辑上,都获得了“历史”的赦免,重构了自我,并成为与国家意识形态达成“共谋”的“新时期”的启蒙主体。
但不管是“复出”作家还是“知青”作家,他们作为“新时代的启蒙者与历史推动者”的精英和启蒙姿态和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有很大的不同。“五四”作家的启蒙主义话语指向的是“封建主义”,是对旧时代的清算,而“复出”和“知青”作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话语不仅指向“蒙昧的封建主义”,而且指向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以“极左”为表征的政治实践。然而,“革命”的“极左”话语仍内在于政党的革命历史中,因此,“启蒙”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相对彻底和决绝,这种“启蒙”话语必须内在于国家意识形态所预留的空间中,一旦“反思”和“批判”的话语超越这种潜在的规定性,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叙述造成伤害,那么对其的“规约”和“训导”将不可避免。因此,“知青”作家虽然以精英和启蒙姿态重述“历史”或讲述个体“记忆”,但这种“历史”和“记忆”都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的文学书写不仅远离真实的“文革”历史,同时也拒绝对参与历史的“自我”的深入反省。
如果说在“伤痕文学”中,“知青”的自我书写和“复出”作家对“文革”历史的讲述,使“知青”这一身份仍然存在“自我定位”与被“他者定位”的结构性裂隙,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姿态,那么,到“寻根文学”中,当文学写作以“文化反思”的方式取代了“伤痕”和“反思”文学对“文革”历史的深究所可能带来的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合法性质疑时,“知青”作家就重新获得了言说历史和现实的权力与机缘。换言之,当文学书写从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思考转向对前现代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反思时,“知青”作家就顺理成章地转移了对“自我”的“文革”历史的拷问而有效地进入了以“启蒙”为主导的“新时期共识”。“寻根是专属知青作家们的一项文学活动,是知青作家们源于内心困惑和解放自我的文化尝试。”[12]而这种以“文化寻根”的方式进行的“民族寓言”书写,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把整个社会和知识阶层组织到了“现代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中。知青作家们也通过内在于“新启蒙”的“文化启蒙”重建了自我的启蒙身份,成为“新时期共识”的历史主体。
“文化寻根”作为“知青”作家的写作起点和重要诉求,彰显的正是他们的精英意识和启蒙姿态。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认为,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把目光投向“文化”的更深层次,也是“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有所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13]“寻根”虽然根植于自我“上山下乡”的个人记忆,但“寻根”的目的却不是回到自己的生命经验、打捞属于自我的生命印记,而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是寻找“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有谁可以代替民族立言?有谁可以代表人类发言?“寻根派”作家正是以他们的精英意识试图为民族和人类立言,以流放后归来的“贵族”姿态对民众发言。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即使是“寻根派”群体这种貌似游离主流的话语实践,也弥漫着权威的教训话语方式,依然是一种潜在的权力的意识形态。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都是以两个孩子的视角为叙述的出发点,对应着五四时期鲁迅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启蒙呐喊。鲁迅式的启蒙是一种深陷于自我的生存悖论和民族的灾难历史的艰难挣扎,因为对于这个要“救救孩子”的启蒙者来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因此,鲁迅式的“启蒙”实际上带有对自我的历史际遇和生存困境的深刻体察,他在以“精英姿态”启蒙“蒙昧的民众”时,实际上也把自我推入了无以救赎的绝望的追问中。但“寻根派”作家的“启蒙”却是一种屏蔽了自我历史的精英姿态,在没有自我的“空洞”的历史和现实中,他们讲述他人的故事,在他人的故事中建构自我的知识者的批判立场。王安忆以“客观主义的叙述态度”讲述小鲍庄“仁义”的历史,对于“小鲍庄”而言,王安忆是一个局外人,“这个局外人虽然不介入‘小鲍庄’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却把那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原样呈现出来。显然,为追求客观就不应当卷入。这个局外人不淡漠、不骄矜。”[14]但是,这个“不淡漠、不矜持”的“局外人”的姿态却恰恰构建了“仁义”的历史叙述,并从小说中站起一个“智慧”的、超然事外的叙述者。阿城的《棋王》通过王一生的故事试图表达他对道家文化的体认,但对王一生和“我”而言,“棋道”实际上呈现了不同的意义,在王一生那里“棋”和“吃”一样是生存方式之一,是对自我的物质匮乏的精神补偿,但在“我”这里,“我”是以“知识者”的“高贵”姿态看到了处于芸芸众生中的王一生所体现出的道家文化的精髓。因此,不管是韩少功、王安忆还是阿城,他们都是以超越民众的“贵族”和“精英”姿态讲述“文化之根”,并在对民族文化“优根”的挖掘和“劣根”的批判中,重建了80年代“启蒙者”的身份认同。
因此,对于“知青”作家来说,不管是他们“启蒙”的精英姿态还是视点下移的民间叙事,都构建了不同于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主体。“‘寻根’作家讲述民众的故事,这一视点下移有作家重归文化母体,重寻精神依托并自我救赎的潜在动因,是渴望解决精神关怀,终结‘他者’话语,重新自我定位的策略选择。”[15]但这种知青群体自我的“精英”身份定位,在走向民间、寻找“民族文化”、启蒙民众的同时,也常常使他们的自我认同陷入尴尬和虚妄,因为,当“知青”作家们带着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精英情结走入民间时,他们本身就已经先设置了和真实的民间之间的一道屏障,使他们“启蒙”或“认同”民间的身份建构遭遇尴尬。
总之,“知青”作家们通过“文化寻根”,走入曾经插队的乡村,一方面在“怀旧”视野中构建了淳朴温情、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书写,并在“大地”、“母亲”、“黄河”、“父亲”等话语序列中重建了自我的“人民认同”。另一方面,“寻根派”也以回到乡村、剥离自我的“历史”叙述方式,重新找到了进入历史的通道,并获得了对历史和现实发言的权力。“知青文学其实过于关注个人的情感记忆,当他们要以群体的姿态跨越现实进入历史时,依然抹不去个人的经验与情感变化。”[16]但是,个人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当历史成为“空洞”的能指,当“个人记忆”获得了合法的权力,“寻根派”的自我认同就呈现出虚妄的一面。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必然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427.
[2]汪晖.汪晖自选集[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
[3]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08.
[4]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0.
[5]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梁晓声.知青与红卫兵[M]∥梁晓声.梁晓声自选集.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297.
[7]钟文.“寻根文学”的政治无意识[J].天涯,2009(1):191-201.
[8]叶辛.关于《蹉跎岁月》答读者问[J].书林,1981(5):35-37.
[9]孔捷生.旧梦与新岸[J].十月,1982(5):242-244.
[10]张承志.我的桥[M]∥张承吉.绿风土.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10.
[11]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12]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J].文学评论,1999(6):114 -123.
[13]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2-5.
[14]吴亮.小鲍庄的形式与涵义——答友人问[J].文艺研究,1985(6):81-84.
[15]孟繁华.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J].天津社会科学,1996(1):58-64.
[16]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