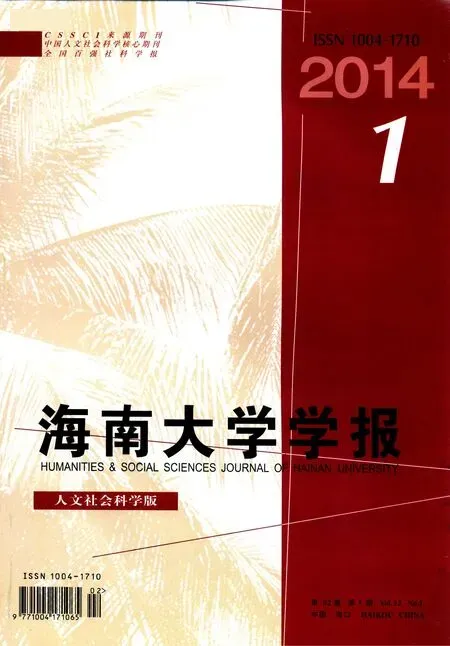哲学社会科学的人学意蕴
何慧琳,邓 鹏
(1.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2.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
哲学社会科学以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趣,涵盖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科学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学科,研究人的思维观念、价值和意义,即人的主观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大体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及其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思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人类所呈现的三个维度。唯有将这三类关系处理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成为可能。毋庸置疑,哲学社会科学所特有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帮助人类处理这三大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1],具有属人的性质。
一、推动人类思维方式变革,实现人与思维的内在统一
人类思维方式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表征着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方式,是按一定结构、方法和程序把思维诸要素结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行模式。思维方式体现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双向运动,是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深刻体现。就其组成结构而言,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外在系统和内在系统。外在系统包括思维主体、思维中介(也可以称作思维工具)、思维客体;内在系统包括知识信息系统、动力调控系统、智力智慧系统①为了准确阐述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思维的变革作用,必须将人类思维方式进行合理划分。目前学界对人类思维方式见仁见智,大致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对人类思维方式进行划分。为了更好地论证本文观点,本文采取了学界公认的由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次印刷,第400-402页)中的观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充分继承既有成果,依托物质中介、精神中介与语言中介,从真理维度、价值维度与情感维度,对人、自然、社会、思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索,实现对精神客体、自然客体、社会客体本质的把握。人类思维方式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工具,哲学社会科学也推动人类思维方式不断变革,其原因有三: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思维方式变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工具。思维工具是将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联系起来的系统,主要由人脑和以生产工具、观察工具、计算工具等为代表的物化思维工具所构成。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之前,人类思维工具较为单一。人类只存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这两大实验,主要靠人脑的感官直觉与猜测性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近代社会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继从哲学母腹中脱胎出来,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思维工具。自然科学以科学实验、数字计算等定量思维来表征自己的科学性,而哲学社会科学则通过理论概括、逻辑推理等定性研究,把握客体的本质。进入现代社会后,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打破了传统社会格局,使社会演变为联系紧密、复杂多变的社会巨系统。“认识现代复杂的社会巨系统,要求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随之改变。”[2]因此,一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平台,运用系统性思维开展研究的全新思维工具——“综合集成实验室”,首先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运而生。
“综合集成实验室”要求研究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归纳出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各个变量,借助先进科学技术和精密仪器将研究对象与各个变量的关系转化为精确数据,并运用“仿真学”原理模拟出研究对象的客观状态来建立现代型实验室。为此,研究对象与各个变量的关系也就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而是涉及了人文、社会等各个学科知识的复杂函数关系。对复杂关系的数据转化仅仅依靠单个数学公式难以实现,还需要运用高度抽象的思维方式,用准确数据表达出来。“综合集成实验室”作为一种新的思维工具,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走向融合的趋势,也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善于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纳入自身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的开放性特征。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将定性、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开拓了人类的思维空间,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思维方式变革拓展了新的思维客体。思维客体是主体的思维对象,是主体思维活动所指向的一切物质、事物和现象,它随着主体的变化而改变其存在的深度与广度。思维客体包括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三种类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自然与社会的未知领域不断成为新的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而学科知识的积累与思维规律的探索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思维的精神客体。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丰富了人类思维的精神客体与社会客体。在人文科学领域,哲学社会科学无论是将考古发掘的新遗址和新文物等纳入研究视野,还是对史学新发现的研究与鉴定,都是对人类思维的精神客体的充盈。在社会科学领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会发生微妙变化,产生诸多新矛盾。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呼唤人类做出新思考。哲学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时代课题,源源不断地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发掘出新的思维客体,这客观上驱使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针对新的思维客体,不断更新旧的思维范式,创新思维方式。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的动力调控系统为思维方式变革注入了活力。动力调控系统是人类思维方式内部系统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子系统,充当了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引擎。动力调控系统总体上属于非理性、非逻辑的,体现为感性思维、表象思维、非逻辑思维,包括了人的幻想、想象、直觉、灵感、顿悟以及感觉、知觉、兴趣、激情等思维要素。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爱因斯坦坦言他的相对论源于直觉,并认为许多物理学原理“都不可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论证,而感觉经验对这个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4]
可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仅需要大胆地利用人类的理性思维,而且要敢于扬弃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经验思维、逻辑理性思维,充分运用人类的情感、意志、直觉、灵感和顿悟等非理性思维,透过各种零乱复杂的社会现象,自由地构建社会现象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探索最普遍的真理,发现隐藏在认知对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将人类从重视理性轻视非理性的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开发了智慧,激发了研究兴趣,培养了创造性思维。伟大哲学家笛卡尔就曾大胆靠自觉和想象非经验性地提出了“以太说”,打破了之前流行的原子论的垄断地位,并坦言,除了通过自明性的自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之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获取确切性的知识。
二、指导并规约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们往往认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事情,与哲学社会科学无关。人类曾经也因此遭受巨大浩劫,付出了沉痛代价。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上功不可没。因为自然科学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比如在人类精神领域出现的唯科学主义、道德缺失、价值失范的问题,在物质领域出现的由于对自然过度开发而引发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还关心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可见,哲学社会科学规避自然科学研究风险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然科学研究总是在一定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价值引导和方法指导。“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5]正确的世界观促进自然科学发展,错误的世界观阻碍自然科学发展。而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脱离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管理、组织和支持,就很难有效开展。在中世纪以前,受朴素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影响,古希腊自然科学在数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进入中世纪,受欧洲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统治和支配,自然科学研究也受到束缚而长期停滞不前。15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唯物主义开始突破神学窠臼,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了18世纪,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形成的“形而上学”一直占统治地位支配着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因此处于搜集材料和对自然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阶段。而19世纪,物理学、化学、生物、海洋工程、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斐然成就,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自然科学研究又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取得更大的发展。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人文动力。“无论科学可能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价值的一次证实。”[6]49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形式,不仅取决于其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还与自然科学家的本性息息相关。人文环境是影响自然科学研究者人性体验与人性观的重要因素,对其在情感、价值、道德、理想等方面发挥引导功能。因此,人文环境通过塑造自然科学研究者的本性,间接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人文动力。
古希腊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所孕育的乐观豁达以及对于自由不懈求索的自然主义人性观,赋予希腊人对自身理性与未知世界无限探索的精神,产生了大批自然科学家,铸就了古希腊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辉煌。到了基督教所统治的中世纪,被封建神学所笼罩的人文环境使科学威信扫地。腐朽保守的宗教思想贬低人的自然本性,兜售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依赖于上帝旨意。宗教裁判树立的火刑柱彻底消解了人类对自我意识与自然的研究兴趣,自然科学家遭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自然科学研究因此停滞甚至倒退。而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类自由、理性讴歌的“人文主义”,使人性从神学掣肘下解放出来。自然科学家重新树立了对于自身与自然研究的信心与热情,自然科学取得了飞速发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把人类从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科学技术对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科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7]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会释放出人类技术理性的恶魔,吞噬专家的“灵魂”,毁坏纵欲者的“心肝”,因为“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8]。技术理性使一切事物都通过单纯“有用”或者“无用”来确认存在的价值。这样,由文艺复兴所确立的启蒙理性丧失了原有的反思与批判维度,作为人类解放力量的科学技术沦为解放的桎梏,致使“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华。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9]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于技术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反思与追问。实质上,人类自身及其命运,理应成为一切科学技术的首要目标,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并没用消除科学、贬低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6]51,科学的人文主义旨在通过对“美”和“善”的诠释与追求实现对技术之“真”的引导与规范。这种思想屡见于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哲学社会科学通过事前对技术目标的伦理考量、技术设计的伦理评估、技术试验的伦理鉴定,事后对技术行为实际效用的伦理评估、价值判断实现对科学技术行为的理性规范与引导,警醒人类科学技术的生成既应符合自然规律,又应符合人的发展必然性。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赋予自然以更多的人文关怀。远古时期,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成为匍匐于自然脚下任由自然摆布的奴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的著名代表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这种思想后经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洗礼,最终导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万物的主宰”的“人本主义”思潮的确立。这强化了人对自然的宰制意识,使人类得到了极大解放。物极必反,开发、利用与征服自然的欲望过渡膨胀,以及技术的滥用,会造成人类对自然的任意肆虐。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因此,“如果要想使人类这种宰制能力永续下去,那么,这种解放就还得包含与自然保持亲密的关系”[11]。这种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重新从人文学角度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社会学视角来考量技术进步在增强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同时,给自然本身以及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反思使人类从人与自然彼此对立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将自然生存权与发展权纳入到人与自然关系中进行考量,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过渡到“非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呼吁人类应当将自然的生存权利与人的生存权同等看待,将人类所确立的工业文明观推演到生态文明观。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对自然生存与发展给予了更多的人文情怀,警醒人类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要加大对自然的保护力度,维护自然的生存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推动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人类实践活动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实践也不例外。人类社会也需要相应的理论为其发展与变革作合理性与合法性辩护。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实践给予了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关照,持续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理论给养。哲学社会科学通过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间接地推动人与社会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协调发展。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库。“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库,意识形态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合力。”[12]具有一定政治、文化、道德、哲学等立场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内自由探索、开展研究,当其中的部分学者的探索成果,不仅能超越学术研究的私人空间,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且还能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这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便从个人学术思想跃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即从学术走向了政治。由个人学术成果到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再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历程。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库,而意识形态则是超越了私人领域的哲学社会科学。
意识形态的生成从“认识活动”向“规限行为”的演进,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从真理向价值的嬗变。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经历了从学术探索到意识形态升华的过程。我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等思想也经历了学者个人探索—学术共同体共识—国家意志的历程,最终成为新时期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意识形态。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充当了人类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也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走向复杂。与之相应,人类的社会生活不仅受到自然科学的统治与支配,还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渗透与浸染。人类社会生活也因此被专家、学者的各种社会理论所笼罩。正如吉登斯所说:“所有的生活形式,部分地正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知识构成的。”[13]人类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处在重要历史变迁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作用愈加明显。
哲学社会科学以批判精神反思旧有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同时又以建构性思维为新的社会制度做出积极探索。在“批判—建构”的理论模式中为社会变革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与政策支持。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与政治思潮,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肩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理论自觉的使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制约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如公平显失、正义不存、差距拉大、矛盾激化等问题,即现代语义上的“社会病”。“社会病”是人与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阻碍了社会发展与长治久安。当然,社会问题本身是实践问题,只停留于经验层面,还需要转化为理论问题。这种转化必须借助于问题意识。因为问题意识既根源于社会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在理性层面的镜像。问题意识的生成就是对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进行提炼、梳理、归纳与总结,并将社会问题集约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的过程。将社会问题集约为问题意识,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要进一步从问题意识出发,通过学术的探讨与批判、交流与交锋等所表征的理论自觉,从理论问题中抽象出最本质的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与探索,最终形成建设性的理论成果服务于执政当局。
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通过问题意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安全预警系统”,另一方面又通过理论自觉为社会稳定提供“安全阀”。在以问题—问题意识—理论自觉为特征的逻辑演进中,哲学社会科学肩负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使命,推动人与社会在更高层次协调发展。
[1]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6.
[2]王伟光.人类思维方式、认识方法的一场革命[J].哲学研究,2009(5):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9.
[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C].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7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3.
[6]萨顿.科学的生命[M].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9.
[7]奥康斯.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2.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9.
[9]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9.
[11]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50.
[12]安维复.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合理化重建[J].学术月刊,2010(9):14.
[13]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