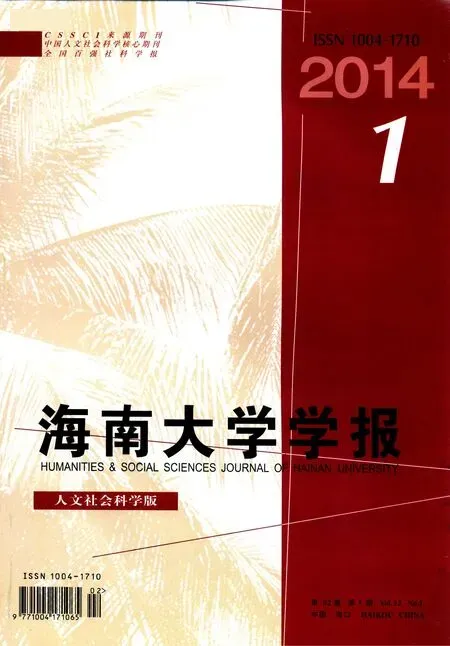古希腊古典学的两种阅读取向
张志扬
既然中国学习西方是摆脱不掉的命运,那就干脆学得彻底些。
晚清到民国,马克思进入中国前,除了小说、艺术、科学的名典,哲学上我们还只是单个人单个人地学,德国的尼采、法国的卢梭、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直到马克思进入中国把“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一同带入,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另两个来源“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作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艺复兴后的“新古典主义”,即“启蒙运动”思潮成体系地带了进来。
西方大潮刚刚涌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旋即关闭了闸门(1949年)。中国的学习眼光转向了苏俄一边,严寒而沉郁的俄罗斯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抗衡因素占住了中国人的思想,强行14年,直到1963年毛泽东以“九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形式与苏俄彻底决裂。1966年爆发了针对私有制最后一个形式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改革开放”的中国补“新民主主义”资本发展一课。
从1979年解冻到80年代中,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两大标志,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第二次启蒙高潮。不到两个10年的功夫,我们就走完了西方“现代化运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个阶段。所谓“正-反-合”的结果:惟西方马首是瞻。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中国学术界迅速但规模狭小而影响深沉地引进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一小部份人像密宗式的发展起古希腊古典学以及包括中国元典在内的博雅通识教育,既诊断“现代性危机”又“反省启蒙思想”,遂而拉开了扭转120年启蒙思潮的强大习惯势头的新战线,使一个“溃败而在押的军队”开始了一小部份人一小部份人地停止了殖民式地尾随……到了该停下来独立思考的时候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扭转乾坤的节骨眼上,作为古希腊古典学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对中国学术起到了特殊的“启示回归”的分水岭作用。
俗话说,“不到头不回头”。
古希腊的自然理性(“自然之光”)是西方现代技术理性的源头。源头与现代发展之间的消长得失,当然是检讨现代性危机的一个内在视角。这对任何类型的民族文化都具有参照的作用。但同时,它又隐含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如果消长得失仅是“进化论”解释得了的,那么,现代性危机只能由现代性来承担,被现代性取而代之的“古典学”则只能看作是被现代性蜕下的“蛇皮”,陈列在历史博物馆中;
二、如果消长得失不是“进化论”解释得了的,那就在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即“现代性是古典性之失”,与“现代性是古典性之得”,同时为真。
两种情况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西方现代性至少可看作西方古典性的一个偏执的单向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古希腊古典学在研究西方文化中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类型或专业方向。因此,我们必须让一部份有志于此的人进入其中浸润陶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无论是研究西方、诊断西方,还是以参照西方回归中国文化的源头,他(她)们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指导者。
除此而外,在我看来,古希腊古典学,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可以为中国人物尽其用,那就是有助于澄清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神学、政治哲学,特别是“悲剧精神”、“强力意志”及其“自然正当”、“人性资本化、技术功利化”、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非人属物义论”倾向等等的“意识形态”实质,即洞穿西方思想的“地中海区域文化种性”的特有本质,消除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迷雾,从而清醒本民族文化种性的平等地位与制衡作用。
对古希腊古典学而言,这是最起码的两种阅读取向,缺一不可。
今天,只有对“哲言-物性”、“神言-神性”、“圣言-德性”的独立互补了然于心者,才有可能提升欲望的等级、望其灵魂引导者的项背。
2014年1月4日 海甸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