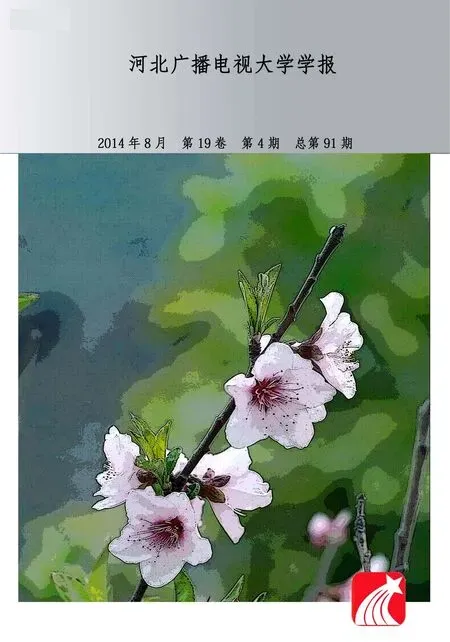浅析苏轼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人生观
周子建
(沧州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沧州 061001)
苏轼的思想很复杂,他博采儒道释众家之长,而弃其短。他一生为国除弊、替民分忧,却屡遭贬谪,尝尽人间甘苦。但他在困苦中尽力解脱,寻找生活的乐趣与诗意。苏轼不幸的一生形成了他独特的混合的人生观,不仅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士人。
苏轼的前半生相对顺利,二十一岁便中了进士,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都有任职,但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职时写了许多批评朝政的诗文,被一些人故意扭曲,说成诽谤皇上,因此元丰二年,苏轼被捕,关入御史台监狱,御史台监狱又称“乌台”,所以历史上称这件事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是巨大的。在近五个月的牢狱生活里,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以至被释放后叹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这次打击后苏轼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和以前走过的人生道路进行反思,感到“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苏轼被释后做了黄州团练副使。神宗驾崩后,由太后执政,苏轼被调入京都,在短时间内连升三级,作了翰林学士知制诰,身居高位。庇护苏轼的皇太后去世以后,哲宗即位。苏轼的政敌当权,把他贬到了惠州,在路上又四次降级。在他刚刚适应惠州生活的时候,政敌又借故将他贬往更远的儋州,从此苏轼再没有回到京城。
一、心向佛教,未忘民生
“乌台诗案”后苏轼对牢狱心有余悸,人生态度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批评朝政,积极用世到不问政治,心向佛教。苏轼刚到黄州时住在定惠院,此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转向佛教。在《安国寺记》中写道:“余二月至黄,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作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要“盍归佛僧,求一洗之”。在安国寺内他经常“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感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自己平时也是“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谴日,不复近笔砚”。这一时期苏轼对佛教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也成了他心灵的一个归宿。尽管黄州之后苏轼曾有一段时间在朝廷任职,但他并未放弃佛教。如任职期间,他曾赞美过范镇:“范景仁生平不好佛,晚年清甚,诚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学佛作家。然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理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可见苏轼此时没有放弃佛教。在惠州苏轼对佛教更加痴迷,他在贬谪到惠州的路上就游历了南华寺。到了惠州他住在嘉佑寺,经常与僧人来往。苏轼在黄州建了一个放生池。在家里他经常焚香默坐。他给侍妾朝云的词中写道:“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把对朝云的感情与宗教之情融合到了一起,可见佛教在苏轼生活与思想中的地位又进了一步。
在这一时期,苏轼的儒家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发挥作用,这从他并未忘记国家和百姓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他对政治很失望,但让苏轼这样一个从小就受儒家教育的封建文人皈依佛教是不可能的。遇到实在忍不下去的事他仍旧“如蝇在饭,不吐不快”。就是在黄州也并不是真的“不复近笔砚”了,偶尔也嘲笑一下当权者,如他在给儿子的诗《洗儿戏作》中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粗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只是批判的意味少了,玩笑的意味多了。在朝时苏轼一方面请求归隐,一方面仍旧为民请命,请求废除青苗法和免役法,并免除赤贫之民的贷款及利息。他仍旧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大臣没有原则地与君主意见一致,唯唯诺诺,认为这会导致亡国。针对宋朝冗员太多的弊病,苏轼提出改革考试的措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打击腐败。在地方苏轼也做了不少好事。在他第二次到任杭州时清理了运河和西湖,并建成了苏堤。同时他也大胆斥责朝中小人。在惠州他向广东引入了先进的插秧工具“浮马”。
在儋州,他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儋州是黎汉杂居之地,汉族统治者经常欺压黎族百姓,对此苏轼写了《和劝农》:“咨尔黎汉,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失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末诉,曲自我人。”批评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他还倡导移风易俗,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落后状态,就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劝当地人民改掉这种风俗。他还写信给中原的亲友要他们寄一些药来为当地百姓治病。另外,苏轼在儋州还敷扬文教,培养人才。《儋州志》记载苏轼在儋州设有东坡书院,以诗书礼乐教学生,为儋州文化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这种关心百姓,尽力为地方作事的做法正是苏轼身上儒家思想的体现。
二、佛道融合,随缘放旷
苏轼既然无心仕途又不皈依佛教,他在道教中寻求到了解脱,在这一时期支配苏轼的是道教思想,其道教与佛教思想也开始融合。
苏轼道家思想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归隐思想的发展与和陶诗的写作。苏轼的团练副使是一个有名无实,俸禄不足以养活自己的虚职。为了生存他必须务农,他在东坡这个地方有十几亩荒地要开垦,还要自己盖房子。他在诗中写道:“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苏轼这一时期有了几乎与农民相等的地位,使他更广泛地接触当地农民,并向他们请教种地的经验。苏轼与陶渊明有了相似的经历,这时他更喜欢陶渊明了,写了大量的和陶诗。由于仕途的磨难和在黄州的锻炼,苏轼真正喜欢上了隐居,在被任命为登州太守时,他写道:“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就是苏轼在京城享受富贵时也对归隐念念不忘。他在一份表章中称:“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朝廷。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优望圣慈念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措之不争之地。”这也表明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对政治斗争心有余悸。他在元佑六年五月的上书中写道:“臣岂敢以哀病之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苏轼在儋州将和陶诗和完,并叹道:“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的归隐思想是外在的仕途坎坷和政治险恶与内在的道家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轼在黄州结识了道士乔仝,并开始修炼养生术。苏轼曾将枚乘《七发》中的戒欲之语题为座右铭:“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这种清苦生活有利养生的观点也是道家思想的表现。
苏轼对道家思想的最精深的理解是齐生死、等物我的境界。他在《苦于乐》一文中说:“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屡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既过之后复有何物?”这种等同苦乐的观点既是作家在体验了黄州之苦与京城繁华之后的体会,也是道家齐生死、等物我的旷达思想的体现。
在儋州苏轼对道家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在《次前韵寄子由》中写道:“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雄,下视九万里,浩浩皆积风。”这与庄子的《逍遥游》有相同的旨趣。他在《桄榔庵记》说“(房屋)生谓之宅,死谓之墟”,这种生死齐一的思想也是道家思想的升华。而最能代表苏轼这种思想的是苏轼在黄州写下的名篇《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在《前赤壁赋》中诗人以超绝的笔调道出了人在宇宙中的渺小,正所谓“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并以一种齐生死、等物我的态度把个体生命融合到全人类生生不息的命运中去,“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以这样的心胸看待人生,区区黄州之贬与生活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后赤壁赋》中他写道:“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明谷应,风起云涌。予亦悄然而悲……”这个“悲”字既是对自己坎坷的命运感到的一种悲怆,也是对人生苦短、宇宙浩瀚发出的一种感叹。
苏轼佛道思想融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他随缘放旷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就是其审美诗意的人生。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生活都是艰苦的,尤其儋州,更是险恶,唐代诗人李德裕在《谪海南道中作》说:“岭水纷争路转迷,桃榔柳叶暗蛮溪。愁冲秋雾毒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苏轼刚到儋州也感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海外困苦,不能如意”,但他总能从艰苦的现实中寻出乐趣与诗意来。苏轼很放达,艰苦的生活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是个诗人,所以能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发掘生活中的诗意。苏轼初到黄州就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诗句。在惠州,苏轼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而且生活得很舒适,他在一首《纵笔》中写道:“白头萧散满秋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在到惠州不久,他就写信给朋友说他已经习惯了惠州的山水,现在一无牵挂,乐天知命了。苏轼对惠州的水果十分喜欢,以至要“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同样以豁达的胸襟容纳了儋州的困苦,从“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之句可以看出,苏轼虽身处荒地,但能以一种悠然自得、兴趣盎然的心态来对待贬谪生活。在《答程全父推官》中说“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苏轼豁达的胸襟可见一斑。他在《汲江烹茶》中写道:“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就是取水烹茶这样的小事,苏轼都能感到极有诗意,以这样的心灵对待生活,再困苦也是美的。同样是被贬,屈原苦苦寻觅找不到出路,柳宗元孤苦穷困终其一生,阮籍面对困境虽然放达,但那是悲哀中的放达,并不是苏轼这种真正的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超越了士人。
三、结语
苏轼虽然在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但他并未忘记社稷与民生,一方面在佛道中寻求医治,一方面为国谋福,为民兴利。儒道释三种思想在苏轼身上的融合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表述的:“在玄学上,他是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精神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佛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方面,他却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实践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1]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6]王水照,王宜瑷,编撰.苏轼及其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陈丽.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J].琼州大学学报,2001,(3).
[8]董雪明,文师华.苏轼的参禅活动与禅学思想[J].南昌大学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