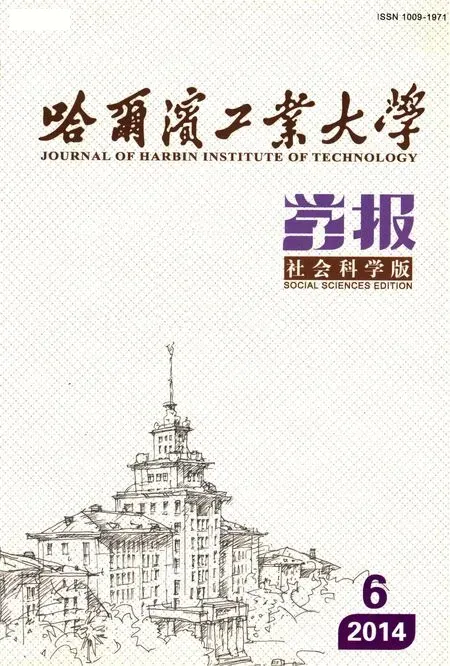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例
刘 春 阳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学术界也有很多探讨,比如讨论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宗教意识、宗教习俗、宗教故事或宗教人物,或者探讨宗教教义的文学色彩以及宗教为文学带来的文体、意境等的变化,等等。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意识到在文学史研究中宗教文学被忽视的状况,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对于宗教文学的定位问题、宗教徒的创作与文学作品的关系等。遗憾的是,在当前的研究中,较少涉及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相关章节的分析来阐释宗教经验在何种意义上能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一、何谓宗教经验?
最早系统论述“宗教经验”这一概念的应该是威廉·詹姆士。在他看来,宗教可分为两个层面,即“制度宗教”和“个人宗教”。“制度宗教”的本质要素在于崇拜和献祭、感动神的程序以及典仪和教会组织等;“个人宗教”关注的中心则是人自己的内心倾向,他的良心、功过、无助以及不全备等。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制度宗教”来认识某种宗教,但实际上,一旦宗教的外部形式离开了内在方面,它就会变成一种没有生命力的躯壳,因为无论哪一种宗教,其创立者的力量最初都是来源于他们个人与神的直接感通,宗教的本质在于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如果离开了宗教经验,也就无所谓宗教了[1]20-22。自詹姆士以后,对宗教经验的探讨从未间断,比如有人认为“宗教经验就是宗教信仰者对于神圣物(神圣的力量、神性物)的某种内心感受和精神体验”[2],或者“信教者对信奉的神性获神圣力量所产生的感知,以及伴随的各种情绪体验”[3],等等。尽管学术界对“宗教经验”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但能够达成共识的是:每一种伟大宗教的产生,必然离不开宗教经验,“宗教的源泉现在是而且从来都是经验。与超自然、先验的维度和与完全的他者的相遇,是每一个伟大宗教的基础”[4]。
宗教经验之所以难以形成统一的定义,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现象,通常与日常感觉经验具有相同的结构。在日常的感觉经验中(例如,看一朵花)存在着三个要素:感觉者(看花的人)、被感觉的对象(被看到的花)以及现象(花的显现)。同样,在宗教经验中也存在三个要素:宗教经验的感觉者;被经验到的物件(日常事物或神秘性的事物);上帝(终极实在)的呈现或者显现。在我们日常的感觉中,感觉对象以一种使我们得以知之的方式向我们显现,比如,是花以其所示的形象向我们显现,而不是我们把它当作一朵花。同样,在宗教经验中,是上帝(终极实在)以其形象或者他的某种行动向我们显现(或呈现),是上帝显现为上帝,而不是我们把他当成为上帝。这种经验的发生,虽有日常经验的影子,但毕竟不同于日常经验,而是在信仰者的宗教活动过程当中,当他的日常经验、日常意识中断之后,上帝或者终极实在才向他显现。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在其《上帝的存在》一书中,从经验者的角度提出了宗教经验的五种类型,在他看来,这五种类型能够囊括所有宗教经验的可能性[5]:其一,以一个普通的、公开的、感觉的对象为中介,对上帝或者终极实在的经验,比如说经验者通过波澜状况的大海或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凉景致见到了上帝,在这里,大海、孤烟、长河、落日都不是上帝,但是通过它们,人与上帝相遇,经验到了上帝;其二,以不寻常的、公开的、感觉的对象为中介,对上帝或者终极实在的经验,这种经验相对于前者来说差别之处只在于这种感觉物是不寻常的,比如某人声称在某个事故现场经验到了上帝的存在;其三,以能够用寻常感性语言描述的个人感觉为中介,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经验,比如说某人在梦中或者某种异象中经验到上帝,这种梦境或异象只能为他个人所感觉,但是能够通过日常语言描绘出来;其四,以不能用寻常感性语言描述的个人感觉为中介,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经验,比如说某人感觉到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不是能用语言形容的;其五,不以任何感觉为中介,当下体悟到上帝或“太一”,这种经验经常会出现在某些神秘主义者的著作里。在这五种类型中,其中有四类有似于日常的感觉经验,但显然并不是日常的感觉经验,而是在日常经验中断的瞬间感受到的。因为在日常的感觉经验中,我们经验到的大海、孤烟、长河、落日等等是在自然感觉层面上的,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功利、理智、逻辑等,因此我们很难对它们形成某种超越性的经验,而只有当这种自然感觉的层面中断后,这种宗教的经验才有可能产生。
宗教经验的产生,除了经验者对日常感觉经验的中断外,伴随着的还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在宗教经验中,情感以其显著的特点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情感或情绪:在宗教经验中的情感,不仅仅是对某种显现(呈现)出来的对象的一般感受,而且是某种高峰体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曾明确提出,宗教经验是一种先于概念分别的情感性的经验,“它是自足的、直觉的、无需以概念、观念或实践为中介”[6]的经验。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认为尽管我们能够通过理性把握上帝的某些方面,但是上帝的神圣性是我们无法用理性来把握的,只有依赖于情感,所以,宗教经验也就是一种情感经验,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是多种情感的复合体。在奥托看来,在宗教经验中,上帝的在场是以三种特定的情感为依托的:首先是依赖感。这是因为,我们作为受造物,时刻都在显示自身的有限性,“有限的自我甚至在虚无中也能意识到‘我不过是零,而您则是一切’”[7]22。这就产生对这种最高与绝对的实在的依赖,依赖他就能得到某种我们缺乏的东西,来弥补我们的不完满性;其次是经验到敬畏感,在“令人畏惧的神秘”面前为之震惊;第三种则是对上帝的神往之情,“神往可以占有某种较为突出的位置并导致平静和激动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它是作为一种奇特有力的推动力出现的,这种推动力指向一种只为宗教所知且其根本性质为一种非理性的理想的目的”[7]37。奥托进一步指出了在这种宗教经验中的情感变化历程。他说:“对它的感受有如微波徐来,心中充盈着一种深深敬仰的宁静心情。它继而转化为一种较为稳定与持久的心态,不断轻轻振颤和回荡,直到最后寂然逝去而心灵重又回到‘世俗的’、非宗教的日常状态。它能……从灵魂深处突然爆发出来,或者变为最奇特的激动,变为如痴如醉的狂乱,变为惊喜,变为迷狂。”[7]13根据奥托的这种观点,在宗教经验中,人们感到与神合一,与神对话,领悟到了神的启示,产生了强烈的激情和满足感。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对宗教经验中的这种情感进行过探讨,在写作《宗教经验种种》的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例证,比如有一个牧师告诉他:“我与创造我的上帝单独呆在一起,到处是世界的美、爱、懊悔,甚至诱惑。我没有寻找他,却觉得自己的精神与他完全融合为一,对周围事物的日常感觉变得暗淡无光。此时此刻,剩下的只有难于言表的喜悦与欢乐。完全描述这种经验是不可能的。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产生的效果,所有单个的音调融为一体,形成优雅的和声,听众只觉得灵魂飞扬,情绪高涨,几 乎 无 法 控 制。”[1]66-67事 实 上,在 宗 教 经 验中,经验者经验到上帝(或终极实在),对于经验者来说,上帝或终极实在是一个具有独立系统的意义单元,通过与它(上帝或者终极实在)的遭遇,使得经验者的生命存在状态得以丰满,这实际上就是宗教经验中情感的高峰体验。
宗教经验中情感的高峰体验性质也为英国宗教心理学家麦克·阿盖尔的研究所证实。他通过大量问卷调查以及跟踪访问,得出结论:“宗教经验会给拥有它的人带来一种与某种强力联系在一起的感觉,这通常是一种与整个创造过程融为一体,并且与一种超然存在相关联的感觉。有此经历的人会有一种喜悦感,觉得更加完整,或被宽恕,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感觉,并且,确信自己与某种真实的东西联在一起;这种经验对他们来说自带其合法性。”[8]
综合起来看,宗教经验实际上是个体对某种对象(事件)的特殊感受,该对象可以是自然事物,也可能是不可名状的、超自然的不可见世界,宗教经验的产生与日常经验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但它起于对日常经验的中断,①有关宗教经验的特征,可参见拙文《缪斯与上帝的相遇——生存论视域中的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其最终的结果是经验者所产生的临在感、幸福感、快乐感、平和感或神圣感。
二、《忏悔录》中的宗教经验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自传题材的经典,全书讲述了他33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最终转向上帝的心路历程。在该书中,他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其宗教经验,但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其皈依基督教时的“花园奇迹”,另一次则是被称为“奥斯蒂亚异象”的经历。可以说这两次经历都是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用来说明宗教经验的经典例证。
在《忏悔录》第八卷,奥古斯丁描述了他无花果树下皈依的奇迹,根据其描述,当时的奥古斯丁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精神状态,摇摆于信与不信之间。有一天他来到花园里一处较远的地方,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让泪水夺眶而出”,并向上帝呼喊:“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么?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在充满绝望、辛酸痛哭呼喊不止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奇迹。奥古斯丁写道:
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到:“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立刻我的面色变了,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披服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9]158
就在这一刻,奥古斯丁解决了他所有的思想问题,皈依了基督教。对于奥古斯丁的皈依,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奥古斯丁真正皈依的是柏拉图主义而不是基督教,因而这一段实际上是奥古斯丁的“虚构”。②认为奥古斯丁皈依的是柏拉图主义的学者主要有G.Boissier,P.Alfric,P.Courcell等,具体可参见Carol.Harrison,Beauty and Revelation in the Thought of Saint August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8对此的讨论。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历程,就会发现这种宗教经验的发生尤其必然性,首先是奥古斯丁孩提时代所受母亲的潜移默化,对基督教的信仰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在其潜意识里对此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在其精神迅速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合适的教师的引导,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然而随着其知识发展和道德的提高,这种印象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迸发了出来[10]。其次,这次宗教经验产生的契机是对保罗书信的阅读,其皈依基督教未尝没有保罗的影子,这从《忏悔录》中一再说自己皈依前灵魂“丑陋不堪”,实际是以“妓女”、“优伶”自喻就能看到这一点。①有关奥古斯丁的米兰花园、无花果树下的这次宗教体验,可参见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83-87页。
《忏悔录》中第二次重点描写宗教经验是在第九卷,记述的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前某一天的情景。他写道:
我们母子两人凭在一个窗口,纵目于室外的花园……非常恬适地谈着,“撇开了以前种种,向往着以后种种”,在你、真理本体的照耀下,我们探求圣贤们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的”永生生命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对着“导源于你的生命之泉”的天上灵液,极望尽情畅吸,对于这一玄奥的问题能捉摸一些踪影。……我们神游物表,凌驾日月星辰丽天耀地的穹苍,冉冉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情绪,向往“常在本体”。我们印于心,诵于口,目击神工之缔造,一再升腾,达于灵境,又飞越而进抵无尽无极的“膏壤”;在那里,你用真理之粮永远“牧养着以色列”,在那里生命融合于古往今来万有之源,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真慧。真慧既是永恒,则其本体自无所始,自无所终,而是常在;若有过去未来,便不名永恒。我们这样谈论着,向慕着,心旷神怡,刹那间悟入于真慧,我们相与叹息,留下了“圣神的鲜果”,回到人世语言有起有讫的声浪之中。……如果永生符合于我们所叹息想望的,那时一刹那的真觉,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吗?但何时能实现呢?是否在“我们都要复活,但不是都要改变”的时候?[9]176-178
之所以要大段引用奥古斯丁的这一段经历,是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一经历中奥古斯丁表达了宗教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时间性”与“高峰体验”。
首先是在这次经验中,奥古斯丁经验到了“永恒”这一时间上的问题。作为一种在世经验,宗教经验不仅揭示了人心理活动的奥妙,而且凸显了人类在生存中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矛盾和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上的关系,即人的生存处境与时间的关联,人作为一个在时间中生存的必死者(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他也只是一个瞬间的存在物),他有没有直面永恒的希望?如果简化一点来说,这实际上也就是瞬间与永恒的关系。在哲学史上,时间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从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追问②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一卷对时间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在他那里,时间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他说,对于时间问题,“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在他看来,时间既是人的堕落的一种标志,又是永恒的形象;既是人的无尽的深渊,同时也意味着希望。具体论述见《忏悔录》第十一卷。相关参考文献可参见Simo Knuuttila,“Time and Creation in Augustine”,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ed.By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到康德把时间看作人的先天感性形式,③康德认为,“时间不是什么从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概念”,而是“先天被给予的”,“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即我们自己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具体论述可见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部分)》,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再到20世纪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对时间问题的探究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从日常经验的角度给时间(客观时间或物理时间)下一个定义的话,时间可以说是从某一点开始,向着一个终结目标的运动。这样一来,在朝向终结目标的旅程中,时间显然就可以有三种存在样态: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种样态彼此纠结在一起:一方面,过去已经过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而将来尚未到来,也不可能把握;而现在则既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它只能是“现在”;另一方面,现在虽然“现在”着,但它很快就成为过去,将来虽未到来,但现在正在成为未来,它是已经到达的未来,过去虽已过去,但现在和未来却又经由它而来。因而,这种复杂而无法把捉的时间,很让人怀疑它存在的真实性。所以奥古斯丁说:“既然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则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时间怎样存在呢?现在如果永久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现在的所以成为时间,是由于走向过去,那么我们怎能说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时间走向不存在,否则我们不能正确地说时间是什么。”[9]242
在奥古斯丁看来,除了“过去——现在——将来”这种维度的客观时间外,还存在着与其对应的“记忆——注意——期望”这种维度的主观心理时间[9]247。根据这种同构性,无论是对将来的期望还是对过去的记忆,都是立足于现在(当下)的,因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当下的,由一个个瞬间的现在组成了其生命的历程。因此,处身于这样一种匆匆流逝的时间中的人,无论他怎样把握时间,他所能把握的只能是一个个的现在,并且必然地面临着死亡,从而让一个个的现在面临虚无。对于这种困境,难道人就不能体验到永恒了么?奥古斯丁以他的这次经验告诉读者,并非如此,因为他是在瞬间经历的,但是在这瞬间的经历中却触及到了永恒,可以说这次经验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就是瞬间与永恒的统一体:这次宗教经验虽然是一次性的、转瞬即逝的,但在这刹那的短暂时间中却包含着永恒。奥古斯丁母子在奥斯蒂亚经历的过程,正是立足于现在,瞬间发生的:他们通过聆听万物的音响,进而理解这种宇宙音响所构成的音乐的真谛,从而顺着宇宙中各种各样的乐音,逐渐接近那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时间、没有任何变化的永恒音乐。吴飞对奥古斯丁的这一经历有着相当深入的解释,他说:“在那里,好像所有的过去未来都不复存在了,他们好像就住在一个永恒的当下,但他们又好像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到了过去的起点,又仿佛随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时间的尽头。这个永恒的当下,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时间点,而是包含着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永恒流动,但又无物流动。”①吴飞《属灵的劬劳——莫尼卡与奥古斯丁的生命交响曲》.见于吴飞的博客,网址为:http://blog.sina.com.cn/wufeister1.奥古斯丁母子在那瞬间所经验到的永恒是一个消弭了瞬间的永恒。但这种永恒也可以说是一个时间,然而这个时间不再是一种客观的时间,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时间,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上的时间。就心理时间来说,他们经验到了“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真智慧”,超越于任何可变的时间之上,就伦理时间而言,则是他们母子在静默无言的一瞬间进入了永恒的存在,与上帝合一,超越了世俗的纷扰,从而达到了存在的丰盈[11]93。
其次,在奥古斯丁的这次经验中,还包含着一种我们能称之为高峰体验的东西。“我们这样谈论着,向慕着,心旷神怡,刹那间悟入于真慧,我们相与叹息,留下了‘圣神的鲜果’,回到人世语言有起有讫的声浪之中”,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语言所不能表达出来的“灵魂出窍”的境界。事实上,奥古斯丁不止一次地谈论到这种灵魂出窍。比如在《〈创世纪〉字义解》第12卷12章中,他也说过:“当心智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从肉体感觉中退还出来,它便成为出窍。这时无论什么东西呈现在面前,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12]而且,这种体验具有唯一性,是一种瞬间爆发出来的,而不具有持续性。所以他说:“如果持续着这种境界,消散了其他不同性质的妙悟,仅因这一种真觉而控制,而吸取了谛听的人,把他沉浸于内心的快乐之中;如果永生符合于我们所叹息想望的,那时一刹那的真觉,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吗?”即使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也经常会提到这种入神所带来的喜乐,比如在第十卷第四十章中,他写道:“有时你带领我进入异乎寻常的心境,使我心灵体会到一种无可形容的温柔,如果这种境界在我身体内圆融通彻,则将使我超出凡尘。”[9]227当然,这种灵魂出窍与天国的福乐,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并不就是同一的,灵魂的出窍并不必然是天国的福乐,但是,如果出窍作为一种境界能够持续到永远的话,就将与天国的福乐毫无区别,因为对于奥古斯丁来说,人是可朽的,在今生都被限定在这一必然的宿命之中,而这种出窍,就是对这种限定的跃出,它的短暂性、瞬间性正加强了这一事实。②有关奥古斯丁在“灵魂出窍”与“天国的福乐”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可参见安德鲁·洛思《神学的灵泉——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起源》,孙毅、游冠辉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177-188页。
虽然奥古斯丁在其著述中并没有对于他的这两次经验加以宗教经验的标签,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能够肯定他的这两次经验可以说是完美的宗教经验,因为在这两次经验中,我们既看到了对时间问题的回答(在瞬间完成对永恒的渴望),也看到了这两次经验所达到的高峰体验。
三、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
考虑到奥古斯丁一向反对撒谎,在宗教事物上更是如此,而且在皈依时还有旁证(阿利比乌斯当时与他在一起)的事实,奥古斯丁的这两次宗教经验不可能是他的虚构。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在这样一部堪称西方文学传统中自传文学经典①学术界对《忏悔录》能否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还存在着争论,但是普遍的观点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作品都呈现的是生活中的自我,文类的混杂并不妨碍其成为了解奥古斯丁的自传。另外,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中,耿幼壮以“自画像”这一绘画体裁为线索,很好地辩护了《忏悔录》的自传性质。可参见耿幼壮,《奥古斯丁的“自画像”——作为文学自传的〈忏悔录〉》,《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的作品中,为何要花费这么多笔墨来描述这两次经验,而对其他关于其自身的生活背景材料和生活细节付之阙如,甚至有时候即使触及到了生活细节又很快略去不谈?比如在《忏悔录》第九卷,在讲他皈依后放弃修辞学教师职位之后,和几个朋友去米兰附近的一个别墅去,并在那里写了一些对话录,实际上这里应该有许多值得交代的细节(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大约是从386年11月到387年3月,并完成了四部对话体著作),但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我已经急于要转到更大的事件了”[9]165。从后文来看,这件更大的事件实际上是他受洗,然而受洗的情节又是一笔带过。同样的叙述方式还发生在其对母亲去世事件的描述上,这件事是奥古斯丁生活中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他又说:“我是匆忙得紧,把许多细节略去不谈了。”没有略去的是“对母亲的哀恋之情”,但回忆的却不是母亲的生活中那些戏剧性的细节,而是“不谈她的遗事,而是追述你给她的恩泽”[9]172,这么多重大的事情他都略去不表,他却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两次宗教经验,显然不是奥古斯丁不知道如何安排情节的起承转合,而是有意为之的。在笔者看来,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对这两次宗教经验的描述,展现了他如何从真切的生活经验中,感悟人性、神性以及人与神的关系等普遍性问题,从而成就了《忏悔录》在神学以及文学领域的经典地位。
要搞清楚奥古斯丁在描述这两次宗教经验时毫不吝惜笔墨的原委,首先有必要了解奥古斯丁对语言文字的看法。在奥古斯丁看来,圣言永存,而人的语言最终都将消失殆尽,因而他对语言文字表现出了很大的不信任,特别是在他回首早年沉迷于世俗文学时追悔莫及。②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一卷中描述了他沉浸于弗吉尔的《埃涅阿斯》不能自拔,为狄多的香消玉殒而哭泣的经历,他自己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教给他知识,而是让他学会了俗世的各种不好的东西。具体可见奥古斯丁,《忏悔录》,页15-19。但是,奥古斯丁对阅读、书写和理解的知识仍是非常看重的,他说:“我愿意在你面前,用我的忏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时在许多证人之前,用文字来履行真理。”[9]185就修辞以及文字的作用,他还专门讲述了其精神导师安布罗斯的讲道方式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刚开始听其布道时并不注重其内容,专注其形式,但还是很有收益。他说:“我不注意他所论的内容,仅仅着眼于他论述的方式,——我虽则不希望导向你的道路就此畅通,但总抱着一种空洞的想望——我所忽视的内容,随着我所钦爱的词令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中。我无法把二者分别取舍。因此我心门洞开接纳他的滔滔不绝的词令时,其中所 涵 的 真 理 也 逐 渐 灌 输 进 去 了。”[9]88-89在这里,论述方式(词令)本身成为灌输真理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古斯丁自己来说,他如何用文字来履行真理呢?他选择了文学创作中最常使用的手法:隐喻。所以我们发现,在叙述这两次经验时,他一面以直白的语言描述自己的内心情感、思想历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喜悦,而另一面又是在不断使用隐喻的修辞方式。可以很容易证明这一点:这两次宗教经验都发生在花园之中,第一次是在花园中完成了与神的沟通,消除了曾经的迷惘、不确信,第二次在花园中母子俩体验到了永恒的福乐,毫无疑问,这里的花园意象象征的是伊甸园,前者象征着背弃乐园后的失而复得,后者则是真正容身于乐园后的幸福状态。不仅如此,皈依时的细节描述也是有所隐喻的,《忏悔录》是397年开始写作,到401年才完成,这距离他386年皈依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他对引导他去读保罗书信的孩子的唱词仍旧记忆犹新,而且还详细描绘,他说正当他痛哭不已的时候,突然听到孩子唱歌的声音,歌唱的内容是“拿着,读吧!拿着,读吧!”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隔壁孩子们玩耍时的嬉闹之声,但奥古斯丁在这里又是使用隐喻,却赋予这个细节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孩子的唱词明显带有神圣命令的弦外之音[14],就像《圣经》中记载的耶和华一次次给予摩西的命令。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两次经验的描述,奥古斯丁在西方文学传统上第一次具体地展示了人的内在生活的丰富性及变化性,从而也使得自传在认识自我、人性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文学样式。著名的奥古斯丁研究者詹姆斯·奥当奈(James J.O.Donell)认为,在《忏悔录》中,“通过对自己思想、情感和回忆的沉思及分析,奥古斯丁提供了古典时代从未有过的自我表现的模型,或许一直到了蒙田、帕斯卡尔对自我的表述出现以后,奥古斯丁才开始有了对手。”[14]在描述皈依经验发生之前,奥古斯丁用了相当长的篇幅直承了他陷于淫欲和俗务的痛苦,接着他谈到了蓬提齐亚努斯的到来对他的影响,他详细叙述了蓬提齐亚努斯给他讲述了两个不信教者阅读完埃及隐修士安东尼的事迹后幡然悔悟,归信基督教的故事,并提到了奥古斯丁自己当时正在研读保罗书信,这一切看似闲笔,但实际上都是为了他记述其皈依奇迹而铺陈。当然,这与他在其他细节上的省略也造成了很大的反差,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奥古斯丁有其特殊的目的,其目的正如德里达所说的:“重要的不是知识,不是让其他人知道发生过了什么事情,而是一个自我的变化或转变。”[15]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肉体上对生理欲望的祛除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价值观念以及生命态度的彻底改变。而这一点对于一部自传体文学作品尤为重要,因为它充分展示了作者自我的不断生成以及对于自我的最终确认。按照有些学者的分析,奥古斯丁陈述其皈依奇迹的铺陈,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即提供一个“他者”的视角,从而能够说明自我得以生成和存在的根据[15]。
对于“奥斯蒂亚异象”的详细描绘同样也是为了说明“自我”,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展开。这次宗教经验的发生是在其皈依之后不久,为什么奥古斯丁刚描述了一次皈依的宗教经验之后,又详细记载又一次“异象”?这里显然还是在使用隐喻。因为第一次皈依意味着从“旧人”向“新人”的转变,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修复,而这一次则是对自我存在的修复,也就是对自我在本体论层面上的确认。在上文中,我们已经非常深入地谈到了“奥斯蒂亚异象”中奥古斯丁母子对永恒的体验,那么自我存在的修复与“永恒”有何关联,为什么首先要由永恒入手?这是因为永恒只能是上帝的存在方式,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永恒不是无限长地延长时间,而是无过去、无将来的永远的现在,也就意味着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而只有上帝能够如此。与永恒相反的就是时间,人和一切其他造物都是时间中的存在,他们是会不断变化、有生老病死的。既然在时间中存在也就有过去、现在、将来之分,但是过去的已经逝去,将来还没有到来,现在又是无限可分的,趋近于无,则人的时间实际上也是趋近于虚无,他能把握的也就是这趋近于虚无的瞬间的现在。这样一来,人的存在与永恒就完全相反了,因为永恒是“存在的丰盈”。在这里也就看到人与上帝之间所横亘着的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人与上帝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作为虚无之物,人要想获得、充实自己的存在,使自己那虚假的存在变得真实而丰盈,就得想法进入或依附于丰盈的存在,而在“奥斯蒂亚异象”中奥古斯丁母子对天国的品尝,也正是进入“永恒”的结果,因而也恢复了被虚无削弱了的存在[11]91-93。但是他又用其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状况在人世间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所以他和母亲很快就“回到人世语言有起有讫的声浪之中”。在“奥斯蒂亚异象”的描述中,奥古斯丁由“永恒”入手,以受造物与上帝的关系为中心,又一次完成了对“自我”的说明和确证,但这里的“自我”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自我,即人这种存在本身。奥古斯丁描述了人无法永远把握现在、只能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不停流逝之中的存在状态,通过这样的叙述,展示了奥古斯丁创作《忏悔录》的真正目的:“使创造自我成为一个生活事件,使自我成为作品形式结构的组成部分,并进而使自己的创造行为和自己的作品纳入到造物主的永恒创造之中。”[12]
至此,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详尽描述的宗教经验,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这两次宗教经验的描述,奥古斯丁非同寻常地向读者敞开了心扉,展示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世界,也展示了一个有痛苦与犹疑、有欢欣与坚定的拥有自我的个体形象。但从其所描述的两次经验中,我们又看到:对自我的珍视必须以抛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旨意才能获得,自我是从与上帝的交通中获得的。显然,这种自我只有在宗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只有和上帝有了交通、有了这种超自然的关系,自我才有价值,即自我必须让身心都为上帝所占有、充满,才最终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将《忏悔录》定义为神学著作,因为奥古斯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上帝的绝对超验性、永恒性如何与人在经验世界里的欲望、需求、希望相联系的问题。
《忏悔录》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要想了解奥古斯丁是谁,了解他的无助、不全备以及最终的拯救,重要的就是要依循他留在身后的文字,溯源他曾经历的人生;如果要了解他怎样将宗教经验转换为文学创作的源泉,重要的是要仔细研究他的语言修辞艺术。而这一点也为宗教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既然“宗教文学史就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宗教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15],那么在研究宗教徒的文学作品时,必然要考虑其文学作品的指向性,即皈依后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必然受到其信仰实践的影响,其作品往往也会带上宗教的意图,作品框架的建构、内容的选择、艺术手法的使用等各方面也就表现出与非宗教徒文学家很不相同的地方,奥古斯丁详尽、细致地描述其两次宗教经验而忽略很多个人生活细节的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宗教文学史的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不仅仅要研究这些宗徒作家创作了什么,还要研究他们所选择的创作内容、语言表达与其信仰之间的关联以及作品的宗教品性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1][美]詹姆士.宗教经验种种[M].尚新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0-22.
[2]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07.
[3]世瑾.宗教心理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48.
[4][美]波伊曼.宗教哲学[M].黄瑞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5.
[5]RICHARD SWINBURNE.The Existence of God[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249-253.
[6][美]彼得森.理性与宗教信念[M].孙毅,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5.
[7][德]奥托.论“神圣”[M].成穷,周邦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英]阿盖尔.宗教心理学导论[M].陈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1.
[9][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0][英]蒙哥马利.奥古斯丁[M].于海,王晓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7-55.
[11]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2]St.AUGUSTINE.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M].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ohn Hammond Taylor.New York,N.Y.:Paulist Press,1982.
[13]耿幼壮.奥古斯丁的“自画像”——作为文学自传的《忏悔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7,(4):82-91.
[14]O,DONELL J J.Augustine:His Time and Lives[G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 Augustin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0.
[15]吴光正.宗教文学史: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