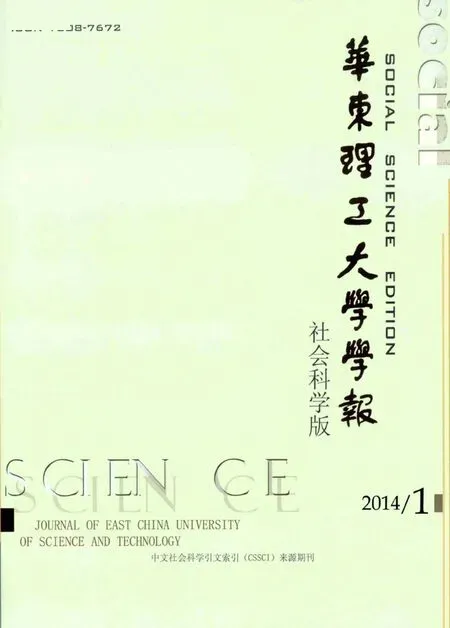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实为深度的“忠实”
封宗颖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一、引言
翻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它既是模仿,又是创造;既是语言的,又不是语言的,这中间异同共在,得失并存。①许崇信:《在异同与得失之间》,许钧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当前,文学翻译正面临着百年以来的最好机遇。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也成为近年来国内翻译界探讨与争议较多的一个话题。“忠实”还是“叛逆”常常会让每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处于两难境地。董桥有过妙喻:“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当前,随着人们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逐步强调与认可,对翻译的认识从对静态文本的关注到对“作者—译者—读者”之间动态关系的重视,翻译已不再被视为对原文的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凝聚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再创造。①贾卉:《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文学翻译不仅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也担负起在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相互沟通、增进了解的光荣使命。②方平:《精彩,并非译文惟一的追求》,许钧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因此,译品的优劣对于能否成功诠释崭新中国形象、实现“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译者的主体性由于受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往往会带着自己文化圈的思维定式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与原作者对话,在解读原作的过程中会与原作产生碰撞、冲突、拒斥或交融,误读、误译和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实践中时有发生,也在所难免。对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与任务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创造性叛逆的含义及表现形式
“创造性叛逆”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最早提出来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③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谢天振则把创造性叛逆分别定义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④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6-156页。前者的定义比较简洁,给人理解的空间也相应地大一些。根据埃斯卡皮的观点,翻译就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就是对原作的叛逆,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事实上,就创造性叛逆的目的而言,它既可以是去接近和再现原作,也可以是优化原作和与原作竞赛,还可以是服务于译者的其它目的;就结果而言,叛逆可以是译者主观努力的结果,也可以是译者无意识所造成的。
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创造性叛逆和忠实只不过是程度之分,他们构成了从逐字翻译到拟议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叛逆和忠实的连续体,都属于翻译的范畴。⑤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7页。研究表明,创造性与忠实并非僵硬的二元对立,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适度叛逆实现忠实,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相互依存,是可以和谐统一的。因此,“创造性叛逆”名不副实,它是表层上的伪叛逆,深层次的真忠实。那么其深度忠实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是将一种文字用另一种文字表述出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到原作和作者、译者与译作,也与读者、出版机构、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相关,因而它不仅仅是纯语言符号的替换。事实上,在翻译中译者面对的是两种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两种文化,担任着文化交流的重任。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他文化无法取代的独特的生命要素,是简单而理想化的“形义”对等无法实现的。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巧妙地运用看似不忠的手段,使译文发生创造性叛逆,实现对原作的深度忠实,达到“忠实”作者、译者、读者,“忠实”于翻译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发展的目的。⑥胡东平、魏娟:《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在《译介学》中,谢天振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概括为两种: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叛逆。
1.有意识型叛逆
有意识型叛逆是译者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做出的主观努力,基本上都是译者在综合影响翻译的相关因素之后选择的结果。因此,对源语文本中不合宜的思想内容,译者完全可以采取一些翻译策略,如:有意识改写,删节和加案语等。有意识的改写即创造性叛逆,指在翻译时,将原文中的一些文字有意识地转换成思想内容有明显差异、甚至完全不同的目标语文字。文学翻译中出现的有意识型叛逆往往值得仔细分析,因为叛逆之处被有意改写的讯息,往往与改写后所要表达的意义同等重要。
文化词翻译中,简单的直译或音译是很难达到效果的,好的译例往往需要对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以及接受者和接受环境做通盘考虑,并进行一定的创造性叛逆。在《红楼梦》颜色词和宗教色彩的处理上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曹雪芹用了大量的颜色词来描写服饰、用具、建筑、环境等,其中“红”是贯穿全书的主色调。一般来说,汉语中,“红”和英语中“red”引起的联想完全不一样。因此为了符合英语文化的规范,让读者感到故事好像发生在英语国家一样,并很快接受这本文学巨著,霍克斯就采用了创造性叛逆的译法。在翻译书名时,他避开“红”字而有意采用了另一书名《石头记》将其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又将“怡红院”、“怡红公子”分别译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和Green Boy,其中“红”都被替换成“Green”。①贾卉:《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霍克斯在译序中也提到法译本、德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和俄译本的书名,都译成了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这一译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红楼梦”在英美和欧洲读者脑海中引起的联想,与在中国读者脑海中引起的联想完全不一样。在英美和欧洲读者的脑海中,“红楼梦”的意思是“一个人睡在一间红颜色的房间里”——这一书名也颇能引起他们优美神秘的联想。遗憾的是,这不是中文书名的意思。②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Penguin:Harmondsworth,1973,P.19,20,46.因此霍克斯选择把“红楼梦”译成“黄金时代的梦”(The Dream of Golden Days),后又译为The Dream of Golden Girls。这种译法是否恰当,暂且不谈,但足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叛逆”时的无奈。也体现出原作跨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世界进入一个与原来社会文化境况完全相异的语境,受到了译入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制约,不可避免会产生创造性叛逆。③郑红霞:《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2.无意识型叛逆
无意识型叛逆在一部作品跨语言、文化甚至时代的传播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了解或粗心大意常常是导致无意识型叛逆的主要原因。即使是有47位大学学者参加翻译的英语《钦定圣经译本》也不能幸免。在文学翻译中,无意识型叛逆的产生常与译者的背景有关,语言知识和翻译经验不足的初学者以及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较大的译者,都比较容易发生此类错误。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有些误读也不能作过于简单的理解。比如:《红楼梦》中一习语的英译:
例: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不想步入院中,鸦雀无闻。
霍克斯译:Bao-chai’s route took her past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The courtyard was silent as she entered it.Not a bird’s chirp was to be heard.
此处的“鸦雀无闻”比喻“非常安静”,杨宪益译为utterly quiet是恰当的,比如说“教室里鸦雀无声”,读者一般不会联想到乌鸦或麻雀。对于霍克斯这样的翻译家、汉学家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错译归因于其汉语文化知识或翻译经验方面的不足,毕竟霍克斯是经过反复思考的,所以还是要多从译者的思维和心理去分析原因。
所谓“无意识型叛逆”,顾名思义,是指译者并无“叛逆之心”,但却由于误解、疏漏以及译笔过于拘谨或过于自由等原因,而导致了不应有的叛逆。④孙致礼:《翻译与叛逆》,《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先是读者,故先有了误读,而后产生误译。人们在与其它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理解别人,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是无意识行为。误译造成信息误导,不符合翻译原则,译者应尽量避免。但是误译有时却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因为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流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和变形。译者在母语文化“先入为主”的干扰下,出现个别不十分恰当的译例也在所难免。
三、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必然性
翻译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就是一定程度的叛逆。译作可以是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也可以是对目标语的客观背离。鉴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译作必须忠实于原作,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讨论的叛逆主要指的是译作对原作的背离。叛逆可以体现在语言、文化和文学性等多个方面。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等多个翻译因素互联互动的整体。①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7页。因此,在整个东西方文学的翻译实践中始终存在着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叛逆性这一貌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问题,主要原因为:
1.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都会在翻译作品上打上各自的印记,一部作品一旦进入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例如:
(1)概念空缺
民族文化的差异会导致“词汇空缺”和“词汇冲突”等现象,如欧美人语言中不会有“皇阿玛”的概念,而“耶稣”等词汇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既陌生又新鲜。
试看以下译例:
例一:Their life style could seem Spartan to a city family with their assets.
译文: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城市里的殷实人家来说,似乎过于简朴。
上例中,Spartan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意即严谨朴实,斯巴达是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 396年古代希腊的城邦,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以简单质朴著称。缺乏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不了解这种人物形象及其所指意义,如非要保留原文中的意象,会让译语读者感到困惑、影响阅读顺畅感。既然使用的是引申意义,就没有必要把“斯巴达”译出来。译文貌似背离原文,实则增强了可读性,同时又保留了作者真正的语用意图。另外,在《红楼梦》英译本中,霍克斯将原著的道教和佛教文化改译成基督教文化,将中国异于英国的文化词汇改写成符合译文读者习惯的词汇。如将“阿弥陀佛”译成“Holy Name,Bless his Holy Name”等等。
(2)文化习语及其独特的表达
作为传承、记载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习语在一个民族语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本民族独特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的习语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可能会导致文化意象的扭曲、变形甚至遗失。
因此,翻译时可以冲破原语束缚,译出意义贴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在翻译“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成语时,也大可不必拘泥于保留“西施”的意象,非把她翻译出来,并不惜加上成段注释,不妨采用现成的英语谚语“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毕竟不同民族除去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之外,还拥有相同的对世界、人生的认知和理解。
另外,霍克斯在对《好了歌》的英译中,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翻译成“A case of‘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英语成语“a wild-goose chase”意为“荒谬之追求”,霍克斯用“goose”代替“swan”,西方读者心领神会)诸如此类归化式翻译,在霍克斯英译本中经常可见,不费吹灰之力,犹如创作。②刘绍铭:《霍译石头记商榷》,载《文字岂是东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6页。
(3)语言的特殊形式:如通过语音、字形或语义实现双关效果
当遇到原文出现谐音、文字游戏或语义双关的情况(汉语中尤其常见),译者往往苦于无法将双重意义传达完整。这时应采取舍弃表层意义、传达深层意蕴的策略,即“译出精神,译出风格,译出原文妙处”。
《红楼梦》里的很多人物名字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它们揭示了人物性格、命运,反映了人物的结局,读者可借此了解到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等。霍克斯在翻译人名时非常重视翻译中读者的因素:“……要记住小说中数以百计不知如何发音的名字,肯定让西方读者不胜其烦……然而译者要忠实于多个要素。他要对原文作者负责,要对译文读者负责,要对原文文本负责。这三者绝非一回事,经常难以调和”。①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Penguin:Harmondsworth,1973,P.19,20,46.基于这种认识,霍克斯另辟蹊径,对主要人物译音,丫环、下人译意,如 晴雯(Skybright)、袭人(Aroma)。谐音双关的名字娇杏(侥幸),译成Lucky;霍启(祸起),译成Calamity;道人、大士、真人、尼姑用拉丁文翻译,如把“空空道人”译为“Vanitas”等,给他们蒙上了几分神秘的宗教色彩,用法语来译戏班人员,如龄官(Charmante)。此外,译文大量使用斜体字,借以表示人物的语气、口吻、腔调等非言语特征。②贾卉:《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的确,译者应当在深入领会原作精神实质的前提之下,不拘泥于原作的字面形式,创造性地表达原作思想,但不可添枝加叶、改变原作的风格。
再如: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中的一例:
Second citizen:A trade,Sir,that I hope Imay use with a safe conscience;which is,indeed,Sir,a Mender of bad soles.③聂玉洁:《刍议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该句以谐音的形式表达了说话人的双关语意。“sole”与“soul”同音,说话人侧重表达的是深层意思,即“我不仅是鞋匠,也能敲打修补冷漠恶劣的心灵。”两位名家译本如下:
朱生豪译:市民乙:先生,我希望我干的行业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过是个替人家补缺补漏的。
梁实秋译:民乙:我做的这一行生意,先生,我希望是问心无愧的;老实讲,先生,我是修补破鞋底子的人。
就巧妙传达该句通过语音游戏实现的双关意义来看,朱译更胜一筹,虽没有准确翻译出“sole”的意思,但道出了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看似叛逆,实则追求了整体的忠实。
2.读者的期待
由于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生活风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有着各自的“文化结构”,也叫“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使得译入语读者本能地接受符合或接近本族文化的事物,而对背离甚至与本族文化相冲突的事物感到困惑难解,甚至排斥。如:要将品牌名为“Poison”的香水引入中国市场,译名就最好不要出现“毒药”二字。有聪明的经销商将其译为“百爱神”虽有悖字面意义,却着实赢得了市场。
可见,译者所处的文化规范、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的个人认知能力、审美情趣、个性特征都会给译作打上接受语环境和译者的烙印。有的译者根据自己的独特的追求目标,大胆地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不仅可以传原作之神韵,有些还能更胜一筹。例如:把“Oliver Twist”(奥利佛·特维斯特)译为《雾都孤儿》,把“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麦迪逊县的桥)译为《廊桥遗梦》把“Waterloo Bridge”(滑铁卢桥)译为《魂断蓝桥》等,均未失原义,又极富创造性。这是因为在英语语言文学中,故事名、书名、电影名好以主人公名字或地名等专有名词命名,而中国文学、影视常以抽象、概括性的文字提示情节 ,告知读者、观众故事梗概,尤以四字成语见多,同时也符合汉语的韵律。以上成功译例使得这些英语电影、文学作品深受中国观众、读者喜爱,不仅延续了经典,也传播了异域文化。这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所取得的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的成功。
四、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限度
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
1.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不能脱离原作的制约
译者只是代笔,而不是抢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写作。有人形象地把翻译家比作钢琴演奏家,同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不同的钢琴演奏家会根据自己对乐章的理解和体会演奏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但他只能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一天地里充分发挥其才能和智慧,进行积极的艺术再创造,决不能脱离《命运交响曲》,把它演奏成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翻译家也是如此,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罗玉君把《红与黑》中于连的一段内心独白“Monstre!Monstre!”(魔鬼!魔鬼!)发挥成“啊!社会的蟊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①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这种过度的主观渗入是不恰当的。
2.创造性叛逆行为应符合原语文化规范
文学翻译作品如同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民族特色,因此翻译中,译者应尽量保留原语语言文化特色。如英国汉学家Herbert A.Giles曾译杨巨源《城东早春》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译文如下: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译者以 early May译“新春”可谓是对原诗的创造性叛逆,尽管该译文也与下文的willows pray构成尾韵,但违反了原语文化规范:在中国五月初已将近暮春,译者没有研究中国的时序景物,就拿欧洲的时序景物来比附,结果违反了同一律。②张今:《文学翻译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创造性叛逆行为应符合目的语文化语境
文学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译文必须适应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主流,在这一前提下产生的译本才能在主体文化中产生深远反响。严复译的《天演论》体现了文体风格上的创造性叛逆。严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更了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心态,因此才投其所好,采用了适合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文字,以中文短句译英文长句,句次不符而要义不失,读起来节奏感强,音调铿锵,与原文可谓貌离神合。倘若严复用的是白话,同样是《天演论》,恐怕未必能在学术界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4.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应该遵守翻译规范
翻译规范是译者创作译文文本的决定性因素。尽管翻译规范的范围不能很客观清晰地界定,而且因时因地而异,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语言文化环境中其“主流”有相当的普遍接受性。诗歌翻译中通常采用“以诗译诗”的同类移植原则就是出于这一因素的考虑。如以诗体和散文体出现的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译成中文时也具有同样的形式,而用汉语文学独有的,而英语文学中没有的元曲译出的莎剧则没有被主流所认同,至多只能是译家自娱性的尝试。③张敏:《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五、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翻译史上,严复所译《天演论》可说是典型的有意识叛逆了,严复在译此书时,只保留了书名的前半部分“进化论”,而把后半部分赫胥黎本人所重点强调的“伦理学”故意不译,进行了“有心的”叛逆。本来赫胥黎著书的主旨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批驳斯宾塞关于进化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曲解,严复却对此进行了叛逆,他不认同赫胥黎的观点,转而信奉斯宾塞的观点,深信进化论可以解释社会的发展,只要不断进行奋斗和变革,中国并不一定必然要灭亡。据说胡适在读了《天演论》后有感于“只有‘变’才能‘适’,只有‘适’才能‘强’而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适”,有意识误译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④陈丽琼:《论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外语》2010年第11期。
由此可见,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在于: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⑤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56页。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⑥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可以说,创造性叛逆的过程也是译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对“叛逆”得当的地方应加以保留和发扬;“叛逆”不当的应注意避免,加以完善。同时,对创造性叛逆行为重要性的论述并不是要否定“忠实”的翻译标准,而是要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来认识和协调“忠实”与“叛逆”的矛盾,以使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忠实”标准,把握“创造性叛逆”限度,达到深度的“忠实”。正确理解了这一概念,承认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有助于我们确立一种自信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接受观念,译者应该积极发挥主体性因素。同时亦对原文及自身所处的语言文化规范主流有清楚的认识,从而兼顾主体性与文化语境的协调,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及社会效应。只有充分发挥我们自己作为译作接受者和整个社会作为译作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精神,根据中国社会自身特点和文学发展的需要译介外国文学,才能做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从翻译实践中探索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对翻译实践有强大说服力和指导价值的规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