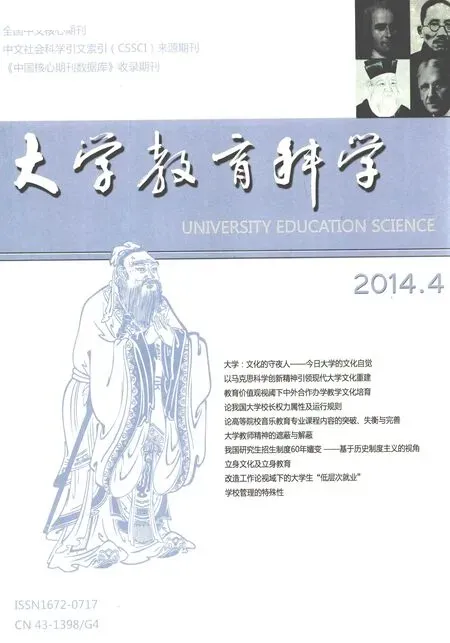大学教师精神的遮蔽与解蔽
□ 王勇鹏 佘君君
大学教师所拥有的思想深度与精神品质直接关系着一所大学的水平与高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师”的意义,正在于其所营造、建构与生成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混沌的道德结合体。而在这个工具理性、文化媚俗与绩效主义泛滥的时代,大学教师精神被时代流俗遮蔽,出现了爱的冷漠、良知的消弭与自由的旁落。这就是笔者试图探寻的问题。
一、大学教师之精神
大学教师精神是大学教师这一群体普遍秉持的价值信念、道德理想、人格风范和精神支柱。大学教师是一个集师者、学者和知识分子于一身。其精神品性必然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截然不同。其为师者的角色要求拥有“爱”的能力,其为学者的角色要求拥有“自由”的品格,其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要求拥有社会“良知”。
(1)爱。爱在教育中,是一种最基本的教育情感。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教育者给予受教育者的,正是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爱的形式——知识、情感、信仰。教育所造就的人,必定是饱含爱与关怀的人,没有爱的教育则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是不道德、无意义的教育。大学教师作为师者的身份客观上要求其具有爱的品质,大学教师因所处地位与职责的特殊性,他们是通过影响大学生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来影响社会的发展的。有爱的教育才会有人,有价值,所以在大学教师便更加需要教育爱。爱的核心是给予,不求回报的给予。正如纪伯伦所言:“爱给予的只是它自己,取走的也只从他自己;爱就在爱中满足。”[1]爱需要大学教师无私的付出;需要他们运用内在的力量去思考人的存在,关注人的价值与意义,追问人的灵魂;需要他们以人的爱的能力和幸福为终极目的;以关怀的方式培养美好人性、以博爱的精神追求人的生命价值、以坚定的信念维护教育的价值性与道德性;在爱与理性之间建立平衡,帮助学生更好地成为自己。
(2)自由。大学的本质即是自由[2]。这种自由是心灵的自由,是求知欲望的释放,是好奇心的绵延,是精神的超越。我们所强调的自由,既基于教师的自然冲动之上、也基于教师的社会责任之上,是合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求真的前提与基础就在于“学术自由”,学术生活的价值内核也就是“学术自由”。唯有学术自由,才能释放学者的学术冲动,促进学术流动性、开放性的生成;进而自由可以演变为单独的思考,也可以生成学者间的自由组织,终而强化学术间的联系。“真正的文化是一种在自由中的活动,它不存在于那些将成为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模式中”[3]。自由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区分,外在的自由就是没有他者对自我的控制,是外在条件保障的自由;内在的自由就是个人不服从于利益、欲望等,没有遮蔽个人对知识追求的天性,这是心性的自由。大学教师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内在的自由,不是看别人或由自身情欲而行事,而是由自己的理性、德性与智慧真正指向个体精神的高贵。校园的大师们都应是心仪真理而自信与宁静、执著而诗意地行走在真理之河畔,不受外界干扰,不随波逐流或奉命研究,维护学术的尊严。
(3)良知。良知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自由本性。它建立在大学教师的理性、德性与智慧之上,保持抵制外部世界的干预与纷扰,成为真理、公正、道德的守卫者,成就一种公共批判精神。大学教师必须从社会公正和理性出发,出于“社会良心和价值维护者”的身份,摆脱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对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随着大学教师对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及矛盾便会愈加明显。那么,是什么精神特质成为大学教师避免同化的支撑力量呢?正是出于一种教育良知,才能让教师不被外部利益和权威所左右。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的阶层,是一个没有直接的自身利益或私利的阶层,具备良知的大学教师才能成为独立、勇敢、正义、自由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在公共领域是不屈从于他人意志下的个人,他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是具有能力‘向’公众及‘为’公众来代表、表明观点、态度或意见的个人[4]。在一个庸俗横流的时代,有良知的教师才能够摆脱那些特定利益或即得利益集团的狭隘性、自私性和肤浅性,以一种对美好的坚持、对痛苦的敏感、对理想的执着,抵抗粗鄙与野蛮,拯救教育与社会的纯粹与朴实。
二、大学教师精神的遮蔽
盛行于今天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官学勾结、商学勾结现象,已践踏了中国学者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更遑论期待中国的大学对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关照,导致了如今中国学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迷失和迷惘,也更有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迷失,大学教师的精神逐渐被遮蔽。大学教师应有的关怀精神已妥协于工具主义,自由思想逢迎于世俗权力,社会良知蒙昧于媚俗文化。
(1)爱已妥协于工具主义。工具主义的宗旨是利益与功用至上,否定情感的存在,将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其目的就是实现当下既得利益的最大化。“知识就是力量”的自然科学的启蒙,极大激发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带来了物质的空前繁荣和科学的日新月异,同时也带来了物化世界对人精神世界遮蔽的危机。正如胡塞尔所说,启蒙以后的自然世界观和科学的实证范式抽调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世界变成了纯粹物化的世界,颠覆了现代世界人的价值序列。“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5],实用成为终极价值。大学教师逐渐对工具主义妥协,对情感与审美的排斥。他们的教学与科研活动,逐渐割裂了生动饱满的教育生活,最终沦为教学程序的操纵者,即成为一个没有情感、爱与价值的机器人。
随着人们对现代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任意夸大,大学科研活动日益市场化、社会化、政府行为化,不少大学教师身受科研经费“诱导”。教师沉沦于金钱与利益的纷争,轻视教育中内在的永恒的价值与人文关怀。于是,一些大学教师:“其一,重科研轻教学,不能以学术嘉惠学生;其二,教学品质下降,荒疏新知,不能获得持续的专业长进;其三,教师过于繁忙、外务繁多,在教学中出现敷衍塞责,随意应付。”[6]此外,学生已经不是教师爱的对象,而是学校与教师谋取自身利益、完成绩效指标的工具,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给予,而是索取,教会学生的更多的是竞争与心计,无关善良与爱。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人身处“物化世界”的包围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退化为商品。大学教师精神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也随之慢慢遭受“有用性”的侵蚀,大学教师的精神世界日渐被对象化的物质世界所遮蔽。大学教师从事研究、探索新知的目的不再是出于“闲逸好奇”的精神追求,而是在于获得自然更多的秘密,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知识,从而发明更多的工业技术,满足人的更多的欲望。大学教师投身教学不再是关注个性发展、尊重生命价值,而是服务于当下社会生产、发展所需的技术掌握者、技能获得者或流水线劳动者,大学教师的生命精神的独特性消失了,仅仅作为一个在机器上发挥职能的固定部件存在着[7]。最终导致部分大学教师日趋成为“功能化的存在物”。
(2)自由思想逢迎于世俗权力。世俗权力源于校内行政化倾向和校外世俗权力对学校的延伸。从校内来看,一些大学学术权力明显的是依附于行政权力,甚至学术权力本身常常被同化于行政权力之中[8]。此外,世俗权力不断向大学渗透延伸,使得大学难以与世俗权力之间有效分隔,大学的专业设置、学科建设、课题申报、晋职晋级、经费、重要的人事任免等,无处不有世俗权力的幽灵在游荡作祟。“其控制下的学术关系演变为上下级关系,首长权力演变成教条,内部管理呆板,决策与行动困难。各层领导更多地只是关心本部门甚至自身的权利”[9]。
世俗权力正在不断侵蚀着大学自治,挤压着大学教师精神健康培育的空间。大学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其存在的主旨,大学教师应该是守护大学求真精神的核心,而地位与权力的争夺使教师丢弃了高尚的灵魂,导致了教师的官本位倾向。如今,大学教师开始偏离本应行走的正确轨迹,将耐住寂寞、潜心研究的精神丢掉,走向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道路,最终远离了自己的学术道路。一些研究人员为了职称、权力而进行的快餐式学术编撰活动,一年可高产数十本专著、教材或论文;或者是低水平重复生产一些学术垃圾;或者只作“官样的研究”,甚至剽窃、抄袭同行成果,杜撰虚假数字或实验数据发表论文。他们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自我约束让位于自我沉沦和自我放纵,甚至逐步滑向学术腐败与违法犯罪的泥潭,玷污了学术的纯洁高雅,动摇了教育的道德根基,扭曲了社会的公平正义[10]。
这些丧失了自由精神的大学教师成为了扮演填充大学科研政绩数字的符号和工具,导致整体学术道德的急剧下滑。大学教师的个性才情等精神性力量被淹没于对世俗权力运行规则的适应之中,难以自由地追求知识与真理、独立地“为学术而学术”,研究氛围越来越显得急功近利,追求数量指标。“尽管我们不能小看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思想偏见、管理需要的巨大作用,而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全盘接受了它,习惯了它,内化了它,喜爱了它,会从思维上、语言上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它”[11]。为了迎合外部世界的各种外在化的诱惑,教师会掏空自身的内心世界,其独立思维也随之消弭,最终变得精神空虚。
(3)良知责任蒙蔽于媚俗文化。媚俗是指为顺应大众,对存在着的丑恶避而不见,刻意美化社会现实的一种态度,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回避,其目的也是为了迎合大多数人。媚俗文化源于精神的虚无,精神上的空虚使得人们厌倦崇高的使命、终极的价值、坚定的信念,大众就无暇关注社会的发展,仅仅沉溺于个人得失之中。他们缺乏独立的思想,以及责任感,只有顺应,只有对自我精神的主动抛弃。“这一大群人(the great mass)很少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去辨认事物,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照着别人所指示的”[12]。
公共生活领域本应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登场的舞台,是呈现大学教师社会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如今一些大学教师却愈发沉溺于琐碎平庸的事物中,回避公共生活,甘愿做一个温顺的奴隶。他们丧失了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为国家、民众利益批判呐喊甚至献身的精神,为正义、真理、美好的追求之情,表现得过于唯上、畏上而不敢言说、不能言说。现在的“文化精英的职责不是去培养公众的头脑,而是变成了对它的批准与赞颂”[13]。他们并未与世俗社会保持应有的距离,甚至依附于世俗权力,让大学也成了“社会大众文化的跑马场”,并没有发挥引领社会文化与精神发展的功能。公共的讨论与辩论也早已不见,剩下的只是温顺的服从。当下的教授已不是学问、学衔的标志,只是获得工资、待遇的一个资格而已。
于是,教师在公共场域的话语权被“他人”所控制或者垄断,教师在公共生活中的反思精神与批判精神消弭,教师的行为就成为了适应顺从“他人”的行为。首先,大学教师过分依赖于主流价值文化,其良知与责任被媚俗荡涤得一干二净,批判与顺应之间的矛盾必然使人们变得麻木。不仅主体性与创造力逐渐消失殆尽,导致自身的思维模式固化,还对人文精神价值及其传播产生极大阻滞。其次,大学教师成为一个容易被操纵的群体,不愿意对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作出判断,不愿意为真正的公共利益以及教育理想承担责任。更严重的是,人们“事实上在潜意识里早已心甘情愿地受人操纵——在被人操纵的过程中反而感到自己时刻处在各种新潮的前沿”[14]。
三、大学教师精神的解蔽
大学教师可以凭借自身在大学中所独具的地位与优势成为自我精神世界的创造者,提升教师队伍和大学整体的精神品质。如何使大学教师精神从工具主义、世俗权力、媚俗文化的世界脱离出来,如何解蔽被遮蔽的大学教师精神就成为每个大学、每个教师需要反思的问题。
(1)走出工具主义,唤醒教育爱。教育情感慢慢地被现实中的钱与权、欲望与贪婪这些强大的外力所摧毁。所以,我们需要让教师需脱离“工具主义”的囚禁,回归到充满爱的教学生活,其本质就是爱的回归。首先,教师要爱教学。现在的教学都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大学教师感受不到教学所带来的成就感与精神实现,这都是因为缺乏对教学的爱,割裂了教学与自我成长的联系。“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我完整”[15]。当教师把自己的职业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时,他才会感受到生活的完满与生命意义的充盈,他才会获得精神的自由。教师才能从职业中得到精神的提升,教师才会真正感受到幸福与美好的存在,才有足够强大的意志抵制物化世界的侵袭。其次,教师要爱学生。教师与学生就是在相互投入中彼此交流、彼此接纳、感受互动与交融,教师的精神也必定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得以生长。大学教师面对的学生都是具备独立思维和完整人格的个体,他们的知识、思维、活力、热情都会对教师施以隐性的影响。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换言之,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对学生饱含热爱的教师,自身也必定是有爱的人,教育爱就成为隔绝物化世界,阻挡钱权魅惑的屏障。
(2)消解官本位主义,享受自由生活。大学教师与大学环境共生,大学教师之精神立于学术自由之场域,教师需摆脱“官僚化”的枷锁,回归到自由的学术生活,其本质就是自由精神的回归。首先,从外部阻止世俗权力对大学自治权力的侵害,淡化“官本文化”,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假若一个大学没有独立性与自由性,便难以产生大学精神,只会沦为政治权利的从属与附庸。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贺麟曾有言,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而大学自治又并不是完全脱离行政干预,而是有边界的“限制”。大学既需要社会足够的资金投入,也需要社会给予大学足够的空间,大学不是世俗权力在校园的延伸,要保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以自身知识立场的方式及时深度地回应社会的需要。具体而言,就是需实现大学的分权,摆脱教师官僚化的角色错位。一方面,大学自己负责本校的管理,包括录取学生、设置课程、选聘教授、筹集资金、支付开支等。再将权力分交给院、系、教师、学生,使其在教学事务处理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大学里,教师才最有资格决定开设哪些科目、如何讲授课程、谁有资格学习高深知识、谁有资格获得学位、谁有资格获评教授等,学术自由不是专业特权阶层自我服务的需要,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是不能讨价还价的[16]。另一方面,推动校际竞争,实现大学的自我约束,进而净化学术氛围。竞争机制的引入既可以松缓高校与政府的联系从而削弱行政的力量,也可以迫使高校积极主动地规范自身。
(3)尊重高雅情趣,唤醒知识分子的良知。高雅情趣可以说是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基础的一种精英文化,它并不是疏离现实、非常态的艺术文化,而是源于现实、却否定、批判、超越现实的文化,其深层本质和核心内涵就是它对社会现实和当下生活的反思与批判。首先,于社会而言,并不是所有文化都需要市场化、简单化、平民化,都需要变得联系现实。高雅文化是一种能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品质的文化,是需要自由生长的文化,而不是加以外部塑造的文化。多层次的精神活动自然产生多层次的文化类型,社会需要尊重大众文化,也需要尊重精英文化。其次,于大学教师而言,更需要实现精神上的自治以抵御“顺应主义”的同化。大学教师需要良好的理性品质。批判并不是对现有公共生活领域的“纯粹反对”,而是建立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基础之上,通过理性和经验来判断,通过智慧与慎思来选择,为人类和社会的更好发展而作出努力。第三,大学教师应拥有对全人类的、整体的、普遍的一种关心,以关怀人性的视角看待我们面对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教师对社会的评判应是出于自身的良知,超越特定的阶级与意识形态,从人类的更高角度对社会制度、权利秩序等器物层面的存在进行反思与批判;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对过去或现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精神层面的存在进行反思和批判。大学教师不仅需要一个清楚的头脑,还要有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有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17]。
[1][黎]纪伯伦.先知:沙与沫[M].钱满素译.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3:17.
[2]唐松林,陈坤.不是顺应而是坚守:重温大学的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1).
[3][印]克里希那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灵[M].张春城,唐超全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81.
[4][以]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6.
[5][德]M·舍勒.价值的颠覆[M].罗悌伦,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1.
[6]李娜,万鹰昕.试论大学教师的学术素养及提升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2).
[7]姜勇.论教师的精神成长[J].中国教育学刊.2011(2).
[8]刘铁芳.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28.
[9]唐松林,张小燕,李科.生命论对机械论的检讨及其大学内部治理策略[J].现代大学教育,2013(5).
[10]范松仁.大学学术不端现象探源[J].大学教育科学,2011(1).
[11][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12][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286.
[13][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20.
[14][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66.
[15][美]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16][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8.
[17]智效民.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