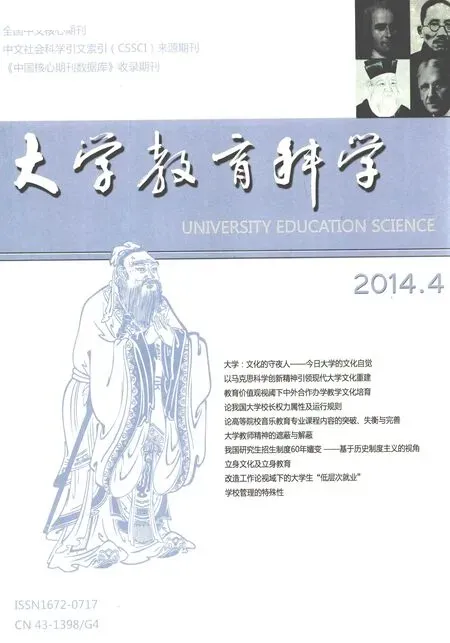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干预:范围、问题与对策
□ 冯君莲 张燕玲
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干预
高等教育资源既包括所有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与个体发展需求所必需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相关的硬资源,也包括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对硬资源的使用和开发所显示出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系统根据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一定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资源分配到高等教育系统中去,以实现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特殊功能。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与资源的配置;二是社会和市场出于自身需要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和投入;三是高校出于学术和教学的需要,如何争取各种资源,并对流入高等学校的各种资源在学校内部如何进行配置和使用;四是个体在一生中何时何地接受何种程度的高等教育[1]。显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四个因素的干预:即政府、社会和市场、高校、个体。在高等教育资金筹措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作为经费配置的两大核心主体之一,通常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的载体(学校) 和个体三个层面进行综合平衡, 研究各类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高等教育中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2]。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政府干预是指,通过政府职能的设置与转化,制定相关法规,建立相应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实施一定的改革措施,对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一定的优化配置。高等教育的政府调节机制具有宏观性、整体性、指导性、协商性、耦合性和灵活性[3]。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调控和拨付两个方面。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影响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通过财政杠杆和税收政策调节高校教育的运行;通过加大对相关专业领域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来某些解决专业人才短缺问题等等。提供信息服务也是政府对高校教育的运行进行调节的手段。政府不直接干预高等学校的融资事务和经济运行,但是可以设法保证高校办学经费在政府预算中应有的比例,开拓高校向社会筹集办学经费的渠道,解决高校财政上的困难,并通过拨款发挥政府对大学的导向作用。
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政府干预的应然范围
毫无疑问,政府应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之所以干预高等教育,是因为高等教育存在“邻近影响(外部性)”和对“不负责任的家长主义的关怀”[4]。同时,政府介入教育的前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在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各国政府都主动承担了对高等教育的调控责任。在我国,政府通过建立法律法规、平衡效率与公平、保证教育投入、提供教育服务等方法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进行干预。
1.建立法律法规
教育立法是促进教育功能实现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目的是把教育工作规律上升为一般的强制性规则,并以此调节教育法律关系,避免教育工作的随意性及其他人为因素对教育的干扰,从而为教育功能的实现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教育立法是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教育的运行进行调节控制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立法可明确高等院校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办学实体的独立法人地位,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明确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明确高校教育与各相关社会经济部门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法律来调节高校与社会的关系、行政机关与学校的关系、行政机关与教职工的关系以及学校与师生员工的关系等,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垄断和反对不正当竞争,确保高等教育在一个规范有序的制度化轨道内运行。但是,教育立法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立法数量,而不关注立法质量。教育立法关键是要理解教育活动的基本价值诉求,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复杂性,通过教育活动本身来决定并反映教育规律。否则,教育法律法规在实践过程中就难以得到执行和遵守,教育功能也就难以实现。
2.平衡效率与公平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经典的公共政策目标的权衡问题”[5],教育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的重要内容和延伸,其重要性曾被描述为“能够潜在地促进和提高整个社会未来福利和人力资本的增长”[6]。实践表明,政府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势资源和优势品牌的集中,有力地提升了我国高校的整体实力。政府不过多地插手学校的具体办学事务和管理,不直接干预高等学校的融资事务和经济运行,也使得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公平,从而更加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公办高校的教育资源主要是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和政策支持,而公办高校的公益性也要求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必须满足政府对人才的计划需求和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7]。教育的公共性也要求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以改善整体教育条件,以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的实现。我国国民人均收入不高,很多家庭经济上仍处于贫困状况,高等教育对这些贫困家庭已经造成经济负担,导致一些学生终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学业。因此,政府通过国家的力量建立公立学校,向社会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服务是政府保障教育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现代世界各国推行普及教育、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一项共同经验。
3.保证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广义上指政府对教育的人、财、物力投入,狭义上则专指政府的经费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8]。经济手段是政府向高等学校施加权力影响、渗透意志、获取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拨款权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根灵活的指挥棒。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是纯粹通过市场来运作的,公共财政拨款一直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从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量来看,政府目前仍然是教育投入增量的重要来源。政府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举办者,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手段,统筹各项收入,干预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教育财政支出。在前一轮高等教育大扩招中,因政府财政投资短缺,众多高校不得不采取融资手段,依靠借贷来兴建新校区、改造老校区、充实和更新教学实验设施,以满足正常教学活动的需要。时至今日,很多公办高校仍负债累累,办学举步维艰[9]。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教产品消费上的外资利益和生产上的外部经济,决定了政府必须负担高等教育投资的大部分以保证教育投入。
4.提供教育服务
高等教育服务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产出,学生消费它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了知识资本[10]。政府在干预过程中能为高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调查及现状公告、国际讯息、改革建议和咨询诊断服务等等。而在政府与社会的角色分工中,政府更加关注公益性、基本的、普惠性的公共教育服务,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各类社会组织也可向社会提供多样的、可选择的教育服务。政府通过信息服务,增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透明度,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教育市场的透明度,消除市场供求双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导致的资源的闲置,使现有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率和高等教育效率。而且,从国民经济宏观总体来看,政府提供教育服务也可以消除市场供求结构上的差异,促使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更加理性,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需要,从而使政府达到调控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也要求政府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使社会公众能享受公平、优质、多元的教育服务。
三、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政府干预存在的问题
我国建国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政府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高等学校的结构、类型、层次乃至招生、就业等均由政府统一调控,学生、家庭、学校无权问津。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造成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不足、增量无力、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使得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干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薄弱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重管理者权力赋予轻被管理者权利救济”等观念的影响,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程序性规范较少,现有规范漏洞较多,具体操作起来很难,可诉性相对较弱,配套立法严重滞后,下层位规范与上层位规范抵触现象屡见不鲜。当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政府的教育投入作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国家对于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过低。
政府对于学校的放权、将学校交由市场,更多的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非法律上的义务与责任,公共教育不但未体现为社会每一个人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务的性质,反而加剧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不平等。这归因于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责和法律责任,国家干预显得力不从心。政府未能对教育发展障碍和教育中的不良环境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监控,乱收费、招生与择校黑幕屡见不鲜、教育质量下降、高校巨额负债与教育腐败等等问题丛生,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维护,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2.资源配置重效率、轻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由于平均主义思想带来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国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且这一导向逐渐泛化到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社会其他领域,也成为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首要原则。因此,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便是协调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然而在整体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若普遍性地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让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追赶发达国家显然不太现实。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对资源进行重点配置,就成了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资源配置出现严重的“重效率轻公平”现象。
为了使现有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高校和重点学科。因此,国家选择重点建设的“211、985工程”大学的师资、设备等方面的条件都要优于普通高校,从而导致不同高校之间的竞争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11]。罗尔斯指出,“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该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不应受到他们的出身的影响”[12]。但是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过度聚集,地域失衡,薄弱地区人才外流、重点实验室“空巢”甚至被摘牌象,最终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这也直接导致入学机会不均等、教育过程不平衡、教育结果不均衡等一系列不公平后果。
3.教育投入有待进一步增加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一元化,国家和政府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这使得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竞争不充分。一方面由于国家办学的垄断地位,几乎不存在其他办学主体,使得不同高等教育办学主体之间很少有竞争;另一方面,公立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也不十分明显,高等教育“等、靠、要”的懒惰意识盛行,高等教育缺乏一种把高校的实际办学效益和质量提高与经费投入直接挂钩的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状况并不是很理想,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归结于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国家高等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中央与地方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均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需要增加等原因。还有学者认为,教育投入状况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是一项投资大、见效慢的社会事业,由于政府官员的任期制,一般都不愿意将财政收入增量投到不能立即出政绩的教育事业”[13]。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来自于社会捐助、学费等途径的投入在整个教育投入整体中仅占非常少的比例,国家在高等教育投入的操作步骤方面缺少可依据的法律规范;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财权相分离、不统一,教育经费的预算也未能单独立项等等,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教育投入状况不理想的原因。因此,增加教育投入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4.教育服务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政府为高校提供教育服务,即政府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教育经费、教育设施、设备和教学实践活动与场地,为教育消费者提供用于提高或改善受教育者自身素质,促进教育需求者人力资本增值的非实物形态产品等等。而教育服务职能的实现途径则更多的依赖于政府。我国政府重管理权力和秩序、轻权利和社会诉求表现明显。这种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一旦产生,就会过多地干预学术事务,而各种行政命令、政策、指示、规定等等也成为左右学术发展方向的“指挥棒”。如,除7部教育基本法和部门法外,10多部教育行政法规以及70多部教育行政规章(清理后)都是由行政机关制定,其中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立法占90%以上,体现出浓厚的对管理、秩序的偏好,对自由、权利的疏离[14]。
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过多干预高校资源配置不仅不利于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不利于实现其服务于高等学校的角色,而且阻碍了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党政为重心的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相应的改革,大学内部既没有建立起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会组织,也没有形成基层教师群体利益表达的民主化的制度渠道。这样,扩大的办学自主权,实际落入了本已十分强大的以党政为中心的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手中,导致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15]。而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对高校教育资源过多的干预。
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
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过度干预导致我国高校存在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弱化等现象,更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是基于学术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行政运作的需要。教育资源牢牢地被行政职能部门所控制,致使大量教育资源在与学术无关的事务中浪费了,学科组织的学术活动、教育活动难以顺利开展,高校自治难以实现。政府可以从干预目标、理念、行为和教育投入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
1.干预的目标取向由“重效率”向“兼顾效率与公平”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公平正义”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自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公共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以来,政府公共政策理念开始向强调公平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充分表明: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项最有效的工具,教育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要求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干预目标取向必须由“重效率”向“兼顾效率与公平”转变。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理念,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目标与促进高等教育效率的政策目标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第一,在制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时,政府应该把教育公平的理念融入到这些具体的政策与规定的制定中来,使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成为制定和规划各项教育工作的核心价值尺度和重要准则。第二,政府应该将教育公平的价值理念贯穿于高等教育的执行与实现过程中来,使实现教育公平成为执行高等教育政策与策略的重要理念和依据之一,使教育公平在教育政策的执行中由被动适应向主动思考转变。
2.干预的理念从“经验治理”向“法律治理”转变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对高等教育资源干预的过程中,倾向于根据已有的经验和法律来治理高校。在执行过程中,政府不敢有新的突破和创新,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提不高。如何使高校面向社会依法办学、真正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真正实现依法治校和使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真正实现依法维权等问题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笔者认为,政府干预的理念应由“经验治理”转向“法律治理”。将政府合理定位于有限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治理型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校的关键,这就要求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对相关问题做出具体的规定。高等教育立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发展高等教育、落实政府责任。政府应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行为法律调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困难,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有规律和法治规律为基础,建立健全高校教育管理中行政性和学术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有效实现大学的自律与他律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适度平衡,正确认识高等教育规律与法治规律的对立与统一,进一步健全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应该致力于政策创新,不能墨守成规,努力实现政府干预从经验治理向法律治理转变。
3.干预的行为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干预过程中权力过度膨胀,政府不是以服务高效为目标而是以管制高效为目标。政府过多地干预高校的学术事务,无休止地制定各种行政命令、政策、指示、规定等等,也严重影响了高校的科研能力,减少了高校的科研成果。因此,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治理机制,政府的干预行为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也迫在眉睫。建立服务型政府是行政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需要扮演的另一种重要角色。
政府为高校服务应包括制定有效的规章制度,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为高校提供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还包括政府为高校提供国内与国际教育信息,为受教育者提供信贷优惠等。服务型政府应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下,通过合法程序和公开民主的方式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职能的政府。政府权力与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个基本要求。同时,构建服务型的政府还要求政府以为高等教育发展服务为核心职能、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因此,在平衡政府权力与高校自治的过程中,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权力性的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政府实施教育行政行为,服务高校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4.干预中的教育投入方式兼顾计划与市场的平衡
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两大部分。政府投入包括拨款、教育的税收减免、专项补助、对学生资助等。社会投入包括学费投入和高校自筹资金,高校自筹资金又包括科技创收、社会捐赠及其他创收[16]。但是由于政府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和唯一投资主体,这就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方式的单一性结构现状,即以政府投入为主体,这也使得教育投入方式偏向于计划形式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干预中在投入方式上应兼顾计划与市场的平衡。
在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中,政府财政和个人支付是主要渠道。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拨款制度是平衡计划与市场的第一步。这就要求政府积极推进中央财政对普通高等学校的拨款制度改革,推行“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的拨款方式,以保证拨款的公平和公正;推动省级财政按有关生均标准对地方高校进行拨款,要按生均成本制定有关标准,使拨款量与招生数直接挂起钩来。可以成立专门的高等学校拨款机构,保证拨款的透明性、兼顾公平与效率,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学校的自主办学。第二步是积极调整高等教育社会投入有关的政策,包括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活动,满足社会对科学技术和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来提高高校的竞争力;努力使捐赠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来扩大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刺激公办和民办等多种办学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等等。
[1]赵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浅析[J].江苏高教,2009(2):45.
[2]鲍威,刘艳辉.公平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间差异[J].教育发展研究,2009(23):38.
[3]杨明.政府与市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28.
[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93.
[5]范先佐.关于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的抉择[J].江苏教育,2009(5):78.
[6][美]Walter W.McMahon & Terry G.Geske,Financing Education:Overcoming Inefficiency and Inequity[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Urbana Chicago Londom,1982:137.
[7]蒋玉珉.中国公办高校资源配置问题的案例研究[J].教育研究,2009(1):102.
[8]臧兴兵,沈红.公共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21.
[9]潘懋元,别敦荣,石猛.论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与盈利性[J].教育研究,2013(3):37.
[10]赵雄辉.试论大学生的高等教育服务消费者身份[J].江苏高教,2007(1):51.
[11]唐小平,曹丽媛.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评估与重构——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3(3):56.
[1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6.
[13]范文曜,闫国华.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OECD与中国[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52.
[14]余雅风.教育立法必须回归教育的公共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114.
[15]茹宁.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高教探索,2011(2):89.
[16]马陆亭.试析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制度的改革方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6(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