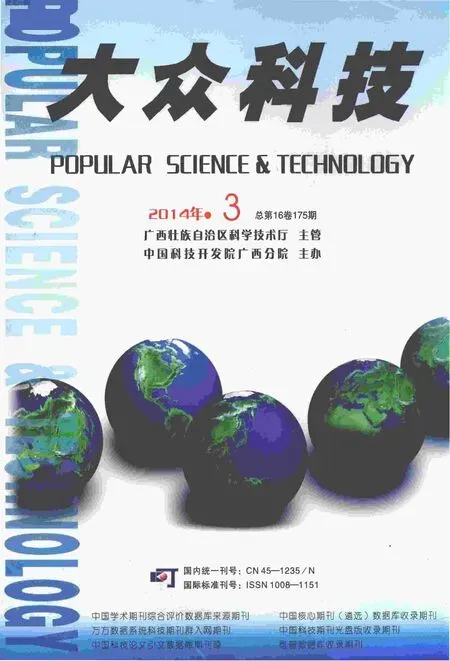略述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
(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2)
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从起家伊始,就带有浓重的集团主义思想。在复杂国民党内各派系关系中他们以武力为靠山,逐渐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并纵横捭阖,几度问鼎中原,由于受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制约,新桂系与中共之间呈现出特殊与复杂的政治关系。研究新桂系与中共之间政治关系,首先要弄清政治关系的本质。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作还是斗争,则取决于各自的利益关系。双方的政治关系也就经历了合作—分离—对立的过程。本文拟就新桂系在复杂的利益思想驱动下与中共的政治关系进行探讨。
1 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
两广统一后,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新桂系经常同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接触。这时,他们对共产党开始发生直接政治关系的,由于双方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利益是相同的,因此从1925~1949年期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的统一战线。
1.1 政治合作初期阶段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得到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援,于1925年统一了广西,并表示服从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觉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力量,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新桂系作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的下属省份,也自然接受同中共的合作。首先,就新桂系自身的利益来说,他们为了清除旧桂系的势力,有必要赞同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同中共作有限的合作,以便得到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1926年1月,国民党广西省一大召开,大会发表宣言称“奉孙总理革命之三民主义努力奋斗,继今以往,广西将划立国民革命之新时代,永远为中国国民党势力所依托之地。”其行动纲领是“提挈省民众向国民革命方面工作”等[1]这些,与中共当时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这是新桂系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姿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得以在广西得到发展和中共各级党组织在广西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许多共产党员能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县党部中担任重要职务,参加了国民党广西各级党部的工作,并担任了其中的一些执行委员、部长和干事职务。这标志着新桂系与中共合作在广西正式形成。由此可见,新桂系在这一时期,虽然他们对在广西出现的革命力量表示不满,但是对工农运动还是支持的,是容许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存在的,同时也为新桂系在基层建立自己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1.2 政治合作中期阶段
1933年4月,蒋要两广当局出兵赣南“协剿”,李宗仁授意前去围剿的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硬碰。1934年11月上旬,蒋给李、白发电令,要桂军在湘江堵截红军,以期桂军与朱毛红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广西。而李、白则在桂东北让出一条走廊,催促红军快走。早在1934年11月9日,李宗仁曾派刘少南为代表与中共代表吉鸿昌秘密接触,希望与中共达成某种协议:只要红军不进广西腹地,而李、白则让出一条路给红军过境。只可惜新桂系代表刘少南刚与吉鸿昌接头,就被蒋系特务干掉,而中共并不知道新桂系的这一意图,致使红军在突破湘江时延误了最佳的时机。李宗仁的这一举止,虽然是为了保存实力、防蒋吞并为日后争雄称霸创造条件,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但客观上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日后新桂系与中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可能。这其实也是新桂系在政治斗争上的一种试探性的举措。从此,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3 政治合作高潮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全民族共同抗战,新桂系与中共双方多在政治、军事活动中联合抗战,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新桂系建立统战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桂系与中共关系达到了蜜月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对此表示钦佩,并积极地与中共我党发生联系,公开表达团结抗战的政治意愿。面对外强入侵,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要剿共,而且要削弱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实现其独裁统治。新桂系对蒋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他们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主张。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理论、新政策,为新桂系与中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表明中共赞成各派政治力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蒋,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时的李、白出于反蒋需要,也寻求国内抗日力量的互相声援,于是1934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共产党员谢和赓到广西与新桂系接触。1935年8月,白崇禧、潘宜之邀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香港做抗日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胡兰畦到南宁,就如何进行抗日救国工作问题多次交换意见,探寻合作渠道和方式。1935年9月,又通过活动分子刘仲容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系,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同年冬,李宗仁、白崇禧为了联络张、杨反蒋,又派刘仲容到西北了解情况,刘仲容先到天津向我党汇报了李、白的动向,代表新桂系与我党取得了初步联系;次年春,刘仲容回到南宁,向李、白两人汇报了西安之行的情况,沟通了新桂系与我党的联系;中共对新桂系倾向抗日,表示赞赏。李宗仁当即表示:“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我们正在进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合。”[2]1936年6月1日,随着新桂系与蒋矛盾的日益加剧,终于爆发了两广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中共对“两广事变”予以支持,并派云广英为代表赴广西与新桂系协商,新桂系采纳了中共的建议,把“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新桂系以民族大义为重,向蒋表示了和平的诚意和抗日要求,蒋迫于各方压力和李宗仁握手言和。不久,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广西全省加紧动员征兵投入抗战,在两个月内,广西征兵十万人,组编 40个团的兵力开赴抗日前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新桂系在抗战初期,倾其全力,把三十年代缩衣节食组建起的空军和军事工业全部移交给国家抗战,任中央调遣。正如李宗仁奔赴前线之前所表示过:“仁等欣聆国策已决,尤庆请缨有路,誓本血忱,统率五路军全体将士,及桂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辞。”[3]
1938年3月,日军在津浦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在行前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白对周提出的实行阵地战的守势和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建议深为赞赏。后来在徐州会战中李、白基本采用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取得台儿庄大捷。从此给国内地方实力派与蒋记中央之间自“北伐统一”后连年纷争打了个句号。也为推动蒋下定决心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为“幸免战祸”而致李宗仁的亲笔函中写到: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这一时期,李宗仁通过寻求中共这个进步力量的合作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声势。
总之,新桂系与中共合作,这一切都不过是新桂系的伪装,在骨子里新桂系只是把与中共合作当作一种策略,一种手段,以增强抗蒋的能力,从而维持广西半独立的局面。
2 维护集团利益是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演变的实质
2.1 政治斗争的表面化
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不同而演变的,新桂系与中共之争实质是维护新桂系集团利益。新桂系虽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合作态度,但是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驱使,使得这种合作态度只不过是其与蒋系争天下的一种手段而已,每当他们感到这手段用得似乎有些反而对已不利或者与他们的政权不能相容时,他们就反过来不客气,共存的关系就消失只剩下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产生对抗性的政治关系。
1926年,随着北伐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在南中国蓬勃地发展起来,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势力,同时动摇了新桂系集团在广西的统治根基。当革命运动深入广西时,新桂系表现出十分的慌恐和“不安”,开始极力镇压广西的革命运动。在他们看来,工农运动是要为我所用,否则便是破坏和镇压。他们由早期加入国民革命时的“容共、支持工农运动”骤而转变为坚决反共。因此,当蒋介石筹划“清党”时,新桂系集团表现出十分地踊跃,积极协同蒋介石剿共。作为新桂系首脑人物之一的黄绍竑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东兰等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是我们参加‘四·一二’事变的主要原因。”“如果蒋介石不反共,而是另一个人反共,我们也会起来跟着走,甚至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4]
自1940年日寇撤出桂南后,广西境内三年间已无日寇的踪影。由于广西、安徽两省中共组织力量加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得新桂系统治阶层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于是当蒋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新桂系不仅参加了这些反共活动,还在事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1940年10月19日,受蒋的指使,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皓电”,诬蔑新四军破坏团结与抗战,强令我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1年1月6日,新桂系配合蒋发动“皖南事变”等等一系列反共活动。在广西,“八办”被迫撤离;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团体相继被关闭;1942年7月9日,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南委交通员张海萍等3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1943年玉林地区又发生“一·一三事件”;南宁地区发生“一·一五事件”等等,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充分暴露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战略意图。随后,新桂系配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10月17日,蒋密令桂军李品仙沿津浦线进攻苏皖解放区,新桂系军队开始参加蒋挑起的局部内战。1946年3月,白崇禧指挥国民党军队向东北人民解放军进攻,占领四平。6月下旬,桂军整编第四十八师参加了对中原解放军的合攻。9月下旬,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集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发动对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的进攻,李宗仁认为他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攻占解放区要地张家口,“是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
在广西,新桂系当局全力转入内战,进行战争动员,强化法西斯暴力统治,不遗余力地破坏和镇压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抗战刚胜利,黄旭初就到广州参加粤桂绥靖会议,随即两省纠集重兵联合“围剿”中共领导的高雷、钦廉和桂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1946年3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广西省国民党党部就发出“奸党三罢运动(罢工、罢课、罢市)对策研讨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对共产党的活动严密防范,以遏乱萌。1948年1月间,新桂系与湖南、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当局密谋成立联防指挥部,以加强的五省边区革命武装的镇压。2月下旬,新桂系当局令第一七四旅的主力分赴左江及十万大山地区,配合当地反动团队,围攻中共领导的人民游击队。此外,广西省内的各种民主势力和民主运动也遭到新桂系的打击和破坏,大批民主人士和爱国师生遭到搜捕迫害或驱赶。
由此可见,一旦新桂系集团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为了维护集团利益就立即站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从属蒋介石的反共、反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与中共进行殊死的斗争,以求获得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2.2 政治斗争的中立性
在合作中求生存,在斗争中又保持中立,是新桂系与中共政治斗争生存策略。新桂系为了保存实力,以军事、政治共同发展谋广西成为具有军事、政治一体的军事集团;对中共的政治斗争关系则采取留有余地的策略,为此新桂系配合蒋介石与中共制造军事摩擦的态度,并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懈怠、阳奉阴违、虚与委蛇。
1931年至1936年间,李宗仁一面抓紧建设广西,一面暗地里与蒋介石进行着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和斗争。正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们既要对红军作战,又要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特别是要提防蒋借剿共之机把我们吃掉。”桂系首脑之一的白崇禧认为:“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蒋)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4]在“皖南事变”后,白崇禧就曾十分苦恼地说道:“老头子(蒋介石)要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拒绝呀。”实际上,皖南事变中,李宗仁、白崇禧并未把他们的广西部队完全拉出来“讨伐”新四军。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事变后代表中央发表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明确提出,要“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顺祝同、司马云相三人”,而没有直接点新桂系白崇禧的名。[5]
国民党中央下令新桂系处置在广西的重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时,李、白则采取“礼送出门”的办法,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离开桂林转移到香港等地提供便利,甚至有的还从中加以保护。如:蒋介石曾亲自下令逮捕共产党员,《救亡日报》主编夏衍等人,桂系民主人士李任仁为了保护夏衍等人。通过电话对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说,当年我们与周恩来、郭沫若和夏衍有过约定,好来好去。如果不履行诺言,恐怕不好,并要求黄旭初想办法给夏衍买飞机票,送夏衍去香港,后来黄旭初一一照办。李任仁、黄旭初帮李克农、夏衍买飞机票离桂;蒋介石指名逮捕的邹韬奋、范长江则得到李济深掩护赴香港;重庆政府指令封闭的进步文化机关,广西当局采取限期自动关闭的办法,让其能够转移人员和财产等等。这些说明新桂系反共是有限度的,他们与蒋介石的反共是有区别的。
由此可见,尽管新桂系与中共不断制造事端,破坏与消灭共产党在广西的组织力量。但新桂系从集团利益出发的,即便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中,他还需要继续利用共产党,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仍然是留有余地,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综上所述,纵观新桂系与中共政治关系演变,我们清楚地看到,新桂系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集团主义利益出发,在战略和策略上,在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和打击谁等一系列问题上,就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和策略,推行与中共的政治关系,充分利用矛盾,争取矛盾一方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逐渐壮大和发展了自身力量。这充分反映出了新桂系与中共的政治热忱和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唯利是图、狡诈善变的政治本性。
[1]赵洪艳.试析新桂系联共思想的产生及其早期与中共的合作[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9(6):72.
[2]陈新建.抗日战争前期中共与新桂系统战关系初探[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6):66.
[3]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226.
[4]莫济杰.新桂系史[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65,313.
[5]王焕福,潘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桂共关系[J].社会科学家,1998年增刊:80.
——“桂系”农业“走出去”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