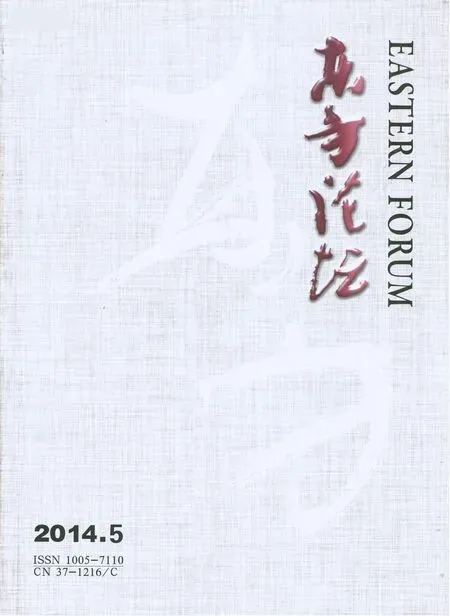莫言、诺奖、批评及批评的批评——对话《对话〈直议莫言与诺奖〉》
王金胜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莫言是当代中国最优秀、也是颇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在获诺奖之后,褒贬毁誉的各类文字频频见诸报端。李建军是一位颇具个性和影响,也由此引发了众多争议的当代批评家,肯定者、批评者皆不乏其人。如此二人,发生“交集”,原因自不难理解。李建军新近于《文学报》“新批评”专栏发表了《直议莫言与诺奖》[1](以下简称《直议》)一文,分析莫言获诺奖的文本内外的原因,从多方面对莫言小说、诺奖、中国文学提出了自己批评性意见。学者孟祥中针对《直议》 一文,在《东方论坛》发表《对话〈直议莫言与诺奖〉》[2](以下简称《对话》),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出于对作家莫言和批评家李建军的关注,笔者认真阅读了《对话》《直议》两文。总体感受是,尽管《对话》针对《直议》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结合莫言作品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但笔者并未看到一篇真正触及《直议》关键论题和问题的文字。这是很让人感到遗憾的,《对话》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并未构成与《直议》的切实而有效甚或有力的“对话”。
一、“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诺奖”“中国文学”及其他
《对话》开篇即提出一个问题:“至于说,诺奖‘颁给了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不是俨然学者玩起了超级大忽悠吗?”[2]作者进而“反唇相讥”:莫言获诺奖遭到了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的李先生的否定,作何解读?”[2]在笔者看来,这个《对话》不知“作何解读”的“超级大忽悠”现象倒是不那么难理解。当然,这需要返回《直议》,将相关话语完整地联系起来看,《直议》的原文是:“‘诺奖’终于在颁给曾经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之后,再次颁给了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1]这就是说,《直议》中所谓“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是跟前面“曾经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并举、相对而言的。若像《对话》一般,单摘出“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1]这一句不禁让人感觉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但若放回《直议》中,问题似乎变得就容易理解了。如此一来,反倒是《对话》的“反唇相讥”让人不知“作何解读”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直议》为何不直说高行健,而偏偏说“曾经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不直说莫言,而偏偏说“现在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偏偏绕着说?如果联系《直议》此后的观点和内容,倒也不难索解:《直议》对莫言、对诺奖持一种尖锐的异见,持一种严厉的审视和批评态度,其作者只不过运用了一种特殊的言说策略,一种让《对话》作者感觉“不舒服”的“带刺的油滑”方式来表述而已。
接下来,《对话》提出了《直议》中另一个貌似不合逻辑的问题,即在莫言已经获诺奖的情况下,李先生仍然认为诺奖“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将中国文学包纳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1]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理解的”思维逻辑,并质问:“诺奖奖给了莫言不算包纳中国文学?只有奖给了李先生推崇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才算包纳了中国文学?”[2]说实话,看到这里,笔者同样觉得奇怪:莫言小说难道不算中国文学?莫言获诺奖难道不是中国文学被世界文学包纳的事实?如果没有莫言或其他中国作家获奖,中国文学就没被世界文学包纳?……带着如此等等让人“难以置信”的问题,笔者“细读李文”,总算大体明白了笔者之所以觉得奇怪的缘由。其实,《直议》所侧重和强调的并非诺奖是否包纳了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诺奖是否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的问题。这同样需要照录《直议》原文:“诺贝尔文学奖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西方文学奖,而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将中国文学包纳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1]就笔者的理解,《直议》的意思是,诺奖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学奖而非它所宣称或多人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其背后有西方人的眼光、视角、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通读之下,就会发现《直议》是在文化的同构与否和“语言的可转换性”这个大问题之下,提出这个问题的,按照《直议》的说法:“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的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各不同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1]此为原因之一,可概括为“美文不可译”。原因之二,就是《直议》第一部分最后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就是一个不具有广泛包容性和绝对公正性的文学奖项。”[1]
二、一则莫言杜撰的语录与《直议》的“修改”
莫言曾在《天堂蒜薹之歌》初版的卷首,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在《直议》中,作者将其“修改”如下:“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政治却自己逼近了小说。小说家总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却忘了想关心人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1]
《对话》 认为莫言所撰“语录”“没有任何毛病,不仅如此,而且含义深刻,富有哲理”[2]。对《直议》的“修改”,《对话》认为“一句富有哲理的话经李先生这么一改,蹩脚味陡然而出,难脱画蛇添足之臼。如此颠黑为白,忽悠读者,匪夷所思”[2]。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直议》语境,来看看《直议》修改是否确为“颠黑为白,忽悠读者,匪夷所思”的画蛇添足。
莫言所杜撰的所谓斯大林语录,其所指应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悲剧”处境和命运,结合20世纪50-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和文学的具体状况,不难理解其具体所指性。
需要注意的是,《直议》“修改”后的话语其所指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化,其锋芒所指并不仅限于莫言所撰“语录”,而应该是《直议》作者所认为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的真正悲剧所在:小说家试图通过疏离政治的方式来保全自己,而政治却并未因此放弃对作家的紧逼;小说家关心自己的命运,试图维持自己现世的生存,却并未体现出对人、人类处境、遭遇、命运的思考和人道主义的悲悯、同情。用《直议》的表达便是:“小说家的主体责任:应该有所为的是人,而不是物;伟大的小说家应该勇敢地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仅仅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1]这才是中国作家和文学的真正悲剧所在。《直议》的表述的实质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精神和内在实质出发,批判中国作家和文学的思想力度和精神力度的缺失。这在《直议》中有进一步的阐释,如在接下来的一段中,作者写道:“他必须有自己对善恶、是非、真假的基本态度和鲜明立场,必须确立一种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体系,否则,他的写作就将成为一种游戏化的写作,成为一种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的写作。”[1]也因此,作者认为“莫言的写作似乎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基础,缺乏博大而深刻的意义世界。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的语境里,他无力建构一个批判性的叙事世界和积极的价值体系”[1]。
三、小说:自在之物?
在谈论“语录”的过程中,《直议》还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小说’作为一个客体的自在之物,怎么可能自己‘逼近了政治’呢?”[1]对此观点,《对话》是不赞同的,在孟先生眼里,小说作品显然不能等同于普通之物:“小说是有‘生命’的创作之物。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打上了自己思想的烙印,好的小说是呕心沥血之作,跳动着作者的脉搏,(按:作者在创作中?)全身心地沉浸在人物的悲喜苦乐之中。”[2]单从字面上看,《对话》的批评自有道理,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原理。但李建军先生所说是不是就“大谬不然”呢?依笔者之见,孟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批评也并不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原因如下:
其一,作为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将其视为一个创作主体(作家)创作出来,等待阅读主体(广义的读者和狭义的读者——批评家)接受、阐释的客体,是合理的。
其二,将此客体视为“自在之物”也有其合理之处。作为作家建构的艺术性再现客体,小说不仅在形式、句式、语言等层面均已固定,并与文本所指涉的客体(社会、历史、心理等)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或反射或折射、或再现或表现、或秉笔实录或扭曲变形等诸种关系。而且,作为客体的文本的意义结构也相对稳定,即使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永远也不会被解读为堂吉诃德、李逵或贾宝玉。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谓“自在之物”是否可以理解为,已经发表、出版而获得稳定形态的作品,自有其相对独立性?笔者觉得,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其三,尽管作品的确属于作家呕心沥血的产物,其中渗透着、涌动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但一旦作品被创作出来并进入发表、流通环节,其意义的生产(阐释、评价、发掘)则不完全被作者所控制,作品的“意义”往往溢出作家的“意图”,一部作品的经典性往往体现在“意义”的持续再生产中。如果作品的意义生产完全听命于作家,完全受作家阐释权利的控制、支配,则不会出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关于这一点,相信作为理论批评家的李先生和孟先生都会作为常识来看待。
那么,为何《对话》认为《直议》的看法“大谬不然”呢?笔者认为其间存在着《对话》对《直议》的误读。通观之下,可以看出,《直议》始终注重莫言小说文本与作家(创作主体)莫言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从未将小说家莫言与其小说割裂开来、区别对待,很显然,李建军先生从未将作品看做与作家无关的“普通之物”,《直议》所言:“‘小说’作为一个客体的自在之物,怎么可能自己‘逼近了政治’呢?”[1]所要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性,“他必须有自己对善恶、是非、真假的基本态度和鲜明立场,必须确立一种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体系”[1]。也就说,此“自在之物”既非康德所谓“自在之物”,也非孟先生所谓“普通之物”。 结合《直议》上下文,也许称之为“为我之物”更合适些,只是作者为着突出作品的相对独立性而策略性地使用了“自在之物”一词。因此,单纯地从《直议》中择出一句话来批判,其合理性是欠缺的。
顺便一提,《对话》本部分在说明作家情感对作品的渗透时,所举“在写到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口中有砒霜的苦味”[2]的例子,其当事人为福楼拜而非巴尔扎克。当然,这可能是个偶然出现的记忆性常识错误。
四、“叙事的平衡术”与“审美平衡能力”
这是《对话》在第五部分提出的《直议》中存在的又一个问题。
结合《直议》语境,可以看到,所谓的“审美平衡能力”,其内涵主要是指,莫言能否避免其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单向度地渲染一种情调和行为”,“清晰地区别美丑、雅俗、高下”,从而创造出“清晰、有力量的价值图景”。[1]可见,“审美平衡能力”属于小说叙事学范畴,是一个叙事美学问题。
这里的“审美平衡能力”与《直议》在第三部分所提到的“平衡术”所指并不相同。关于“平衡术”, 《直议》具体表述如下:“莫言小说叙事的平衡术实在太老练了。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就其内在的本质来看,是拒绝‘平衡’的,而是倾向于选择一种犀利的、单刀直入的方式来介入现实。”[1]同样置诸语境,此处所谓“平衡”“平衡术”所指的是世俗利害的考虑与小说叙事创造之间、美学与政治之间的权衡,作家的“聪明”、世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本体性矛盾。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直议》第三部分对《蛙》的解读,其主要观点不妨援引如下:“如果非要说莫言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那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软弱而浮滑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他善于发现尖锐的现实问题,善于表现冲突性的主题,然而,如果往深里看,你就会发现,莫言在展开叙事的时候,通常会选择这样一种策略,那就是,避开那些重要的、主体性的矛盾冲突,而将叙事的焦点转换到人物的无足轻重的行为和关系上来。”[1]概括地说,所谓“平衡术”的基本意思是,基于现实利害而在现实表现问题上趋与避的衡量。
其实,《直议》与其所引王彬彬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即都认为中国作家过于发达的生存智慧、过多的现实利害权衡,导致了其作品缺乏积极的思想力度和“意义深度”,而这与“真正的现实主义”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不属于孟先生所说的“自相矛盾的批评”:“两处批评,两相映照,彰显出批评家高超的语言艺术,把莫言玩弄于股掌之上,本来是自相矛盾的批评,在语言的花样翻新之下,似乎显得各有其妙。”
五、“思想”“感觉”与文学:关于莫言演讲中的两个观点
莫言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如此论及“思想”与小说艺术价值的关系:“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针对此言,《直议》认为“这里的判断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原因是:“在长篇小说叙事里,‘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思想的叙事,必然是浅薄而混乱的叙事,也就是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思想’与‘感觉’、‘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从来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同一关系。在真正的文学大师那里,感觉是渗透了思想力量的感觉,而思想则是充满感觉血肉的思想,——他们既是理性的‘善思’的思想家,也是感性的‘善感’的诗人。”[1]
《对话》则认为莫言的这段话“没有什么毛病”,《直议》所批判的实则是批评者自己设立的“两个‘假想敌’”。 《对话》将莫言的这一说法进一步归纳为:“小说写作过程中,理性力量不能太过强大,太过强大了,写出来的作品势必干巴巴的。”并认为“这不是莫言的创新,是老生常谈”,“写作不能忽视理性的力量,更需注重感性的力量,这有什么好非议的”。[2]
将莫言《直议》《对话》的说法逐一阅读、加以对照,笔者同样觉得《对话》存在着对《直议》观点的误读。需要注意的是,《直议》谈论思想与小说叙事的问题,同样也是在一个更大的问题之下进行的,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直议》第四部分的第一句话:“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1]《直议》引述莫言原文,其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一个批评的材料、例证,《直议》真正批判的对象是莫言写作(尤以长篇为著)中的“无思想和无深度”问题,而非《对话》所言“两个‘假想敌’”。《对话》所提到的“两个‘假想敌’”,一是“没有思想的叙事,必然是浅薄而混乱的叙事”,[2]另一则是“‘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从来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对立关系”[2](按:《直议》此句的完整表述为:“‘思想’与‘感觉’、‘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从来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对立关系”。不知为何《对话》在摘引这句话时,省略掉了“‘思想’与‘感觉’”)。在笔者看来,这两句话并未构成《直议》批判的对象,当然,莫言的话里也“根本没有李先生设定的这两个问题”。不知《对话》如何从《直议》中读出了“两个‘假想敌’”,也不知读者该“作何解读”?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对话》并未与《直议》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和交锋,后者针对的是莫言小说中的“一个致命问题”,而前者谈的是一般的创作理论问题。从内在本质上看,《直议》并未否认《对话》谈及的基本原理问题。不同层面上的交锋,犹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看似雄辩滔滔,实则并未产生出耀眼的思想火花。按照笔者的理解,《对话》似应对《直议》提出的关于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进行论辩和反驳。
莫言在谈及“思想”与小说艺术价值的关系时,顺理成章地谈到了“感觉”与自己创作实践的关系:“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1]《直议》在如此引述之后,作如下分析、判断:“就算小说写作的确‘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小说家也不能毫无边界地描写感觉,不能将人物写成完全‘感觉主义’的动物。然而,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就是感觉的泛滥,就是让作者的感觉成为一种主宰性的、侵犯性的感觉,从而像法国的‘新小说’那样,让人物变成作者自己‘感觉’的承载体。”[1]
《对话》则认为莫言的观点及其表述“也就(按:已经?)够全面的了”“已经辩证了”且“合乎只说正确大话的心理定势了”[1]。看到这里,笔者不禁为《对话》作者的质朴、实在而几乎哑然失笑了。难怪作者对李先生“在莫言没有说只要感觉,不要思想的情况下”尚且“强烈不满”、进而“一大串言过其实”的“指责”深感不满。
其实,莫言在“感觉”问题上的看法与对“思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且这并非其原创性观点,用《对话》的话说,就是这些看法基本属于“老生常谈”“正确大话”的范畴。因此,《对话》顺承这些“老生常谈”再加一些注释性的铺展,也并未生发出具学术启示性的观点。
关于“思想”与小说艺术价值问题,笔者还是比较认同《直议》的入思路径和基本观点。当然,这是一个极具阐释难度的论题,笔者学力有限,仅举几例,权作进一步深入思考此问题的契机。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似乎很少有国外作家谈及一个作家因思想过于强大而伤害小说艺术价值的问题,反倒是国内作家频繁谈及。这个反差,不禁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作家的思想已经过于强大而使小说艺术性大打折扣了,还是相反,抑或别的什么?
20世纪卓有影响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加耶夫在其代表作之一《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方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及其历史命运、地位,书中论及的重要作家也是思想家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赫尔岑、索洛维约夫、安德烈·别雷、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其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是无可争议的经典小说家,其代表性创作体裁主要为长篇小说。
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被称为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的以赛亚·伯林在其思想史巨著《俄国思想家》中也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俄国各时期杰出作家的思想、心灵、识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进行了全面而生动的分析。
无怪乎学者、作家曹文轩先生①曹文轩,作家,学者,评论家,著有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天瓢》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等。在阅读纳博科夫②纳博科夫,著名俄裔美籍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为创作于1955年《洛丽塔》和1962 的《微暗的火》,《文学讲稿》是其代表性理论批评著作。《文学讲稿》时“发现了一个残忍的对照”:“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除了写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外,还有相当可观的文学创作理论或文学理论方面的文字(鲁迅、艾略特都是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而我们当代的作家却大多只有几篇鸡零狗碎的‘创作谈’而已。这是文学素养方面的差距,上升一步说,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3](P218)就长篇小说来看,卡夫卡、昆德拉、加缪、马尔克斯、纳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托尔斯泰、索尔·贝娄等大师级作家的作品中无不包含着巨大的思想容量,卡夫卡、加缪的长篇甚至成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的作品则充满“一种特殊的文学情趣”:“这种情趣的特点是冷静,充分理性化,使用大量知识,带有形式化、技术化倾向。”[3](P216)而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与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创造性贡献是分不开的,与其作品思想的深刻度和文化蕴涵的丰厚度是分不开的。当我们看到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先锋性、反叛性、实验性的美学实验时,当我们为其形式的复杂、晦涩而感到难以卒读时,是否会想到在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品背后恰恰包蕴着作家们对当下人类更复杂、更难以索解的内在和外在的生存图景和困境的深度解读和整合性把握。恰恰是这些构成我们理解上的障碍或被我们所轻忽的东西,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主导创作动机和叙事资源与动力,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思想内质和叙事诗学的基本形态。
莫言的确“没有说只要感觉,不要思想”,而且,据笔者推测,不仅莫言不会说,“聪明”的中国作家们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莫言的确是聪明的,“在一段话里用了三个不能‘太过’,设了三道防线”,但这些“正确大话”又有何益:何谓“思想太过强大”,何谓“想得太过明白”,何谓“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相信没人能真正把握其真髓吧。
相对于在“思想”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折中公允,莫言谈“感觉”时更有感觉。莫言认为对其“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批评是“赞美”,这是否意味着莫言“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直议》中这样的说法:“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就是感觉的泛滥,就是让作者的感觉成为一种主宰性的、侵犯性的感觉,从而像法国的‘新小说’那样,让人物变成作者自己‘感觉’的承载体。”[1]祛除《直议》的贬义色彩,祛除莫言自己的褒义色彩,对“感觉”的突出应该是莫言小说的突出特点,这一点相信任何读过莫言小说的人都不会否认,也早有文学史将莫言、残雪等作家放在“感觉主义”论域中分析。到底是褒是贬,应该是扬是抑,还有褒贬抑扬辩证分析,评论家应该享有以具体文本为依据,以艺术规律为评判准则的充分自由与权利。
遗憾的是,《对话》第八部分在关于“感觉”问题也并未展开实质性的有效“对话”。其一,《直议》对莫言“感觉的泛滥”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文本的阅读基础上,并非如《对话》所说“在莫言没有说……”的条件下。也即《直议》对莫言的批评尽管使用了莫言讲演的内容,但只是作为自己分析、论证的材料而已,它针对的是莫言小说中的“感觉”现象而非莫言讲演中关于“感觉”的说法。其二,《直议》批评莫言小说“感觉的泛滥”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所论述的是一个小说叙事诗学或形态学问题,而《对话》批评、阐释的则是文学创作发生学和文艺创作心理学问题,如其所言:“小说写作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文学写作从感性出发,这是圭皋。思想蕴涵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人物的成长,情节的发展变化逐步形成。不从感觉(生活)出发,从思想(概念)出发,那不是文学……”[2]换个说法,《对话》所论“感觉”是尚未以文本形式凝定下来的“感觉”,而《直议》所论“感觉”则是已经以文本形式凝定下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充分构成了小说文本叙事和小说叙事诗学的基本要素,成为批评家进行文学文本分析的重要对象。《直议》对《天堂蒜薹之歌》等的分析即属此种“感觉”。因此,两文所论同样是属于不同论域的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莫言谈论“感觉”的路径和方式与孟先生是一致的,即也是将“感觉”置于创作发生学和文艺创作心理学论域。就此来看,《直议》所说“就算小说写作的确应该从感觉出发”[1],就不应简单地像《对话》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李建军先生的“无可奈何地认可”之举,而是一种“姑且如此”、以退为进,重新回到问题论域的策略。因此,孟先生的批判,其效果,借用《对话》的说法,就是“再批判,除了强词夺理,不可能有奇迹出现,至多是抓鸡不成,落了一把鸡毛”[2]罢了。
还有一点,孟先生指出《直议》存在的普遍现象和突出问题是,李建军先生“自己把话说绝了”。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就“感觉”“思想”问题来看,就是李建军先生认为莫言小说“无思想和无深度”“感觉的泛滥”,若用“太过”句式转换一下,就是“思想过于贫乏”“过于放纵感觉”,且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二者有紧密的因果逻辑关系。从上述分析中,笔者认为《对话》显然忽略或避开了这一点。
最后,为求直观,让我们尝试着用莫言谈“思想”问题的方式,来模拟一下李建军先生如何谈“感觉”:“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放任感觉的泛滥,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毫无边界地描写感觉,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感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理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思想的话,势必会浅薄而混乱。”[1]试想一下,这段话有什么大毛病呢?这应该算不上创新,也许根本就是“老生常谈”吧。如果上述“感觉”模拟还不算离谱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那样说你就觉得刺耳,不能接受,这样说你就觉得顺畅、合理呢?为何会出现如此乖谬的现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思想”一下呢?
六、李建军的莫言批评、莫言获诺奖
据笔者对《直议》和《对话》的阅读,总感觉《对话》存在诸多对《直议》的误读之处,其批评看似有理有据、义正辞严,但时有批评错位的别扭感。其中原因,除了分裂语句,脱离论述语境以外,还有就是《对话》的批评尚未顾及《直议》作者的莫言“批评史”。
鲁迅先生曾如此谈及微观文本研究:“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4](P220)因此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4](P225)据此来看,《对话》在“摘句”时存在割裂《直议》论述完整性的问题,存在未顾及《直议》“全篇”即上下文语境的问题,还有就是未能顾及《直议》作者“全人”即其批评理论、方法、立场,尤其是莫言“批评史”问题。
限于篇幅和论述的重点,本文将不对《直议》作者的文学批评做整体性的分析评价,而仅谈谈最后一个莫言“批评史”问题。《直议》作者对莫言的批评可谓“其来有自”且“源远流长”。即以《直议》所重点分析的《檀香刑》为例,作者早在2001年就有《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5]一文,从文体、语法、修辞,叙事的分寸感、真实性,叙事模式、技巧等多方面批评此部小说,这篇文字也颇为作者本人看重并多次收入其论文集①就笔者所见,《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曾先后5 次收入李建军先生本人所著《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大象,还是甲虫》(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此文还被收入李斌、程桂婷主编《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关于《蛙》,作者也于2011年撰有论文《〈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6]。二文均早于莫言获诺奖的时间。在其他非莫言专题的论文中,李建军也多次对莫言小说提出批评。因此,尽管《直议莫言与诺奖》发表于2013年1月10日,却是作者一贯对莫言的批评立场、思想和观点的合理延续,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对于这样的基本事实,一个批评家是不应该轻忽的。由于这个被作者忽视的事实的存在,《对话》所说的“原本一个好端端的作家莫言,只因得了诺奖,一夜之间,大祸从天而降”[2]也就成了一个“假想敌”式的问题。也正是这个貌似很不起眼的“细节”被作者有意无意放过了,使得《对话》不仅会对不明就里的读者形成误导,更影响了作者对文中一些问题的判断,进而对文章本身的学理性、说服力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对话》在第一部分的最后,就对当代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指出《直议》作者逻辑思维的矛盾和混乱,并质疑后者:“自己如此的逻辑思维,怎么能激烈地批评他人不懂逻辑呢?”[2]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直议》原文,对此《直议》的表述是:“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有的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并不低。”[1](按:这是《对话》所说的“一方面如数家珍”),在《直议》的第五部分也即最后部分,作者又写道:“我们应该明白,从整体上看,我们时代的文学并不成熟,作家们的人文修养水平和文化自觉程度都不很高。我们要知道,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其实仍然是‘不配’获奖的。与‘别国大作家’比起来,我们时代的作家,其实仍然差得很远。”[1](按:这是《对话》所说的“另一方面”)。先看第一句,紧接此句《直议》列举了汪曾祺、史铁生两位作家,加上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北岛、王小波、韦君宜、丛维熙、陈忠实、路遥、章诒和、杨显惠、蒋子龙,数量已达11 位。而在此前,作者刚刚指出:“在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俄罗斯,也只有蒲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尔仁尼琴(1974年)和布罗茨基(1987年)五位作家获奖,其中蒲宁是流亡作家,而布罗茨基则已加入了美国国籍,实质上应该算是美国作家的。”[1]就此来看,这一判断是合理的。再看第二句,目前中国作家队伍之庞大,作品产量之高,可谓世界第一,但其整体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显然也不能让人满意,这也是事实。仅就《直议》中提到的作家而言,试问当代中国作家中,有几人能超过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巴金,又有几人能比肩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契诃夫、高尔基、勃兰兑斯、乌纳穆诺、卡夫卡、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在笔者看来,《直议》的这两个判断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即二者并非自相矛盾的判断。
除了上述所论,还有一些问题,如“思想”与“领导出思想”的“思想”问题、“思想”与“理性力量”及“说教”问题、“思想”与“概念”“观念”等问题;“思想”“感觉”与作家的主体权力关系的问题等等,都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姑且不论。
总体来看,《对话》因在事实材料的摄取上存在着轻忽之处,在分析、论辩的过程中存在着割裂《直议》论述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及抽离具体语境和跨论域批评等问题,并未顾及“全篇”“全人”,因而该文并未达到切实而有效的“对话”目的。
[1]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N].文学报,2013-01-10.
[2] 孟祥中.对话《直议莫言与诺奖》[J].东方论坛,2014,(1).
[3] 曹文轩.阅读是一种宗教[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4] 鲁迅.“题未定”草·七[A].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J].文学自由谈,2001,(6).
[6] 李建军.《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N].文学报,201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