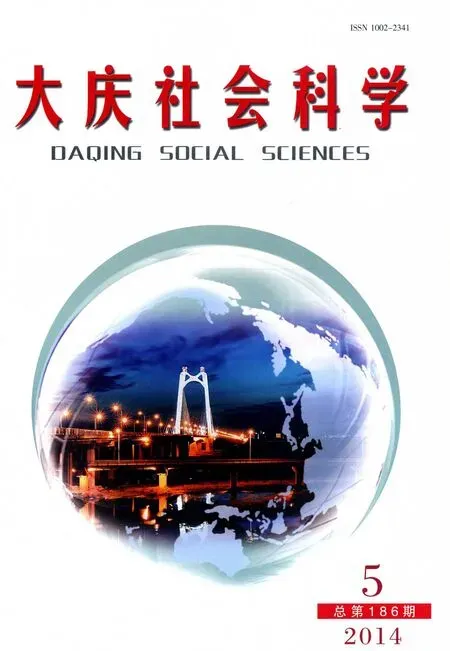18世纪波兰亡国的原因探析
陈 翔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位于中东欧地区的波兰是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的一个欧洲大国,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逾千万,居于欧洲第三位,在中东欧地区有着非同寻常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就是这个长期雄踞欧洲的强国,经过一系列的变故,在18世纪末期竟然灭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复存在。1772年8月,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瓜分波兰的条约,波兰失去了1/3的领土与1/3的人口。1793年1月,俄国伙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使波兰成为一个面积仅为2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00万的小国。1795年10月,俄、普、奥三国第三次达成瓜分波兰的协定,将波兰彻底灭亡,并长期消失在欧洲的政治地图当中。波兰的亡国有着鲜明的世界历史教训和深刻的国际政治启示。
一、不善的政权治理导致国内纷争不断
政权,尤其是中央政权的巩固与完善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强盛的重要保证,也是一个国家能力的重要检测器。16世纪以后的波兰,大力发挥民主精神和民主力量,结果过度化、极端化与变态化的民主形式导致波兰中央政权的治理能力弱化,国内纷争不已,地方割据在无政府主义的信条下猖獗蔓延。
14世纪时,波兰实行的是等级君主制,权力机构是由贵族、僧侣、市民三个阶层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没有明确的权力中心,权力分布较为分散,国王的作用和地位不明显。1573年,波兰制定并通过“亨利条例”,建立了贵族民主制,形成“自由选王制”。所谓“自由选王制”,就是取消了传统的王位世袭制,国王由大贵族自由选举产生。同时规定了国王的权限,即国王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会议,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擅自决定宣战、媾和、征税等重大事务,甚至连婚姻等个人事务都需要议会的批准。1588年的法律则规定国王和政府官员不能随意搜查贵族家庭。1652年,波兰议会确立“自由否决权”,宣称在议会投票时,必须采用全额通过的原则,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任何决议都是不能通过的。
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体现着波兰对民主精神的渴望和民主价值的追求,波兰也被看作是当时欧洲最为民主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贵族民主制带来的弊端与问题是明显和深刻的。“自由选王制”为国外大国势力的干涉与插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573—1795年,波兰共选举了11位国王,其中有7位是外国人,包括1573年登上波兰王位的法国亨利王子。[1]在此间,欧洲大国特别是法国与俄国,为了争夺对波兰的控制权,相互斗法。比如1696年波兰国王杨·索别斯基逝世后的法俄之争,为了争夺波兰王位爆发了1733—1735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63年奥古斯都三世死后的复杂局面并引来俄国的武力干涉。
同样,按照“自由否决权”的特定要求与相关规定,波兰议会的决议很少能够获得通过。在波兰第一共和国(1569—1795年)的最后百余年里,总共召开了77届国会,其中42届由于采用了自由否决权而被迫中断。[2]352在1652—1707年间,波兰议会召开过55次,仅仅7次通过相关决议,剩下48次作废。这使得中央权力部门的涣散,执政能力效能的低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普遍。中央政权的弱化,为地方割据发展势力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中央政府的有名无实,无政府主义的现象日益蔓延。地方贵族割据势力逐渐强大,并拥有军队、法庭和独立的行政机构。全国各地的大贵族只知道自己所在地区的利益,无视波兰国家的整体利益,甚至对波兰的国家危机和外部威胁也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在波兰面临瑞典、俄国侵犯之际,还有些地方贵族势力投敌卖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奢求政府通过均势外交博弈维护本国的独立地位和领土完整呢?
另外,在“黄金自由”和极端民主的制度环境中,波兰国内的政争是极为复杂和剧烈的。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和价值追寻,波兰国内大致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两派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强国策略以及国家大政方针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并引发带有国际背景的内战。1768年,法国支持的改革派在南波兰地区成立“巴尔同盟”,反对俄国支持的傀儡政权。这场内战不仅破坏了波兰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还引来了国际干涉,并最终导致俄、普、奥三国的瓜分。
二、不振的经济成效促使波兰国力渐衰
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与进步,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是国际行为的支撑,也是国际地位的保障。波兰在18世纪前后经济发展的不力促使其国力的衰退,并最终导致其亡国。
首先,波兰的劳役制庄园严重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活力的提升。农奴制在13—14世纪几乎全部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消失。[3]而在15世纪,波兰重新兴起劳役制庄园,波兰的多数贵族都拥有一个或几个村庄的农民,占地面积可达到60~80公顷。这种形式的农业经济依托对农奴和农民的掠夺与剥削,压榨农民的劳动力。而当时欧洲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已经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形式,商品经济已得到广泛发展,农民的人身自由与经济独立趋势愈加明显。这种逆社会发展潮流的经济生产方式导致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中断,更多的商人投资农业与土地并成为新的地主,自然经济趋势加重,资本主义的萌芽迟迟得不到发展,统一性的全国市场前景相当黯淡。在全国性市场形成不明朗之际,波兰的对外贸易出现严重危机。长期以来,农业是波兰主要的经济产出部门,粮食是波兰主要的出口产品,西欧是波兰粮食最主要的出口市场。17世纪后期,伴随着西欧农业革命的开展和灌溉技术水平的提高,西欧各国如英国与法国,基本实现粮食自给。严重依赖西欧市场的波兰面临着严重的外贸形势,同时粮食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俄国与英国的粮食产量和出口量的大幅度增长严重威胁着波兰的粮食出口。17世纪前期,波兰每年平均出口粮食为58,000瓦什特,17世纪后期下降到每年32,000瓦什特,18世纪初又下降到10,000瓦什特。[2]275这给波兰农业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波兰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受挫极大。
其次,波兰劳役制的“再现”招致城市的相对衰落,阻碍城市工业的发展。在西欧国家纷纷进行工业革命以及城市大发展的时候,波兰的城市显露出衰败之气,工业生产部门尽显颓势。波兰的“农奴制再版”剥夺了城市参与政治、使用农村劳动力以及购买土地的所用权利,城市商业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大批城市工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到农村与郊区谋求生机,波兰全国甚至出现城市农业化的怪象。以采矿业与冶金业为主的工场手工生产部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压制状态突出。更何况波兰缺乏普鲁士、俄国等邻国那样有着优良和发达的海港,从事商业贸易。此外,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的这百余年时间里,欧洲各国(包括西欧与东欧)纷纷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改革,寻求富国强民之策,并各自取得不菲的成就。而在农奴制泥潭中挣扎的波兰,毫无作为,我行我素,缺乏振兴工业和发展商业的有效对策,盛行于西欧且屡试不爽的重商主义政策始终没有成为波兰的经济国策。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欧各国,还落后于东欧的俄国、普鲁士等邻国。经济上的积弱不振必然带来国家综合实力的绝对与相对的下滑,为俄、普、奥三国瓜分和灭亡波兰埋下了经济上的根源。
三、不息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催生波兰的内忧外患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任何国家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需要面临的问题。尖锐的民族矛盾与严重的宗教争端是一个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重要因素。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加上不当的民族宗教政策促使波兰国内紊乱百出,并招致国外插手,最终将国家引入灾难的深渊。
民族问题通常与宗教问题是相互交织和相伴而行的,这在波兰体现的尤为突出。作为斯拉夫民族的波兰,在10世纪中叶的皮亚斯特王朝时期(大约960—1386年),开始信奉罗马天主教。后来随着国土的变迁以及移民的增加,国内的民族成分与宗教信仰逐渐多样化。居住在克拉科夫、波兹南、利沃夫等地的犹太人,说犹太话,信奉犹太教,占波兰全国人口的10%,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分布在格但斯克、托伦等西北波兰地区的德意志人,讲德语,信奉路德派新教。在小波兰地区,加尔文派新教的信徒较多。生活在立陶宛、乌克兰等地的居民,东斯拉夫人居多,信奉东正教。德意志人、斯拉夫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等族群之间的争斗不断,新教、天主教与东正教为教权、教义和特定利益辩论不止。
17世纪,伴随着欧洲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波兰国内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化,波兰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天主教徒有资格担当公职,“不从国教者”则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当时的波兰,“不从国教者”有两类,一是生活在波兰西北部的大约20万新教徒,二是居住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60万东正教徒。[4]338新的教规引起德意志人、白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的不满、抗议与斗争。原本相对安稳的犹太人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大部分特权被剥夺。遭到全国性迫害的犹太人被迫移民到俄国等国家,对波兰的政治经济发展又造成了相应的冲击。
波兰的民族宗教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严重的国际干涉,使得波兰“内忧”增加的同时,“外患”接连不断。瑞典、普鲁士等新教国家以保护新教徒的安全为由频频干预波兰内政,并引发一系列战争,如瑞典与波兰之间的1622—1629年以及1655—1660年间的战争。俄国在1686年与波兰缔结《永久和约》,波兰保证境内教徒的信教自由,打着维护东正教徒信教自由的幌子干涉波兰内政。其实,俄国等国就是在“信教自由”和“民族原则”的旗号下干预和瓜分波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信教自由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民族原则只是俄国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5]况俄国一直以来将斯拉夫民族的波兰当作“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控制乃至兼并之心长期存在。
可以说,波兰作为一个东西欧结合部的国家,一个东正教、天主教与新教交织处的国家,一个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等多民族国家,其民族矛盾与宗教歧异是必然的。一元化的宗教政策加剧了这种复杂和棘手的民族宗教问题,导致国内忧患不绝。外国势力的介入强化了波兰的危机与困境,并最终导致国家败亡的地位。这也应验了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的一句话,即“波兰终将会因为宗教冲突招致灭亡”。
四、不利的周边环境加快了波兰灭亡的进程
地缘形势通常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格局和基本生存状况。一般来说,近邻国家比远距离国家对特定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6]18世纪的波兰,所面临的周边环境是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是特别艰难的,主要邻国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都是实力远远在它之上、且扩张野心极其强烈的强国。
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最为重要的权力变更是俄国的强势崛起,并成为东欧最为强大的国家。在彼得一世的精心操作下,经过与瑞典长达21年的北方大战,俄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成为东北欧地区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1756—1763年战争之后,俄国权势的极度膨胀与法国国力的相对下滑成为此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结构性特征。俄国不仅有着恢弘的国力支撑,还有着强烈的霸权欲念。北上打败波罗的海霸权国瑞典的战略设想已经达成,获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国家目标已经实现。南下打击奥斯曼土耳其以及获取黑海出海口的设想正成为一种战略行动。于是西进赢取欧洲霸权就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国际战略。在西进欧洲的过程中,素来以“栅栏”和“篱笆”著称的波兰无疑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与绊脚石。也只有通过“波兰之钥匙”,才能开启欧洲霸权之大门。可以说,控制、占领、吞并波兰成为18世纪俄国大战略中的重要议事日程。波兰的衰弱为俄国的战略计划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1772年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之际,波兰仅有军队1.8万人,俄国则有35万之多。[3]340
普鲁士的崛起成为18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起于北欧平原的勃兰登堡(1701年改为普鲁士)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外交谋划与政治操作成为18世纪欧洲权力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作为“暴发户”型国家的普鲁士,源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国内浓烈的军国主义传统,对领土扩张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和极其强烈的动力。同时,面临着其国土的支离破碎,尤其是东普鲁士与普鲁士本土隔着波兰的领土,影响国家的行政管理与民族整合。在这种情况下,领土居欧洲第十位、人口占欧洲第十三名的普鲁士拥有欧洲第四大军队,并不断加强军备,强化训练。强军就是为了备战,身旁孱弱的“欧洲病夫”波兰已经一蹶不振,江河日下,为普鲁士蚕食波兰土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波兰的另一个强大邻国奥地利对波兰也是觊觎已久,谋取其领土之心一直存在。尽管历经30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及7年战争,哈布斯堡奥地利国力下滑趋势显著,但毕竟经营有道,仍然作为一个二流大国在欧洲大陆纵横捭阖。在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被普鲁士夺去发达的西里西亚后,奥地利急切渴望从弱邻波兰身上获得补偿,尤其是波兰的加利西亚成为奥地利急于得到的土地。
俄普奥三大强邻环伺的周边环境使得战略位置重要且国力衰弱的波兰显得弱不禁风和不堪一击。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瓜分是18世纪一个主要的政治风尚,是各国君主来解决他们之间分歧的一种合理途径。[3]334这种瓜分政治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均势传统有着极大的恶关联性。应该说,均势在近代欧洲国际关系演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广大中小国家而言,均势是一种残酷的原则。[7]俄、普、奥三国对波兰肆无忌惮的瓜分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中东欧均势局面进行的。而与波兰有关的英、法两国此时已将关注点转向国内事务和海外扩张,无暇也无意顾及东欧和那里发生的一切。波兰的灭亡就注定在这一常在机理的过程当中。
五、结束语
作为中世纪重要的东欧大国,波兰亡国的教训是惨痛的,亡国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政治上采用贵族民主制导致治理困境、内政不修与内乱不止;“再版农奴制”严重阻碍其经济的与时俱进和作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促使内外忧患不断,俄、普、奥等强大邻国的领土野心和霸权图谋使其周边环境极为不利并最终被瓜分和灭亡。波兰的亡国悲剧体现了无政府主义下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国弱受人欺、国衰被人压的国际政治常在机理和运行模式都蕴含在波兰的灭亡悲剧之中。
[1]高德平.列国志:波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4.
[2]Gierowski.History of Poland:1505-1764[M].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PWN,Warszawa,196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Baron J E,Edward D A.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8)[M].Cambridge,196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7-181.
[6]William C O,David S M,Fred A 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New Jersey:Prentice Hall Inc,1983:186.
[7]Harvey S,Benjamin A M.The Substance and Study of Bord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76,(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