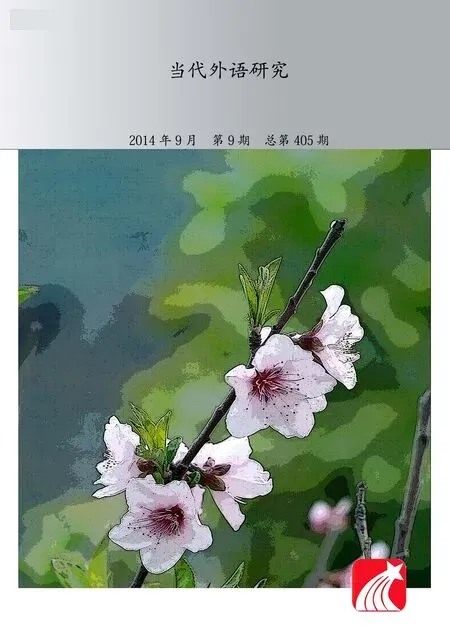湘·杜瓦
——异族舞女的主体性建构
吕晓菲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041004)
湘·杜瓦
——异族舞女的主体性建构
吕晓菲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041004)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缪斯”——湘·杜瓦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下“失声”,饱受审美中心主义者的认知暴力和霸权话语的操控,从而导致主体性的沦落。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黑色维纳斯》挖掘了湘这一被迫沉默的边缘女性形象,并赋予她话语权,解析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卡特对施加在她身上的殖民主义审美话语体系进行批判,重构了湘的主体身份。
湘·杜瓦,审美中心主义,殖民主义话语,主体性
1.引言
安吉拉·卡特1985年的短篇小说《黑色维纳斯》①重写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情妇——湘·杜瓦的经历,卡特了赋予这个沉默、受人摆布的女性以自主的力量。波德莱尔以黑人情妇湘为灵感创作了一组诗歌:《异域的芳香》、《珠玉》、《猫》、《长发》,然而湘本人的故事鲜为人知,她只存在于与诗人相关的表述中。卡特一直以女性主义者自居,积极投身妇女解放的激流,对西方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进行抨击,极力为失声人物发出声音,述说被掩盖者的故事。她重写了神话传说、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复述并编写了源文本故事,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为女性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一条重新定位自己的重要途径。与卡特其他作品不同的是,《黑色维纳斯》不仅赋予女性人物开口说话的权利,还涉及对东方/西方这一二元对立思维的反省和批判。这要从卡特创作这部短篇小说的背景说起。
因为想发现未受犹太-基督教影响的文化是怎样的形态,1969年卡特用获得的毛姆文学奖奖金东渡日本(Munford 2006:51)。这与巴赫金所论不谋而合:我难以认识自我形象,需要借助“他人眼中的我”来达到对自我形象完整性认识(参见秦勇2009:89)。实际上,日本生活培养了卡特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包容。评论家洛那·萨奇(Lorna Sage)将卡特的日本之旅看作一个过渡仪式,在日本,卡特丢失了原来的她,找到了新的自我,在看待他者时保有自省的态度。置身于另一种文化语境,卡特的身高、肤色被日本当地人视为外国人,但她将异国身份、他异性和男性激情的对象结合起来,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性别问题:“我的女性意识由旅行者引起的身份冲突铸造而来,我的政治意识也因此而来,那是个痛苦又有启迪意义的过程,被看作不同肤色的人,先被定义成高加索白人然后承认你是女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并非白人,因此没理由尊敬和爱戴他(她)们”(参见Munford 2006:62)。她在自传体短篇《一份来自日本的纪念》中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在日本情人眼中“神秘他者”的形象:“我变成了某种凤凰,某种神话中的兽,是一颗来自遥远异地的宝石。我想,他一定觉得我充满无可言喻的异国情调”(卡特2010b:10)。对卡特来说,日本是他者国家的纽带,不仅她将日本看作他者,在纯粹日本文化氛围中,她本人也被看作他者,是无法同化的外国人。如此,卡特从描述他者转而反观自身,体现了自省意识(self reflection),更新了自我认知,为描写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混血儿他者——湘·杜瓦奠定了认识基础。
2.异族舞女——他者文化形象的话语与书写策略
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显在东方主义”(Manifest Orientalism)②概念是一种“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所做的明确陈述”,一种表层的单个学科和文化产品。与西方相比,东方落后、堕落,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欧洲殖民主义表述系统中大量列举黑人的“异类化”特征,其本质是消除他者与自己共有的人性,从人种、文化和道德诸方面否定他者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19世纪与生物学根源联系在一起。人种分类学的追随者热情讨论何腾托人(the Hottentot)是大生物链上最低等级,从人种学上支持白人与黑人的固有差异(参见陈永国2009:334)。众所周知的何腾托维纳斯——萨拉·巴特曼在法国巴黎被裸体展览,死后也不得安宁,拜伦·G·居唯耶解剖了她的尸体,并发布科学报告,展示黑人女子和猿类的众多相似之处(参见吉尔曼2009:327)。自此,何腾托女性有了“科学的、权威的依据”,成为黑人女性的本质性代表。布丰评价了黑人的淫荡和像猿一样的性欲望,他说这种像动物一样的性欲如此强烈,导致她们和猿交媾(同上:326)。这种以“权威”、“科学”知识语境展现的“显在东方主义”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种族差异,将黑人女性牢固地定位在白人男性的对立面。
西方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在“显在东方主义”话语链条中“贡献”了自己的“科学”认知:《论外行分析》(“Essays on Lay Analysis”)一文用“黑暗大陆”一词把女性的性形象与殖民地的黑人形象联系起来。其意图正是要探索这个隐藏的黑暗大陆,解释女性性行为的真理,好比人类学家揭示黑人本质的真理一样。将女性身体比喻为“黑暗大陆”,喻指不可捉摸、不可知的神秘领地(转引自陈永国2009:340)。19世纪欧洲殖民话语体系中,黑人女性不仅代表被性化了的女性,而且代表堕落和疾病的来源。正是这种不洁净和疾病组成了女性的两种形象,即黑人与妓女的最终联系,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他者身体差异的内在恐惧。博尔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话语经过层层浓缩成为:乌托邦,或无法无天的旷野;高贵的野蛮人或原始人;伊甸园或圣城。而不列颠——伟大的不列颠——则是这一切的主宰。殖民地的背景可以不同,但这种结构性隐喻不变,从而成为生生不息的“旅行的隐喻”,在殖民文学书写中表现为性别歧视主义及对于“他者”的疏离(参见赵稀方2009:187)。
如果按照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总结的异国情调书写策略,波德莱尔与同时期的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三种策略,凸显了“性感化”的加勒比海与埃及文化。一是“空间的断裂”,即呈现那些不同于注视者文化的异域自然风景;二是“戏剧化”,将他者的属性和文化变成舞台上的场景,以便更好地标示出注视者与被注视、被观察的“他者”的距离;三是“性感化”,在书写中支配他者,与他者建立暧昧关系,渲染肉体享乐(Pageaux 2001:180-81)。波德莱尔被湘吸引,觉得她新奇,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欲求对象,并为湘身上的香气着迷;福楼拜的艳遇对象——舞女兼妓女哈内姆身上散发的檀香在湘这里变成椰油香、麝香;诗人特意以她为原型创作组诗。但细读诗作,不难发现其中的气味描写、景物意象多是诗人的想象性阐释,明显受到“隐伏东方主义”(Latent Orientalism)的影响:“惰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则或多或少地永远存在于隐伏的东方主义中”。“就任何意欲对东方重要性进行表述的人而言,隐伏东方主义为他提供了一种清晰表述的能力(enunciative capacity)”(萨义德2007:260)。没有哪个书写、思考东方的人可以避免东方主义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制约(同上:264)。波德莱尔几乎是无意识地(当然是无法感触地)确信:“湘在蓝色大洋怀里有个瑰丽的家”(7),他在诗里写到:
悠闲的海岛,获得自然的恩赏
长满奇异的树木,美味的果实
妇女的眼睛天真得令人惊异
男子们身体瘦长而精力很旺……而那绿油油的罗望子的清香
在大气中荡漾,塞满我的鼻孔
在我心中混进水手们的歌唱。(波德莱尔2012:32-33)
湘作为波德莱尔的缪斯,作为一个“想象性替代物”启发着诗人的创作灵感,诗人幻想和她在慵懒的小岛上生活,岛上有镶着宝石的鹦鹉、棕榈树、紫色的花丛等等,一组异域风景展现在眼前。湘的头发、身上散发的“神秘”香气在成为殖民地岛国异域风情的代表,成为异国女子与生俱来特质的明证:“你一绺绺头发密布绒毛的岸边/我要热烈陶醉,陶醉在由麝香/椰子油、柏油混合的香气里面”(同上:36)。有关殖民地的异质性、柔弱性、怠惰性方面,欧洲白人艺术家在内容表述上大同小异。
萨义德(2007:264)指出,隐伏东方主义可以促成人们形成一种特别男性化的世界观,这体现在旅行家和小说家的作品中,男性艺术家带着性别歧视的有色眼镜考察异族妇女: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利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无休无止的欲望(其实是殖民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福楼拜对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的理解和描述与波德莱尔笔下的湘有异曲同工之处。哈内姆“粗俗得可爱”,情感上无拘无束,床上的虱子“令人恶心的臭气”与“身上散发的檀香”混杂在一起,代表着男性艺术家憧憬的“美妙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女性气质”(同上:242)。然而旅行结束后,福楼拜在信中记录道:东方女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她可以跟一个又一个男人上床,不加选择。福楼拜的态度反映了对待被殖民者的情感分裂和焦虑。在这里,文学作品为帝国主义创造出一种情感结构支持。西方话语对东方的表述,表露出一种深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指向“他者”性,既是欲望的目标也是嘲笑的目标。
波德莱尔也存在同样的含混心理,他曾发表过对女人的看法,认为她们“不完整的教育,以及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不胜任,极大地妨碍文学作者将她们视作家务工具和淫欲对象之外的东西”(参见皮亚2012:51)。在札记《我心赤裸》中,波德莱尔进一步评论:才智敏锐的人喜欢妓女胜过社交名媛,尽管她们都同样愚笨。在1851年的《正派的戏剧与小说》中,波德莱尔再次宣告:一般来说,诗人们的情人比卑鄙下流的低级妓女好不了多少。在1846年的《令人宽慰的爱情格言精选》中,波德莱尔无法抗拒湘对他的吸引,生动地体现了对“偶像”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愚笨乃是美之饰品;正是愚笨给了她们的眼眸这般沉郁的明澈,宛如黑黢黢的池塘,以这般油质的宁静,宛如热带的大海。愚笨里总是蕴藏着美;它远离皱纹,它是神圣的化妆品,保护我们的偶像避免像我们那样被思想啮咬,我们这些卑鄙可耻的学者啊!”(同上:53-56)
《东方学》详细描述了一系列西方男性艺术家的东方之行,有时“令人恐惧”但大多时间非常诱人的东方,如何作为他们的想象性替代物存在于东方旅行的记忆中。霍米·巴巴则抓住了隐伏东方主义对他者的幻想这一特征,引用弗洛伊德的拜物教(fetish)来分析“殖民类型”的心理机制:不是承认这种阉割事实,他们建立一个偶像来代替妇女阳具的缺失……恋物症患者既承认妇女是阉割的又否认这一事实,所以他们对偶像既爱又恨,它代表了阳具的在场和不在场。殖民主义者出于缺失和差异导致的焦虑,发明了“殖民类型”,把种族特征固定下来,描述成具有不变永恒的特征,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殖民主义话语中爱恨交加的暧昧、矛盾心理体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焦虑乃至妄想(贺玉高2012:74)。
3.湘·杜瓦主体性的沦落
湘来到宗主国巴黎,她“吃了很多苦头”(9),但我们可以确信——一个只会说克里奥尔方言的黑人女性在巴黎的生存境遇必然恶劣,她是斯皮瓦克定义的“属下”或贱民,她们没有话语权,不能表现自己,只存在于与波德莱尔有关的传记和诗歌中,被白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表现,成为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受害者。波德莱尔的传记作家帕斯卡尔·皮亚(2012:54)对湘持贬斥的态度:“湘·杜瓦表现出据说是混血儿的所有缺点。奸诈、说谎、放荡、花钱无度、嗜酒,尤其是愚昧无知。与其陪伴艺术家,或许她更适合在卖淫界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居唯耶解剖了何腾托维纳斯——巴特曼的尸体,发布“科学”报告之后,波德莱尔写了首名为“居唯耶的判词”的诗歌与之呼应,所以卡特认为波德莱尔把这些“判词”铭刻进了“黑色维纳斯”组诗中(Gamble 2001:35)。维纳斯原本象征女性特质的柔美和纯洁,后来在文学艺术、神话中逐渐演变为妖娆、带来视觉快感和性诱惑的女性形象,而“黑色维纳斯”反映了维纳斯在种族、性别歧视的影响下在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形象再现。卡特十分反感男权文化构建的女性形象,比如胜利女神、缪斯。1985年接受凯伦·歌尔德沃斯(Kerryn Goldsworthy)采访时,特别提到了《黑色维纳斯》的创作思想:“湘·杜瓦本人并不情愿做一名缪斯,实际上,成为缪斯是她此生度过的一段最糟糕的时光。波德莱尔的朋友或传记作家都认为,他对杜瓦非常宠爱,然而实际上他压根没把她当人。我是说,你不能把缪斯当作实在的人来看待,她一旦不能激发你的创作灵感,就不能称之为缪斯了”(转引自Gamble 2001:155-57)。缪斯实质上是一个神化了的他者,是将女性放逐、排挤到边缘地位的方式之一,女性可以是男性艺术家灵感的来源,但是她们本人被禁止拥有创作灵感。在《黑色维纳斯》中,诗人总是带着粉红色羊皮手套来玩弄她的头发,湘的身体被男性目光化解为分裂的个体,诗人以湘为灵感创作的《长发》、《舞动的蛇》、《异域的芳香》进一步将湘“他者”化、客体化。
湘被诗人包养起来,为他跳裸体舞,以满足波德莱尔的视淫快感:“珍惜着他那好不容易激起的性欲”(14),成为劳拉·穆尔维定义的具有“被观看性”(to-be-looked-at-ness)价值的色情符码,被观赏者(通常是女性)担当男性欲望投射对象被赋予的视觉和色情效果,成为色情场面的中心主题,从脱衣舞到性感海报,女性凝聚着观看的目光,迎合并指向男性欲望。湘的舞蹈是诗人特意为她设计,“由一连串淫荡的姿势组成,妓院私房风格但不失品味”(8)。湘披挂着波德莱尔为她准备的手镯和珠链(人造赝品),被诗人制作成“东方化”的舞者,诗人观看舞蹈时总是西装革履,从不与湘共舞,对“他者”的疏离性显而易见。萨义德(2007:135)指出,东方被观看,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依照霍米·巴巴的观点,这种疏离行为重申了殖民者的完美自我身份,隐含了殖民者惧怕变为“杂交性”主体的心理。男性殖民者通过凝视黑人情妇的权利关系结构,似乎穿透了这些难以驾驭的不祥之物,恢复了理性的完美控制,消除了恐惧:“他们的关系中很重要的是,当她换上私密的赤裸服装,穿戴无关裁缝的首饰与胭脂,他必须保持十九世纪男性的公众装束,长礼服(剪裁精致)、白衬衫(纯丝料,伦敦师傅量身定做)、牛血色领带以及无懈可击的长裤”(21)。
而东方女性从不谈自己,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和经历。是他在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他是外国人,是男性,相对富有,正是这些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使波德莱尔、福楼拜之类的白人男性艺术家可以占有湘·杜瓦、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的身体,而且可以替她说话,告诉读者她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卡特挪用了男性殖民者的叙事视角,构建起一组二元对立:黑人/女性/自然和白人/男性/文化:“她简单的肉体,才是最可厌的作假”,“她的皮肤是公众财产,她是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物;他是人工的,是文化的产物……”(20)。
湘“最突出的特质是对任何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点来抽的东西抱着迟滞的怨恨。饮食、燃烧,这些是她的天职”(9)。她像猫一样懒惰,跳舞时并不专心,诗人有时也觉得她愚蠢无知,这显示了殖民主义话语的矛盾心理:一种既否认又肯定的态度,西方人与陌生的异域文化猝然相遇时所产生的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困惑感显露无遗。在卡特的文本中,被殖民异族女性与兽性和怪异行为等殖民主义类型话语再次联系起来。
日本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学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认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施行入侵和控制的施虐形式(sadistic forms)”,殖民主义最典型的暴虐是对他者进行审美至上的“尊敬和崇尚”,东方主义的特点并非忽视他者,而是在审美中“括除”(bracketing)他者,把东方从相关的历史和受压迫的现实中分离出来,对之采取审美中心主义态度,这样在审美之外仍然可以对其施虐和压迫,从而造成民族国家不平等的事实。而任何不进行“非括除”的东方观,都是唯美主义的暴虐(Kojin 1998:151-53)。诗人波德莱尔对杜瓦正是进行了这样的唯美化书写,一厢情愿地将她作为黑色维纳斯,满足自己对异国神秘情调的想象期待,“括除”了湘来自加勒比中下阶层、经济困窘、为小剧院跑龙套养活自己、在巴黎艰难度日等问题,只愿意看到一片异域的旖旎风光,环佩叮当的异族舞蹈,因为这些能满足艺术家淫欲的性感身体。萨拉·亚特(Sarah Artt)认为,卡特总是挪用男性殖民者的视角描述异族舞女,某种程度上成为“男性代言人”、父权话语的传声筒。笔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卡特在审美领域之外对湘进行了“非括除”(unbracket),其破除殖民主义审美暴虐的努力显而易见,“挪用”是为了“废除”③,“回溯”(the voyage in)到欧洲或西方话语体系中,与它混合,才能改变它,迫使它承认被边缘化或被压抑和遗忘的历史。在人物塑造上,湘代替传统小说的白人,成为女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现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经历。卡特的重写为湘赢得了话语权,使湘走上自我发现之路。
4.湘·杜瓦的主体性重构
卡特还原了湘的出身背景,首先排除了印度洋上的模里西斯。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或马提尼克——如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可能是湘的祖先居住地,异族通婚在当时很普遍,法国居民的情妇都可以脱离奴隶身份跻身克里奥尔的中产阶级,但卡特推断:湘的出身要低贱得多,可能是白人殖民者与殖民地黑人所生的混血儿:“她……纯粹是殖民地的孩子,是殖民者——白色的、专横的——播下她的种”(17),当地小孩骂她“黑母狗”,说明她作为混血儿存在身份认同危机,无法与宗主国白人认同,当地黑人也不认同她,将她看作异类。
霍米·巴巴提出,殖民者自恋式的被直接言说的要求,即他者应该认可自我、认可其优先权、实现其纲要、充分供应实际是重复其指涉并使其分裂的凝视静止(生安锋2011:98)。少数族的叙述权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它也表征着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被听到、被认可的权利。叙述权就是一种阐述权——一种对话的权利:即对众宣讲和聆听宣讲的权利、表意和被阐释的权利、叙说与被听到的权利(27-35)。卡特在文本中赋予湘抵抗性阐释的机会,抵抗在阐释的过程中发生。在波德莱尔构建他想象中的克里奥尔异国风情的时候,遭到了湘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嘲笑。诗人说湘的舞姿像条蛇,但湘打赌他没见过蛇,“根本没见过蛇的动作——那一整套横向的迅速击打……如果他见过蛇移动的样子,就一定不会这么说”(13)。湘拒绝回到诗人憧憬的殖民地岛国:“才不去那个鬼鹦鹉森林!别带我沿着奴隶船的路线回到西印度群岛”(7)。卡特笔下的湘并未感激这位包养她的诗人,因为湘的自我完整性被“爆裂成碎片”,被“另外一个自我粘在一起”;波德莱尔的“活动、态度和眼神”将她固定、僵化在殖民欲望的矛盾之中。但是这种企图压制湘的注视权利在湘的心中产生一种叛逆的渴望,进而发展为一种对立的注视。卡特在《黑色维纳斯》的创作中赋予沉默的女性说话权利和意识萌醒,被注视者回视、盘问观看者。湘原本作为客体被诗人凝视,被编码为淫欲对象和色情对象,作为黑色缪斯为诗人提供诗意的想象,但卡特的重写使湘拥有了独立主体姿态,回敬给波德莱尔一个他者的注视,对诗人强加在她身上的自恋式的殖民话语类型进行了抵抗性的解码。
拉康的“镜像阶段”为湘通过舞蹈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提供了理论依据:婴儿在6到18个月的时候进入镜像阶段,婴儿开始对母亲的身体产生敏感,因此对自己的身体有了认识。正是借助于对身体的认知,个体成为独立的实体。湘的觉醒正是从展示身体开始的,卡特笔下的湘不再是波德莱尔的“影子”情人。虽然为了经济利益沦为男性艺术家赏玩的客体,但她拥有主体意识,为诗人跳舞时哼唱着诗人听不懂的克里奥尔小调,时常走神思考自己的未来,想通过跳裸体舞养活自己,至少好过沦为站街女。湘的舞蹈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殖民窥淫癖的注视,更是为了确立她作为主体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黑人女性身体的定型性再现。波德莱尔作为白人男性殖民者的认知能力在此受到质疑和嘲讽:“他那双灵活明亮的黑眼盯着她披戴珠饰的肌肤,仿佛真入了迷,好个容易上当的笨蛋”(8)。贝尔·胡克斯(2009:377)认为,黑人也有能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仅可以“盘问他者的注视,而且可以回视对方,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命名”。
卡特让湘带着批判性的目光审视诗人的自恋与无知——“‘笨蛋’!她说,语调几乎是温柔的,但他没听见”(8)。波德莱尔的凝视成为湘体验自我完整性的参照,在被动中主动借助他人的视角,为认识自我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同时质疑、抵抗了来自白人艺术家的凝视目光。单向的权利关系结构通过“回视”成为一种协商、交流关系。白人通过权利使将他者再现为整体化的建构,而这种权利“完全超脱于我之外……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它的影响就像蟒蛇蜕皮一样可以摆脱掉”(生安锋2011:32)。胡克斯(2009:377)指出,“权利关系中的从属阶级从经验上懂得应该有一种批判性的注视”,那些压制从属阶级“他者”注视权利的做法只能产生一种对立的注视,并且在这种叛逆的注视中获取力量改变现实,改变从属“他者”的命运。
湘借助波德莱尔的外位视角,从他人对我的感受中感受自我。卡特在文本中让湘与诗人之间形成平等对话的关系,彼此印证了彼此的存在。“他一天到晚对她颂诗,使她疼痛,愤怒,擦伤,因为他的流畅使她没有语言,使她变哑。”(18)湘因为没接受过教育而被迫沉默,虽然她赋予了诗人很多灵感从而创作出灵动的诗篇,但她本人被拒绝进入语言体系,因此“那诗是对她永远的冒犯”(18)。虽然湘仍被迫沉默,说着不合文法的语言,但在与诗人的互动中已然察觉到差异和不平等所在,体悟到自己作为异国女性的存在,自我意识开始萌醒,时刻努力冲破反复论说被殖民地的话语模式。
但是,对于湘这样的“属下”、“底层人民”,获得自我的完整生存仅仅依靠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卡特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如果她反正得靠裸体跳舞为生,那她为什么不能靠裸体跳舞直接换来手中实实在在的钞票,赚钱养活自己?”(10)这个观点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圣经《第二性》中也有所体现,以往学者对这部著作的解读主要针对女性的社会建构属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但在这一解读中,波伏娃关于经济独立对精神自由的重要性论述被忽视了:女性在展现自己,获得崇拜者欣赏时,并不否认将自己奉献给男人的被动的女性特质,她让这种女性特质具有魔力,从而征服了超越性,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波伏娃2011:410)。卡特《受虐狂的女人》(TheSadeianWoman,1979)中对父权文化中的婚姻制度作出批判:“两性间的关系是由妇女对男性在经济上的依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的”,“所有为结婚而嫁人的妻子不过是通过契约的形式性交”。在《黑色维纳斯》中借湘之口道出:“在一个付钱的男人面前跳裸体舞跟在一群付钱的男人面前跳裸体舞没有何差别”。“卖淫是数目问题,也就是一次付你钱的人不只一个。(这里包含着伦理学的反讽)。”(9)痛快淋漓地批判了父权文化统治下婚姻制度的虚伪和对两性关系强加的道德限制。默里·布克金(2008:127-29)认为,父权制道德把女性降低为一种黑格尔式的他物,加以反对、否定、抑制。而等级制出现后产生的伦理学,是对人类主体作用的粗暴否认,是被“创造来辩护支配关系”的,是一种压抑下的道德。女性作为牺牲品,男性作为进攻者,被带入一种道德体制。然而,伦理学相对于它创造出来辩护支配关系的理性标准而言,总是脆弱的,“可能会引发反叛”。
在以现金交易为思想体系的社会,金钱意味着权利。由于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她们就失去了其他方面的自由。卡特以积极肯定的笔触描写卖淫者、妓女,强调了性关系本质上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经济权利达成合约,由此对父权文化关于妻子与妓女、婚姻和卖淫、道德和罪恶等传统等级划分进行了颠覆和挑战。波伏娃(2011:411)对金钱的观点更激进:“女人从自男人那里索取来的金钱和效劳中,找到对女性自卑情结的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甚至消除了两性斗争”。“当然这不仅出于贪婪,让男人付钱——这是把他变成一个工具。女人由此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工具;也许他以为‘占有了她’,但是这种性的占有是虚幻的;是她在经济这坚实得多的领域占有了他。女性集聚起来的金钱,保证了她经济自主,她们把自身作为客体奉献给男人,重新成为主体,并且提高了精神自由度。”卡特让湘在波德莱尔死后重返加勒比,靠自己之前积攒的财产,靠售卖诗人生前的手稿,过着富裕、体面的生活,这种对湘的美好祝福认可了妓女或卖淫女的生活权利。卡特让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打破了男性独享主体而女性沦为客体的惯例,支持女性,包括妓女和卖淫女做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主体。
5.结语
社会与自然多样性的观点,一种视“差异性”为多样性中的统一,转变为一种等级制心态,后者把十分微观的现象也排列为围绕着“低等”、“优等”概念确立起来的金字塔。等级制心态促动了人类对愉悦原则的放弃,它对“低等者”承担的辛劳、牺牲和“优等者”随心所欲的享受和纵情是一种袒护(布克金2008:9)。《黑色维纳斯》中湘被诗人比作“猫”、“蛇”等各种动物,被耻笑是个“巨型信天翁般的无知黑女孩”(18);而信天翁被看作“呆傻笨拙”的大鸟。女性与自然作为生命世界共同体的一部分总是被等级制心态驱动的统治逻辑所贬低、压抑、操纵,卡特对这种统治逻辑、等级制心态提出抗议,在小说中挪用“优等者”思维将波德莱尔也比作一种动物:企鹅。生长在在南极这个永寒之地,它们“穿着”和诗人一样的长礼服,但宠爱妻子的它们把珍贵的蛋托在双脚上,让妻子出外享受愉快时光,这段文字寄托了安吉拉·卡特解决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理想方式:“两性乌托邦”的理想王国。如果“爹地”——波德莱尔像企鹅,“我们会快乐得多,风是信天翁的归属,正如家是企鹅的归属”(19)。卡特并不想让湘处于“优等者”位置,从而嘲笑和讽刺诗人,而后用另一种统治逻辑代替以诗人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义逻辑,而是期待“女子和情人等待风起,带他们离开这阴郁的公寓”(18)。某种意义上,卡特构建的两性乌托邦具有一定的自由生态主义思想:希望自然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在一种新的生态感知和一种新的生态社会达成和解,实现自然与人类、人与人的重新和谐。
附注
① 文中小说原文的引文均出自卡特(2010a)。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② “显在东方学”主要指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始终处于变化中,“隐伏东方主义”指西方人始终不变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的视角,对待东方的强者心态。湘˙杜瓦虽然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并不属于中东、近东、亚洲地区,但是《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语境与不同类型的权利斗争都具有启发性,本文谈论西方/东方二元对立,并非仅建立在地理位置依据上,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霸权主义话语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框架内展开讨论。
③ “废除与挪用”源自《帝国反击》一书,由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提出,原指后殖民作家与殖民者使用的标准英语之间存在着“废除与挪用”的关系。“废除”是抛弃英语作为唯一标准语言的特权,“挪用”指后殖民作家对英语进行改良和创新,使它成为表达殖民地人民经历的工具。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回溯”也指代同一种行为。
Artt, S.2012.Ambulant fetish: The exotic woman in Black Venus and Master [A].In L.Phillips & S.Andermahr (eds.).AngelaCarter:NewCriticalReadings[C].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177-85.
Bhabha, Homi.2003.Differ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A].In R.Young (ed.).WhiteMythologies[C].London: Routledge.35-51.
Boehmer, E.2005.ColonialandPostcolonialLiterature(2nd ed.)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ter, A.1979.TheSadeianWoman:AnExerciseinCulturalHistory[M].London: Virago.6-7.
Gamble, S.2001.TheFictionofAngelaCarter:AReader’sGuidetoEssentialCriticism[C].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135-50.
Kojin, K.1998.Use of aesthetics: After orientalism (Sabu Kohso trans.) [J].Boundary25(2): 151-53.
Munford, R.(ed.).2006.RevisitingAngela:Texts,ContextsandIntertexts[C].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51-70.
爱德华·W·萨义德.2007.东方学(王宇根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安吉拉·卡特.2010a.黑色维纳斯(严韵译)[A].焚舟记[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3-27.
安吉拉·卡特.2010b.一份来自日本的纪念(严韵译)[A].烟火[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3-16.
贝尔·胡克斯.2009.对抗性的注视:黑人女性观众[A].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75-89.
波德莱尔.2012.恶之花(钱春绮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贺玉高.2012.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默里·布克金.2008.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10.
帕斯卡尔·皮亚.2012.波德莱尔(何家炜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0-60.
秦勇.2009.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桑德·L·吉尔曼.2009.黑身体,白身体:19世纪末艺术、医学及文学中女性性征的图像学[A].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22-44.
生安锋.2011.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蒙娜·德·波伏娃.2011.第二性(郑克鲁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赵稀方.2009.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玄 琰)
吕晓菲,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电子邮箱:lwf_xfy@163.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妇女解放路径的中国特色研究”(编号11BKS07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I106.4
A
1674-8921-(2014)09-0063-06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9.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