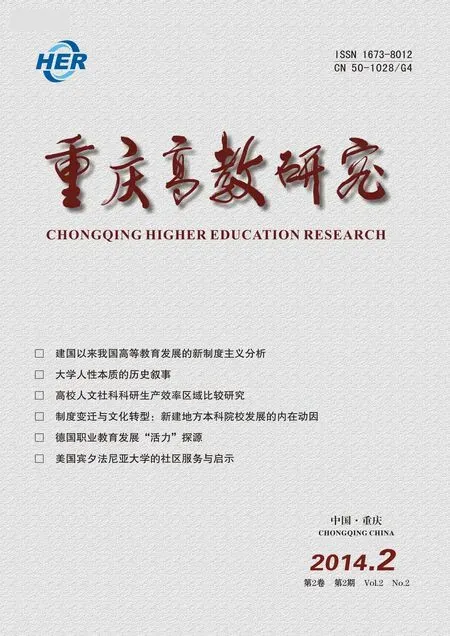张力与平衡: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
——读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平和光 ,傅 岩,孙龙存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是第一本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由美国的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于1977年写作完成。该书于1978年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被评为“1977 —1978 年度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推荐的杰出学术著作(1977 —1978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 Selection of Choice)”[1]。1987年,该书被王承绪教授翻译,后经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进到我国,对我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以及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发现,从1999年到2012年,针对该书的研究论文已有数百篇。在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哲学》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之后,本文试图从“张力”的视角出发对该书作一个解读。在解读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何谓“张力”。“张力”(Tension)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物理学领域,指同一物体两相邻部分的大量分子之间引力的总和在宏观上表现为张力。之后,“张力”一词被引用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比如,在心理学领域,“张力”可以指精神或情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在文学领域,“张力”可指两个事物的语词所代表的思想在特定语境下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不协调与不和谐,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从哲学的视角来讲,张力有三重含义:一是在矛盾中保持联系,即要把对立的两极联系起来,而不应该把两者割裂开来;二是在对立中进行互补,即在差异性中看到同一性,善于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三是在动态中维持平衡,即要使两极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使两者能够和谐、统一[2]。可见哲学领域的张力已被赋予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在任何其他领域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张力能成为人们分析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而本文恰是从“张力”的哲学角度来诠释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一、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张力
布鲁贝克根据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同,把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类是以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把以“闲暇的好奇”精神追求作为其目的,他们认为无论是高深学问的选择或传递,还是高深学问的批判或创新,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而不受学术价值的影响;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把“闲暇的好奇”精神作为探索深奥知识的目的,而且他们更强调知识的“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的目的,知识的最终价值是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可见前者的逻辑起点在于高深学问,后者的逻辑起点在于社会的需要,因此两者出现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其冲突根源在于 “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的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的问题。”[3]18世纪布鲁贝克认为两者冲突表现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统治美国的高等学府。在建国初期,美国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依据主要是政治性,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像德国大学一样重视研究),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开始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到19世纪末,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的大学里并驾齐驱,交替地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我们是不可能忽视政治论哲学的存在,因此如何在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保护高等教育的价值自由?如何去拿捏认识论和政治论之间的张力?布鲁贝克认为最佳途径是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为现实主义认识论的补充,即重视实用主义。唯有满足社会的需求才能赢得社会和政府的支持,才能使高深学问自身的本体性功能得到实现。但是,从本体论上看,无论认识论还是政治论都缺乏对生命的关注。康德说:“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目的决定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4]。雅斯贝尔斯说:“大学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参与者的天性[5]。我国的冯建军教授在本世纪初指出:“教育是因为人的生命而存在,生命的生长需要才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致力于生命全面而和谐、自由而充分、独特而创造地发展是教育的根本使命。”[6]由此可见人的生命存在与本性的发展才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高等教育的根基仍然在人,人本身是出发点,人本身是目的[7]。高等教育的使命就是让受教育者的人性得到充分而和谐的发展,实现由“现实自我”到“应然自我”的超越,从而获得新的生命。
二、高等教育服务的对象: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张力
精英教育指培养少数精英人才的教育;而大众教育则是相对于精英教育而产生的,美国教育家马丁·特罗以高等教育入学率为指标,把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当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于15%时,高等教育则处于“精英阶段”,超过15%时则进入了“普及阶段”,处于15%~50%之间则属于“大众化阶段”[8]。自大学产生一直到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高等教育的对象仅限于少数学术精英,能享受到高等教育体现的是一种特权。但从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不仅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对个人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起着分配作用。高等教育可以分配个人的社会地位,以致无数青少年觉得上大学是一种责任,从而迫使高等教育发生三大重要转变:第一,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第二,“教育特权”向“教育权利”转变,即“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向“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转变;第三,英才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因此,这三大转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高等教育是特权还是权利?到底谁应该接受高等教育,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假如高等教育向大多数人开放,如何维持高深学问的水平,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
对于这些问题,布鲁贝克在批判“平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两种水平的高等教育。布鲁贝克认为:“一所大学如果试图办成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万能机构,那不是骗人的就是愚蠢的。”[3]78因此不能期望传统高等教育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他主张建立一个包含了实行精英教育的尖子大学和面向大众的初级学院高等教育体系,这样的体系能够同时兼顾公正和平等。而初级学院恰是一种特别合适的机构,一方面,对于一些准备转读四年制课程的学生,它可以开设学术性学院前两年的课程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它还能提供咨询服务、补偿性训练和职业性训练,并且还提供继续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高等教育内部的双轨制。对于布鲁贝克的观点还是比较赞同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一项特权,每个人都应该有权享受高等教育,但由于个人能力、兴趣以及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因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证每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面前都享有均等的机会,确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对于弱者还要提供补偿性公平。在这个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保证各阶段、各层级间的畅通,然后根据学生的能力和过去的成绩鼓励学生从底层向高层转移,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来发展精英教育,从而使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和谐共存。
三、高等教育内容的选择: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张力
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译作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但区别于自由教育。普通教育强调传授根本意义的原理性知识,在赫钦斯那里这种知识指古典名著课程,在布鲁姆那里指组合课程,而在博克那里又指核心课程。普通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有价值的人。用卢梭的话说,“在使爱弥儿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他首先要使他成为一个人”[3]81;而专业教育,早在中世纪大学建立的时候就已存在, 主要是培养社会所需的医生、律师、牧师和官员等。但是专业教育的地位一直低于广博的教育。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专业教育才稳健地渗入到大学中来,这不仅体现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和职业教育中,而且渗入到本科教育领域。专业教育主要是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定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以便能更好地谋生,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即培养社会职业所需的高级专门人才。由此可见,专业教育是以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其价值取向,强调教育内容的专门性、职业性和实践性,其目标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各种高级专门职业人才;而普通教育是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为其价值取向,强调教育内容的基础性、普遍性和广博性,其目标是培养社会所需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人。两者可谓是一对矛盾体。
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人只能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而不能成为通才。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个难题:是应该进行普通教育而把专业教育留在专业教育阶段和研究生阶段进行,还是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大学本科同时进行?布鲁贝克则认为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马克思主义说过矛盾即事物的对立统一。因此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作为一对矛盾体必然也有统一的一面,表现为普通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基础,专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深化,恰如凯伦所说:职业是文化之根,文化是职业之果[3]95。一个人不仅必须为工作做好准备,而且要为可能的转变工作做好准备,因此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由此看来,布鲁贝克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却难以超越两者的对立从而在根本上达到更深层的和谐统一。其实无论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目标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本身上来。我国的石中英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事业,其价值不仅仅在于维持个体直接的生命活动,也在于使个体生活得更有意义、更高尚。”[9]教育只有使受教育者人性得到彰显,人格得到发扬,情感得到熏陶,视野得到拓展,能力得到提升,自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冲突,从而超越对立达到更深层的和谐统一。
四、高等教育基本学术价值: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张力
何谓学术自由,布鲁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美国哲学家胡克把学术自由定义为:“学术自由指的是在专业上够资格的人享有自由去探讨、发现、出版并教导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看到的真理。这种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听任何权威指挥,除非该种限制及权威来自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在那些专业学科中建立的真理或结论。”[10]对于大学来说,学术自由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是其生长的精神支柱。对于其存在的合理性,布鲁贝克引用富奇斯的话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富奇斯,1963)[3]46从认识的方面讲,即自由是追求真理和学术纯洁性的前提条件;从政治角度看, 即学术自由需要政治的保障,而这种保障主要通过法律保障才能实现;从道德方面看, 学术自由好像是学术专家的特权, 事实上,这种自由恰恰也是为了民众利益,因为高等学府是社会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机构,是社会了解世界的主要工具,并为人类改进自身生活条件提供资源。可见学术自由是追求学术真理的条件,那么是否意味着学术自由是绝对的呢?
布鲁纳则认为学术自由是受限制的,他认为假如学术自由毫无限制,就像经济上的不干涉主义没有限制一样成为灾难。而学术自由的限度之一就是学术责任,学术自由是建立在学术责任基础之上的自由,而学术责任是在学术自由的范围内所要承担的义务。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指出的:“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二者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11]用哈耶克的话讲,“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结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12]在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学术责任,布鲁贝克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从学术研究的规则来看, 学者有义务向社会证明其学术观点的正确性和客观性,而学术的结果由学者质问学者而不是政府;其次,从学术研究的范围来看(其本质涉及的是价值判断),对于可能威胁到人类生存后果的研究如干细胞研究、核裂变、生物基因的再合成等应该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假如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是否要对其实验的意外后果负有责任?但至少应该向同事和世人警告研究可以预见的危险后果;最后,从研究的过程来看,研究者要划清言论和行动的界限,同时要把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区别开。
五、高等教育的组织管理:学术自治与外界干预的张力
从中世纪以来,学术自治作为大学最悠久的传统之一,一直是大学自始至终孜孜追求的目标。何谓学术自治?我国的袁祖望认为:“学术自治指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机构的控制或干预,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付诸实施。”[13]学术自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本身自治,二是学术组织自治,三是学者自治。大学为何需要自治?布鲁贝克分别从理论上、实践上和法律上作了分析。从理论上讲,高深学问是超出一般性的知识、复杂性的知识和神秘性的知识,因此只有专家型学者才能够深刻的理解高深学问,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就应该让专家教授独立自主的去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从实践上来讲,如果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话,就应该让教师掌握学术活动的控制权。比如应该开始哪些课程以及如何讲授这些课程,谁最有资格来学习研究高深学问(招生),哪些人达到了毕业的要求,谁有资格成为教授,自己的学术自由有没有受到侵犯等等;从法律上讲,布鲁贝克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方面的自治实践已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例如:“在密执安州的一场诉讼中,州最高法院认为大学不受州立法机关控制(斯特林对密执安大学董事会诉讼案,1896)。”[3]32可见学术自治是由大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有了自治,大学才能健康发展,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大学自治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也许现在不是,但不是绝对的。”(黑瑟林顿,1965;考利,1980)[3]33英国高等教育家阿什比认为大学自治产生以来就受三种力量的影响和干涉,即政府、社会、大学自身的逻辑。学术自治为什么是有限度的?首先,绝对的学术自治一定会要求绝对的经费独立,这种程度上的学术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大学由于经费问题必然要接受政府、企业或个人的资助,一旦大学接受了这些资助,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这些力量所带来的附加条件;其次,在学术知识价值选择上,学者是否诚恳公正公平地考虑到民众的利益,谁来判断以及谁来监管他们;再次,假如学术自治过分集中,他们就有可能只关注学术本身而忽略社会和人的需求。由此可见,大学自治必然会受到外部的干预,那么大学该如何处理学术自治与外部干预的关系呢?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管理机构的组成人员可以由校外人士和校内学者两方面组成。因为由校外组成的管理者更能在代表公众对学院或大学的兴趣以及把这些院校的观点向公众解释清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校内学者又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以保持相对的自主性。“缺少了前者,大学就会信息不准;缺少了后者,大学就会变得狭隘和僵化,最后必然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3]37
六、结语
诠释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不是最终的目的,诠释过后所要深思的是如何理解、评价、拿捏和维持好高等教育哲学的内在张力的问题,以便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要在坚持认识论和政治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增加生命论的分量,高等教育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展现什么职能,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都要回归到人身上,因为人性的发展才是教育的最终追求;其次,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都属于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要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且要时刻关注教育机会的均等;再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的引领下发展普通教育,但必须把人作为两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学者要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但是在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更要主动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最后大学要坚持学术自治,尽量排除外界的干预,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大学只有把自身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人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Paul L, Dressel. Book re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by John S.Brubacher[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84, 55(4):529-531.
[2] 李醒民.两极张力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5-62.
[3]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4] 康德.论教育[C]// 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497-506.
[5] 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7.
[6]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3.
[7] 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04.
[8] Trow Martin.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M].Berkeley, Calif: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73:7.
[9] 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3.
[10] 眭依凡.学术自由理念与大学校长治校[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3):13-18.
[11]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桥,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
[12] 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7:83.
[13] 袁祖望.论大学自治[J].现代大学教育,2006(6):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