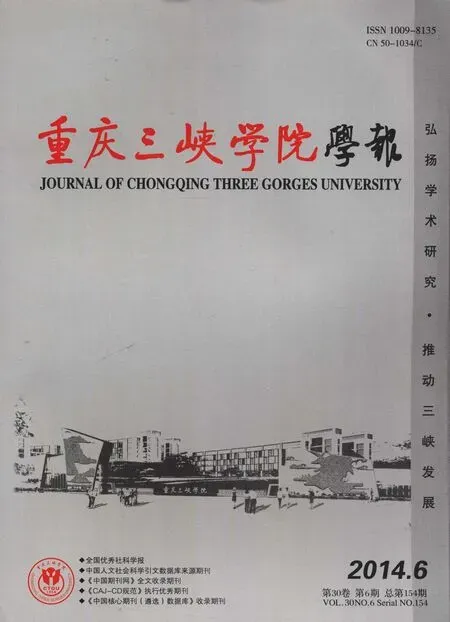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
——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为例
崔 璨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
——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为例
崔 璨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潮流,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在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潮的这段时间,以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其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以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为切入点,将小说中的家长形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梳理和分析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独特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透过这一新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问题小说”;家长形象;类型划分;五四运动
“问题小说”是典型的五四启蒙运动的产物,它(问题小说)探问人生的终极意义,观照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生存真谛。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问题小说”这一概念由周作人提出。在1918至1919年之间,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和《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借肯定日本近代“问题小说”的价值来提倡中国的“问题小说”创作,指出“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是尚未成立的,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一个重申说,一个特创新例,大不相同,并明确提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1]299。同一时期,沈雁冰则在《文学与人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评论性文章中写道:“现在热心于新文学的,自然多半是青年,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大力提倡“为人生”的“问题小说”。[2]周沈二人对于“问题小说”的提倡促进了此类小说的创作和发展。1919年初,北大学生团体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罗家伦、俞平伯、王志熙、杨振声、欧阳予倩、叶绍钧等人相继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作品,其中的《是爱情还是苦痛》、《花匠》、《这也是一个人?》等作品已开始显示出“问题小说”的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斯人独憔悴》,正式开创了“问题小说”的风气[3]47。“问题小说”也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和高潮,成为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学创作潮流。
一、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研究价值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将“问题小说”的主旨内容归纳为反思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是这样描写“问题小说”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从‘为人生’出发,创作的小说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4]164傅子玖《中国新文学》中将“问题小说”定义为“探索人生问题的小说”。[5]229钱理群、温儒敏等人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认为“问题小说”和“问题小说”作家是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而引出的,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明显的“为人生”的写实小说的倾向。[3]47毫无疑问,五四“问题小说”自其诞生之始便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其关注的范围自然涵盖了家庭问题以及由家庭问题所引发出的一系列家长和子女的冲突与矛盾。
近些年来,学术界的一些文学研究者开始更进一步地重视“问题小说”的价值,并有将其看作重要的文学流派的趋势。如郭仁怀认为:在评介“问题小说”时,要重视它的题材特点和艺术效果,不能一味去谈它探索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样有可能把读者导入庸俗社会的泥淖。[6]初清华认为“问题小说”作为文学革命后较早的小说创作实验,已涵盖了现代小说创造的思维模式,在文本形式上呈现出散文化倾向。[7]龙泉明也认为“问题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作潮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小说创作领域最初的社会性成果。[8]“问题小说”处理“问题”和“小说”的关系上已部分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近代小说。其他一些学者则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来探讨“问题小说”,在“问题小说”的“公共性”等方面得出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9]可以看出,对于五四“问题小说”而言,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研究价值,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问题小说”可以获得不同的研究结果。从家长形象这一新的角度来切入“问题小说”的研究,在内在思路上继承了五四“问题小说”为人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实际的文本分析中,家长形象的存在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为清晰的阅读参照,使读者能够更为精准地把握五四那个变革时代的精神内涵。
在分析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价值时,自然不能离开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称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10]6这场运动最为显著特征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用新的价值体系来取代旧的价值体系。以此便不难理解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的焦虑和挣扎。在五四这样一场剧烈的文化变动中,社会大众在新旧价值的接受与转换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而这种文化交替的内生性撕裂感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力和困惑感,使得他们带着严峻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的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问题小说”中的所谓“问题”涉及到了人生问题、家庭问题、婚恋问题、劳工问题、女权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等诸多在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可以说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上的主要问题纷争和流行思潮。
虽然五四“问题小说”所表现的“问题”有很多,但几乎所有的“问题”小说都涉及到了家庭问题。而在这些表现家庭问题的小说中,作者对于家长形象的刻画是较为丰富与深刻的。在一些作品中,作者是以显性的方式将写作的视角主动地投向家庭,批判了传统中国和那个时代的家庭中所暴露的各类问题,以启蒙者的姿态向那些蛮横无理的家长们做出了挑战。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和《两个家庭》、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庐隐的《一封信》等。而一些作品则是将家庭问题视为其他社会问题的附带品,借由其他社会问题的描写来被动地反思家庭问题。在这些小说中,家长们既是家庭悲剧的制造者,又是家庭悲剧的受害者。如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和后来发表的《海滨故人》、王统照的《沉船》、叶绍钧的《隔膜》、以及俞平伯为数不多的小说《花匠》等。无论是主动地暴露还是被动地反思,家庭问题是五四“问题小说”中最为显著的问题之一。而写家庭问题的“问题小说”作家中,又尤以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人为甚。
五四运动已过去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问题小说”中所反映出的一些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却依然存在着。五四“问题小说”所表现出的家长形象更是凭借着他们强烈的文化思维模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小说”来说,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都还有许多可以挖掘的内涵和意义。
二、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类型划分
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中,作者笔下的父母形象是多元的。他们(指“问题小说”中的父母)并不是完全以负面的封建卫道士的形象出现,相反,有的父母却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思想意识。如果以是否是城市人、是否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否能够接受新思想等因素作为区分条件的话,那么可以将“问题小说”中的父母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中,首先一类父母形象就是那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但拒绝接受新思想的城市保守派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在冰心的“问题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冰心的散文创作在文学史的地位要高于其小说创作,然而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进行“问题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对于其“问题小说”的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1919年下半年的《晨报副刊》上,年仅19岁的(当时还是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学校的大一学生)的冰心便发表了《两个家庭》。在随后的几年,冰心又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超人》等“问题小说”。在冰心的这几部“问题小说”中,其对父母形象的刻画是较为一致的。无论是《两个家庭》里的陈太太还是《斯人独憔悴》中的化卿先生,他们都是那种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城市人。从作者对于他们的描写来看,他们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如在《两个家庭》中,陈先生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家庭悲剧,“我屡次地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立地整理改良。”[11]19而化卿先生在干涉其两个儿子参加进步运动时也说:“要论到青岛的事情,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论理应该归与他们。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哪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像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地得罪了?眼看着这交情便要被你们闹糟了,日本兵来的时候,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仍是政府去承当。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你自己想一想,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报德?是不是不顾大局?”[11]26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指“问题小说”中的父母,下同)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并不似传统社会里的家长,开口之乎者也、仁义礼智(虽然化卿先生也有类似的话语,但考虑到通篇的对话,还是不将其作为主要话语方式),也是在用新式的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来说服自己的丈夫和子女。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出传统社会的家长制的窠臼。他们始终将未成年的子女当做是绝对服从自己的附属品,而没有将其作为平等的人格独立体来对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是贾政似的封建家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版。虽然我们承认他们对于子女也是充满爱意的,但是这种爱意却裹挟着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和对家庭权威的恐惧。在《斯人独憔悴》的结尾处,化卿先生在终止了颖铭、颖石兄弟的学业后,颇为得意地说自己已经为儿子们安排好了出路。他用牺牲子女自由的权利来获得自我的满足,用自以为是的道理来强迫子女接受自己的观点和思维,并且在实际行动上宣告了子女自由生活的灭亡。
虽然冰心的写作年代是在民国时期,但是以化卿先生为代表的父母们还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新思想。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者从阶级分析法的角度来解释化卿先生这个人物形象,将其定性为阻碍社会革命的封建保守主义者。可是在小说的叙述中,化卿先生是在新的民国政府里任职的大官。若是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者,这不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冰心对于化卿先生的形象塑造其实和鲁迅关于讽刺辛亥革命的小说(如《阿Q正传》、《祝福》等)有相同的理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社会仅是从制度名称上进行了改变,但潜藏在民族文化心灵深处的糟粕却没有发生改变。如果以人的现代性这一价值标准作为衡量尺度,那么“问题小说”中以化卿先生为代表的父母则无疑是穿着现代的衣服、却裹着一副封建传统心肠的人物。他们只是把“之乎者也、忠孝礼义”等词语变成了“不懂国情、难解民意”等在当时较为“现代”的说辞罢了。
“问题小说”中的第二类父母形象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乡下人或城市边缘分子,他们苦命地挣扎在生活之中,对于所谓的新思想则是完全没有自觉意识。对于这类家长形象,我们又可按照作者的褒贬取向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五四时期家庭问题的受难者,一类是五四时期家庭问题的制造者。
就五四时期家庭问题的受难者来说,首先要提的便是庐隐在小说《一封信》中的人物——萧妈。庐隐的这篇小说主要是通过对于天真姑娘梅生不幸遭遇的描写,揭示了万恶的旧制度对于贫苦家庭的摧残。小说中,萧妈为了葬自己的母亲,只得将自己的女儿卖给了当地的财主恶霸陈老爷。[12]11在作者的描写中,萧妈并不是以一个负面的形象示人的,可对于梅生的不幸遭遇,萧妈却也难逃其责。庐隐通过这篇小说,表达了自己对于贫苦人家的同情之情。此外,在王统照的小说《湖畔儿语》中,作者也借小顺这个孩子的遭遇,表达了对于贫苦家庭不幸命运的悲悯。在《湖畔儿语》中,小顺的父亲成了躺在席上不起的烟鬼子、后妈则为了生计成了在家接客的妓女。[13]36成人世界的肮脏与龌龊对于还是个孩子的小顺来说是莫大的伤害,而其父母则无疑要对这份伤害承担一定的责任。无论是《一封信》中的萧妈,还是《湖畔儿语》中小顺的父母,他们本身就是家庭问题的受难者。而随着他们的受难,他们的子女也连带着承担了苦难。可无论是萧妈还是小顺的父母,他们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抗意识,只是苦痛地承担着,或者是采取自我毁灭的方式来逃避生活的不易(如《湖畔儿语》中小顺的父亲)。在“问题小说”中,作者对于这种现象明显是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来描写的。庐隐和王统照等“问题小说”作家已经开始明白这苦难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他们自身造成的,但碍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于问题根源的揭示显得不那么明显和清晰。
而叶绍钧“问题小说”中的父母形象则表现出十足的罪恶之态。在叶绍钧“问题小说”的代表作《这也是一个人》中,主人公伊的生身父母、公公婆婆、丈夫等所有人都把她当成是一个物件。她在父母眼里,是一个可以卖钱的东西;在公公婆婆眼里,她是一个可以传统接代的生育工具;在她丈夫眼里,她则是一个可以发泄性欲的玩偶。[14]99伊在家庭里,完全没有自己的自尊和自由可言,她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我的意识,故而叶绍钧在描写这个人物时发出了“这也是一个人!”的悲鸣。在叶绍钧而后的小说《隔膜》中,虽没有直接描写家庭生活,但却借相逢、饮宴、闲聊三个场景的描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14]156
“问题小说”中第三类较为典型的父母形象是社会水平处于中等的城市一般市民阶层,他们能以平等的姿态来面对子女,也能够接受新思想,但对于新思想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庐隐的小说《两个小学生》中,国枢和坚生的父母就是这类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庐隐的小说《两个小学生》讲的是还处在小学阶段的国枢和坚生参加政府请愿的故事。在面对新潮与变革等问题的态度上,国枢和坚生的父母显得和前两类父母不太一样。他们不似化卿先生那般强烈抵触新生事物,也不似萧妈那样对于革命新潮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更不像伊的父母那样完全将子女当做是可以贱卖的商品。在小说中的一些对白能够很明显地反映出这些特征,如国枢的母亲在听说自己的孩子将要去参加请愿运动时,便表现出了十足的为难之情,她说:“这么点小孩子,也学管那些事。请什么愿?倘若闯出祸来,岂不是白吃亏了吗?没的吓得啊爹妈的心都碎了!”而国枢的爸爸则说:“他们学生去请愿,按理说只有有效没效罢了。断不至有什么意外的祸事,他既是一定要去,也就让他去,小孩子们也应该使他们锻炼锻炼。”此番争论之后,国枢的父母也都同意让他上街去请愿,但反复叮嘱其要小心。[12]15对于这类父母来说,他们了解新潮思想,也在心底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进步运动,但当面对危险丛生的街头运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时,他们就显得有些迟疑了。他们希望社会的变革能够发生,但是却不希望为这场变革流血的人是自己的孩子。
纵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对父母形象的刻画是非常丰富的。而对于父母形象进行刻画之后,其背后所蕴含的家庭问题也就显得十分明显了。无论是以蛮横姿态来阻止子女接受新潮思想的父母、或者是无视子女尊严、将其当做商品进行买卖的父母来说,其最核心的问题都是在于是否把子女当做是一个平等自由的人来看待。平等和自由是现代文明最为基础的价值尺度。因此,“问题小说”中所谓的家庭问题其实也就是人的自由的问题。在小说的语境中,这种家庭问题又具体地表现成了子女有意无意地对于人身自由的追求,对于个性自由的追求、对于婚姻自由的追求等众多子问题。
三、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新旧思想交锋碰撞的时期。处于时代变革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也会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之于其个人和其家庭的影响。这一时期,有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男女逃离封建家庭的束缚,选择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但也有很多青年男女在封建家庭与现代家庭之间徘徊不前。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作家多是一些青年学生和年轻教员,借由对家长形象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家庭观念。“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是作者抨击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个窗口,而家长形象本身则在小说构建中承担了描述历史的叙事功能。
从时代发展的横向来说,“问题小说”作家对于家庭问题的暴露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生活问题剧就大量反映家庭问题,而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更是在其著作《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即说:“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15]3对于家庭的理解是东西方都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五四“问题小说”作家也紧抓时代的脉搏,并借由他们的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于现代家庭的向往与热爱。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说,五四“问题小说”中对于家长形象的描写在无形中表明了作者逃离封建传统社会的决心。在传统中国,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长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传统中国视域下的“家”的概念是多元的,它不仅承担着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维护社会伦理、调节社会矛盾的类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功能。在一些封建皇权管制衰弱的地区,以宗族伦理为载体的家权辐射范围和实际影响力要超过封建皇权。马克思·韦伯就在《儒教与中国》中宣称:“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局限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威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16]110这一说法在后来被温铁军进一步地表述为“国权不下乡,乡下唯宗族,宗族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7]3虽然学术界对于家权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存在着一定争议,但是大家都无法否认家族文化对于传统中国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处在时代变革中的“问题小说”作家已经具有了觉醒意识,他们不愿意在传统家庭中压抑个性、接受封建伦理对自己个性自由的摧残。所以,部分“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正是代表了那个腐朽与衰败中的封建社会,而作者则通过对其的描写来间接地控诉封建传统社会对人的迫害。
在“问题小说”中,作者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来进行写作的。他们多以当时社会中的青少年为其小说创作的主人公,透过其遭遇的种种故事来反思各种问题。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很多时候是带着先行的姿态纳入到作者的写作中的,因而在人物的饱满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呈现出一定的脸谱化倾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五四“问题小说”作家的思想动向,他们虽未在作品中直接提倡该用哪种主义,却也在时代的洪流巨变中开始怀疑过去、思考未来,对于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一种极为不满的忧伤情绪。
从五四“问题小说”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上来说,小说中的部分家长形象确实代表了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然而,“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又并不总是以负面形象示人,有的时候他们是站在进步思想的对立面,而有的时候则是将信将疑地去试图接近进步思想。在“问题小说”中,家长们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处在变革与焦虑之中,对于家长形象的描写其实是作者在借家长之口来表达自我对于五四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而这一切又无疑给了读者们一种较为复杂的阅读观感,使得读者能够更为真切地理解“问题小说”及其所反映的各类问题。这种复杂的情感抒写反映出以“问题小说”作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者在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守旧之间的纠结与踌躇。透过“问题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处在时代变革中的人们在心灵深处处于挣扎和摇摆不定的焦虑倾向。
“问题小说”中的父母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父母形象的缩影,他们自身的思想以及对待子女的教育方式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虽然“问题小说”对于家庭问题的描写不似后来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那样来得猛烈与深刻,但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初创之作,其精神与意义也是值得尊重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还在无形中起到了启示未来的预测功能,这不得不引起文学研究者更近一步的重视。
不可否认,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中的父母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已经渐渐或已经离我们远去,那种板着面孔说教的封建式大家长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少。可是,“问题小说”中家长们的部分思维模式却坚硬地保留到了现在。在面对自我所做出的一些恶的行为时,越来越多的人们会选择用一种去正义化的思维来使自己释然,用社会上的大恶来原谅自己的小恶,通过这种方式来模糊真与假、善于恶之间的分野。在面对一些历史变革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谨慎而又狡猾的态度来巧妙地规避自己的风险。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中,有这些思想的还是父母,我们无法在五四年轻一代的身上找到这种影子。相反,我们从很多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是年轻人对社会的深切忧虑和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声声呐喊。但到了现在,当时的“年轻人”变成了“后来的父母”,“后来的父母”则又成了这代年轻人“父母的父母”……几代人过去了,这些思维模式却如同民族性格中的基因密码一般一代接一代地流传着。若是说到当今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问题小说”中的父母形象是否早就已经为我们埋下了伏笔。
四、结 语
从1919年到1924年间,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经历了短暂的创作热潮。毫无疑问,作为我国现代小说发轫期的作品,其小说创作在文学性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家并没有给那个时代开出明确的药方,只是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家庭中所存在的问题,多数作者借由这些问题来抒发作者的伤感之情,并以此来启发社会大众的深层思考。这一度也成为部分学者诟病“问题小说”价值不高的因素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较为纯粹地愤慨似写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文学的独特性和纯洁性,使之没有被诸如政治因素等外力绑架。
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的父母形象是多元的。对其进行不同的类型划分可以使读者更为清晰地把握“问题小说”所反映的家庭问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隐忧。而“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本身又在小说中承担着叙述历史、刻画当下与启示未来的三重功能,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小说”的文学价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读者重新去阅读五四时期涉及家庭问题的“问题小说”时,依然会觉得很真切。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成为读者的阅读障碍,反而成了激发读者沉淀和思索的触媒。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作家留给我们的难题依然值得我们理解和消化。
[1]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M]//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集(上).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2]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弢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傅子玖.中国新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郭仁怀.五四问题小说中的问题[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4):117-112.
[7]初清华.再探“问题小说”——兼论小说现代思维模式的形成[J].苏州大学学报,2005(4):63-68.
[8]刘勇,龙泉明.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出场——“问题小说”新论[J].江苏大学学报,2005(3):69-73.
[9]官志红,欧阳锋.论中国现代问题小说的生成及其公共性镜像[J].求索,2013(11):126-128.
[10]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
[11]冰心.冰心全集:第一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12]庐隐.庐隐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13]王统照.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王统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4]叶圣陶.叶圣陶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15]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16]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17]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Parental Image in the “Problem Novel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ing Xin, Lu Yin, Ye Shaojun and Wang Tongzhao
CUI CAN
(Wendian Colleg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The “problem novel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on it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climax to the ebb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uch authors as Bing Xin, Lu Yin,Ye Shaojun and Wang Tongzhao, etc expressed their deep reflection on life and social issues through their “problem novels”cre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arental image in the “problem novel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classifies the images into several specific types, and then carefully analyzes the parental image’s unique role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behind the “problem novels”. From this new perspectiv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in the “problem novel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problem novels”;parental image;classification of specific types; the May 4th Movement
I206.6
A
1009-8135(2014)06-0083-06
2014-06-20
崔 璨(1992-),男,安徽淮南人,安徽大学文典学院人文科学实验班学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