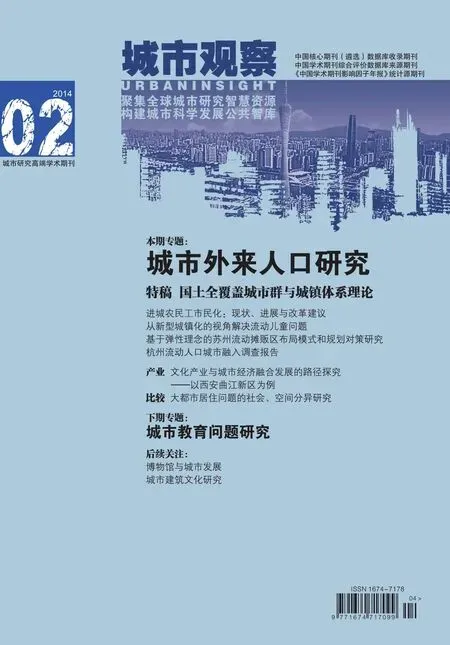移民融合与城市层级的定位
——有关移民研究中地方性问题的理论化
◎ [英] 尼娜·格里克·席勒 爱莎·卡格拉尔
移民融合与城市层级的定位
——有关移民研究中地方性问题的理论化
◎ [英] 尼娜·格里克·席勒 爱莎·卡格拉尔
本文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城市重构的理论化,建议用层级比较的方法研究移民的定居问题和跨国联系。通过提出“城市层级”的概念,本文探讨了后工业化城市重构的不同结果与移民融合的不同路径之间的关系。在“地方性”的理论化上,移民问题学者以民族国家和族群为分析的主要单位,而城市重构问题学者则未关注移民的研究。移民路径形成并反过来作用于城市的差异化定位。移民被视为城市层级的缔造者,城市在全球力场下的不同定位,决定着移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重新调整城市层级 移民融合 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 跨国主义 新自由主义重构
一、引言
本文认为,研究移民迁出、定居和跨国融合问题的学者应通过比较性研究将“地方性”问题理论化。在国际移民学术领域中,城市往往是以为移民提供定居和工作的空间承载物形式而存在的。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其实是那些被称作族群或弱势群体的移民人口。笔者认为,由于研究移民问题的学者们“从族群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因此他们往往未能仔细推究移民与其流出地、定居地之间的动态关系(Glick Schiller et al.2006)。他们对于城市的各种新自由主义重构,以及这些进程如何重组全球的资本和移民,关注度极其有限。
本文还涉及关于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及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即有些学者虽然对当代城市层级的重新调整展开研究,但却未能将移民视作当代城市重构的参与者。当然也不乏一些关于移民与城市问题的独到见解,譬如Taylor和Lang便观察到,“人员与资金在本国与来源国之间流动的此起彼伏,使得聚集大量移民的城市与全球的联系更强”(2005:2)。在全球城市研究中,移民一般被视为劳动力,只有一小部分学者考察了移民在当代城市中对参与全球性新自由主义进程的积极贡献(Garbaye 2005; LeGales 2002; Mitchell 2003)。尽管总的来说,关于城市新自由主义重构的研究十分活跃,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城市学者极少提及移民与城市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未能形成一种研究移民融合问题的比较视角、或曰一种足以分析地方性、全球重构进程与移民融合进程三者之间关系的能力。
在界定术语后,本文首先评述了那些有碍于形成分析框架的概念性问题。它们正是移民问题与城市重建和重塑进程问题的交集所在。随后重点论述了城市重构的各种理论,对于重建一种能够通过移民融合的各种路径,将地方性问题理论化的移民研究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章进而对移民定居与跨国联系的层级比较进行论证。最后,笔者以此为出发点,就移民作为城市层级缔造者问题展开探讨。本文还考察了城市在全球力场下的各种定位与移民在特定城市重建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
二、术语界定
首先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地方性和融合这三个术语进行界定,因为它们对于建立分析框架而言至关重要。新自由主义是指构成当代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系列资本积累的内容,包括组织劳动力、空间、国家制度、军队力量、管辖治理、从属关系以及主权(Harvey 2005; Jessop 2002)。我们将上述内容所带来转变的累积效应以及与之相伴的政策和技术归纳为新自由主义重构。新自由主义重构包括缩减由国家提供的服务和福利,引导公共资金和资源流向扶持包括医疗卫生和住房在内的民营服务型产业(通常被称为公私合营),通过摆脱对包括关税和劳动者权益在内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国家干预来不断推进全球化生产。
新自由主义概念的基石之一,便是国家一直持续但并不均衡地缩减对城市经济的投资。它打破了对受领土限制的政治实体的固有认知,所带来的结果是被称为地理尺度的空间关系上的质变。人们无法再将城市、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视为一系列嵌套式的领土关系。一些城市理论学家将新自由主义下领土治理的这种重新排列表述为“重新调整尺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改变了它们与全球、国家和地区之间连结性的衡量尺度,从而实现“跳级”(Swyngedouw 1992)。“重新调整层级”这一术语的出现,解决了重新界定城市的地位及其重要程度的问题,不管是在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在以城市为基础的制度实力的全球等级体系中。过去人们对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理解是以空间地理学为参照的,视其为从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的层级或从等级体系中抽离出来的分析对象;而现在,“全球性和地方性(以及国家性)则被视作互为构成要素”(Brenner 2001:134_5)。
我们用“地方”这一术语来表示更宽泛的新自由主义活动实际构成的具体空间。根据语境的不同,地方所指可以是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个集群乃至一片地区。本文以城市为焦点着手分析,以此来限定新自由主义变革的时空性。随着全球的城市人口比例越来越大(2007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中各有74.8%和43.8%为城市人),移民也越来越多地在各类城市中定居(United Nations 2008:12)。在移民问题上,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从全球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将城市作为分析的关键对象,探讨移民融合路径与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实现之间的联系。
在讨论将境内和跨境移民与当地制度连结起来的关系网时,我们使用“融合”这一术语。所有有关移民社会关系的术语——一体化、包容、同化、融合和跨国界等——在词义上都具有政治屈折性,原因是它们是在各国关于移民问题的特定语境下形成的。然而“融合”一词由于在英语世界的学术界已使用了几十年,因此其政治性修辞较少(Portes 1995; Schmitter Heisler 1992)。而我们研究“融合”的起点,便是移民个体以及他们塑造的关系网和这种关系网所形成的社会场域。于笔者而言,社会场域并非一种关于空间的比喻,而是由地方性、国家性乃至跨国性的层层关系网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体系(Glick Schiller 2003,2004; Mitchell 1969)。最重要的是,这些关系网植根于不均衡的实力当中。
三、概念障碍
有一些概念妨碍了移民问题研究者们对“地方性”进行理论化,因为在资本的全球性重构过程中,这些概念被重新包装了。它们无不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深深地植根于移民问题研究和关注移民问题的城市研究之中。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是在研究社会和历史进程的过程中从个别民族国家的范畴看待问题的一种取向(Beck 2000; Martins 1974; 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2002)。它将民族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有些学者给这种方法贴上了“包容性”社会理论的标签,因为包括涂尔干、韦伯和帕森斯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理论学家,他们都以民族国家的领土和制度为边界来对“社会”下定义(Urry 2000)。不过我们更倾向“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一词,因为它更能清晰地说明众多有关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所倚赖的政治性假设与关切所在。无论是批判移民问题研究中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还是论及将社会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的“边界陷阱”,都不能否认国家的领土边界、制度和监管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Agnew 1994:71)。
移民问题学者早在构建移民同化、一体化或融合等理论时,便已开始聚焦将社会凝聚在民族国家之中的制度和文化准则。以国家的领土边界作为社会边界引发了一种逻辑模式,即移民变成了社会团结的首要威胁;而一般的假设是,本地人之间享有共同的社会准则。在人们心目中,外来者来自与自己不同的国家乃至不同的社会,因而他们往往被刻画成带有独特的民族准则。一直以来,大部分移民理论都无视每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分界与文化分界,以及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共享的植根于领土边界内外的社会、经济、政治进程、关系网和制度中的经历、准则和价值观。
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妨碍了移民问题学者将某些地方的移民融合问题与过去乃至现在由全球资本的不均衡重构所推动的社会和经济进程联系起来。尽管移民研究中对地方性理论化可以建立在跨学科城市移民问题研究所提供的丰富的实证基础之上,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即便是跨国移民问题的研究者也不能完全解决地方性/全球性的症结所在——即在完善地方性理论化的同时,有助于其当代变革。
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妨碍移民问题学者对地方性进行理论化的概念障碍包括:
· 将地方性的全球属性限制在全球城市的范围内;
· 拿范式城市以偏概全地归纳地方乃至国家;
· 坚持从族群的视角看待问题;
· 以跨国社会群体而非跨国社会场域为研究对象。
四、城市与移民身份的重新调整
当然,并非所有论述移民与城市问题的社科理论流派都是在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这一框架之下形成的。针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的文献,为在移民问题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地方性的理论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这些文献不会仅仅关注一组特定的全球城市,而是将所有城市都视作全球性,并将它们置于不同的力量轨迹中加以区别对待(Brenner 1999;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MacLeod and Goodwin 1999; Smith 1995)。研究新自由主义重构进程的学者不会将城市归入后工业化或全球化的范畴,而是强调对于那些不再倚赖工业化生产的城市,资本重构对这些城市里的劳动力、住房存量、企业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政策等有何比较意义。
他们认为,地方政府为寻求比较优势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日趋暴露在资本市场之下,被迫通过竞争赢得投资,用于后工业化城市向“新经济”基地转型。例如,城市规划者们会听到这样的建议:
……一座城市想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谨记自身处在全球化市场的环境中。只有那些有能力发展自身和吸引全球性高价值服务型企业的城市,才有机会接触到全球的客户、雇员和合同外包服务并从中获利,最终推动本地的优质发展。(Taylor and Lang 2005)
城市政府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打造城市品牌以推广城市,因为国家也同样在进行尺度上的重新调整(Brenner et al.2003; Jessop 2003)。国家非但没有丧失其在城市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反而更加积极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展开区域间不均衡的城市化发展。国家层面的重构进程是通过选择性空间干预来实现的,即重新强化某些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以提升其竞争力。通过向某些地区提供国家性质的补贴、政府购买和扶持诸如机场和科研机构等的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国家依然是不均衡空间发展这一新模式得以形成的主导者。在此背景下,城市间不但要为争夺全球资本、同时还要为吸引各种形式的国家扶持而展开竞争。
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形象上的彻底改变来吸引国外资本和推广城市,即将自身打造成知识、金融、休闲以及旅游中心(Brenner et al.2003; Holland et al.2006; MacLeod and Goodwin 1999; Zukin 1995)。必须指出,在这些新经济产业中,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区分已然模糊,它们两者都是知识和旅游产业兴旺发展所必需的。在产业改革时期,每座城市因区位优势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际遇,譬如有的毗邻港口,有的则临近铁路或高速公路。关于城市层级重新调整的分析已然表明,当代所有城市都必须为获取一系列新型资产而展开竞争。当前,为了吸引诸如计算机相关技术等的新经济产业,城市必须提供某种包含人力资源、高等教育、文化和休闲设施在内的配置。
城市层级的概念非常有助于系统地研究新型城市竞争。如果我们先不把尺度视为一种固定的地理空间关系,城市层级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在层级力场交集的范围内通过相对定位而获取的动态传导关系。我们将城市层级定义为一种差异化的城市定位,它是由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的制度构建所决定的。这有助于我们对物理空间中动态的当代资本重构进行理论化。在研究移民与城市相结合的问题时,全球城市框架是将城市置于“空间组织等级”之中,而我们的定义不仅建立、更是超越了全球城市框架,折射出一种比较性的研究方法(Friedmann 1995:22)。
这一方法引出了城市层级重新调整的概念,在其投射出的序列中,每座城市的相对定位都是其新自由主义重构举措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些城市的层级相对较高,有的则相对较低,我们可以用高层级和低层级来表示这一城市定位序列的两极。不同的定位反映出并塑造了城市与地区、国家、跨区域乃至全球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城市层级是一种基于力场的相对度量,而非基于人口密度或全球城市学者所假设的新经济联系程度的度量(Beaverstock et al.1999)。城市的相对梯级定位有时可以通过城市的人口规模或城市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的延伸范围反映出来。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那些物理空间延伸范围较大或人口较多的城市在实力上不及一些规模相对较小但却因经济、政治或文化中心的身份而处于高层级或顶层级(世界级)的城市。
有必要指出,城市的层级定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基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确定性过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重构一直以来都是由当前的政治和制度环境所形成的,而这些政治和制度环境本身就是原先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管理、制度与政治安排的产物(Leitner et al.2007)。如此一来,新自由主义下的城市化是通过与每座城市的历史和组织结构遗产密切相互作用而呈现出来的。同样,城市的社会力量——包括重新调整层级进程中的移民机构——也是在这些遗产中形成的,也会受到以往的政治让步和政治联盟的影响。即便一些城市经历的层级调整进程相似,每座城市的历史和制度背景都在重构进程的实施、遭受质疑和地方参与者协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比较性角度:移民在各种融合路径中的缔造者身份
显然,关于新自由主义城市重构的文献为我们带来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视角,可籍此研究与移民定居和跨国联系相关的地方性问题的重要性。可惜的是,梯级比较的方法仍未得到移民问题学者的重视,而研究新自由主义城市层级重塑的理论学家也较少提及移民融合问题。移民在城市经济、文化和政治中的地位是由每个城市的新自由主义重构轨迹所造就的,他们本身就是这些城市为重新定位而展开竞争的要素。移民在劳动、创造财富、养家糊口以及创建社会制度的过程中,也促成了城市在国家和全球市场中以及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等级中的定位。移民与城市的文化表现相互作用,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治理。
移民还通过对城市全球形象的重新评估参与到城市层级重塑的过程中。每座城市的领导者都愿意吸引资本并将他们的城市作为一个被全球认可的品牌来营销,因此他们会重新评估移民的存在价值。虽然也许只是一些特例,但在某些社区或城市,移民已成为一种可流通资产。作为提升竞争地位的一种因素,城市的文化多样性也已成为文化产业中一项可供买卖的城市资源(Çağlar 2007; Scott 2004)。移民还带来了跨国联系,能将城市与资本流、物流、思潮、新想法和文化表现等联系起来。简言之,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全面参与者,移民影响着城市治理、发展乃至社会运动形式的变革,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研究的中心问题。因此,移民可以从多方面扮演尺度的缔造者。
Smith和Favell(2006)等学者早已开始探讨移民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认为技术移民是一座城市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McE-wan et al.(2005)指出,移民的跨国关系可以给城市带来它所梦寐以求的全球联系。除了这些一般性的描述,我们还需辨析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当代城市的新自由主义重塑,意味着某座城市为移民带来了这样的机会:它改变了地方治理的发展态势、就业岗位的性质和质量、文化的表现和宣传形式、以及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
一座城市在力场等级中的相对位置也为本地和跨国移民差异化的生存及融合机遇打下了基础。移民有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融入城市生活,对城市重塑轨迹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这要取决于城市的层级定位。通过考察城市经历新自由主义重构与层级重塑进程的不同路径,城市问题学者可以更容易地将移民面对其所在城市的各种发展态势与其积极参与其中的发展态势作比较。这一方法也便于研究者了解移民机构会在何种情况下帮助城市重新找回它在全球的位置,或者保持其主导地位。如果研究人员从差异化定位的角度来比较城市,便有可能系统地考察移民融合与跨国联系途径的变动,以及当某座城市的领导者希望重新塑造或重新定位城市时,上述路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要考察城市的不同定位对移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首先第一步是建立一种描述城市相对定位的术语。在下一章节,笔者将会用顶层级、高层级、低层级和底层级等各种定位属性来比较城市。通过对其地位获得全球认可的城市展开一系列探索性的案例研究并由此获取数据,我们大致了解了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移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描述,亦称为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这些数据包括我们自己研究的两座底层级城市——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哈雷市和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必须强调的是,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要给城市进行归类定型,而是要体现城市在一个动态的实力序列中可能所处并且需要不断调整的位置。这些术语并不代表某种类型,但却是差异化实力在整个序列中的表现。移民本身会形成一部分联系,并延伸至其他城市乃至各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城市在序列中的定位却影响着移民与某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一)顶层级
伦敦、纽约、巴黎等顶层级城市之所以特别,是由于它们多样化的新经济产业和文化或政治资本的大规模积累,为移民融合和跨国联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例如,顶层级城市依靠的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各类技能的移民,随时可以通过全球人才招聘行业将他们锁定。这种全球性的移民网络是雇主们的重要资源。当然,为了维持金融、文化和服务等行业的基础设施,这类城市也需要有低收入移民。简言之,各类移民的流入为这些城市维持多样化的全球联系提供了支撑。
直至不久前,移民在这类城市中的各种融合路径才为人们所了解,原因是其中还涉及大量围绕族群和各种身份认同所组织起来的社团和机构。由于这些城市既是旅游集散地,同时其文化多样性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才,因此顶层级城市是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的表现及其机构的拥护者。移民问题学者将他们的精力浪费在这些顶层级城市中具有本地或跨国联系的族群组织上,从而忽略了移民融入这类城市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处于序列较强一极的城市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撑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族群机构,使其成为该市文化资本的一部分,为其城市定位作贡献。只有当我们将这些顶层级城市与处于全球实力序列其他位置的城市进行比较时,才能体现这些城市中的族群组织的特性。
(二)高层级
那些具有与成功发展新经济产业相关的新型文化和资本积累的城市,占据着相对较高的层级。与顶层级城市的情况相类似,处于高层级的地区依赖于一系列移民融合途径,也同样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和无需太多技能的工人。只不过这些移民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与顶层级城市有所不同,因此表现为这些城市相对较弱的竞争地位。高层级城市的移民融合路径非常多样化,包括族群路径,其作用不仅可能超越文化产业,也许还会在城市取得高层级地位的能力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拥有600多家企业总部的达拉斯-沃思堡便是通过包括德州仪器和一些大型制药公司在内的发达的知识经济取得其高层级城市的地位。2006年,该地区信息通讯行业的职位规模名列美国第三位(Sturgeon 2006)。作为一个高科技经济基地,它需要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工程师和医药行业人才。而大多数岗位是由通过移民关系网招募而来的移民从事。根据一家医疗人才专业机构的数据,巴基斯坦裔的关系网是达拉斯医生职位招募的第二大重要来源(Sturgeon 2006)。Caroline Brettell的研究证实,类似德州仪器公司里的“印度多样性小组”等在地方企业支持下成立的跨国移民组织,是该市重要的高科技劳动力来源。换言之,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直接扶持那些围绕同乡身份认同而组织起来的移民跨国社团。这些社团在该市获取以及维系其日益增强的全球竞争力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由于移民组织及其跨国分支的关键作用使得达拉斯-沃思堡在全球重要性的提升,具体而言就是积极地从他们的移民来源地招募全球技术人才,它们在大都会区中的地位也愈发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也开始强调多样性。达拉斯市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口号“达拉斯:多样、活力与进步之城”,它还是“全美100个最具族群多样性的社区之一”。这些技术移民人才的存在,不仅为他们受雇的企业创造了实力与财富,同时也为他们所在城市的层级定位作出了贡献。
(三)低层级
低层级城市里的移民所面临的前景和扮演的角色则完全不同。在序列中处于该等级的城市也许会有一定的在全球拿得出手的新经济产业基础,但这种基础的规模和广度都非常小。由于其重构战略可能依赖或受制于某种劳动力非常稀缺的产业,如医疗专业人才,又或者由于这座城市对专业人才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低层级城市在重建本地经济和全球定位的过程中,可能会特别依赖于移民。但这些城市也许并不具备有实力扶持移民跨国组织的企业架构。譬如,由于缺少像达拉斯-沃思堡那样的新型高科技产业或者使其能与毗邻的纽约市媲美的金融服务业(会计、广告、银行/金融、保险、法律和管理咨询中心),美国费城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著名大学和医院。费城的政经领袖努力以这些机构为基础将这座城市重新打造成一座拥有高收入专业人才和优质生源的知识中心。
与达拉斯-沃思堡不同,费城的族群组织并不扮演跨国人才招聘机构的角色。相反,这种招募一般由当地自行组织,面向能够胜任大学院系、医疗机构和学生机构的所有移民,他们将成为费城的知识产业所需的大都会“创意阶层”。作为回报,移民带着现成的资金和文化资本以及对大都会生活的向往,为城市中心带去人气,完成当地的中产阶级化。他们在城市中扮演的转型角色有助于进一步招募和挽留“全球人才”,进一步以一座多元化、宜居、高档购物与旅游中心的形象来营销这座中产阶级化的城市。
在费城这样的低层级城市中,移民不仅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更影响着一系列的城市社区再建设。他们对于边缘社区的投资意愿可能会引发地产价值重估,推动物业价值上升。在某些情况下,移民对社区的重构也许并非朝着城市领导者和规划者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例如,移民企业和商人通过进驻费城中产阶级化的市中心以外的低收入社区和修缮那里的住房,实现对这类社区的再开发,从而推高了当地的物业价格。这种再开发反过来也影响了对费城的重塑和营销(Goode 2006)。在通过“医疗-教育”产业重新定位和宣传费城的背景下,行业中被称为国外人才的移民并没有与族群的范畴结合起来。城市领导者在重构城市时,包括非裔美籍专业人才在内,都不太支持族群或文化多样性组织。这些组织反而形成了反对工薪阶层社区中产阶级化的声音。
(四)底层级
沿着序列继续往下,是那些在重构上不太成功、但仍然具有一定全球性资本投资的城市。也许这些城市的领导者们下了重本对城市进行重新建设和重新塑造,但却未能建立成规模的新经济产业部门,如知识、旅游或娱乐等产业。如果没有这些产业,移民的跨国关系网和他们对重新定位城市大都会形象的贡献都会大打折扣。因此,技术移民在这里不受重视,哪怕是那些在本地获得文凭的移民也只能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在移民祈求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无形中承担起本地和跨国关系网的任务。他们遵循的途径也许不止一种,而通过族群融合的路径也并不一定最显著的。当地既没有充足的政府、企业或慈善资源,也缺乏专业技术移民这类社会阶层去维系族群组织。
通过对2001~2005年间底层级城市的研究,我们认识到,移民在底层级城市中的融合路径不同于地位较高的城市。我们选取了两德统一后经历了严重工业退化和人口缩减的原东德城市哈雷,以及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老牌工业城市曼彻斯特(Glick Schiller and Çağlar)。在这两座城市中,国家对社会服务和资源的扶持由于向新自由主义转型而有所降低。造成的结果是,那里几乎没有针对移民的扶持资源和以族群为基础的组织机构,也没有用于组织这类活动的企业或慈善资源。从整体上看,当地人口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
在曼彻斯特,即便是有技术背景的移民也只能在那些跨国集团旗下的小型工厂打工。在哈雷,由于当地政府禁止以非法移民或难民为主的移民参加工作,加上岗位供不应求的情况相当严重,因此本地人几乎垄断了包括非法岗位在内的工作。如此一来,做小本生意便成为这两座城市中的一部分移民为数不多的融合途径之一,但即便如此,它也难以构成一个足以为绝大多数移民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这些从事小本生意的移民分布在不同的社区,特别是那些集中在城市中心的移民,他们对于城市的再开发和中产阶级化而言尤为重要。
当曼彻斯特的政治领导人需要重振被遗弃十多年的市中心小商业时,他们寄望于移民实现项目的快速启动。那些有意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做生意、用崭新的店铺门面代替原来的二手服装店和空置物业的小老板们,绝大部分是由移民构成的。城市开发者们可能会设想,在未来的曼彻斯特,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中心将会吸引高科技人才和游客。然而,在本研究进行之时,移民个体户的主要价值还只是在于其在主干道中产阶级化上起到的作用,而并非在于该市族群特色与文化多样性的营销之上。
哈雷市的重新改造的尝试吸引了民营资本和技术工人,而重塑形象的尝试则基本上是失败的。它依然摆脱不了一个失业率高企、缺乏本地产业的城市形象。2005年,哈雷市在其官方网页上以高科技产业中心自居,但该网页上能够列出的只有一家巧克力工厂和一间即将关闭的铁路车皮组装厂。20世纪90年代,小商业主要面向移民个体户,原因是装修位于闹市的店铺门面门槛低、费用又不高,但那些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本地人却不具备经营零售业的经验。结果是,技术移民成为个体户,进驻修葺一新的市中心商铺。笔者于2001年调研的市中心地区,虽然当地只有4%的人口为移民,但有12%的商铺是由移民经营的。他们做的生意都很实惠,为大部分只能靠低收入工作或社会救济糊口德国人解决了衣食问题。他们从各个方面提振了经济,改善了许多当地过去社会分化悬殊的困境。
一方面,这些城市缺乏吸引和留住大批所谓“创意阶层”(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新移民)的机遇结构,因此难以形成大都会式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与此匹配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曼彻斯特和哈雷的定位催生出其他形式的移民融合路径,如不依赖族群的创业途径。根据我们在这两座城市其他地方的研究发现,移民还带来了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跨国关系网,使本地人和移民有机会接触本地、国家和全球层面的资源与社会资本(Glick Schiller et al.2006)。作为许多城市中移民活动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一,宗教为曼彻斯特和哈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移民融合途径。
底层级城市的层级定位为移民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在序列中处于较有利位置的城市融入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机会。这个序列不仅代表着不同城市在资本关系网的实力方面处于怎样的位置,也代表着其移民机构不同水平的定位。移民在城市架构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取决于当地的机遇结构与发展潜力。从全球性序列的角度进行思考,让研究者可以探究移民对某些地方的城市经济和政治在新自由主义重构上的相对权重。
通过我们所研究的序列中四种处于不同定位的城市案例,总结得出两点有助于日后研究假设的结论。首先是城市的定位与移民融合路径的选择范围之间的关系。处于序列顶端的城市,其移民融合具有更多的方式(族群、文化/大都会、宗教、创业等),它们为移民创造了参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遇;而越往序列的另一端,移民融合途径的可选范围就大幅缩减。在底端,即对于那些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位失败的城市而言,移民融合的路径选择非常有限。譬如在底层级城市,移民通过族群融合的路径就不太行得通,因为那里能够从族群角度投入到应对和组织移民参与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资源少之又少。
不过移民融合路径选择的多寡与某种移民融合路径是否适合某座城市,两者是有区别的。移民融合路径对某座城市的影响取决于这座城市在序列中的定位。处于较低层级的城市,族群融合模式活跃的可能性较小,那里的路径选择也可能不多,但这都不妨碍移民对当地有重要影响。其余的路径——如创业或宗教——它们不仅可能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可能对于移民融入当地更加奏效。
上述两个结论直接指向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在辨析移民与城市尺度重新调整之间的各种关系模式之后,接下来便是对不同梯级定位的城市进行考察,为何某些城市里某一种路径比其他路径更适合。其他问题还包括:
· 移民融入城市的主要路径与移民作为尺度缔造者对重构进程的贡献之间有什么关系?
· 与移民融入一座城市密切相关的路径对这座城市的尺度重新调整进程是否有积极贡献?
· 为何某些移民融合路径在某些城市能够得到当地政府和主导产业部门在政策上等各方面的支持,而在其他城市则会被忽略或得不到扶持?
系统地考察这些问题能让移民问题学者更充分地对待地方的历史、结构和转型,同时让城市问题学者正视城市生活尺度重新调整过程中移民的重要性。
六、结论:重新调整移民和城市研究的尺度
尽管在移民问题研究中涌现出像“城市转型”(Prakash 2002)这样的新成果,但关于移民融入城市的研究依然只是国家福利和机遇结构项目的一部分。本文旨在促使移民问题学者与城市重构问题学者之间展开对话,旨在通过对比的方式对“地方性”进行理论化,承认移民是城市生活重建的积极参与者。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不同层级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多的移民问题学者也在这些城市展开研究,他们更应该也更可能关注不同城市的层级问题。同样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城市重构问题学者面临的挑战是,从对比的角度研究城市层级的重塑,将作为积极参与者的移民囊括于此进程中。
这种研究在关注各种不同模式的同时,还不能忽略本土化的特性。尽管我们认为移民在城市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因城市的层级定位而有所不同,但我们并没有否认某个地方移民历史的重要性。不管城市在整个层级定位中的位置如何相似,它们的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复合层次决定了特定地方的融合模式,因为那是建立在地方特有的代表物、遗产和期望值之上的。通过关注移民在特定城市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便是对于处在相似层级的城市,研究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学者也能更好地考察其城市层级调整过程的差异。
通过将移民看作是新自由主义进程的组成部分,城市重构问题学者能够动态地捕捉到新自由主义的进程。考察移民不同本地和跨国联系途径有助于从历史和背景的角度研究新自由主义尺度的重新调整(Ong 2006)。未来也可以通过每个地方的历史路径依赖与其全球力量之间关系的交集来进行研究,后者是城市层级定位形成的原因。
过去的移民问题研究有选择性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待本地的全球重构问题,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假设全球化同时也是一种本土化进程,并且是一种在空间上不平衡的本土化,那么移民问题研究就必须承认和分析这些涉及到移民的本地或跨国融合的进程。如果脱离了对移民的流出地和定居地在过去和现在的重构分析,移民问题研究将无法进行(Çağlar 2006)。当务之急是将地方性、移民和全球重构之间的动态分析理论化。用层级的方法研究移民动态,有助于将全球化的不均衡特性和动态融入到我们的研究之中。
本文提出的城市层级概念,为分析当代城市(或城市地区)发展的结构和进程提供了一个比较性的框架。它是一个以地方为基础的概念,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资本积累的过程和动态,不一定局限于国家范围内,与控制着不同程度的财富和权力的国家形成互动。
比较性的角度为我们带来更清晰的研究思路,考察城市重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移民融合路径,以及由移民自身形成的融入不同层级定位城市的路径。通过将机遇结构的本地特有动态与城市重构和城市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层面重新定位的动态联系起来,使得移民融合的机遇-结构优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为移民和城市政策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参考文献:
[1]Abu-Lughod,J.(1999)New York,Los Angeles:America’s Global Cit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Agnew,J.(1994)‘The territorial trap: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1):53_80.
[3]Amin,A.and Graham,S.(1997)‘The ordinary city’,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 Geographers,22(4):411_29.
[4]Amiraux,V.(2001)Acteurs de l’Islam entre Allemagne et Turquie:Parcours Militants et Expe’riences Religieuses.Paris:L’Harmattan.
[5]Barth,F.(1969)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Boston:Little Brown.
[6]Baumann,G.,Vertovec,S.,Schiffauer,W.and Kastoryano,R.(eds)(2004)Civil Enculturation:Nation-State,School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the Netherlands,Britain,Germany and France.New York:Berghahn.
[7]Beaverstock,J.,Smith,R.and Taylor,P.(1999)‘A roster of cities’,Cities,16(6):445_58.
[8]Beck,U.(2000)‘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51(1):79_105.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列出部分参考文献)
Towards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Locality in Migration Studies:Migrant Incorporation and City Scale
Nina Glick Schiller,Ayse Çağlar
Building on the scholarship that theorises the restructuring of cities within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this article calls for a comparative scalar approach to migrant settle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Deploying a concept of city scale,the article posi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ing outcomes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post-industrial cities and varying pathways of migrant incorporation.Committed to the use of nation-states and ethnic groups as primary units of analysis,migration scholars have lacked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locality; scholar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have not engaged in migration studies.Yet migrant pathways are both shaped by and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tial repositioning of cities.Migrants are viewed as urban scale-makers with roles that vary in relationship to the different positioning of cities within global fields of power.
urban rescaling; migrant incorporation;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ism;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D523.8
10.3969/j.issn.1674-7178.2014.02.003
尼娜·格里克·席勒,人类学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都市文化研究所所长,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爱莎·卡格拉尔,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教授。
(编译:陈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