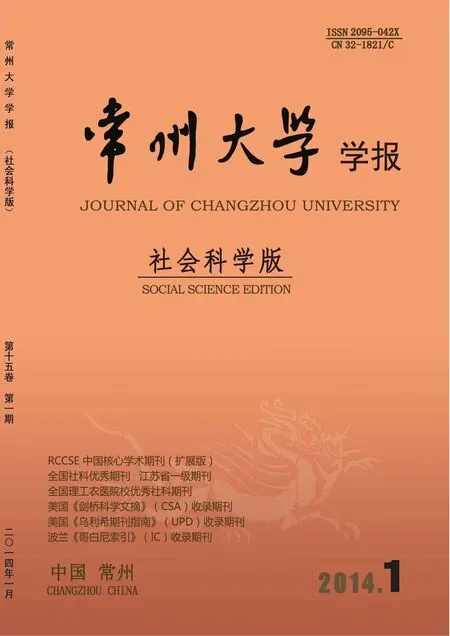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
——《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徐一超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
——《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徐一超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湘行书简》可谓《湘行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衍生关系,却分别有着“即时记事”和“延时创作”的不同写作特征。《散记》中呈现了临对不定性命运“固执”担当、求取生存的边地水手形象,却与最初“书简”的陈说颇具差异,体现出能动的建构性。《湘行书简》记存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湘西生命由怜悯到敬、爱的情感更变过程,《散记》中的边地水手则是这一过程中逐渐孕生的生命观影响下的文本“构象”。“构象”过程体现出沈从文希望以原乡生命力补济现代文明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他的生命观可以被视作一个以“命运”、“意志”为边际二维的复调、动态的“连续统”。
沈从文;生命观;《湘行书简》;《湘行散记》
1934年初,沈从文为探望母病返回家乡,于舟行途中向北京家中写下后来被整理为 《湘行书简》的数十封家书,返京后又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后来集为《湘行散记》的各篇散文。集中各篇表面上“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1]388—389这次回乡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离湘进京,在现代都市与边地故土、现实与记忆的“时序错置”、“空间位移”[2]情境下居处10年后的一次变动性时空行旅。《书简》可谓《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无疑具有衍生关系;另一方面,“书简”的随行随写、私人记述与“散记”的事后创作、公开发表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就为二者对类同对象的差异性呈现创生了空间。本文试图以《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为考察对象,分析沈从文复调、动态的生命观,尤其是其中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
一、“固执的单调”与“单调的延长”:《散记》中的边地水手
沈从文曾谓《湘行散记》写的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1]390,往来于河溪之上的边地水手的确是《散记》中的主要形象系列。《湘行散记》记述的湘西弄船人一生都在如火般热情的河流上求取生存。由于水势湍急,激流、漩水、礁石众多,驾船往来且时常要跳入水中使船上行的水上人时时都有被水冲去的危险。水手们与死亡是如此濒近:
只见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只活动,可是人一下水后,就即刻为水带走了。在浪声哮吼里尚听到岸上人沿岸喊着,水中那一个大约也回答着一些遗嘱之类,过一会,人便不见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然而这种与死亡的相邻对水手们而言,实在是一种常态——“这件事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水手死后,“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桃源与沅州》)。以“便”、“就”、“了”标识完成时的叙述语调突显了一个被平静接受的既成事实,叙述者与水上人同具一种静视死亡的冷静。在作者笔下的湘西,临对死亡的镇静与平和似乎是普遍的生命态度:辰州的矿坑坍陷,那些“到地狱讨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地方的妓女因病死后,“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赊购简陋棺木甚至借取“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桃源与沅州》)。
水手、矿工、妓女,边地的生命个体在种种无可预料的变动面前都显出平静与无力,而足以左右生命结局的未知力量就是所谓的“命运”。在河街人家的火堆旁,“我”与乡民谈天,“到后来谈起命运,那屋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各人眼望着熊熊的柴火,心中玩味着‘命运’两个字的意义,而且皆俨然有一点儿痛苦。”(《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在人力不可及的命运面前,包括湘西水手在内的生命个体显然具有一种被动的无奈;这种个体与命运间的存在关系,能够从作者惯用的陈述中得到确证:那“行将来到的风雪”,是“摊派到这只船上”(《鸭窠围的夜》);在水手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箱子岩》)。命运总是以主动、进取的态势向生命个体“袭”来,一种“命定”的悲剧气氛无疑笼罩着边地生命。
船泊鸭窠围的夜晚,一种生命的音响曾经摇动了作者的心襟:
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算算日子,再过十一天便过年了。“小畜生明不明白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十天八天?”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这小畜生是为了过年而赶来应在这个地方死去的。(《鸭窠围的夜》)
听着固执而柔和的羊叫声,“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夜泊者参悟到什么?《圣经》中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53:6);“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诗篇》,49:14)。触动沈从文的与其说是小羊的叫声,毋宁说是羊羔隐喻的生命状态:生命的指向预定却不可知,人类临对命运的无知、无力正与牲畜相同。深夜水畔的羊叫声正如渔人击柝的声响,于无边的岑寂中划开声音的孔道,“单纯到不可比方”。然而正如夜泊者感受到的,静寂中一缕单调的音响分明于巨细差异中显现出“固执”的质感;若将无边的静夜视作充满可能性与不定性的生命状态,单调的音响也就一体两面地呈示出生存的单调纤弱与固执坚强。
事实上,《散记》中边地水手的生存状态正像作者在《鸭窠围的夜》中形容的暗夜中的声响,是“固执的单调”与“单调的延长”。船只逼入急流乱石中,船上人不问寒暑,都要敏捷地跳入急流中,“在水里尽肩背之力使船只离开险境”(《桃源与沅州》)。纵有为水冲去的危险,小船上滩时,他们也“不能不向白浪里钻去”,却又必定能在激流中求生(《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水”既是水生们生命险况的所在,又是其生存的依赖:“他们明白水,且得靠水为生,却不让水把他们攫去”(《湘行书简·滩上挣扎》)。这是一种生命的担当、生存的搏战:冷静地接受甚至积极迎向险恶的生存环境,且要在不定性与风险中求取确定性的生存。
湘西水手们被命运无故抛掷于边地山水之间,在根本上孤独无助、身陷困境,却能以“工作上与饮食上的勇敢”(《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演绎生命“实存”与“能在”的意义,通过对存在可能性的领会与担当实现生命过程的填充。他们为了求生,“在每个日子里每一时间皆有向水中跳去的准备”(《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实具“向死而生”的意味。水上人既吼着“老子要死了”(《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唱道“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又喊着“要来就快来,莫在后面捱”(《湘行书简·滩上挣扎》),正是以一种担当、“除阻”的姿态迎向生命的终结: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散记》中的边地水手无力左右命运,时时受到命运不定性的威胁,但他们固执地选择死于生存搏战的生命终结方式,担当而非逃避命运的“派定”,这实际上就通过支配死亡赋予了生存的过程性意义。“天地不仁”却又“生生不息”,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通过边地水手的形象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命图景:个体生命在不定性命运面前求取生存的“固执的单调”与“单调的延长”。
二、“不,三三,我错了”:《书简》的“即时记事”与情感更变
边乡水手在作为《散记》“底本”的湘行书信中早已现身,却在记述中体现出与《散记》颇具差异的形象特征与情感蕴涵。书信的随行随写赋予其“即时记事”的属性,这一历时性的写作也记存下还乡者对边地水手情感态度的更变过程。
沈从文在题识“十三日下午五时”的信中初次提及湘西水手:“‘我今年五十三,十六岁就划船。’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四百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小船上的信》①)在这里,记述者并未铺展边地水手的生存图卷,而是通过年龄、长度的“量”的感受表露了对水上人经验与技能的赞叹,体现出即时体验的直观感觉特征。
十四日下午,沈从文写道:“像这样大雪天气,两毛钱就得要人家从天亮拉起一直到天黑,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水手们》)对湘西水手生存境况的初次述及竟呈现出与《散记》全然不同的态度:来自都市的还乡者为边地乡民感到不平。他接着写道:“他们的希望只是多吃一碗饭,多吃一片肉,拢岸时得了钱,就拿去花到吊脚楼上女人身上去,一回两回,钱完事了,船又应当下行了”。在沈从文眼中,水手们止于食与色的人性需求,“他们也是个人,但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虽未细加陈说,但沈从文已经体察到边地船夫与都市居民在生存上的相异。
在这一天的信中,沈从文还向张兆和提及“活泼有趣勇敢耐劳”的麻阳籍水手,称“这些人都可爱得很,你一定欢喜他们”。(《水手们》)不过,沈从文当时坐的却是一条“桃源划子”,他称“不幸得很,遇到几个懒人”,“看到他们早早的停泊,我竟不知怎么办”。(《忆麻阳船》)归乡者始终惦念着行程的耗时,而船夫们“全不知道我如何发急”(《泊兴隆街》)。但由于天气太冷,“不忍要他们在水中受折磨”(《忆麻阳船》),沈从文也就“不好意思催人下水拉船”(《过柳林岔》)。沈从文对水手们驾船缓进的无奈与不满,正是急于返乡的主体对“侍者”的情感态度。
沈从文的“不忍”蕴含对乡民生存状态的同情。十五日,他写道:“船夫不好意思似的一面骂野话,一面跳上岸去拉纤,望到他们那个背影,我有说不出的同情,不好意思催促”(《过柳林岔》)。此后的信中,他又不止一次表露出类似的情感:“眼看到那个能干水手一个人爬在河边石滩上一步一步的走,心里很觉得悲哀”;“心中煎熬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工作折磨到他,实在是很可怜的”。(《滩上挣扎》)悲悯情感多少隐含了主客体之间的隔膜与身份上的差序。
在还乡旅程的最初阶段,沈从文就是这样与湘西水手们拉开了身份距离。在外来的还乡者眼中,边地水手是与城里人全然不同的生命存在。沈从文既感叹水上人的生存经验与技能,又为其恶劣的生存条件感到不平与怜悯,对水手们缓慢驱进下的行程感到焦急与无奈。返乡者总是以城里人的立场对边地的差异性生态表象做出直观的反应。
随着行程推进,沈从文对边地水手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看到他们我总感动得要命。……我现在正想起应当如何来写个较长的作品,对于他们的做人可敬可爱处,也许让人多知道些,对于他们悲惨处,也许在另一时多有些人来注意。”(《滩上挣扎》)既感动,又敬、爱,同时怜悯其生存的悲惨,这种复调的情感变动显示出还乡者对边地生命的思考及其深化。
一月十八日上午,沈从文遇到一个“白须满腮,牙齿已脱”的水上人,他为了拉纤的价钱与船主嚷了许久,尔后主动跳入水中出力。见此情景,沈从文心生疑窦:“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横石和九溪》)“人那么老了,还那么出力气”的水上人无疑深深触动了沈从文,在感喟乡民生活“无所为”的同时,他开始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在下午的信中表达出自己的思考:
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历史是一条河》)
坚决的自我否定其实是一种自我超越。从“居上者”的怜悯到“居下者”的敬、爱,沈从文情感表达的这处“突转”反映了还乡者身份定位的选择性调整。在旅途“侍者”身上,沈从文看到了担负命运、无所逃避、求取生存的庄严忠实、可敬可爱。从他最初感叹生存“无所为”的乡民身上,沈从文也读解出“为自己”、“为儿女”的生命寄托。在他看来,个体在艰困环境中为了生命本体性的存在与延续所做的担负、努力,就是四时交递下生存过程庄严的意义。
事实上,边地水手们的 “勇敢耐劳”是沈从文最初就感受到的,只是与此相较,船上人恶劣的生存环境更能在鲜明比照下对这个在现代都市生活了十年的还乡者造成冲击。但在与水手约十天的日夜相处后,沈从文最终超越了面对边地表象时城里人的身份本位,在湘西的恶劣环境与水手的求生状态中偏向了后者,并从中初步开掘出自己的生命哲学。因此,《湘行散记》对边地水手的表现是作者在还乡体验中历经情感更变后的选择性结果,其中的态度转向与思考深化起始于沈的湘行途中,更贯通了从“书简”到“散记”的写作命意与趋向。
三、从“书简”到“散记”:“延时创作”中的湘行“构象”
从“书简”的“即时记事”到“散记”的“延时创作”,书写者进一步推衍了还乡途中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后形成的情感态度,通过对边地形象的能动性构建(“构象”)传达出自己的生命观念。这一构建行为的取向就是塑造出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水手形象,表现他们身陷命运不定性的生存境况与这一背景下的生存意志。
前已提及,沈从文曾在信中向张兆和抱怨自己所坐“桃源划子”上水手们的懒惰。在他后来所写的《湘西》一书中,桃源的弄船人也是脾气“马虎”,“很多是瘾君子,白天弄船,晚上便靠灯”(《常德的船》)。《湘西》作于战中机关、难民向湘西内撤之际,沈从文希望“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1]393在这种力求客观的记述态度下,“桃源划子”上的船民的确是慵懒而怠惰。然而在收于《湘行散记》的散文《桃源与沅州》中,沈从文只字未提桃源水手的“马虎”与烟瘾;他们变得“有胆量,有气力,有经验”,成为敏捷勇敢、勤劳协作的形象。虽然收入低下,又时时面对“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不能而淹死的危险,但他们仍“不问冬夏”,“尽肩背之力”经营生活。这正是对不定性命运的担当态度。
从“书简”到“散记”,作者对水手形象的“重构”不止于此。那个曾让还乡者感慨“无所为”的生、进而引发生命意义追问的老迈水手,在《散记》中却体现着生存的努力与执著:“看他那数钱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还曾在书信中记述一个小水手落水后又获救的可怜情景,并表露了自己的同情:
差点儿淹坏了一个小孩子,经验太少,力量不够,下篙不稳,结果一下子为篙子弹到水中去了。幸好一个年长水手把他从水中拉起,船也侧着进了不少的水。小孩子被人从水中拉起来后,抱着桅子荷荷的哭,看到他那样子真有使人说不出的同情。
(《滩上挣扎》)
在散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捞救小水手的年长水手和他的敏捷、“可爱”却成为叙述表现的主体:
他却一手支持篙子,还能一手把那个小水手捞住,援助上船。……他一面笑骂着种种野话,一面却赶快脱了棉衣单袴给小水手替换。在这小船上他一个人脾气似乎特别大,但可爱处也就似乎特别多。
这样,一个勇敢敏捷、生命力高扬的水手形象被建构起来,水手在“散记”的叙述中成为受到肯定、欣赏的对象。而作者的情感表露也从“说不出的同情”转变为“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感情”,显得意味深长。
在“书简”中,水手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历史是一条河》),在“散记”中,“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从“是”的陈述到“摊派”的形容,对命运分定的强调正渲染了边地水手们充满不定性的生存环境和他们在命运面前的被动、无力。在最初在书信中,沈从文这样记述了鸭窠围的小羊叫声:“羊还在叫,我觉得希奇,好好的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夜泊鸭窠围》)而在第一部分已经呈现过的《散记》引文中,对河应和着的另一只羊却被隐去了,余下的孤羊夜吟固执而柔和,牵引夜泊者的思绪:“这小畜生是为了过年而赶来应在这个地方死去的”。小牲畜的生命结局早已为人所预定,但人的生命结局又何尝不是为“命运”所预定而不可知?
但在对命运感一维强化表现的同时,这个湘行的“构象”者更要突出边地水手对生存的勇敢担当:
他们逃避激流同漩水的方法,十分巧妙。他们得靠水为生,明白水,比一般人更明白水的可怕处;但他们为了求生,却在每个日子里每一时间皆有向水中跳去的准备。小船一上滩时,就不能不向白浪里钻去,可是他们却又必有方法从白浪里找到出路。(《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
与《书简》中的相应段落(“底本”)相较②,《散记》的叙述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边地生命结构的层次与递进秩序:水上人必须依靠水(命运的分定),深知水中潜藏的生命威胁(对命运的静视),却时时有迎向死亡的准备(对命运的担当);他们钻入白浪践行其生命意识,在与危险的搏战中求取生存(“除阻”的生存实践)。而《散记》中增加的这一表述——“却在每个日子里每一时间皆有向水中跳去的准备”——则突显出边地水手通过迎向生命结局填充生存过程性意义的决断与担当。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历时性梳检与同题材比照,可以看出《散记》中边地水手的“构象”本质。湘行者的还乡体验,其实是一个对边地表象选择接受并思考体悟的过程。《湘行书简》“即时记事”中的情感更变正体现出沈从文选择的调整与接受的转向,与此伴生的则是一种生命观的形成;而从“书简”到“散记”的“延时创作”,则是这一生命观投射下的文本“构象”,同时也以写作实践巩固、传达了沈从文的生命哲学。
四、“因事挤出”的文明本位与迎向现实的生命观
然而,是什么促成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边地水手情感态度的转变,进而孕生出他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及其文本“构象”?这一切表面上都在湘西迥别于都会的生态表象影响下发生,实质上却与还乡者主观的选择接受与思考体悟密切关联。诚如卢卡契所言,“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3],边地环境对沈从文的影响必然与其固有的心灵结构相呼应。其实,沈从文的还乡体验与这一过程中的生命体悟都和他离乡多年后思想观念的文明本位紧密相关。
身在都市的沈从文常以“乡下人”自称,他对湘西世界的用力描画也给人精神原乡的印象。然而,已有论者关注到沈从文“以拒绝‘都市’的方式介入都市”的内在“反相”,湘西“原乡”实是他乡。[4]历经现代文明的沈从文虽对其多有诟病,但无论在个体生活还是民族关切的立场上,他都以前指性的现代文明为本位,而非希冀边地前现代文明的复归。他的文明本位立场在其返乡体验中足可见出。
在散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还乡者面对故地美景,感叹“多美丽的一幅画图,一首诗!”他接着写道:“但除了一个从城市中因事挤出的人觉得惊讶,难道还有谁看到这些光景矍然神往。”“因事挤出”的身份认定别有意味,“挤”字流露出身属其中者暂时游离于外时的复杂心绪。
正如此前所述,沈从文还乡途中对边地水手们最初的情感态度——不平、同情,无奈的不满——都体现出明显的“城里人”身份意识。他还每每将边地水手与城市中人并举,并表露出把“他们”作为表现对象的写作意愿:“看到他们我总感动得要命。我们在大城里住,遇到的人即或有学问,有知识,有礼貌,有地位,不知怎么的,总好像这人缺少了点成为一个人的东西”(《摊上挣扎》),“一看到这些人说话,一同到这些人接近,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想好好的来写他们一次”(《水手们》)。作为一个本位于现代文明的还乡者,沈从文以“他者”的眼光发现了边地的“他者”,从对两种生存方式差异性表象的直观体认中生成了叙说的冲动。而“他者”的存在正有赖于沈从文的文明经验。
更重要的是,文明经验触发的叙说冲动最终反哺式地指向了对现代文明的观照与补济:沈从文意欲通过能动性建构的文本形象“让人多知道些”边地水手的“可敬可爱处”(《摊上挣扎》)。他感叹道:“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表现出现代文明社会职业作家的身份自觉,希望通过 “自己这份工作”——写作——诠释自己的文明立场与关切。与此相呼应,有别于书信私人写作特征的散文创作因其在大众传媒上的公开发表,正能为沈从文的文明关切创生传播与影响的可能。《湘行散记》的写作因而成为主客观条件共同催生的文本实践。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正“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型范”(《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在文明的现代性进程中,种种不定性的外在因素正向个体生命甚至整个民族“袭”来,即使是边地湘西也无从抵拒这一文明进程。在个体情感上,文明进程带给沈从文原乡变乱的哀戚,还乡者坦言《散记》诸篇其实“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1]390;但在文明本位与民族进步的立场上,沈从文又信奉“一分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箱子岩》)。在他看来,故地乡民自足、单调的生存状态“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1]390,“时间正在改造一切,尽强健的爬起,尽懦怯的灭亡”(《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正如命运对生命个体的“摊派”与“分定”,是无可抗拒的进程。因此,原乡变动引发的一己乡情纵然痛苦,却只当抑制,成为“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与“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
既然认为文明进程不可抵据,沈从文只能转入如何“应对”的思索。而恰恰是在边地水手身上,他寻得了个体与民族应对文明进程的理想方式:边地水手之于生存困境与个体、民族之于文明进程何其相似,而水上人的“狂热”可以、也应当被改造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箱子岩》)。还乡之旅中的“人事”使沈从文“增加无量智慧”,“这里的人同城市中人相去太远,城市中人同下面都市中人又相去太远了,……此后关于说到军人,说到劳动者,在文章上我的观念或与往日完全不同了”(《过新田湾》)。带给还乡者“智慧”并引发其观念变动的,正是边地生命对于现代文明进程的意义与启发。“无言”与“不易形诸笔墨”的是一己乡情,而“想好好的来写”的,正是文明本位立场上领悟到的边地启迪。
就这样,沈从文据于现代文明的本位,建构起理想中的湘西水手形象,他们于外在不定性面前的过程性担当,他们生命意志的高扬,正是民族在文明进程中匮缺与需要的品质。沈从文笔下的边地水手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象征无言地承受“现代性”的批判[5],而是以其前现代的生命力量补济现代文明。这一还乡途中生成的生命观,实在具有迎向现实的意味。散文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的辰州军官,正体现了现实情境下不悖于沈从文理想的生命状态:
当前严重的事实紧紧束缚他们,……他们明白一切,却无力解决一切。然而他们的身体都很康健,那种本身覆灭的忧虑,会迫得他们去振作。……这些人界于生存与灭亡之间,必知有所选择!
无力解决却“明白”一切,向着“覆灭”振作、求生,这与边地水手多么相似。“选择赋予一个人的本质一种庄严”③,在生存困境中的自由决断诠释了存在的意义,实现了生命的担当。相形之下,长沙几个“患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的青年学生“一见我别的不说,就提出四十多个文坛消息要我代为证明真伪”。在沈从文看来,这些青年学生不去考虑自身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对生存既毫无信仰”,对一两个作家的轶事却津津乐道。他们在困境中将生命的力量消耗于生存进程之外,这样的生命态度为沈从文所轻视。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还写道:“我很愿意尽一分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我愿意好好的结结实实的来作一个人,可说不出将来我要作个什么样的人”。“时间”是过程性的可能性,面对不定性的时间,沈从文把握甚至沉醉于生存发展的可能,虽然存在的最终状态并不可知,但他要通过“结结实实”的生命过程创生意义。
五、沈从文的生命观:一个复调、动态的“连续统”
沈从文30年代初的这次还乡体验孕生了《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的写作,以及生长于二者差异性空间中的生命哲学。静视不定性命运却又固执地担当、“除阻”,这一文明本位与迎向现实的生命观在民族战争到来,他所预感的文明变乱成为全局性现实的三四十年代,获得了赓续、发展。
王晓明曾阐析沈从文独特的小说文体:“先以歌咏田园诗般的散文笔调缓缓地展开对湘西人淳朴风情的细致描述,最后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一下子打断前面的歌咏,把你推入对人生无常的强烈预感之中。”[6]453而创作于30年代那次还乡前后的《边城》既是这一文体的集大成者,却也是“最后一位出色的产儿”[6]454。从用力于对“天地不仁”、“人生无常”的表现到这一模式的收煞,30年代初期正是一个转折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两度还乡④,经历了现代—前现代的差序体验,并于第二次返乡途中逐渐形成本文所分析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还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忧、外患开始共生,民族危机日益深化。那么,可否大胆推想,这三者之间存在深有意味的关联?
在这一全局视阈下,沈从文在创作中体现出的生命观或许可以被视作一个复调、动态的“连续统”(continuum)。数学领域中的这一概念在此意谓一个在边际间连续渐变的有机整体。沈从文生命观的边际二维可以分别视作“命运”与“意志”,其生命哲学随其人生经历、创作历程在此二者间动态滑动。
作为“连续统”的生命观是复调的,沈从文既承认个体生命在不定性命运前的虚弱、无力,又肯定了生命存在过程的担当、“除阻”与决断。将沈从文解读为纯粹的非理性主义者或是纳入完全的启蒙理性立场都是偏颇的。生命观的“连续统”又是动态的。诚如王晓明所言,《牛》、《菜园》、《三三》等一系列20年代小说创作都表现出沈从文对命运无常的认知,但《边城》以后的小说明显偏离出先期的路向。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从原乡水手身上汲取到生命的力量,这种“生命意志”在40年代与作者的文明本位、民族关切密切结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可以说,随着个人文明体验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沈从文的生命观逐渐由“命运”一极向“意志”一维滑动。
最后应予指出的是,无论这一滑动怎样显著,它都发生于复调的“连续统”之内。沈从文肯定生命的意志,于整体上却并不认为个体生命可以左右、超越命运;他推崇的只是“悬置”不可知命定结局的过程性担当。即使在40年代,他依旧感受到“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7]。而类似的悲剧感受,在1948年起的“天地玄黄”中,定当更为强烈。沈从文四九年以后的文化选择,亦可视作对自身生命观的忠实践履。
注释:
①《湘行书简》由沈从文次子沈虎雏在1991年根据原始信件整理、编辑而成。除《小船上的信》原有标题外,各信标题均为整理者所拟。本文括注均据《湘行书简》中的后拟标题。
②见《湘行书简·滩上挣扎》。
③[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转引自冯至.决断[J].文学杂志,1947(3):200.
④除却本文涉及的一次外,沈从文还曾于1931年陪伴丁玲母子返回湘西。
[1]沈从文.《湘西散记》序[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M]//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226.
[3][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52.
[4]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第十二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434—484.
[5]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1.
[6]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M]//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修订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
[7]沈从文.长庚[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9.
On“Image Construction”in Xiangxing and SHEN Cong-wen′s View of Life:The Sailor Images from Xiangxing Shujian to Xiangxing Sanji
XU Yi-c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Xiangxing Shujian can be seen as the source of material for creation of Xiangxing Sanji,the contents of which are interrelated but endowed with different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simultaneous writing”and“lagged writing”.The sailor image in the essays of Sanji is one who“stubbornly”put up with the uncertain fate and strived for a living in a remote area,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version in Shujian and shows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feature.Shujian records the emotional change process of SHEN from pity to awe and love towards life in Xiangxi during his trip to hometown.The sailor image in Sanji is the discourse“image construction”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view of life gradually produced in this process.The“image construction”process reveals SHEN′s hope to implement modern civilization with rural vitality and his concern about real life.SHEN Congwen′s view of life can be depicted as a polyphonic and dynamic“continuum”related with“destiny”and“will”.
SHEN Cong-wen;view of life;Xiangxing Shujian;Xiangxing Sanji
I206
A
2095—042X(2014)01-0084-07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1.019
(责任编辑:朱世龙,沈秀)
2013-10-06
徐一超(1990—),男,江苏无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