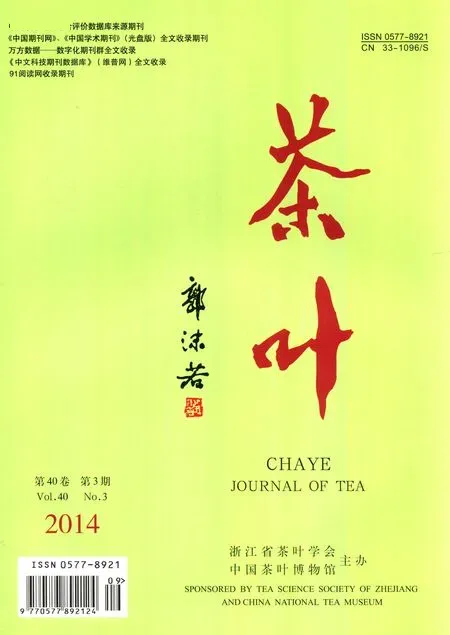“淡如秋水净,浓比夏云奇”
——忆吴觉农的好友,茶人佘小宋、叶鸣高先生
吴 宁
“淡如秋水净,浓比夏云奇”
——忆吴觉农的好友,茶人佘小宋、叶鸣高先生
吴 宁
茶人佘小宋先生(1895-1969)和叶鸣高先生(1915-1992)是吴觉农先生的好友。佘小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吴觉农同在芜湖二农任教,以后又主持浙江衢州东南茶叶改良场的工作,他也翻译多本 生物进化论。叶鸣高先生在东南茶叶改良场、崇安茶叶研究所研究茶叶。1954年后在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教书。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回忆佘小宋、叶鸣高先生的几件往事。
佘小宋;叶鸣高;东南茶叶改良场;吴觉农
前几年,我在杭州的时候,常去爷爷的老朋友陈观沧先生家聊天。观沧伯九十岁了,但六十多年前的事他却记得清楚,讲起来有声有色的。他的妻子佘世芳娘娘也很健谈,特别是讲到她父亲和她在屯溪、祁门的经历。观沧伯家两代人与茶人联姻:世芳娘娘是爷爷的老友佘小宋先生的女儿,而陈伯伯的女儿陈春之又是叶鸣高先生的儿媳,这样三家茶人就成了亲戚,我们在一起回忆茶人佘小宋和叶鸣高先生的话也就多了。
一
世芳娘娘对我说:“我爸爸和吴伯伯在二十年代就认识,同在芜湖农校教过书……”。
1922年的夏天,爷爷从日本回来,由浙江农校的老校长吴庶晨介绍他去芜湖二农讲茶。爷爷在上海一收到聘书,就乘船去报到了。一到学校,他兴冲冲地带着写好的茶学讲义和新式茶园规划去见校长卢仲农,可他失望了:原来学校是因为教病虫害教师的突然离职请他来代课的,而且学校也没钱建茶园。卢校长要他与农校的学监佘小宋去谈谈。
爷爷很不高兴,他对佘先生说,学校“误导”了他,他是一心来教茶的,只代教昆虫学怎么行呢?佘先生说,这一两年,学校的经费的确紧,有时连教师的薪水都欠了,一时的确拿不出钱来建茶园。他安排爷爷先住下,又借去了爷爷的茶讲义和茶园规划,约爷爷第二天到学校的试验农场走走。
第二天,小宋先生带着爷爷去试验农场,那里有成熟的果园、菜园、养蚕室。他对爷爷说,二农原是安徽公学,辛亥革命以后,安徽急需农业人才,卢校长就把公学改成了农校和商校,还带着学生老师开辟了这一大片试验农场。
佘先生对爷爷说,你的这份讲义很好,这学期你就来开茶学课好了,二农的学生来自浙江、安徽、湖南,家里多有茶,这门课有用。小宋先生建议爷爷茶课从调查土壤和选择“小气候”开始,茶园就由学生来建。他说,农校的试验农场什么都有,只缺茶籽,茶秧。青弋江边的集市上有安徽各地来卖茶的茶农、茶商,能找到安徽各地最好的茶籽茶苗。爷爷听了很高兴也惊奇,小宋先生竟对茶学如此熟悉。原来他曾在安徽茶务讲习所教过书,在日本认识的胡浩川、方翰周都是他的学生。
那一学期,爷爷在二农教茶树栽培,他与学生们开辟了二农的茶园。 1925年春,胡浩川先生来二农任教,也在这片茶园中花了不少心血。十三年之后,1936年,吕允福先生来这里时,正赶上芜湖发大水,而在学校的南坡上,那这一片郁郁葱葱的茶园却安然无恙,茶树长得很茂盛。
二
小宋先生是安徽铜陵县大通人,1895年生, 曾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世芳娘娘搞不清父亲是究竟是哪年在中国公学读的书了,只是说他上学时,梁启超先生是校长。根据胡适先生的“中国公学史”那就应该是在1915年到1917年间。1917年公学停办之后,小宋先生就在芜湖和安庆办教育。
1923年,小宋先生的妻子儿女都在老家铜陵,他单身一人住在农校,他的寝室在爷爷隔壁。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打太极拳,然后读书,早饭后就忙校务了,晚上的大块时间,他都用来译书。他曾对爷爷说,他信达尔文也信孔夫子。 爷爷问他孔子和达尔文有没有矛盾?他笑笑:“人生就是自相矛盾嘛”然后加一句:“进化论要从外面引进来。文化还是中国的好。”
小宋先生是学化学出身但他对生物学入迷,他遇到爷爷的时候,正在翻译杰阿司 华生(J.A.S Watson ) 写的一本科普的《进化论》。那本书不仅文字浅显,而且还有很多清晰的图片,爷爷印象最深的是一棵“生物进化”之树,标出了地球上亿年生物从虫、鱼、哺乳动物到人的进化,人站在树顶上。小宋先生一边读,一边把书翻译成白话文,请爷爷先读,提问题。爷爷说,他对于生命是怎样形成和进化的了解还是来自于小宋先生的译文。
在这之前,爷爷他们都熟悉《天演论》中“物竞天择”这个概念,但天演论主要是给了他们 “中国不进化也就要亡国了”的紧迫感:“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选择。而佘小宋对于进化论的兴趣是纯科学的,他常发与众不同的“怪论”。他说,严复的《天演论》文字精采,在社会进化论上却走极端,并不代表赫胥黎的本意。那时,爷爷常为几家报刊写些小文章,他就建议小宋先生也把他的这些观点发表一下,佘却说,西方进化论的好书多得很,翻译都来不及,轮不到他的一知半解。
小宋先生读过好几遍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著,写过不少笔记。他的墙壁上有一张地图,上面标着达尔文乘船去南美和大洋洲考察的路线,是从根据达尔文1831到1836年随小猎犬号周游世界的笔记手绘的。胡浩川先生曾对爷爷讲起,四十年代在屯溪,大家都知道佘先生有一本补了又补翻烂的的英文字典,他不仅通英文,还自学了德文、法文和俄文,都是只能读,不能开口讲。
1923到1924年间,芜湖的政局不稳,学校闹学潮,港口闹工运。 爷爷是一心兴茶,不大关心政治,他以为小宋先生也是一样,直到有一天,爷爷在街上走,看到一群学生示威,用石头砸一家豪宅的大门,而小宋先生就站在学生中间。爷爷怕事,连忙转身“逃” 了,装作没看见。回到学校之后,佘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爷爷也就不问。在爷爷的眼里佘小宋一心科学,生物学,而且办事沉稳,三思而后行,那次在街头相遇,真使他震惊。
三
因为学校里发不出工资,学生又常罢课,爷爷在二农只呆了一年,下一次与佘小宋共事是在十三年后的浙江万川了。
1940年秋天,在重庆中茶公司技术处搬到浙西衢州万川,成立东南茶叶改良场之前,爷爷到屯溪请小宋先生去改良场做总务,佘虽然答应了下来,却对爷爷说,恐怕在万川不能长久 离“前线”太近了。爷爷说,真给小宋先生说中了。在万川九个月后,就又搬到了福建。
当时的东南茶叶改良场,除了省参议员陈牧的房子是“现成的”以外,几十个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安排。佘小宋当总务,实际是总管,什么都要安排。这时中茶在重庆,在香港也有好几位有经验总务 为什么一定要请安徽屯溪茶叶管理局的佘小宋呢?爷爷对屯溪的方君强先生说,改良场是白手起家,非佘先生不能胜任,特别小宋先生懂得“人的化学”,会调配。加上中茶技术处的人要去祁门、婺源、三界茶场实习,茶场的头头脑脑都是小宋先生的学生,都会尊重他。
1941年春,佘小宋全家住在屯溪了。佘世望,小宋先生的儿子那年七岁,记得父亲本来是每天回家,去了万川之后,就很少见到了,家里只有姐姐佘世芳和母亲。
去万川安排爷爷的朋友叶作舟先生,读叶先生打“前站”的日记,就知道万川一切都是从头起的,而技术处的几十个人到了万川以后,食住行都靠他。技术处的人去联系这些茶场,订下日期,谁去谁不去,去多久,也都是佘先生安排的。
除了主持日常的工作,小宋先生还要应付场里各种突发的情况。当时做《万川通讯》记者的林芹(珊)回忆说,1941年正在紧张的制茶时节,场里的倪仲光先生在衢江中游泳淹死,是小宋先生一面与沦陷的上海家里联络,一面在万川主持办理后事。不久,一位最有经验,大家尊重的中茶雇员,开化华埠的厂长刘畛先生因失恋突发神经病,把一对来航鸡养在床上喂牛奶,又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谁敲门都不开,大家都怕了。朱刚夫先生只好连夜去找佘先生。刘畛还真听小宋先生的,不仅开了门,还乖乖地随着小宋先生回福建养病。读当时的《万川通讯》、《安徽茶讯》不大看到佘先生的名字,但他却真是东南茶场的核心。
1942年之后,佘小宋一直在屯溪的茶叶管理处,他与方君强、傅宏镇先生主持安徽茶叶管理处的工作。据他小儿子佘世望说,1946年之后,他就在上海的法医研究所上班,一直做到退休。 奶奶曾提起,大概是在1964到65年间,佘先生退休来北京住在他大儿子家里,爷爷曾几次约他来家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却没有来。直到那一次,爷爷才从朱刚夫先生那里了解到,佘小宋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1925年与张秋人在芜湖办过新民中学,与陈独秀也有往来。小宋先生学俄文和德文的目的是为了读马列原著。原来小宋先生介绍爷爷认识的、在芜湖长街上办“芜湖科学图书社” 的汪孟邹也是地下党,图书社隔壁的徽州会馆,就是地下党碰头的地方。
到了八十年代,爷爷只是偶尔提起佘小宋了。娘娘们只是记得他还是称他“小宋先生”,是爷爷二十年代的习惯,透着对佘的尊重。
佘先生是1969年在北京走的。在文革之中,打打杀杀之时,不知他有没有被斗,被吓,那年他七十四岁。
四
观沧伯讲到了1942年他与佘先生两次从崇安去祁门,又从祁门回到崇安的经过,他研究红茶分级,佘先生研究红茶中化学提取物。每次四十多天,多是步行,偶尔也坐烧木炭的长途车。 一路上,佘先生对他很照顾,去的时候,他们一人背一袋的安徽香椿干馅的面饼子,观沧伯在路上总是很快就把饼子吃完了,佘把自己的饼分给他大半,他好象是神仙,不饿不渴。
那一年,福建山里的桥梁为了防止日寇进犯都被破坏了,山与山间只有两根树木捆在一起的独木桥。观沧伯说,“我看到桥下的百丈深渊,腿擞擞抖,而佘先生先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于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跟过去,有时是连滚带爬过去的。佘先生对他说,走独木桥是在安徽芜湖走浮桥时练的,青弋江上的桥以舟为墩,人踩上晃得厉害,风浪一大就更令人心惊胆战,比起那浮桥,福建山里的独木桥稳多了。
四十年代,世芳娘娘给安徽茶叶管理处当会计,有空也帮助方君强先生抄抄写写。我奶奶1942年从上海去福建,路经屯溪,对世芳娘娘印象特别深,说她穿着一身男装, 头发剪得短短的,声音脆亮,人是格外的泼辣精干。那时候,方君强、佘小宋和傅宏镇几家都住在屯溪柏树的一栋大房子里。世芳娘娘对我说,“方先生人特别和善,他给我们牵的线。在这之前,我爸爸早就看中了观沧,只是不好开口。”
世芳娘娘还说,“我们结婚之后,养过几年的蜜蜂,蜂箱,巢框,摇蜜机是爸爸和观沧做的。 我们养蜂,爸爸也常来帮忙,他最欢喜观察“蜜蜂社会”:观察蜜蜂之间的“分工”“交流”和“配合”。 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蜜蜂、人和蚂蚁有这样高度组织的社会。爸爸真是有趣,喜欢讲猿猴到人,喜欢把人与蜜蜂和蚂蚁相提并论。”
那时,我刚刚读完小宋先生在1937年翻译的《人类的史祖》和1940年翻译的《长生论》。这两本书不仅研究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进化和长寿,也涉及文化的进化,哲学、心理学,也有章节探讨社会性昆虫和人的社会性。在那个年代里,通过翻译这几本书小宋先生对人类社会的了解竟是这样的丰富! 没想到八十年后,与爷爷一样,我了解人类的生物与文化进化也是从小宋这几本“过时”的译文开始的。
沿着街道往前走,邂逅了路旁的刺玫花。成团成簇的小花相依相伴在枝头,绽放着淡紫、淡红的花冠,煞是繁盛。那样娴静、羞怯,织一份柔情向我倾诉着相逢的喜悦,此时我只能静静地注视着她们,凝眸无语。擦肩而过的是下晚自习的学生们,他们披着月色,涂抹了一路的欢歌笑语,把疲惫和困乏泼洒了一地。
小宋先生走后的五十年来,生物学的研究各个领域日新月异,生物进化与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的许多边缘学的研究,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人的社会行为,和人的本性最终都是来自几百万年的生物进化和几万年的文化进化,读这些有趣的书,我常会想到小宋先生。然而在写这个故事时我也常常问:根据他对进化论的了解和对严复的批评,小宋先生怎么会放弃改良,而选择了革命呢?这也许正如他讲的,人生就是自相矛盾的。
五
今天在武夷山作岩茶的人中,大概已经没有人认得叶鸣高了。但在爷爷办茶叶研究所的年代,叶鸣高先生是研究所的昆虫和树种专家,不仅研究所的人都知道他,武夷山各岩的包头和茶工更熟悉他。
爷爷是在1939年认识叶鸣高的,张堂恒先生在他回忆中提起那年春节,“与同学在浙江温州的旅馆里等吴老”,他的同学就是叶鸣高。以后叶鸣高就去了重庆,在中茶公司技术处上班。1941年初,从重庆到浙江衢州万川东南茶叶改良场,然后来到武夷山。
在福建崇安时,我父亲、姑姑们都记得叶鸣高先生:中等个,分头, 一副厚眼镜。别的叔叔阿姨们见了他们都很亲切,只有叶先生见了他们爱理不理的,把他们当小孩吧。有几个月,爷爷还请他给我父亲吴甲选补过英语和数学,我父亲说,叶先生的普通话里带着很重的苏北口音,讲得又快,可不好懂了。
观沧伯伯说,叶鸣高在中茶公司之后,一直是研究茶树病虫害。1941年,在去祁门调研之前,听爷爷讲茶树品种分类是复兴茶业的关键,叶鸣高就提出要“改行”,研究茶树品种。爷爷说,“你现在是研究病虫害的“专家”了,我们缺你不行,能不能两者兼顾呢?”结果叶鸣高从祁门回来,真的背回了两套标本: 一套病虫害,一套祁门茶树品种。他与严忠合作不仅对祁门茶树的病虫害做了详尽的调查,又采集和制做了祁门县平里、城区凤凰山、凫溪口茶树标本。只缺了历口,是请观沧伯伯1944年在祁门做分级红茶试验时补上的。
研究所搬到福建崇安之后,叶鸣高又是“双管齐下”:研究病虫害兼收集茶树品种。那年,武夷山茶树煤病泛滥,许多岩上的茶丛枯死,特别是在马头岩一带,介壳虫寄生杀死了90%以上的茶树。叶鸣高整理了二十多种昆虫标本,出过《崇安茶树煤病之初步调查及鉴定》的单行本。 武夷山茶树品种丰富,绿水青山之蕴藏着绚斓缤纷的岩茶传说,叶鸣高真是入迷了,整天在山里转,找岩上的人聊天。说来也怪,他在研究所没有什么朋友,却与各岩的茶师、包头们关系好得很。除了天心岩的大红袍之外,包头们对他不保密,他可以去各岩看茶树、看茶工们制茶。
叶鸣高几本很珍贵的笔记,里面有详细的岩上每株茶树特征、茶树生长状况的记录,和每株茶的历史和传说。他珍视从包头那里得来的传说,那都是茶农多年经验及试验的秘密,说要了解武夷山岩茶树品种,非要访遍各岩的茶师,而且要访多次。
叶先生的妻子吴兰征是武夷山天心村人。她说,叶鸣高为了得到九龙窠那株大红袍的枝条,挖空了心思。他先要弄清哪一棵是大红袍。 因为大红袍的名贵,天心寺里的僧人怕外人来剪去繁殖,就用半岩中的“奇兰”鱼目混珠。终于有一天,清源岩的周包头带他去认过九龙窠西坡上的大红袍。正巧,在天心寺看着大红袍的僧人是吴兰征的远亲,趁僧人下山去吃午饭,叶鸣高冒险爬到天心岩上, 剪了两穗”大红袍“的枝条。以后他又在北斗峰发现了两株大红袍,也剪穗扦插在研究所的茶园里。我爷爷给这两株大红袍起名“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因为天心岩的大红袍是“偷剪”来的,“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默默无闻地长在“北斗”的旁边。
我爷爷的侄女郑仲仙说,她的丈夫吕增耕刚到武夷山时曾与叶鸣高同宿舍。那一阵,正赶上日本敌机常来轰炸,镇上的房屋被炸,企山研究所的一位炊事员被炸死,人心惶惶的。叶鸣高却仍然每天去山里收集病虫害的标本,增耕和陈舜年也跟着他进山。一路上,都是叶鸣高讲话,苏北口音加上叶鸣高的思路跑得太快,增耕听不大懂他的普通话。幸亏陈舜年能听懂,他爱和叶鸣高抬杠。陈舜年也是绍兴人,他就成了增耕的“翻译”。
仲仙娘娘说,叶鸣高讲话挺 “刻薄”,不管是谁都要讲,但他讲完了也就忘了。叶对爷爷很敬重的,可爷爷讲话,他有不同意见,也会当场提出,好在你爷爷挺了解他,有什么讨论会专门叫着他,说是多听听“反面意见”很有益。
仲仙娘娘与研究所的出纳徐珠是好朋友。听徐珠说,1943年,张堂恒在印度参加远征军,叶鸣高把自己的每月的工资分三份:一份自己,一份寄给张堂恒的父母,一份寄给自己的父母。他弄不清怎样往日本人占领地汇钱,就请徐珠帮他办。有一段时间,研究所的经费紧一时发不出来,他让徐珠先汇给张家,剩下才寄自己的父母。
在武夷山的时候,叶鸣高与尹在继同办公室。尹伯伯也对我说过,他(叶明高)聪明绝顶,又 “怪”, 很是自说自话, 思路快得不得了,讲话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别人跟也跟不上。他的办公桌今天要这样摆,明天要那样摆。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讲到他两手同时写字的本领更神了,他的书法和诗写得好。用毛笔,一只左手,一只右手,写一幅对子,同时两手各写一联,字很潇洒。
他还说,叶鸣高固执。陈舜年英文好,那几年,你爷爷让陈舜年负责审订《茶叶全书》全译稿,叶鸣高、许裕圻、叶作舟好几个分别审订章节。为了茶专业名词的一致性和文字的顺畅,陈舜年对叶鸣高的中译文做了修改,而不知什么原因叶鸣高却硬是一个字都不让改。两人争得厉害, 一直争到你爷爷那里,最后你爷爷请叶元鼎先生“仲裁”才算数。
六
1951年叶鸣高应张堂恒之招去了武汉华中农学院茶叶专修科教书。1954年,专修科并到了杭州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叶鸣高很高兴。他是浙大毕业生,去浙大也就是回家了,加上他的好友张堂恒也已经在那里了,观沧伯说,叶鸣高刚从武汉来杭,他就急着要去武夷山取名枞回来扦插。当时正是盛夏,张堂恒说这时去取枝条一定扦插不活,叶不信,两人就打赌。那次叶鸣高从武夷山带回了很多岩茶枝条,种在华家池的茶园里,竟然都活了!张堂恒请我们好几个人到奎园馆去吃了一顿面。
叶鸣高先生的妻子吴兰征回忆说,“他不懂政治,常常会讲些大实话,又没交什么朋友,落难了,也没人帮一把。1959年的国庆节前,浙农大茶学系已经搬到了梅家坞。全系到乡下参加整风,那是“反右”后的一年。别人都回来了,只有叶鸣高没回来,我去问,系里的人说是被保卫处的人带走了。保卫处说他有思想“问题”被送到留下果园去劳动教养了。
“留下果园离华家池有三十多里,我去看他,他住在一个潮湿的蕃薯窖里,我们谈了一夜。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被送劳改。反右前,他没有提过意见,也没写过大字报,对领导是蛮尊重的。他说也许是弄错了,那晚,他有心思给我讲讲“留下” 的来历:长毛造反,杀人放火,一个长毛的头子娘舅住在留下,那个头子托人捎信给娘舅说,明天要去留下烧杀,他要娘舅让亲戚们在门口插一株杨柳,这样长毛不会去杀那一家。他的娘舅心好,就告诉全村人在门前都插杨柳了,全村人都活下来了。叶鸣高讲,所以叫“留下”。留下,就是没被杀掉。”
叶鸣高被送去劳改之后,家里生活没有来源。吴兰征就去给火车站附近刀茅巷里给一有名的中式衣服的裁缝打下手,先是补衣服,边学做衣服,她做了十八年的裁縫,直到叶鸣高被放回来。叶鸣高的哥哥弟弟也每月每人给她寄十五元钱。就是这样,吴兰征养大了四个孩子。在被送去劳改的十八年里,叶鸣高换过多个劳改农场,每个农场她都去过,她为叶鸣高冬天做棉袄,夏天做衬衫。她一次次地找学校,找浙大、杭州市的领导,也去过北京,给毛泽东写过信,却弄不清叶鸣高被送去劳改的原因。吴兰征说:“讲他是反革命,是漏网右派,加上他家里的地主成份。他家在江苏泰兴,兄弟三人,没有田地,只有一个果园和果树。
提起叶鸣高,张堂恒先生的妻子朱良沄对我说:“我是1958年从监狱里放出来的,1959年回到杭州。 我到杭州的时候,叶鸣高已经被送去劳改了,记得张堂恒很难过,他与叶鸣高是好朋友。 他常说,‘叶鸣高是替罪羊。他替了我们很多人的罪。’”
当时的右派是有指标的,张堂恒本来要被划成右派,要划,没划上。反右之后,叶鸣高就被拉去顶了。
张堂恒先生的这几句话深刻。在那所谓“阶级斗争天天讲”,阶级“敌人”有指标的年代里,每次运动中,我们每个幸存下来的人都要有“替罪羊”,那些最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最少私人关系,讲真话的人就为我们 “替罪”了。
去年,我在1946年的《闽茶》杂志中找到了叶鸣高写的,“武夷祁门茶树品种之调查与研究”。这篇文与他在武夷山时写的 “崇安茶树煤病之初步调查及鉴定”也就是我所能找到的他文字了。记起吴兰征曾对我说:“他从认识我的时候起,就想写成一本中国茶树品种的书。在他在被送进去劳改之前,他中国的茶区都走遍了,只是没有去过西双版纳。”最后一次离开陈伯伯家,他站在楼梯口对我说,“今天恐怕没人记得佘小宋和叶鸣高了? 你写了会有人读么?”他的这句话一直跟着我。
坦白地讲,论对茶叶的研究和茶业的发展贡献,爷爷他们那一代人,包括佘小宋、叶鸣高先生所做的是有限的,是比不上现代人的,而且他们的时代也离今天的社会很遥远了。但二十世纪上半世纪很特殊,虽然他们那一代茶人的物质生活很贫乏、思想单纯,但他们每人都有个性,有个人的兴趣和追求。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态度去吸收的西方人文与科学,与今天中国从西方搬来的那种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形成了对比。他们生活清淡如秋水,他们的人生经历又是“浓比夏云”的。只可惜我对他们的了解太有限了,拾到的只是零散的生活碎片而已。
Mr. Xiao-song She and Ming-gao Ye
WU Ning
Mr. Xiao-song She (1895-1969) and Ming-gao Ye (1915-1992). Both of them were good friends of Jue-nong Wu. During the 1920s, Xiao-song She and Jue-nong Wu taught at the Second Agriculture School in Wuhu, Anhui province. In the 1940s, Xiao-song S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Southeast Tea Research Institute in Quzhou, Zhejiang province. Ming-gao Ye worked in both Zhejiang and Fujian provinces for the Tea Research Institute. He was an expert in tea plant disease and tea arboriculture. He taught in the tea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fter 1954. This paper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recent years that recall a few stories of She and Ye.
Xiao-song She; Ming-gao Ye; Southeast Tea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an Tea Research Institute; Jue-nong Wu
2014-04-16
吴 宁(1957年-),女,20世纪8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美国佛州大学民族音乐学硕士,卫理大学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硕士,现住美国德克萨斯州,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孙女,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杭州联络处外籍会员。
K826.3
E
0577-8921(2014)03-1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