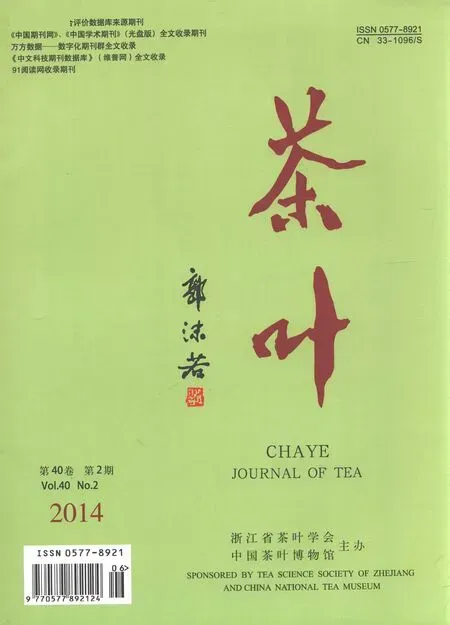“有匪君子,终不可谖”
——回忆我的爷爷吴觉农的好友范和钧、向耿酉俩先生
吴 宁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
——回忆我的爷爷吴觉农的好友范和钧、向耿酉俩先生
吴 宁
范和钧先生(1905-1989)和向耿酉先生(1913-1992)茶叶专家, 吴觉农先生的好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同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之后又分别去了安徽、福建、四川和云南等茶区种茶制茶。1949年以后,范和钧先生在台湾办茶场。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回忆范和钧、向耿酉先生的几件往事。
范和钧;向耿酉;上海商品检验局;吴觉农
一
在奶奶的记忆里,她和爷爷第一次见到范和钧先生和他的妻子允琴是在1932年冬,去参加邹韬奋、胡愈之所发起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捐的一次聚会。虽然他们与范和钧只是经愈之介绍,寒喧了几句,但这一对气质不凡的年轻夫妇,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爷爷却说,他和范和钧应该是在商检局碰面的,那一次,范和钧先生是为法国茶叶专家当翻译。去年,我还真在1933年6月18日的 上海《申报》上找到了爷爷和范和钧先生在商检局碰面的消息,全文如下:
法政府派員來華調査,現法政府所派之調査專員古博氏(Jean Goubeau)已於上月到滬。古博係法國農業工程师,曾在安南(今越南——编者注)農業研究所担任茶師十餘年,對於東方茶業情形極為熟諳,到滬後即與法領事所派之譯員范和鈞前往浙皖贛及兩湖產茶各地調査。日前回滬後並訪實業部上海商品檢騐局局長蔡無忌及該局茶葉檢騐技正吳覺農,關於華茶運菲及栽製等方法之改善雙方討論至四五次之久。據檢騐局負責人員吿記者,博氏認為,着色茶葉之禁止及集合力量向外宣傳為挽救華茶之根本要圖。又該氏到安徽祁門時,曾参觀安徽省立茶葉改良塲,對於該塲本年辦理運銷合作之成功及試騐栽製方法等之方針亦多稱譽。(古博)氏在本埠尚須參觀製茶商家數處後,即擬前往日本調査。
爷爷说,也就是在那一次,范和钧把他写 “中国洋庄绿茶调查记”交给他,请他指教。爷爷读后,十分兴奋:这位在法国学数学和艺术的年轻人是第一次接触茶,却能把徽州、平水和龙井制茶工艺的描述得如此到位,对上海土庄茶店茶着色的经过和 洋行茶庄的舞弊以换取最高利润的各种情形写得如此清楚,而且还对振兴华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真是难得的很呵!第二天,爷爷去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打电话邀请范和钧去参加商检局的茶叶工作。
奶奶说,那时候,吴家和范家离得不远,他们常常往来。范和钧曾对奶奶爷爷讲起过他怎样去法国留学学数学到变成在巴黎修理中国明清漆器艺工的经历。
1923年,范和钧从浦东高中毕业,考取了学校勤工俭学的奖学金,去巴黎大学读数学,谁知到了1924年冬,国内的奖学金突然断了,后来才知道是管理基金会的人把基金拿去赌搏,输掉了。这一下他们这几个留学生不要讲上学,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同住的两个中国学生去了农场打工了,范和钧从报纸上看到巴黎拉丁区的几家古董店在聘用修补中国漆器的漆工,他一家家去试。因为完全没有漆工的经验,他先是一家家被拒绝,但也就是在应试的过程中,他观察学会了怎样搅漆,怎样用漆刷、削刀和凿刀,很快,他找到了一份修补漆器的工作。
在巴黎的几年里,范和钧慢慢接触到许多在国内早已绝迹的,明清两代的珍品。种类之多,艺术之美,使他陶醉,于是改学艺术,他白天在中国古董行修补漆器,晚上去巴黎工艺美术学校去上课。那几年里,在巴黎古董行打工的中国人很多,然而能够达到专业水准(法国古典派)修补明清两代古漆器的人却仅有范和钧、苏州的江小鶼和杭州的雷圭元三个人。
范和钧先生1930年从巴黎回到上海,本打算是做漆器生意的,他一面在法国驻沪商务处做商务翻译工作,一面到扬州和苏州等地去寻访漆器艺工和收集各种漆器。收到的漆器以后他家里摆不下了,就摆到了我们家里。我的娘娘们还记得我家在楼上过道和亭子间的架子上都摆着漆器的花瓶、茶具、砚匣和碟子。
他的妻子娄允琴在法国学医,回到上海后,在一家法国人开的广慈医院里妇产科做医生,我的小娘娘就是她接生的。那一次奶奶产后意外大出血,多亏了允琴救了她的性命,很多年之后,允琴与小娘娘在旧金山重逢,还提及那一次。
奶奶听允琴讲,她与范和钧是同乡,他们的亲事是父母之命,从小就订下来的。范和钧的父亲早逝,是母亲把他带大,而他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又因病去世。范和钧在上高中时,就鼓励允琴来上海到圣玛丽亚中学读书。范和钧在法国几年之后,把在修理漆器的钱攒起来,接允琴去巴黎读医,直到1931年初回国,大女儿琅绨是1929年12月在法国出生的。
二
1933年,范和钧先生一到商检局, 就开始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的茶和农学书,他写了多篇有关茶业的文章,在《国际贸易导报》上发表。 那几年,他发表的文章很多,读导报几乎可以追溯他的工作内容和进展。 加上他精通英法日三国语言,翻译了不少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产茶国制茶的文章。 他写的文章著名范和钧,译文著名范樱。范和钧是1905年出生在日本,正赶上樱花盛开的之季节,其父給他起名范樱。
那时候,冯和法先生是商检局《国际贸易导报》的主编,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了,冯很欣赏范的敏锐分析和文字能力,他想拉范和钧給《中国农村》写文章。有一次,两人一起喝茶,冯拿給范一些《中国农村》还未发表的文章请他先读为快。可过了几天,范对冯说 这几篇文章太偏激了,火气大,不大合他的味口。从此,冯和法一直把范当成不参与“左派”政治的人。1985年,他们在北京重逢时,范和钧提起 1925年在法国,他的艺校同学柳圃青曾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一事,冯和法大为惊讶。他对范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人生真是不公平,你早就当过党内人了,却还要讲我们办的《中国农村》偏激,我“偏激”了六十多年,到现在还在争取,还在党外”。
1935年的茶季,范和钧与钱梁在祁门平里茶场,研究红茶萎凋和发酵。
钱梁对范和钧的印象是做事很严谨,做人很随和。当时在平里的还有胡浩川、冯绍裘、徐方干、姚光甲、张维以及平里合作社的章家茶农。胡浩川和徐方干都曾在日本静冈学茶, 冯绍裘先生刚刚在修水做过两年宁红,有很多实际经验。能人在一起,主意多,想法多,难免意见不同。特别是与徐方干先生,争强好胜,喜欢抬杠。他与胡浩川先生常会因为对各种试验结果发生争论。而范和钧却是只做不讲。那次去祁门,范和钧带了他不少印度和锡兰的制茶的文献和书,他说这些文都囫囵吞枣式的读过,那次要把关于红茶烘焙和发酵章节都翻译出来,作参考。钱梁问他为什么从不参加讨论,他笑着在纸的边边上写下“多闻阕疑,慎言其余。”八个字。他说孔子要他‘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保留意见,直到很有把握时候,才谨慎地说出。’ 这次在祁门,他只是要体验学习,到不了很有把握,能和这几位制茶“专家”一起做茶,听听他们争论,他也能学到东西,很快活。
有一天,范和钧与钱梁在河边散步,发现了几棵漆树,很高兴。他一有“忙里偷闲”的机会就会去用漆刀,插管和木桶去收漆汁。他教钱梁怎样收漆,他把“漆”字写在地上说:“你看,上部是木,左右各一撇,像切破的树皮,插管外导。”他还对钱梁说,漆树和茶树的原产地都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的漆树与茶树一样,都是移植过去的。茶树长在山上,烂石砾壤中香气才高,而漆树长在河溪旁,肥沃深厚的土壤中漆汁才丰富。
1938年初,范和钧与徐方干先生受中茶公司的委托去筹建湖北恩施茶场,刚到时,场里的几乎一无所有,两人手巧,一面自做萎凋架、改造揉捻机,发酵箱和烘炉,一面等着从香港订制的茶机和兴建的厂房。几年之后,当黄国光、张志澄带着重庆中茶的学员们来恩施实习时,还用过范和钧、徐方干手制的工具。到了春天,冯少裘先生也来了,这是继祁门之后,三人又碰到一起做红茶的机会。他们那年所制的几百箱的“恩红”运到武汉去销售,评价极好。
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去云南考察,同年十二月,他与张石城先生在佛海(现在的勐海)建茶场。范和钧先生写过很多文章,但从来不提自己,他的佛海经历是唯一的一篇,是在1985年应邀为中茶云南茶叶公司成立五十周年所写。范和钧的回忆言简意赅,细读那平静的文字,却能感受得到他惊心动魄的经历。
1942年范和钧回到重庆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与学生谷应开办了重庆大西机械制茶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他回到了上海后,很快去了台湾在那里的三叉茶场当场长。范的小女儿梅蕾说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茶场的管理入了轨道,他就一边为美国的茶与咖啡杂志写稿,一边自学装制短波收音机。1954年,茶场关闭,他又去开办台湾的第一家种鸡场, 养欧洲的洛岛红,蛋是红的;澳洲的来航鸡,蛋是白的;还有美国的黑石斑。退休之后,他就专心地去研究漆器工艺,创作了很多精湛的作品,陈列于在台湾华岗博物馆。
三
范和钧先生在一生中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茶书:《中国茶业问题》(1937年6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另一本是漆器艺术:《中华漆饰艺术》(1981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
《中国茶业问题》这本书是爷爷与范和钧先生的合著的(1937 上海商务印书馆)。然而当我细读了这本书之后,有两点感受:一、自1922年我爷爷从日本回到中国之后,他与他的许多茶人朋友都对当时中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问题做过很多调查研究,写过不少文章,《中国茶叶问题》没有提出更多的新内容;然而,因为它的全面、深入,而且组织严密,条理清晰,一气哈成,如果有人想要了解中国当时的茶业问题,读这本书是最合适的。二、这本书应是范和钧先生的著作,至少书的最后一稿是范和钧一人执笔。从茶园经营、茶叶制造、茶叶对外贸易、茶业组织到茶叶检验很多细节和例子用的都是来自他1933年之后的各种实践。 我在读了范和钧所写的全部文章之后,感觉这样有系统地整理和分析,层层剥笋地深入是他的写作特点。范和钧先生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 书中的声音不是慷慨激昂的呼吁,而是经过深入、周密的思考之后的沉潜陈述。无论深读或浅读,这本书的确充满了范和钧的“个性”。
钱梁先生曾讲起过,爷爷与范和钧等一起筹划了这本书的提纲,我想,爷爷是有建议,有参与的,但书是范和钧先生写的。为什么要写两人合著,而且爷爷的名在前?是不是与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来向爷爷约稿有关?今天已没有知情人了。
范和钧先生1978年所写的《中华漆饰艺术》是漆饰艺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一本。中国历史上,记录漆饰艺术的专著只有明代黄成的《髹饰录》,而近三四百年来中国没有此类著作,只有一抄本在日本。中国古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先生曾说过,《髹饰录》是中国工艺技法中最难得、最有代表性的两本名著之一(另一书是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 范和钧从1924年在法国修补中国漆器开始,都是自己的摸索,从未读过任何这方面的专著。直到1971年,在他做漆工近五十年之后,才第一次读到了《髹饰录》。《髹饰录》 的著者明代的黄成与注释者杨明,也都是漆工出身,有极丰富的实践经验。范和钧读后,很受启发,但又觉得黄明很多地方没有写清楚。黄喜欢用象征和比喻的方法对漆饰的工艺手法作说明,这样一来文字就变得生涩难懂了,有些地方也过于简略。所以范和钧决定自己也写一本来弥补《髹饰录》之不足。范和钧先生的《中华漆饰艺术》在台湾出版之后,不少漆饰艺术家认为比黄明的《髹饰录》更有实践指导意义。我对漆器艺术的了解还是从收集范和钧先生的故事开始的。读了范和钧先生的《中华漆饰艺术》和黄成的《髹饰录》之后, 我才了解漆器工艺从商代就开始了,种类之多,艺术之灿烂,然而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范和钧从修补,到仿制,到创作,所有的心得体会,所有的经验都是来自个人的探索和揣摸, 来自与同伴们的切磋,讨论。范和钧对学习没有文字“记录”的传统艺术之难的切身感受太深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1933年他来学茶,在记录 制茶工艺时就不放过任何细节,对当时各地的传统制茶那样的重视。
范和钧的这两本书,一本写在他兴茶的开始,另一本写在他做漆器艺术的结尾,相隔四十多年,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陈言和空话,对中国传统的茶和漆器艺术充满了感情,他能够把他和别人在实践中所孤单和直接、自发的感受和见解积累、综合、系统化,使之成为有实用之书,有价值之书。
四
我家上辈的人每次提起范和钧先生,都不能不提到向耿酉先生。他与范和钧先生是连襟:向耿酉先生的妻子娄梅芯是范和钧先生的妻子娄允琴的妹妹。
听奶奶说,向耿酉是江苏江阴人,可他的讲话、动作、穿戴却顶像我们浙江的绍兴师爷,总是穿中式长袍,从来没见他穿过西装。讲话拖着长声,颇有点东晋名士处世的精神。一有空,他就会温点绍兴老酒,一边喝,一边读他手抄的《世说新语》。
向耿酉先生是很有能力的人,话不多,可办法多。他参加商检局工作早,常在祁门,胡浩川先生特别欣赏他。两人在一起讲制茶,也琢磨《世说》里的故事。1936年安徽祁屯茶区产地检验委员会成立,胡浩川为祁红区主任委员,向耿酉为他的副手。1939 、1940年间祁门开办茶叶训练班,向耿酉在屯溪,胡浩川每次都会请向耿酉来做训练班课长。
我家从1936年起,搬到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怡德里14号,是一座三层楼。 娄婆婆带着范和钧的妹妹和范和钧先生的女儿丽娜在我家楼下住着。向耿酉和钱梁、汤成在商检局的几个人,常来我家,就与娄梅芯谈上恋爱了。
他们结婚时,我爷爷奶奶都去了。结婚前,爷爷有一次问他是怎么和范家的小女儿谈上恋爱的,向耿酉说是像“温峤娶妇”。《世说新语》中,温峤的姑母刘氏请他为自己的女儿找婆家,温就几次不提名的 “毛遂自荐”,最后,自己就当上了新郎倌。据说,向耿酉常是这样,讲话总喜欢用《世说新语》中掌故来幽默一下。
爷爷说过,向耿酉这个人的性格,可用“若无其事”四个字来形容。1937年末,爷爷带着几个人从三界去武汉,先是坐船,后步行,没有东西吃,就喝水,既困难,又危险;而向耿酉却是一路添草加叶地讲故事,讲得挺生动。从南昌到武汉他们坐的是火车,走走停停,一路上日本人一直丢炸弹,火车上的人都像惊弓之鸟,只有向耿酉一有机会就侧头酣睡,还打呼噜。四十年代,他与钱梁在南平共事时,遇到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时,大家都躲起来,而他就在住处煮五香蚕豆,警报解除了,蚕豆也煮熟了。
陈君鹏先生在我家最爱讲的是文革中期,向从干校回来,他见到向耿酉说他瘦了。向耿酉说,“在五七干校劳动,头脑里污浊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天天地去掉了,所以就瘦了” 讲完哈哈大笑。以后,上海的几位茶人来北京,讲到向耿酉总会提起这个玩笑。直到我读了《世说》才发现,原来是从西晋庾公访周伯仁的故事中化出来的:周伯仁说庾公胖了,而庾公问周伯仁在忧虑什么而瘦了,周伯仁道:“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只是清淡之志一天天增加,污浊的思想一天天的去掉。”。
钱梁伯伯说过,在1949年之前,向耿酉是常常用《世说》中掌故开玩笑的,“三反”以后就少了,到了文革之后,也就用过这一次。
钱梁伯伯还说过,耿酉兄的口袋里从来都没什么小钱,四十年代初,在屯溪茶叶管理所,大家都喜欢到旧伙滩上去掏宝,去买小古玩,可他什么都不买,说是不为“物”所累。来时一个小铺盖,走时还是小铺盖,里面卷着就有那几本手抄的《世说新语》和两件长衫。1949年后,不知哪次运动被整,一害怕,把这几本《世说》也给烧了。1983年,中华书局余嘉锡先生所著的《世说新语笺疏》初版, 正赶上陈舜年先生来京,爷爷特意让他去买一本带回上海送给向耿酉。
五
1985年秋,范和钧先生在北京与爷爷、冯绍裘、冯和法他们又见面了,这是他们自 1949年分手之后唯一的一次。爷爷与范和钧三十年没有联系了,范和钧的大女儿琅绨、二女儿丽娜都留在大陆。1954年,琅绨在北京结婚,她拉奶奶去参加,在婚礼的宴席上我的奶奶代表她的家长成了她的证婚人。我的娘娘在师范大学上学时,曾与范和钧的二女儿丽娜在篮球场上碰遇。
幸亏爷爷的学生,重庆复旦的谷应先生与范和钧的女儿琅绨一直保持了联系。1981年,谷应给爷爷来信,顺便送来了范和钧先生在美国的地址和范和钧一家的消息。经过黄国光先生的努力,民进中央邀请范爷爷来中国访问。
在收集范和钧故事的采访中,听我家人和范家后人回忆起范和钧来家里看望爷爷的细节,那天,冯绍裘、冯和法、黄国光先生也来了。爷爷和奶奶请家里的两个阿姨做了一桌丰盛的常熟菜,我父亲吴甲选正好在家休假,在院子里,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整理几位八十多岁老人的聚会,使我联想到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对他们来说,那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时刻;充满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惊喜;老人们交换台湾、大陆老茶友的信息,那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感受;直到告别时,他们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惆怅。而近些天来,大娘娘找到了范爷爷回到美国后给爷爷的信和我父亲拍的那张珍贵的照片,这封短信却比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更使我感动。他写道:吴老、陈老前辈:当你们温暖的手掌和我接觸的瞬间,一股亲情,恍如天外飞来,如同隔世。这段美好的回忆,将永远铭记在我心头。別后托福顺利出院,即将离津,赴申返美在即。附上照片数桢,請予点收,甲选弟所摄亦请遥寄天津北马路第二十八医院范嫏娣大夫收,不必寄美,以便在家信中夹来美国,似较直接寄来美国为便。邹前辈秉文記念諸事,静待前辈寄资料来美。即颂
健康快乐!
晚 范和钧 十一月十八日
Mr. He-jun Fan and Gen-you Xiang
WU Ning
Mr. He-jun Fan (1905-1989) and Gen-you Xiang (1913-1992) Both of them were tea experts and life-long friends of Jue-nong Wu.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they worked at the Shanghai Commodity Inspection Bureau. Later they went separately to the provinces of Anhui, Fujian, Yunnan and Sichuan to develop various tea farms. After 1949, He-jun Fan worked in Taiwan on tea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recent years that recall a few stories of Fan and Xiang.
He-jun Fan, Gen-you Xiang, Shanghai Commodity Inspection Bureau, Jue-nong Wu
2013-10-29
吴 宁(1957年-),女,20世纪8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美国佛州大学民族音乐学硕士,卫理大学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硕士,现住美国德克萨斯州,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孙女,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杭州联络处外籍会员。
K826.3
E
0577-8921(2014)02-1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