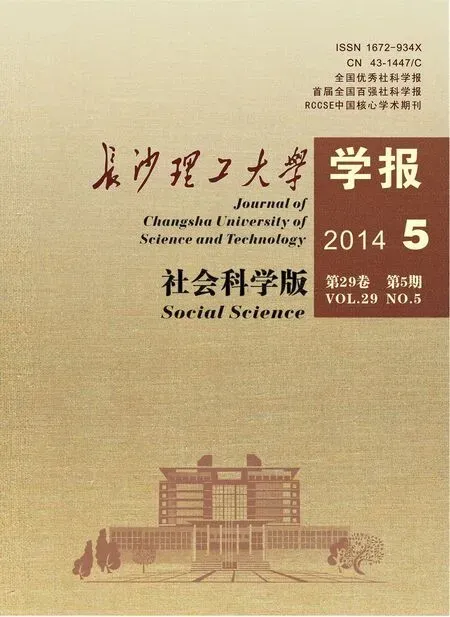论《巴曼尼得斯篇》中“一”与“是”的辩证关系
傅畅梅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部,辽宁沈阳 110136)
论《巴曼尼得斯篇》中“一”与“是”的辩证关系
傅畅梅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部,辽宁沈阳 110136)
在《巴曼尼得斯篇》中,柏拉图分析了各个相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它们结合的可能性,以解决极端相反的相在个别事物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各个相中,“一”与“是”的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一”如果不与“是”相结合的话,它就是孤立绝缘的,最后甚至连自身都不是。而如果“一”与“是”相结合的话,“一”就可以与其它的相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整个世界的网络。柏拉图的“通种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修改发展而来的。“一”与“是”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启示作用。
一;是;通种论;多
黑格尔说:“但是真正辩证法的详细发挥,则包含在‘巴门尼德’中,这是柏拉图辩证法最著名的杰作。”[1]要找到《巴曼尼得斯篇》的理论起点我们必须回到开篇,在这里通过齐诺反对多元论的展示,柏拉图引出了对话的主题。经过“苏格拉底”的概括,齐诺的论证是如此展开的:如果存在是多数的话,那么存在的部分与其它的就会既是类似的又是不类似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类似并不是不类似,同样,不类似也不能够是类似。于是,对于存在的多元论的设定也就被证明是错误的了。整个对话都是建立在这个起点之上的,即相反的两极是否允许结合的可能,而这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极端相反的相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以及极端相反的性质是否能够在个别事物身上结合。因为个别事物的存在根据不得不在相的依附之下,但是个别事物分有相又遇到了困难。这就是解决作为原型的“相”与个别事物相联系的逻辑问题。所以书中的巴门尼德又通过后来的八组推论具体分析了在何种条件下不同的相能够在个别事物身上相结合。不同的相解释了个别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相之间的结合解释了为何不同的性质能够在一个个别事物身上同时出现。比如“苏格拉底”是“多”,因为我们能够在他身上区分出左和右、前和后、上和下。然而他依然是个单独的个人。因此“一”和“多”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相就在个人中结合起来了。于是,齐诺对于可感世界的具体事物的质疑就被苏格拉底对于相的质疑所取代了。“以相论去解释相反性质在事物身上的结合,必须假定:其一,相不是存在于事物身上的性质,而是存在于事物之外的同类事物的标准模型;其二,相与相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否则相反之相就可能结合在一起了,而这种结合是不合逻辑的。这就是所谓相与事物之间、相与相之间的分离。但在这篇对话中,这种分离的观点刚被少年苏格拉底提出来,就成了巴曼尼得斯批判的靶子。当然,这实际上代表了后期柏拉图对自己中期相论的自我批判。”[2]
下面笔者以“一”和“是”这两个相的关系为主,来探究柏拉图相论的思想变化。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一”(one)与“统一”(unity)在很多时候是混着使用的,“一”和“统一”都是一种整体性和等同性。“一”能够被理解为任何事物,只要这个事物能够被把握为是个统一体,与某物相等同(在我们对之命名之前,或者对之赋予描述之前)。“一”实际上是个最普遍的术语,在这篇对话的大部分内容中,“一”最好被理解为是一个占位符,即x,使某物类似于断定的主语。这种统一性的“一”与“是”的不同关系表现出柏拉图对于相的前后期态度。
一、分离论中“一”与“是”的关系
在第一组推论中,“如果一是一”,在这里重点在“一”,而非“是”,相当于“如果一一”。此处开始了“是”在不同方面的用法。陈康在注释中也反复提到这里的“是”不等于存在,是比存在包含的范围更广。关于“是”的问题是哲学史上的经典问题。“它是”(itis)中的“是”究竟代表什么?“是”这个动词的未被表达的主语,即“什么”是,能够告知我们整个对话所依照的逻辑架构。柏拉图对此问题没有具体论述,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把系词“是”的用法分为了三方面:判断的连接词,指称主词本身和表示定义的等同。并通过相应的是者的区分引出了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在第一组推论“一是一”中“是”的用法是一个逻辑谓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部分有这样的表述:“‘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即不是有关可以加载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它只不过是对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用在逻辑上,它只是一个判断的系词。”[3]在这里,康德区分了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后者具有规定性,扩大了主词的概念,而前者只是把对象设定在与我的概念的关系之中。
“如果一一”中的“一”同“上帝”在有些方面比较相似:同样是思维高度抽象的产物,与现实个别事物对立分离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实际上,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秘化理论将“一”等同于善的理念或者是《蒂迈欧篇》中的上帝。“一”隔离孤立,闭锁自己,只有“一”——“一”关系,没有“一”——“是”关系。“一”不与“是”结合,推出一是非多。因此一也就没有部分,缺少了部分,一也就不能是整体,于是一不是整体,不是部分。甚至不类似自身,不等于自身了。因为一没有部分,所以它也没有开端、中间和末尾,因为这些都是部分。因为开端和末尾都是界限,没有开端和末尾的一也就没有界限。没有界限也就没有形状:一方面它不是圆的,因为圆形需要各个极点到中心的距离是相等的;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直的,因为直线需要它的中间点处于两个极点间的最短直线上。总之,一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的单位,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看来是没有维度的。因为一没有部分,因此它也没有位置。一不能处于任何地方,无论在任何事物中或者是在自身中:如果一在某个别的位置的话,它就会被它所位于的东西所包围,也就会在许多地方被它的许多部分所接触。而正因为没有包围接触,所以一不在其它里。因为没有被包围,所以也不在自身。处于自身中会预设自身的分离,处于其它中需要不同于一的某物的存在,也就是多。因为不处于任何位置,所以一不能够运动或静止。一个不可分的事物不能够移动到别的事物中去,因为这会预设一个不在的地方。而统一同质的事物也不能够围绕着它的中心,因为没有维度和距离的话,也就不存在中心。如果一不在自身中或者别的地方的话,那么一也就不能够是相同的。如果一与其它的相同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了。而如果一与自身相同的话,那么它也不是一了。实际上,它被内在地分割开来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事物是一,它不能与其它事物相似或者不相似,因为不可能存在其它的事物。如果一不能够相同、相异、相似、不相似、等同、不等同于自身或其它的话,那么一也就不能够被衡量。一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通过它一能够被定义或者判断。因为一不能够存在、灭亡和变化,一也就不能够比自身或其它更年轻或者更年长。于是一就不在时间中,一也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既不是一,也不是。一不能被命名、言说、臆测、认识和感觉。从第一组推论得出结论,“是”在这里就是连接“一”这个相与其他相的逻辑,同时也就是连接相与个别事物直接的逻辑。如果没有“是”逻辑相连接,那么“一”不仅不能与其他相或者个别事物发生关系,甚至最后“一”连自己本身都不是了。
巴门尼德的“一”也就相当于黑格尔的“纯存在”,黑格尔认为:“纯存在或纯有之所以当成逻辑学的开端,是因为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4]纯存在与“一”一样,是先于一切规定性的,它们不能够被直觉、感知和表象,也就会一种最原始的规定性。但是巴门尼德认为只有“有”才是存在的,“无”根本不存在:“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多表达的存在物的。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把它固定在那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上。”[5]而黑格尔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有”的这一阶段,只承认“有”的真实性是片面的,黑格尔认为“纯有”也就包含着“纯无”:“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6]而正是通过这种有与无的辩证运动过程,才使得概念从抽象到具体一点点螺旋式上升发展:“如果说,无是这种自身等同的直接性,那么反过来说,有正是同样的东西。因此,‘有’与‘无’的真理,就是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变易。”[7]后期柏拉图用通种论代替了分离说,“一”也就跳出自己的限制,与不同于自己的甚至是异于自己的相结合,下面本文考察这个过程。
二、通种论中“一”自身的展开
对于柏拉图来说,“是”(tobe)可以被把握为“是(F)”[tobe(F)]的不完全形态。因此,在许多文本中,“x是”必须被理解为“x是(F)”,也就是说,这代表着x具有某种特征,不管文本有没有提及。尤其是在《巴曼尼得斯篇》的这一部分中,“一是”应该被理解为“一是(F)”,一也就具有了不管是那种的特定的特征。第二组推论中“一是”的重点就在于“是”,“一”这个相被设定为与“是”相结合的了,“一”分有“是”。“一是”(oneis)包含着“一”和“是”两个因素:“这样,一的‘是’是不同于一的;否则‘是’不是那个的‘是’,那个,即一,也不分有‘是’,讲‘一是’和讲‘一一’,反而是相似的了,现在的这个假设不是:如若一一,乃是:如若一是,什么结果必然产生。”[8](P189)“是的一”和“一的是”相同,而与“一”相异。这样“一”就与“多”相结合了。于是一与各种相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一既是一又是多,既是整体又是部分,既有限又无限。一也处于时间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一”之相同“动静”、“类似不类似”、“相等不等”结合起来了,总之,如果一是的话,那么一就是一切了,于是解决了极端相反的相之间如何相互结合的问题。“一”与普遍逻辑相结合,相与相之间、个别事物与个别事物之间、相与个别事物之间也联系作用起来。
第三四组所讨论的问题是,如果“一是”的话,对于不同于一的其它的会产生什么影响。陈康指出:“‘其它的’本是一个相对的词。这里所谓‘其它的’,乃是‘异于一的’。‘一’是‘一之相’的简称,如讲分有‘一’犹言分有‘一之相’,正如讲分有类似,意即分有‘类似之相’……‘异于一的’即是异于一切任何的‘相’的,即是个别事物。”[8](P281)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其它的也就是一作为相所包含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在第三组中的“一”被把握为“是的一”,也就是能够与其它相分有并且被个别事物所分有的第二组中的“一”,因此,其它的也就成为第二组中“一”所成为的一切了。而第四组中的“一”是第一组这种的隔绝的“一”,同样的结果,其它的也就什么也不是了,而且甚至连自身都不是了。这两组表现的是在个别事物中相是如何结合的问题,同样证明了“一”必须分有“是”,个别事物才能分有不同的相。第五组讨论的是如果“一不是”,对“一”会产生什么后果。这里的“不是”是相对的,因此它既是又不是,从而使得变易成为可能。第六组也讨论“一不是”对于“一”产生的作用,但是此组的“一不是”是绝对意义上的不是。第七组讨论相对意义上的“一不是”对其它的导致的结果。第八组讨论绝对意义上的“一不是”对“其它的”造成的后果。总之:“‘如若一是’,‘一’既是一切(推论Ⅱ.),又不是一切(推论Ⅰ.),‘其它的’既是一切(推论Ⅲ.),又不是一切(推论Ⅳ.);‘如若一不是’,‘一’既是一切(推论Ⅴ.),又不是一切(推论Ⅵ.),‘其它的’既表现为一切(推论Ⅶ.),又不表现为一切(Ⅷ.)。”[4]
在“一’与各种相的结合中,“相同”是个比较容易产生歧义的结合相,本文下一章对之进行分析。
三、“一”与“相同”的关系
巴门尼德认为“是一”不同于“是相同的”,统一和相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马尔科姆(MalcolmSchofield)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琼斯是个首相,但是当他在与妻子谈话的时候,他就忘记自己首相的身份而不会责怪他同事的办事无力,因此琼斯作为丈夫的角色不同于首相的角色。[8](P34)巴门尼德注意到如果x成为与y相同的,那么它并不必然成为同一个,它可能成为多个。因此巴门尼德思考的是变化中的同一。(1)“是一”不同于“是相同的”。(2)一与自身相同。因此(3)一与自身等同,但并不是通过自身而与自身等同。通过自身与自身等同也就是因为“是一”而与自身等同。同样参照上面的例子,是首相不同于是丈夫,而如果首相是丈夫的话,那么并不是因为自身而是成为丈夫,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自己是首相而成为丈夫的。因此,最后得出了结论(4)一,虽然是一,但是也是多。
这种“一”与“等同性”之间的差别在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的第二部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柏拉图反对我们只能说“人是人”,而不能说“人是好的”的观点而提出的。“当我们说到人,我们给他许多附加的名称,把颜色、形状、身材、缺点、优点归于他,在所有这些和其他无数的论断中,我们说他不只是一个‘人’,而且也是‘好的’,以及其他许多说法。我们把某个给定的事物当做一,然而把它当作多来谈论,用许多名字称呼它。”[9](P54)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能够说“人是人”而不能说“人是好的”是矛盾的,是因为他没有将属性和等同性区分开来,因此不得不设定“人是好的”显示的是两个东西的同一,然而实际上“人是好的”表现的是两个非等同的事物中的一个描绘另一个的特征。
由于这种差别的产生,“一”也就与“多”相联系起来。一与多的关系不在于一个理念如何能够由许多理念构成,或者一个理念参与到许多事物中去却依然保持同一。实际上,一与多的关系在于统一性与多元化的意义。这是在《巴门尼德斯篇》137c—166c中所探究的问题。《巴门尼德斯篇》中的论证表现出统一性和多元性在所有的存在物中是无所不在和紧密相连的。
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将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相同和相异作为六个相通的种,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种类之间相互结合;二、存在和相异贯穿所有种类,并相互渗透;三、相异(或不同)分有存在,相异由于分有存在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它分有的那个存在,而是与之不同的存在,由于相异与存在不同,所以它显然非常可能就是某个‘不是’存在的事物;四、在相异中拥有某个部分的存在与其他所有种类都不同,由于相异与其他种类全都不同,所以相异不是其他种类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它们的总和,而只是相异本身,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无法驳倒的,存在不是亿万事物的堆积,其他种类也不是,无论是某些种类还是所有种类,在许多方面存在,在许多方面不存在。”[9](P67)柏拉图用“是”将相与相之间构建出了一种指谓的关系,于是整个世界的网络也开始搭建完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出了如果“一”封闭自己,不向外展开的话,那么它自身都会有丧失的危险。柏拉图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哲学家,在抽象追溯出第一起点后,如何使得这个第一起点在世界中展开,也成为哲学家们不容回避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笛卡尔从我思中推出了世界的存在,康德以作为预设的极点的先验自我意识为制约,通过想象力将之落实到认识过程中去。黑格尔的纯存在是纯有,同时也是纯无,只有通过与对立面的转化生成才能够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这些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运演思路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柏拉图通过将“一”与“是”相结合,实现了各个相之间的联系,其后来的通种论也是基于此的。
[1][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郭斌,张竹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216.
[2]徐长福.异质性的得而复失——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读解[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9-68.
[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476.
[4][古希腊]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M].陈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189.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53.
[6][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30.
[7][德]黑格尔.逻辑学[M].杨一立,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6: 195.
[8]MalcolmSchofield.PlatoonUnityandSameness[J].TheClassicalQuarterly,NewSeries,Vol.24,No.1.
[9][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One”and“ToBe”in“Parmenides”
FUChang-mei
(HumanitieandSocialScienceDepartment,ShenyangAerospaceUniversity,Lioning,Shenyang110136,China)
Inthe“Parmenides”,Platoanalyze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variousphases,andraisedthepossibilityofcombining themtosolvetheproblemofthecoexistenceoftheextremeoppositephasesintheindividualthings.Ineachphase,thecombination of“one”and“tobe”isgroundbreaking.If“one”doesn'tcombinewith“tobe”,itisisolatedinsulation,andfinallyitisevennotitself.Andif“one”and“tobe”combinetogether,“one”canbelinkedtootherphases,inordertobuildouttheentireworldnetworks.Plato'stheoryofthecommunionofgeneraisalsomodifiedandevolvedonthisbasis.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one”and“tobe”alsohadinspirationonthelaterphilosophers.
one;tobe;thecommunionofgenera;many
B502.232
A
1672-934X(2014)05-0029-04
2014-08-13
傅畅梅(1972-),女,辽宁大连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