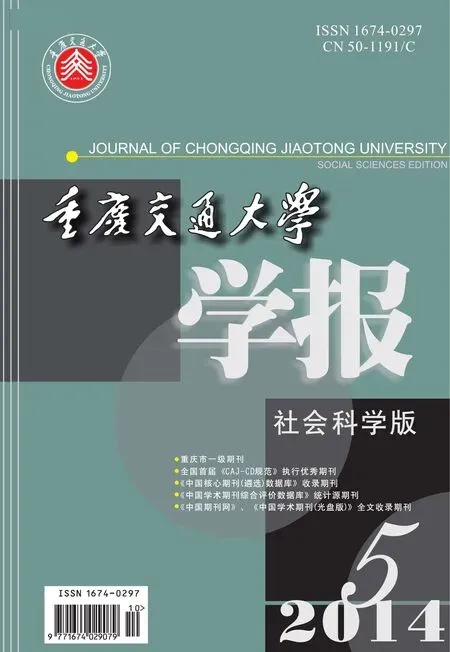梦幻与现实之间
——弗兰克·奥康纳笔下的儿童形象
张 伟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梦幻与现实之间
——弗兰克·奥康纳笔下的儿童形象
张 伟
(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弗兰克·奥康纳是20世纪爱尔兰著名短篇小说家,儿童题材在其近200篇短篇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奥康纳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为文本,分析此类作品中呈现的儿童形象,即充满童真的“母亲的孩子”和心灵孤独的“私生子”,试图挖掘作品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内涵,深入了解爱尔兰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
弗兰克·奥康纳; 梦幻与现实; 儿童形象; 母亲的孩子; 私生子
一
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1903—1966)是 20世纪爱尔兰著名短篇小说家。儿童题材在奥康纳近200篇短篇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作品记录了小主人公拉里·德莱尼(Larry Delaney)琐碎的日常生活和酸涩的成长经历。1996年帕特里克·科特(Patrick Cotter)将拉里·德莱尼系列收录在《拉里·德莱尼:孤独的天才》(Larry Delaney:Lonesome Genius),这本书从儿童的视角完整地呈现了拉里富有童趣的家庭生活,又以成人的眼光审视着爱尔兰底层民众的生存窘境。此外,奥康纳非常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被人遗忘在世界阴暗角落,心灵孤独、寂寞的私生子。奥康纳认为童年是人生历程中可以把个人内心的紧张、冲突、矛盾外在化的阶段。在奥康纳的文学作品中,儿童一般都会在梦幻与现实两个世界来回穿梭,一边是美好、温馨、惬意,甚至是有些诗意的幻想情景,另一边是沉闷、冷漠、压抑,亦或是有些肮脏的现实生活。无论是充满童真的“母亲的孩子”,还是心灵孤独的“私生子”,都渴望尽情享受富有童趣和想象力的儿童世界,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令人疑惑不解的成人世界[1]。
二
(一)充满童真的“母亲的孩子”
“‘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源出于古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意为儿子生来对母亲有着某种性爱,而对父亲则有着嫉妒心甚至仇恨。”[2]96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五章第四节分析《俄狄浦斯王》时,第一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并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爱双亲中的一个而恨另一个,这是精神冲动的基本因素之一……”《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事情就是这样”[2]100-102。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行为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愿望,即每个人从童年就开始的精神冲动模式。“《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感动我们现代观众,就在于我们与俄狄浦斯具有共同的永久不变的精神冲动——‘俄狄浦斯情结’。”[2]105在人类无意识的最深处,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理结构,如果对父母的这种特殊情感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将会导致成年后的心理障碍。
《我的恋母情结》(My Oedipus Complex)无疑是对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理论的真实演绎,小说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勾勒出小男孩对母亲的依恋和对父亲的敌视。拉里已经五岁了,在此之前他很少见到父亲,因为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父亲都在军队里,每次回家都“像圣诞老人一样来无踪去无影”。早饭后,母亲总是带着拉里去圣奥古斯丁教堂听弥撒,祈祷父亲早日平安回来。拉里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既丰富又充满乐趣。然而,突然有一天父亲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这个家,拉里与父亲争夺母亲的家庭战争渐渐拉开了帷幕。母亲对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求必应,反而对父亲温柔体贴,呵护备至,因此拉里和父亲的关系日趋紧张,直至一天早晨父子之间上演了一场争夺大战。“爸爸这时已经失去了耐心,朝我扑了过来。在妈妈惊慌的眼神下他失去了自信心,最后只是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感到义愤填膺:这个陌生人,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因为我天真的求情他连哄带骗地从战场回到了我们这张大床上,现在居然还敢打我。我一声接一声地尖叫着,光着脚丫子在地上跳个不止……妈妈穿着睡衣站在那里,仿佛为了我们爷儿俩心都要碎了。我希望她心里的感受也像面部的表情一样。但是她这是活该。”[3]224从此,拉里和父亲成了公开的“死敌”,在他眼中,父亲是个十足的“坏蛋”“恶魔”,他甚至期待上帝能再次把父亲送回战场。于是,我们读到下面的一段对话。
但是与此同时我得让爸爸知道我只是在等待,而不是投降。一天晚上他特别讨厌,在我头上唧唧喳喳地说个没完,我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妈咪”我说,“你知道我长大了打算干什么吗?”
“不知道呀,宝贝”她回答道。“干什么呀?”
“我要跟你结婚”我不动声色地说。
爸爸扑哧地笑出声来,不过他没听懂我的意思。我知道他这是在装蒜。不管怎么说吧,妈妈听了很高兴。我觉得她可能是为自己有一天会摆脱爸爸的统治而感到轻松[3]225。
奥康纳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父子对峙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我们读到这里也不自觉地为这个煞有介事的孩子和那个值得同情的父亲开怀一笑[4]。当然,作者在拉里身上承载的绝不仅仅是小男孩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恋母情结”;小说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渗透着作者对战争、宗教、政治、婚姻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对爱尔兰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关注。父亲回来之前,拉里的生活相对简单、宁静,因为他终日沉浸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天一亮我总是醒来,把前一天要做的事情都抛到脑后,觉得自己像太阳一样要发光,要欢笑了。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过着简单、清晰、充满希望的生活了。我把双脚从被子底下伸出去——我管左脚叫左太太,右脚叫右太太——还为她们设计了各种富有戏剧性的场景,让她们俩讨论当天的事务……”[3]215-216这时,父亲却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打破了拉里平静的生活,即使每天早晨“左太太”和“右太太”继续她们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似乎不像往常那般轻松、愉快。
虽然小说从拉里的视角观察父亲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变化,但是读者不难看出叙述过程中的成人思维痕迹。本应该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一家人,为什么父亲扮演了“坏蛋”“恶魔”和“陌生人”的角色?究竟是上帝还是人类发动了战争?为什么父亲回家越来越晚,他和母亲的争吵越来越多?母亲到底是从哪里找来6先令17便士把弟弟索尼买回来的?显然,拉里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成人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小说的结尾,拉里和父亲拥抱和解,“圣诞节那天,他破天荒地特意给我买回了一个真正非常漂亮的铁路模型”[5]227。读者对小说内涵的理解和对20世纪爱尔兰社会问题的思考自然不会终止于这样一个快乐的结局。
奥康纳在《初次忏悔》(First Confession)、《小当家》(The Man of the House)、《醉汉》(The Drunkard)、《圣诞节的早晨》(Christmas Morning)和《父母身世》(The Study of History)等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记录了Jackie,Sullivan等小男孩家庭生活的瞬间,刻画了同样纯真、可爱、富于想象力的儿童形象。母亲几乎是这些孩子生活的全部意义,父亲在他们的生命中却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色;他们是奥康纳描写的一系列“母亲的孩子”。他们和拉里一样拥有厚厚的窗帘所遮挡不住的丰富多彩的儿童世界,也一样为现实生活遇到的各种麻烦苦恼不已。
奥康纳是父母的独生子,他出生时父亲远在战场(爱尔兰自治运动);短暂的童年时代由于父亲长期不在家,他几乎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母亲将自己身为孤儿而得不到的母爱完全倾注在奥康纳身上,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典型的母亲的孩子”;他为第一部自传《独生子》(An Only Child)最初选定的标题正是“母亲的孩子”。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如命,动辄打骂母亲出气;母亲性格温顺、隐忍,为了坚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可以牺牲一切。父亲和母亲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他的血液里斗争,他继承了父亲的忧郁、粗暴,也保留了母亲的单纯和乐观。奥康纳时常从父亲制造的噩梦中惊醒,很长一段时间都痛恨自己的父亲,平时尽量避免使用father,而用he或him代替。为了摆脱痛苦的现实世界,奥康纳每天躲在阁楼里,醉心于借来的书本、画册,还有自己编排的各种戏剧,他多么希望这样的美梦永远不会结束。终于有一天,这个曾经爱做白日梦的小男孩长大成人,他拿起那支属于作家的笔写下了童年的回忆、成长的经历,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爱尔兰孩童的梦想与困惑。
(二)心灵孤独的“私生子”
短篇小说《流泪的孩子们》(The Weeping Children)、《男性原则》(The Masculine Principle)、《妄想者》(The Pretender)、《树林里的孩子》(The Babies in the Wood)和《基于借来主题的一组变奏曲》(A Set of Variations on a Borrowed Theme)(以下称《变奏曲》)都是关于被父母遗弃的私生子与收养他们的孤苦无依的老妇人相依为命的故事。奥康纳十分关注爱尔兰底层民众,特别是生活在社会边缘,被人遗忘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境况令人担忧,他们的寂寞无助值得同情,因此奥康纳笔下有很多心灵孤独的私生子和老年人。私生子是儿童世界里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特别是父母精神上的鼓励和关怀,这些孩子无所依靠,内心空虚,容易走向情感的极端。他们渴望母爱,憧憬温暖的家庭生活,却备尝人情冷暖,独自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世界。
《流泪的孩子们》讲述了小女孩玛丽被母亲遗弃2年之后重新回归家庭的故事。英国人乔·桑德斯(不信教)和爱尔兰姑娘布里吉德(信奉天主教)结婚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南斯,然而孩子的到来却让布里吉德变得性情古怪,她一会儿精神忧郁,一会儿脾气暴躁。乔一直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后来才知道,妻子婚前曾经在伦敦与别人生下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一直寄养在科克市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家。乔性情温柔,却也刚强,他明明知道要面对周围人的流言蜚语,还是决定把玛丽带回家抚养。“要是大人,不论是男是女,你可以扔下不管,任凭他去漂流,可是对一个孩子你不能这么做。孩子完全没有自理的能力。”[3]316几经辗转,乔找到了收养玛丽的瑞安太太,“一个红脸颊、五大三粗的高个子女人”。让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是,瑞安太太身边还有5个与玛丽处境相似的孩子,她是在丈夫去世后开始照料他们的。乔看到这些身世可怜的孩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来到那道挡板门前,又看到了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一幕:篱笆上一盏灯,白色的门柱旁边四个小孩挤在一起,低声嘀咕着。”[3]321商量好第二天来接玛丽,乔和宾馆经理科尔曼驱车赶回宾馆。“上路之后天已经黑了,汽车的前灯照在翠绿的河堤上,像舞台布景似的,但是却遮住了他的脸,因此他很高兴。”[3]321此刻,黑色的夜晚是他最好的伪装,或许这个悲天悯人的男人已经满眼含泪,思索着自己的行为,更为瑞安太太收养的孩子们感到揪心。
乔永远也无法忘记他带着玛丽离开的时候,那些站在路边、目送他们远去的孩子们的身影。“汽车发动的时候,他转身朝孩子们挥手。这些孩子站在道路上,手上抓着他送的礼物,他看到孩子们都在默默地流泪。他觉得这些孩子的哭泣与现实生活中那些孩子的哭泣不同,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哭泣的时候是很放纵、很可爱的,而他们的哭泣像老年人,仿佛世界已经离他们而去了。现在他明白了刚才自己为什么不敢亲吻他们。如果他亲吻了这几个孩子,他就不能把他们留在那里了……玛丽身体前倾,像入了迷似的摸着自己漂亮的新鞋子。科尔曼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眼睛注视着山间弯曲的道路,他那张肥胖、阴沉的脸上毫无表情。”[3]322-323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哭泣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是向父母撒娇的表现;私生子游移在人类情感世界的真空地带,他们的哭泣只能代表内心卑微的呐喊和无助的叹息。玛丽没有留意昔日小伙伴的眼泪,她全神贯注地盯着脚上穿的新鞋子;司机科尔曼面无表情,似乎早已对此事司空见惯。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者着重描写了布里吉德纠结的心理,乔对待玛丽这件事情的态度和他见到瑞安太太以及她身边的孩子后的真实感受。透过作者对乔细腻的心理描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被世界抛弃的孩子们孤独的心灵。
如果说玛丽是一个幸运儿,她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拥有一个不顾世俗偏见、能够包容她的继父,那么泰瑞和弗洛里就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树林里的孩子》也是关于寄养在别人家的私生子渴望得到父母的疼爱,最终梦想破灭的故事。泰瑞和厄尔利夫人还有她儿子贝利生活在一起,康纳阿姨偶尔会来看望泰瑞,她每次来都会带很多礼物。弗洛里是泰瑞的“小女朋友”,已经9岁了,穿过一片小树林就是她住的村子,她和科兰斯夫人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天,康纳阿姨又来到这里,她带着泰瑞去山顶玩耍,并偷偷地告诉他,她马上就会和一个英国人结婚,到时候她会带泰瑞去英国生活,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第二天,泰瑞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要去英国的消息告诉了弗洛里,弗洛里非但不相信泰瑞的这个好消息,反而狠狠地挖苦他一番。
“那么,她又为什么把你扔在这里呢?”
“她没有把我扔在这里”泰瑞说,弯下身向她脸上泼了一些水。
“当然啦,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她悠闲地说着,把脸稍微转了一下以免溅上水。“她假装是你阿姨,但是我们都知道她是你妈妈。”
“她不是,”泰瑞尖声叫道,“我妈妈已经死了。”
“哦,他们总是这样跟你讲。”弗洛里平静地说,“他们也是这样跟我说的,但是我知道这都是谎话。你的妈妈根本没死。她和一个男人有了麻烦,她的母亲让她把你送到这儿来甩掉你。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5]141-142
也许弗洛里不想失去唯一的朋友,也许她羡慕泰瑞有一个关心他的阿姨,嫉妒他不久要去英国,故意这样说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什么阿姨来看她,也没有人给她买玩具。这段对话对泰瑞打击很大,两个孩子彻底闹翻,然而更糟糕的是,康纳阿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来。几个月之后,康纳阿姨和一个沃克先生开车过来,他们带泰瑞去海边玩了一整天。“他对沃克先生当自己爸爸的主意感到满意。他一定是个好爸爸。他很有原则。”[5]144晚上,泰瑞又哭又闹,不肯去厄尔利夫人家,他害怕阿姨和沃克先生会把他扔在这里不管。此后的每个星期天,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泰瑞都会跑出来。他靠在马路旁边那家小酒馆的墙边,眼睛死死地盯着过往的车辆,希望能看到沃克先生的汽车,可是每次他都眼泪汪汪地回到厄尔利夫人身边。弗洛里看到泰瑞这么可怜,主动与他和好。
“但是,为什么阿姨不像以前那样来看我了?”
“因为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不让她来。”
“他为什么不让?”
“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弗洛里同情地回应道,“难道你不明白,这个英国人没有合法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不介意,但是你阿姨嫁的人是她工作的店铺的老板,科兰斯夫人还说,他怎么会看上她的,而且他不喜欢你阿姨来看你。你看,她就快有合法的孩子了。”
“难道我们不是合法的孩子吗?”
“哦,不,我们不是。”弗洛里沮丧地说。
“我们什么地方出错了吗?”
弗洛里也经常问她自己这个问题,但是她太骄傲不能让一个像泰瑞这样的小男孩看出她还没有找到答案。
“全部。”她叹息地说[5]147。
泰瑞和弗洛里相互依偎着坐在一起,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远处,夜班火车爬上了山谷,黑夜覆盖了那片神秘的小树林。5岁的泰瑞听不懂弗洛里的话,为什么愿意给他当爸爸的沃克先生没有合法的宗教信仰呢?什么样的宗教才是合法的呢?为什么阿姨不能带着他去英国幸福地生活呢?为什么他们不是合法的孩子呢?为什么亲生父母把他们扔在无人问津的偏僻乡下呢?本该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却不得不面对这么复杂、深奥的社会问题。两个孩子感到迷茫、困惑,他们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还是大人们做错了什么事,只能默默地忍受命运的安排。《变奏曲》中海格特小姐说,爱尔兰到处都是这样惹上麻烦的年轻姑娘和不知如何安顿的私生子。弗洛里认为都是由于父母的自私自利,他们才会被遗弃,殊不知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保守、愚昧的思想认识,以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等诸多因素才是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源。
三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其“精神自传”《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中曾写道:“每个人的作品,不管是文学、音乐,亦或是图片、建筑,还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永远都是他自己的写照。”[6]奥康纳对儿童题材的故事情有独钟,他喜欢在叙述中追忆自己童年时代滑稽可笑的“小事件”,也喜欢从成人的角度去观察孩童无意识流露的“愿望”和“恐惧”。“从某种意义来说,拉里再现了他自己;他既是牵线木偶,又是控制木偶的人。”[7]同拉里一样,奥康纳从来不避讳自己是“母亲的孩子”,“恋母情结”对他来说不是个可怕的字眼。母爱是伴随他一生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柱,与父亲疏远则体现了那个时代爱尔兰家庭生活的印记。源于自己在英国的经历,奥康纳塑造了很多“私生子”的儿童形象。这些孩子被父母丢弃在偏远的乡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更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奥康纳何尝不是一个被祖国母亲抛弃的孩子呢,他曾经被迫辗转于英国和美国,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他深刻地体会到“无家可归”的艰难处境。侨居海外几乎成为20世纪爱尔兰作家的共同命运,其中有很多作家孤独终老,客死他乡。然而,奥康纳并没有一味地怨恨自己的祖国,他对爱尔兰始终怀着“爱之深,责之切”的复杂情感。无论身在何处,奥康纳总是以爱尔兰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创作对象,祖国和故土是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1]O'Connor Frank.Day Dreams and other Stories[M].Pan Books London and Sydney,1973:9.
[2]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弗兰克·奥康纳.奥康纳短篇小说选[M].路旦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林六辰.成人眼中的童真——评弗兰克·奥康纳独特的叙事手法[J].外国文学,2005(4):15-25.
[5]O'Connor Frank.Collected Stories[M].New York:Knopf,1981.
[6]Matthews James.Voices:A Life of Frank O'Connor[M].New York:Atheneum,1983:viii.
[7]Matthews James.Frank O'Connor[M].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76:70.
(责任编辑:李晓梅)
Living in Between Dreams and Reality The Children Images in Frank O'Connor's Short Stories
ZHA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Fujian 365004,China)
Frank O'Connor is a very famous Irish short story writer in the 20th century.A large number of his almost 200 short stories take children as the major characters.Based on this kind of stories,the children images,which are innocent“mother's boy”and lonely“illegitimate children”,are analyzed.The profound cultural and social connotation is unearthed in order to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common people in Ireland.
Frank O'Connor;dreams and reality;children images;mother's boy;illegitimate children
I106.4
A
1674-0297(2014)05-0086-04
2014-03-04
福建省教育厅B类社科研究项目“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的主题研究”(JB11279S),三明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的主题研究”(A201010/Q),三明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项目“基础英语教学团队”(ZL0710/JT)
张伟(1982-),女,山东滨州人,三明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