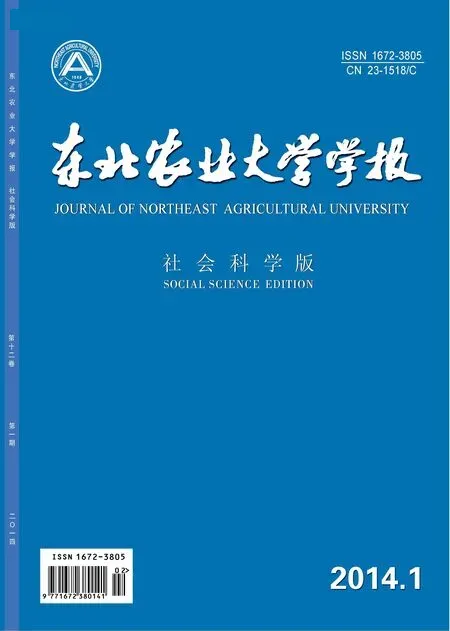论爱·摩·福斯特三部幻想小说中的原型
张莹
(福州大学,福建福州 350000)
论爱·摩·福斯特三部幻想小说中的原型
张莹
(福州大学,福建福州 350000)
爱·摩·福斯特在其早期创作的幻想小说中,创造性地运用源于原始自然崇拜和古希腊神话的原型意象以表达其对生命本质的解读。其创作思想与卡尔·荣格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理论不谋而合,可以说,他是荣格原型理论的实践者。以《惊恐记》《另类王国》《始于科娄纳斯之路》为例,福斯特借助自然原型和人物原型,表现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心理意识,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原型意象构成福斯特幻想小说的实质内容,亦是其长篇小说原型的主要源流。
荣格;原型;集体无意识;福斯特;幻想小说
爱·摩·福斯特是英国爱德华时期的重要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我国文学评论界一直对其长篇小说颇为关注,相对而言,对其短篇小说的研究较少。学者大多着眼于人文主义思想、意象与象征、现代主义、性别与同性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等阐释理论和方法,而对福斯特作品各类原型意象的解读不多,王成和张福勇①参见王成,张福勇:《“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潘神的象征呈现》,载《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3~115页。、李建波②参见李建波:《美拉姆普斯之寻:福斯特两部小说的原型与主题》,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55~60页。曾撰写相关论文,但所涉仍是其长篇小说。英美国家具代表性的福斯特评论家中,仅W·斯通、乔治·汤普森较多地关注福斯特作品中的神话与原型。W·斯通在《山洞与山:爱·摩·福斯特研究》部分章节中,论述福斯特在其小说中运用了荣格的原型,认为这是福斯特自身压抑的心理表现(指涉其同性恋倾向);乔治·汤普森关注福斯特小说中的神话和宗教原型,并在《爱·摩·福斯特的小说》一书中将其作品的神话象征与浪漫主义神话象征作了区别。
神话和原型是福斯特小说,特别是被他称为“幻想”的短篇小说之内蕴所在。这些原型随其创作生涯产生阶段性演变,因而应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系统解读。本文运用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阐释福斯特幻想小说中的原型和意象,不仅有助于了解福斯特创作初期的生命观和哲学思想,洞悉其欲表现的爱德华时代工业社会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带来的冲击,也有助于理解和探析其日后创作的长篇作品中其他原型和意象。
一、幻想——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福斯特的文学创作始于被其称为“幻想”的短篇小说。他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幻想“暗指了超自然因素的存在”,幻想作品即“以‘幻想’的名义唤起所有栖居于低空、浅水与小山之中的生灵,所有的法翁(牧神)和德律阿得斯(森林女神),所有记忆的失误,所有言语的巧合,所有的潘神和一语双关……”[1]并列举了幻想的写作手法:“将神祗、鬼魂、天使、猿猴、怪物、侏儒、女巫引入日常生活;或是将普通人引入无人之境,引入未来、过去、地球内部,第四维空间;或是深入人格里层或将人格分割开来……”[1]纵观福斯特的短篇小说,来自原始自然崇拜和古希腊神话特别是与大地、自然界相关的原型意象是必不可少之成分,充分体现了福斯特所界定“幻想”作品的特性。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和诗人(如叶芝、乔伊斯、托马斯·艾略特等)采用的“神话方法”(mythical method)不同的是,福斯特并不仅仅把原型意象当作艺术表现手法,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探索人类深层无意识。
福斯特的作品总是致力于揭示身处现代文明漩涡中的个体生存状态,特别是个体的深层心理意识。他非常强调人的深层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曾言:“每个人都具有双重人格,一种是表面的,另一种是深层次的。表面层次的人格有着自己的标志……是有知觉的、活跃的;……深层次人格是非常奇特的事物,具有普世性。它在许多方面就像个傻瓜,但是缺少了它就没有文学。因为,除非一个人偶尔把一只水桶沉入其中,否则他无法创作出一流的作品。”[2]福斯特认为,由于艺术作品源于内心深处,包含人类深层意识中的共有元素,因而它所激发出的精神能够使人产生共鸣。其艺术创作思想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理论几乎不谋而合。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两个层次,属于表层的无意识含有个人特性,称为个人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依赖于更深的一个层次,即“集体无意识”,“因为这部分意识并非是个人的,而是普世性的”[3]。在荣格看来,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最重要内容是原型,它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的集体无意识之显现,其本质是一种神话形象,而艺术创作的过程“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通过这种造型,艺术家把它翻译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并因而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源泉”[4]。对荣格而言,艺术创作的核心与归宿即为表现原型,因而其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不可避免地存在神话原型。原型理论揭示了人类心灵同自然万物乃至宇宙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正是福斯特在其幻想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斯特的幻想小说创作可以被看成是对荣格原型理论的实践。以福斯特早期创作的三部短篇小说《惊恐记》《另类王国》《始于科娄纳斯之路》为例,其故事情节虽然各异,但深层的结构模式和主题基本类似,场景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均与栖息着神祗的森林树木密不可分。福斯特借助原始自然宗教和古希腊神话原型意象,来表现自然的力量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以期于人类历史中理解和认识现代生活的失落与毁灭,并从古典世界中找到秩序和约束、生活意义以及心灵和谐。
二、潘神的力量
小说《惊恐记》讲的是一位郁郁寡欢、懒散无聊的英国男孩尤斯塔斯和亲戚朋友在意大利乡村拉韦洛镇附近一山顶栗树林野餐时,与潘神接触后脱胎换骨的经历。故事以一位野餐参与者的叙述展开,在他眼中,那座布满沟壑、山脊都被枝繁叶茂的栗子树覆盖着的巨大山谷就像一只大绿手,“正痉挛地抓挠,要把我们控制住”[5],山下的拉韦洛镇是“另一个世界”。这些描述似乎在暗示山上的栗树林和山下的拉韦洛镇分属两个不同世界。荣格的原型理论中,树或森林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是母亲(大母神)原型的变体,“比如教会、大学、城市或者乡村、天空、大地、森林……都可以成为母亲的象征。原型往往联系着代表肥沃与富饶的事物和地点:哺乳宙斯的羊角、一块犁过的田野、一座花园。它可以附属于一块岩石、一个山洞、一颗树、一股泉水……”[3]故事中的栗树林成为大自然母亲原型的象征,如大母神的子宫一般,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尤斯塔斯和其他野餐者进入栗树林,意味着走进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世界,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和自然原始的状态,拉韦洛镇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则是被繁文缛节所束缚的意识世界,通过那只“大绿手”试图控制尤斯塔斯等人的精神与肉体。
在树林里,正当几位野餐者玩意正浓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寂静降临了——“一切绝对静止,全然无声;一种悬念和焦虑悄然而生”[5],然后“一阵微风从对面的山脊悄悄吹下来,所到之处把浅绿色变成了深绿色”[5]。这一串怪异的景象使野餐者陷入极度惊恐(panic),他们感到“不是像人那样害怕,而是像动物那样害怕”[5],并开始往山下跑,期间故事的叙述者“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所有的感性和理性渠道都被堵塞了”[5]。当他们事后返回林中寻找被遗忘的尤斯塔斯时,发现他躺在林间的空地上,不远处留着几个山羊蹄印。这个男孩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书中所描述的诸多细节及小说题目The Story of a Panic,暗示潘神(Pan)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潘神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和牧神,头上长有山羊的耳朵和犄角,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是山羊后腿。它是大自然的化身,代表自然的力量和原始的生命力。正如其亦人亦兽的外形,潘神所代表的大自然有美好诱人的一面,也有狂野和未知的一面。传说潘神常常会使身处空寂场所的人产生恐惧,因而潘神在福斯特的故事中又是“阴影”的原型意象。
阴影是荣格界定的四种集体无意识原型之一,是人类自我意识中隐密、受压抑的部分,亦是个体惧怕成为的“那种东西”。荣格认为,当个体面对集体无意识时,首先遇见的是自己的阴影,并产生“迷失在自身之中”的状态,因为“在意识的领域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似乎是‘主因’自身。但是如果跨过阴影之门,会恐怖地发现我们是未曾见过的主因的客体。这一认识必定令人不悦,因为没有什么会比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更具幻灭性。它甚至会引发原始的恐慌……”[3]以叙述者为首的野餐者们在栗树林经历的原始性恐慌,暗示了他们在集体无意识世界中遭遇自己的阴影,他们身上的原始野性如洪水般决堤而入,使其意识世界中由各种社会繁规建立起的意识防线濒于崩溃。但荣格同时认为,阴影并不总是负面的,“它包含的消级、幼稚或原始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了人的生命力和装点了人类存在”[6]。正当成年人在恐惧中挣扎着逃回意识世界时,年仅十四岁的尤斯塔斯直面阴影潘神的降临。从栗树林出来后,原本无精打采的尤斯塔斯仿佛获得新生,其原始的生命力和激情被激发了,艺术创造力也得到了释放。他如动物般精力充沛、富于激情地跳跃、喊叫着,甚至满怀温情地亲吻以往不屑一顾的农妇,并与旅馆服务生热内罗成为好朋友。更令叙述者不可思议的是,原本语言乏味的尤斯塔斯竟“试图表达连最伟大的诗人都几乎无力表达的主题”,并且“崇敬地赞美大自然的威力及其各种表象”[5]。尤斯塔斯成了唯一能够领悟大自然全部精神、获得自我认识和觉醒的人,正如他对热内罗所言,“几乎所有的东西我都理解了,那些树木、山峦、星星、流水,我都能看见”[5]。
但是具备领悟潘神能力的尤斯塔斯“对人一点儿都不理解”,他最大的恐惧是被那些试图约束和教训他的成年人关进“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鲜花,看不见树叶,看不见天空,只看见一堵石墙”[5]——的旅馆房间。尤斯塔斯最后选择逃离,他跳出窗户,消失在丛林中,用热内罗的话说,“他明白他得救了”。福斯特以窄小房间和广袤树林之间的对比,揭示了世俗社会对人性的禁锢——它隔离了人与自然、人类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通过栗树林和隐栖其间的潘神这两种代表大自然的原型意象,隐喻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和现代人内心的困顿。对福斯特而言,大自然既是人类生命的创造者,亦是人类生命的拯救者,是把个体从压抑和社会习俗中解放出来之力量。
三、围不住的“另类王国”
与尤斯塔斯有着相似经历的是小说《另类王国》中的伊芙林·博蒙特小姐。《另类王国》以维吉尔《牧歌集》中的诗句开始:“谁;你在逃避;你这蠢驴;就连神仙也住在森林里。”[5]伊芙林一遍遍地重复这些古老诗句,表达她对充满神灵的人类往昔和原始自然世界的向往。这位爱尔兰姑娘是庄园主哈考特·沃特斯先生的未婚妻,她来历不明——既没有家人,也没有钱——但她对神灵居住的森林有着难以言表的热情。她喜欢穿绿色裙子,“她的身体来回摆动,薄薄的绿裙子在身上轻轻抖动,象征无数叶子”[5]。在旁人眼中,她“很多方面其实还是个孩子”“她的灵魂还没有发育健全”[5],福斯特似乎是在暗示这位童心未泯、略带原始野性的姑娘即为从大自然深处走来的自然之子。
为博得伊芙林欢心,哈考特买下自家草场边上被称为“另类王国”的一片山毛榉树林。“另类王国”,如同它的名字,意味着两个不同王国的存在。这“另一个王国”便是集体无意识世界,代表人类曾经共同拥有的自然世界。在伊芙林眼中,树林是共享的天然家园,也是生命起源,是人类爱的见证和孕育生命的起点。附近的村民恋爱时,会按照沿袭了几世纪的传统,到树林里刻下名字首字母,这样天长日久,其后代就能从深入到木质的字母中知晓祖先的名字。荣格曾指出:“生命树起初很可能是一株硕果累累的宗族谱系之树……,许多神话中都说人类来自树木。”[7]福斯特则再次以“树林”这一常见的母亲原型意象,体现人的生命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伊芙林为拥有一片森林而欣喜万分时,哈考特提出要在“另类王国”周边建一道栅栏和一座带锁的大门,这令伊芙林感到困惑和惊恐。栅栏在此成了墙或障碍物的原型意象。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不仅是把林地围起来,还是意识与原始无意识之间的分水岭。伊芙林要求哈考特“永远别把我圈进去。我必须在外边。我必须在谁都能联系到我的地方”[5],她把自己想象成了“另类王国”中的树林,害怕被哈考特禁锢在栅栏内失去自由,也担心附近的年轻恋人不能再来树林刻下名字。然而,世俗的哈考特无法理解树林承载的精神内蕴,想的仅是拥有和控制林地的产权和伊芙林,栅栏对他而言只是地产之间的分界线和林地的保护屏障。福斯特以“栅栏”象征存在于意识世界与原始无意识世界之间的一堵无形之墙,它不仅隔断人与自然和过去的联系,而且将人们禁锢在意识世界中,愈加远离曾经共同拥有的无意识世界,失去可从自然获得启示和生命原动力的途径。当栅栏建起来后,伊芙林不理会哈考特的追逐,“跳着舞离开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她往回跳,跳过几个世纪,直到所有的房屋和栅栏都倒掉,地球成了阳光下的荒原。她的衣裙像一棵树的树冠裹在身上;她强壮有力的四肢像大树枝;她的喉咙像树上部的光滑树枝,那树枝朝着清晨致礼或朝着露水闪烁”[5]。栅栏没能拦住伊芙林,她逃进“另类王国”,变成林中的一棵树,与自然母亲融为一体,或者说她回到了久远的洪荒时代——原始无意识世界。显然地,伊芙林和哈考特是希腊神话中达芙妮与阿波罗的原型变异。在希腊神话里,小仙女达芙妮为躲避追求者阿波罗的追赶,逃进大地之母盖亚的怀抱,变成一棵月桂树。伊芙林,这位现代的达芙妮也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中获得拯救。
四、现代俄狄浦斯的困境
与伊芙林相比,卢卡斯先生没有那么幸运——他没能获得想要的王国。小说《始于科娄纳斯之路》是福斯特继《惊恐记》后第二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从意大利转到希腊,主角由年老的卢卡斯代替少年尤斯塔斯。卢卡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随波逐流地过了大半生,已对生活失去兴趣。为实现年轻时对希腊的憧憬,他与小女儿埃塞尔一起到渴望已久的希腊旅行,同伴们把这对父女比作“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卢卡斯似乎对古老的希腊存在某种期待,因为希腊“让他感觉不满足,而生命的萌动就存在于不满足之中”[5]。在他们下榻的小酒店边上,有一棵巨大的空心悬铃木树,一股泉水从树干中涌出,“给树皮覆盖上一层蕨草和青苔;随后泉水通过骡道,流到远处,造成了肥沃的草场”[5]。当地人还在树上凿了个祭坛供奉圣母。感到惊奇的卢卡斯走进树洞,品尝了甘泉,然后闭上眼睛张开双臂靠在树干上,他感觉自己像在河里移动,“只意识到脚下的水流,只意识到万物汇成了一条河,而他就在河中移动”[5]。当他睁开双眼时,“一种无法想象的、无法确定的东西飘过万物上空,使万物变得容易理解,变得美好”[5]。如同《惊恐记》中的栗树林,悬铃木树也是大母神原型的化身,是生命之树。荣格认为,水在神话领域同样具有母性的含义,亦是无意识的象征,“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生于泉水、河流、湖泊和海洋”[7],而“在梦境与幻想中,大海或其他庞大的水体代表着潜意识”[7]。小说中,年过半百的卢卡斯置身树干的洞里,在梦幻中顺水漂流,隐喻了卢卡斯犹如走进大母神的子宫,回到无意识世界,在那里得到新的生命体验,获得重生。从那一刻,他与自然界、与周遭的人事物产生共鸣,使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不仅发现了希腊,而且发现了英格兰和全世界,发现了生活”[5],并产生就此留下的念头。然而,卢卡斯的感悟没能影响同行者,因为他们“觉察不到流溢在自己四周的自成一体的美”[5]。这位现代的“俄狄浦斯”,在“安提戈涅”的强拉硬拽之下终于又回到英国。
福斯特在《始于科娄纳斯之路》中巧妙地运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原型人物“俄狄浦斯”,影射卢卡斯的人生悲剧。当年的俄狄浦斯为从罪孽深重中获得解脱而踏上流亡之旅。而今,对生活已无所求的卢卡斯也进行着一次追寻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旅行。不同的是,执着的俄狄浦斯在命运之神的召唤和女儿安提戈涅的支持下,最终留在他神谕里指定的流亡终点科娄纳斯,而卢卡斯却未能回应大自然的原始召唤,“永远生活在自己重新得到的王国里”[5],他在女儿埃塞尔和其他旅伴的强行安排下,离开本该成为归宿的“科娄纳斯”。俄狄浦斯的厄运和悲剧终结于科娄纳斯,他的灵魂获得了拯救。但卢卡斯的悲剧却始于“科娄纳斯”——如果说来希腊之前他尚未意识到自己是被禁锢在世俗的意识世界中的囚徒,那么在希腊的旅行中,悬玲木树洞已为他开启了通往精神自由的大门,使他探索到生活的真谛,但可悲的是,他没能像俄狄浦斯那样坚定,而是屈服于世俗压力,重回意识世界的繁杂琐碎之事中,百无聊赖地消磨余生。当埃塞尔从旧报纸中得知他们曾驻足的那个小旅店在其离开的当晚被悬玲木树压倒,里面的人无一生还时,她庆幸自己拯救了父亲,但她无法知道其所拯救的只是卢卡斯的躯体而非灵魂,他的灵魂在离开“科娄纳斯”那一刻起已经逝去。卢卡斯的遭遇揭示了现代人迷惘、徘徊的精神状态,他们渴望获得心灵释放,但当面对生命深处的原始呼唤时,却已无力回应。
五、结语
福斯特置身于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旧交替时期。在福斯特看来,现代工业文明破坏了人类与孕育和延续着一切生命的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传统文化和个人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坚信人类只有回归自然,在历史往昔中才能寻找到心灵归宿和获得精神救赎的力量——因为“认识过去我们才能掌控未来”③转引自Laurence Brander,E.M.Forster[M].London:Rupert Hart-Davis,1970。。对他而言,神话原型意象是通往人类过去,也是揭示挣扎于新旧激荡环境中的现代人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其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特征具有永恒的普世性。美国学者朱迪福·赫兹谈及福斯特的幻想小说时曾言:“它们是对神话故事进行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再创造。”[8]的确,福斯特在这些作品中从不简单复述那些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从丰富的祖先文化中撷取与自然和大地息息相关的神话原型意象,对它们进行加工并置于现代场景,从而探索和挖掘人的无意识领域,展现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所经受的根基失落、信仰动摇、人格分裂等精神困境。正如乔治·汤普森所说:“福斯特应用神话和象征既不是回归浪漫传统,也不是沉迷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学和象征主义形式,而是对20世纪人们的心理需求做出大胆和独特的回应”[9]。因此,可以说神话和原型构成了福斯特小说的实质内容,亦是其长篇小说中此类原型的主要源流,以不同形式呈现在其长篇小说中。
[1]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Forster E.M.“Anonymity:An Enquiry”in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M].London:Edward Arnold and Co.pp,1925.
[3]卡尔·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4]卡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5]E.M.福斯特.福斯特短篇小说集[M].谷启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Jung,Carl.Psychological Reflections.[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53.
[7]卡尔·荣格.转化的象征[M].孙明丽,石小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8]Judith Scherer Herz.The Short Narratives of E.M.Forster[M]. London:Macmillan Press,1988.
[9]George Thomson.The Fiction of E.M.Forster[M].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7.
I106
A
1672-3805(2014)01-0067-05
2013-08-26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荣格原型视阈下的爱·摩·福斯特小说研究”(2012B104)
张莹(1968-),女,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