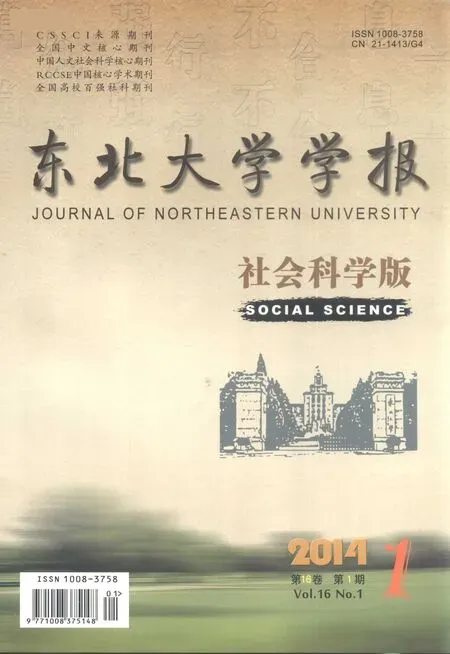超越男权话语的女性叙事
——论艾·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对灰姑娘模式的解构
段红玉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超越男权话语的女性叙事
——论艾·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对灰姑娘模式的解构
段红玉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灰姑娘文学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成话语是浓厚的男权中心意识,即女性地位的攀升需要依赖婚姻(男性)得以实现。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虽然启用了灰姑娘模式,但是将其放置于现代社会语境之中,从身份、阶级和性别三个维度揭露其内在矛盾性和潜在危机,同时依照成长小说的书写轨迹,使人物的成长动态地偏离灰姑娘模式,并最终解构了这一模式。此外,门罗对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视,也反映了她的理性和冷静,从而使整个“灰姑娘”命运变奏的叙事更加完整可信。
灰姑娘模式;男权话语;女性成长;《乞女》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正以其蓬勃的发展态势丰富着世界文学。这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佼佼者,如澳大利亚的南非籍作家库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籍英语作家奈保尔;新西兰的弗洛姆;加拿大的阿特伍德和艾·门罗。这其中,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门罗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她曾两度获得加拿大吉勒文学奖,三次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9年获英语文学界最高奖项布克国际文学奖。2013年门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享有“当代契科夫”美誉的艾·门罗,凭借着她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当今英语文坛占据了制高点。
门罗是典型的女性文学作家,她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选取女性作为主人公,以写实的叙事描绘当代女性的生活状态,从伦理、文化、性别差异等多维视角进行种种微观的透视。门罗的女性书写极具理性特征,在她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背后暗藏着哲学家的冷静。在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盛行的今天,门罗的笔触触及到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对女性生存现实的哲学关照,具备独特的阐释价值。在我国,艾·门罗的研究,已处于起步阶段。在已有的研究中,有的从某一文本出发,解读门罗的女性观或婚恋观;有的从叙事的角度探讨其人文关怀;还有的研究门罗创作的修辞手段;也有学者另辟蹊径,关注门罗的苏格兰性。本文拟就门罗的中篇小说《乞女》为例,通过文本细读,解读在婚姻维度下,门罗对女性成长主题的书写与反思。中篇小说《乞女》(The Beggar Maid)创作于1977年,是门罗的早期代表作。女主人公罗斯出身贫寒,父亲去世后,家中只有粗俗的后母相依为命。罗斯通过发愤苦读,赢得奖学金并进入大学读书。在大学里,她阴差阳错地认识了富家子弟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来自于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家,而他是这个帝国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帕特里克强烈地爱上了罗斯,罗斯在与其经历了种种波折后走入了婚姻。然而,这场童话般的婚姻却在罗斯的毅然放弃下戛然而止。走出婚姻的罗丝如鱼得水,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灰姑娘遭遇白马王子并通过婚姻实现命运转机的故事[1]为西方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神话原型,已深深地植根于读者的阅读记忆里。命运不济的灰姑娘因美貌、贤良受到王子垂青并施以婚姻,从而实现了自身的救赎。这一文学事件在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的同时,伴随着对它不同形式的复写,愈发加深了读者对婚姻救赎贫家女这一主题的价值认同。灰姑娘及灰姑娘类型的文本往往运行着这样一种模式:一个地位卑微女性(最好是美貌的贫家女),如果具备了男性欣赏的某种美德(隐忍,顺从,贤良,等等),那么,她们就可能赢得男性尤其是富有或权势男性的爱情垂青,并通过婚姻(男性)实现地位的提升。我们姑且把这种模式称为“灰姑娘模式”。这一模式背后的生成话语是浓厚的男权中心意识:女性作为被男性审视的“他者”,她的地位的攀升需要依赖婚姻(即男性的救赎)得以实现。“灰姑娘模式”常以变体的形态存在于文本当中。这些文本的共同特点是用大团圆的结局再现了婚姻救赎女性的母题。
门罗的小说《乞女》虽然也启用了灰姑娘模式,但是她采取了颠覆的策略。她把这一模式放置于当代社会语境当中,揭示了它的内在危机;同时依照成长小说的书写轨迹,使人物的成长逐渐偏离灰姑娘模式,最终通过女主人公对豪门婚姻的放弃和走向独立,解构了这一模式。门罗笔下的贫家女罗斯,面对富家子弟帕特里克的爱情垂青,经历了从沉默到呐喊,从“失语”到“发声”,从选择的犹豫到毅然放弃的转变。通过罗斯命运的逆转,门罗反驳了“婚姻救赎贫家女”这一接受话语,颠覆了男权意识形态下对“灰姑娘模式”的价值认同,从而有力地呼应了发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性运动浪潮。
二、《乞女》的女性叙事对灰姑娘模式的解构
1.身份差异:“灰姑娘模式”的内在危机
《乞女》启用了“灰姑娘模式”。女主人公罗斯具备了构成“灰姑娘”身份的完整要素:贫穷,美貌,丧父,继女。男主人公帕特里克则具备了“王子”的身份要素:富有,高贵,商业帝国的“王位”继承人。罗斯的美貌成为帕特里克的凝视对象,她的隐忍顺从更是符合帕特里克对女性的道德期待。恋爱伊始,罗斯用沉默掩饰内心的真实,用隐忍面对爱情的遗憾,用顺从博得恋人的好感,用违心获得两人关系的平衡。她的自我意识尚在沉睡,呐喊还在蛰伏。与罗斯的“失语”和隐忍相对照的是帕特里克的男权意识。帕特里克是典型的男权话语操控者。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点题之笔:
“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周围都是穷人”。罗斯对他说,“你会把我家住的地方看成垃圾堆的!”
“但我很乐意!”帕特里克说,“你穷我也乐意。你很可爱,就像那个乞女。”
“谁?”
“《国王科菲多亚与乞女》。你知道,就是那幅画。你不知道那幅画吗?”[2]
“国王与乞女”正是帕特里克与罗斯关系的投射。一个是威严的父权话语操控者,一个是沉默而顺从的“灰姑娘”;一个是施恩者,一个是受惠者。一幅画的隐喻有力地揭示了灰姑娘模式下两性话语权利的失衡状态,映射女性作为“男性他者”而存在的地位,昭示了这一模式隐含的男权中心话语,为解构这一模式进行了话语准备。
罗兰·巴特在《现代神话》中指出:现代神话是经过神话化程序后的话语系统。这类话语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遮蔽性,对能指和所指的历史内涵进行遮蔽,使偶然性显得不朽,其实质是充当意识形态转化的工具[3]。灰姑娘的童话即是这样一套话语系统,它遮蔽了王子与贫女的社会阶级和文化身份的差异,抽取出婚姻救赎女性这一男性中心话语。灰姑娘模式的类文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对阶级和身份等社会语境进行了遮蔽,从而使婚姻救赎贫女的主题具有了可能性。门罗在《乞女》中,把灰姑娘模式放置于现代社会语境之中,从身份认同、阶层差异等现实的书写考察灰姑娘模式的内在矛盾性,从而揭示其潜在的危机。小说中多次强调罗斯与帕特里克来自不同的阶层。阶层的差异使他们的关系危机四伏。阶层(也可译为阶级)代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帕特里克与罗斯,一个来自庞大的商业帝国,拥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一个来自清贫的乡村之家,带着挥之不去的贫民意识。即使在爱情光环笼罩之下,二人关系的危机也已初露端倪。口音作为阶层差距的外在表征,首先被门罗提取出来。对于罗斯的口音,来自上层之家的帕特里克十分不屑。同样,帕特里克瞧不起罗斯的朋友。随后,来自家庭背景的冲突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危机。帕特里克的家人掩饰不住对出身贫寒的罗斯的轻蔑甚至怠慢。帕特里克与罗斯的家庭同样格格不入:从器物摆设到饮食菜肴直至谈话风格都无法引起他的兴趣。虽然罗斯的后母极尽迎合之能事,但总与帕特里克背道而驰。
两个人悬殊的阶层差距使其无法对彼此形成身份认同。阶层,代表着不同的集团利益,无法跨越;身份,作为个体的外在属性,难以抹杀。罗斯与帕特里克的身份差距,犹如难以逾越的鸿沟,使他们貌似平静的关系暗藏危机。“灰姑娘”及灰姑娘的类文本之所以能使“王子与贫女”的爱情神话成为可能,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故事的社会政治语境,弱化了灰姑娘与王子的身份和阶层属性,突显了男权中心意识,使贫家女通过婚姻实现地位跨越的神话具有可能性。门罗在《乞女》中还原了这一话语的社会语境,从政治真实的角度揭露其内在矛盾性,为解构这一主题进行了政治准备,同时也使小说的叙事更具现实的批判性。
2.成长的轨迹:“灰姑娘模式”的偏离
成长小说的一贯模式是主人公离开原有的生活,在历经一系列的磨难之后,冲破原有的认识,领悟生活的真谛并走向成熟,这其中常常会有一位领路人,协助其成长[4]。《乞女》中的罗斯也遵循着这一成长轨迹。离开乡下小镇的罗斯,经受了一系列的生活磨练:她通过发奋苦读,赢得奖学金进入大学;在大学里,她吃苦耐劳,依靠打工甚至卖血来求得生计;与帕特里克的爱情更是让她变得理性而冷静。与此同时,她也遇到了一位“领路人”协助其成长。亨肖博士是有点女权主义味道的人物,虽年逾古稀却仍独善其身。她鼓励罗斯独立自主,希望她不要依赖男性而生存;她欣赏罗斯聪明好学,多次与她畅谈理想,鼓励她追求事业;她质疑罗斯与帕特里克的关系,警告罗斯不要为了金钱接受爱情。
在灰姑娘的童话叙事里,灰姑娘也有一位领路人,那就是用“水晶鞋”构建灰姑娘与王子童话婚礼的仙女,她是引领灰姑娘走进男性殿堂的始作俑者。门罗在《乞女》中,解构了这一形象。亨肖博士作为罗斯与帕特里克关系的解构者,唤醒她的自我意识,协助她偏离灰姑娘模式。渐渐地,罗斯的自我诉求日益清晰,骨子里雄心勃勃。她告诉亨肖博士,她要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在与帕特里克的关系上,罗斯原有的被动逐渐消解,从“审视”的对象走向“审视”的主体。她审视帕特里克的刻薄、阴柔及其对家族的屈从;她不能容忍男权意识烙印下“国王与乞女”的关系模式;她清醒地意识到阶层的差距横亘在两人中间难以跨越,开始对这场羡煞旁人的童话婚礼踌躇不定。显然,罗斯的成长开始偏离灰姑娘模式,她正试图突破男权话语,走向主体的独立。这一偏离为“灰姑娘”形象的最终解构预设了伏笔。
在灰姑娘的童话叙事里,灰姑娘处于“失语”状态。她的个性和精神的缺失完成了灰姑娘形象的“符号化”过程。门罗在《乞女》里彻底颠覆了这一形象。伴随罗斯的成长,她的精神世界日渐丰满。从小心翼翼的乡村少女到知识女性;从对爱情的模糊理解到理性认知罗斯的成长完成了一个圆形人物的动态成长轨迹。这其中,罗斯的“呐喊”成为标志性事件。“凭什么我就一定会爱你?我本来就没什么错,可你为什么老觉得我有错?你轻视我,你轻视我的家庭和我的出身背景,你认为你是在给我施恩惠……”[2]。罗斯的呐喊一针见血,她清晰地指明了两人关系中男权话语在作祟。从沉默的“乞女”到呐喊的罗斯,从对男权话语自觉服从到自发突破,罗斯的形象与“顺服的灰姑娘”发生了错位。伴随她自我意识的完全苏醒,罗斯的成长偏离了灰姑娘模式。
3.空间的位移:“灰姑娘模式”的解构
对灰姑娘模式的最终解构,门罗采取了迂回策略。她让热恋中的二个人重归于好,让罗斯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走入婚姻。在保证了叙事并不突兀的前提下,解构灰姑娘模式。
童话研究学者杰克·赛普斯在对包含灰姑娘在内的格林童话进行研究时,总结了这些话语中女性的共性:“女主人公要学习成为被动、顺从、自我牺牲、勤奋、隐忍和道德上中规中矩的人。……她的管辖权是在家中或城堡里。她的幸福取决于是否符合父权社会的统治。”而“男主人公的管辖权是开放的世界”[5]。由此,空间具备了性别的属性。城堡(或家庭)作为一种封闭自足的空间划拨给了女性,而男性则成为宏大叙事的言说者拥有广阔的公共(社会)空间。灰姑娘模式遵循的正是这样的空间性别划分。
在以往的表现灰姑娘主题的文本中,通过将女性最终安置在家宅的空间,为婚姻救赎女性的主题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样的结局在《乞女》中遭遇了解构。进入了家庭空间的罗斯,很快就嗅到了这个空间的封闭、狭小与琐碎。这个空间再也承载不了她丰满的精神世界。终于,这场童话婚姻在罗斯的去意决绝中戛然而止。走出婚姻的罗斯,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伴随着罗斯对豪门婚姻的毅然放弃,从封闭的“城堡”(家庭)向“城堡”以外的公共空间(社会)的成功位移,婚姻救赎贫女的神话宣告破裂,灰姑娘模式彻底瓦解。
三、结 语
从沉默到呐喊,从“失语”到“发声”,从众人艳羡的爱情到童话婚姻的破裂,门罗完成了“灰姑娘”命运的变奏与改写,也完成了一个当代女性从成长到成熟直至完全独立的女性叙事。罗斯的成长超越了男权话语,在解构灰姑娘模式的同时宣告爱情不能依赖施舍,婚姻无法实现救赎,女性自我才是命运的主人。这样的宣告在小说发表的上个世纪70年代,尤显珍贵,它有力应和了发生于当时的西方女性运动浪潮。爱情与婚姻,在门罗这里,不是女性成长的最终归宿,而是她们成长的催化剂。
美国当代作家厄普代克和拜厄特把门罗比作当代契科夫和福楼拜。门罗不虚此评。她的小说往往于平凡中见深刻,扑瞬间显锋芒,无论对于女性作家还是女性文学,门罗的这一风格都显得难能可贵。《乞女》的女性成长叙事通过对灰姑娘模式的解构,反驳了男权话语的绝对权威,打破了婚姻救赎女性的神话,张扬了个性和勇气。同时,门罗的冷静还体现在她对罗斯放弃婚姻的时间选择上,即罗斯“能自己挣到钱的时候”[2]。门罗深谙女性的自我拯救是以经济的独立以及社会身份的确立为前提,否则,她将只有再次依附婚姻而别无选择。那么,罗斯超越男权话语,走向自我的新生的叙事将会自行瓦解。正如有学者所言,门罗的小说“用纪实的手法描述女主人公在生活和工作中同男权进行抗争,……生动地记述她们的自我意识过程,宣扬她们在坚定地追求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俗的勇气”[6]。虽然女性反叛婚姻,追求人格独立的主题在历来的文学书写中并不少见,但门罗在《乞女》中所彰显的女性力量和勇气,更具现实的召唤意义。
[1]格林兄弟.格林童话[M].魏以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0.
[2]艾·门罗.乞女[J].谭敏,译.译林,2011(4):111 129.
[3]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2.
[4]虞建华.杰克·伦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68.
[5]Jack Z.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M].New York:Routledge,2006:6.
[6]耿力平.评《加拿大英语文学史》[J].外国文学,2010 (6):66.
The Feminist Narrative Beyond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Cinderella Mode in Alice Munro’s Female Initiation Novel The Beggar Maid
DUAN Hong-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Underneath the literary discourse of Cinderella is the patriarchy-centered consciousness, which holds that women’s promotion is realized by men’s favor of them.In Alice Munro’s female initiation novel The Beggar Maid,Munro sets the Cinderella mode in the background of a modern society,where she exposes its inner conflicts and cris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dentity,class and sex.Munro follows the writing model of an initiation novel to depict a dynamic female hero,and finally deconstructs the Cinderella mode through the heroine’s breaking away from marriage. Furthermore,Munro’s emphasis on the heroine’s economic independence makes her narrative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inderella mode complete and reliable.
Cinderella mode;patriarchal discourse;female initiation;The Beggar Maid
I 3/7
A
1008-3758(2014)01-0107-04
(责任编辑:李新根)
2013- 06- 20
段红玉(1971-),女,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