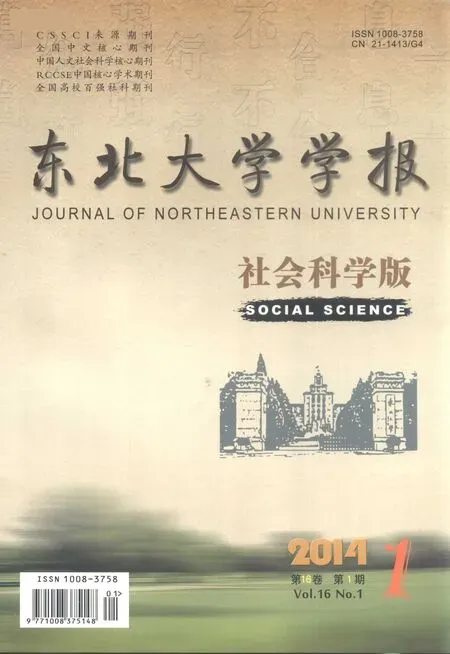国外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实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杨晓楠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受世界人权理论发展和立宪主义影响,“二战”后大部分国家在宪法文本中增加基本权利条款。作为效力等级最高的法律,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远非宣示性的,尽管刑法等一般性法律已将部分基本权利在部门法内得以实现,但我们不能回避一个关键问题,基本权利条款本身的效力是否只能通过部门法实现?如果部门法未能尽数规定公民基本权利,是否意味着未被规定的基本权利效力将会落空?再者,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对象是否仅限于立法、行政机关?如果一位公民侵犯了另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宪法层面上能否让侵权者提供有效的救济,抑或一定要转化为其他部门法救济方式?本文从比较法视角研究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实现路径,以美国宪法中“国家行为人”理论的新发展、德国宪法中的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和加拿大的宪法实践为例,为我国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实现模式提供借鉴。
一、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实现路径梳理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立法机关在制定部门法时,应依照合宪性要求,尽可能将基本权利转化为部门法权利,从而使基本权利得以实现,这是法治运行良好的表现,可以看做基本权利由立法机关主动且间接实现的路径。但在这种实施方式下,基本权利已经顺利转化为其他部门法权利,并不涉及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适用,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本文讨论重点在于基本权利条款本身对国家与公民(或私人组织)、公民(或私人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权利条款在国家与公民(或私人组织)之间效力的实现,由于这一法律关系的主体间存在着不对等性,因此,称为宪法的纵向效力实现;另一方面是指基本权利条款在公民(或私人组织)之间效力的实现,由于这一法律关系属于平权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路径被称为宪法的横向效力实现。
1.纵向效力实现
宪法是一种公法规范,各国宪法理论均不否认其纵向效力,基本权利条款可以对国家立法和行政行为构成一种有效控制,成为防止国家机关滥用公权力的有力武器。然而,基本权利条款纵向效力的具体实现方式也依赖各国的宪法审查和监督机制,公民可以获得的实际救济方式有所不同。在分散式的司法审查模式(以美国为例)和集中式的专门法院审查模式(以德国为例)下,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可在具体诉讼中直接审理国家行为对私人基本权利侵害的情况,根据基本权利条款决定所涉法律的合宪性,并以宣告法律无效的方式对国家侵权行为施以宪法性救济。法国是欧洲唯一没有建立宪法司法审查的国家,在2008年宪法改革之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主要负责事前审查,不能审查已经生效的法律是否违宪,而且提起事前审查的主体并非基本权利实际遭受侵害的人,而是政治团体,因此,对于“政治对立程度不足而没有被提交审查的法律,可能侵害基本权利但却长时期存在于法律秩序中”[1]。但在改革之后,法国宪法委员会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审查已生效的立法是否有违反基本权利条款的情况,因此,即便在法国模式下,公民基本权利纵向效力大多也可以实现。
2.横向效力实现
宪法属于公法范畴,在基本权利条款的横向效力上,各国做法不一,大致有几种类型。
(1)完全无横向效力。这种模式只承认宪法的纵向效力,认为宪法的直接实施者是立法、行政机关,其效力对象应是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非一般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而完全否认宪法条款可以在私人法律关系中产生效力,基本权利必须转化为部门法权利才可以在私人法律关系中实现其效力,司法机关不得在私权利案件中适用宪法。
(2)间接、有限横向效力。这种模式同样强调宪法的公法属性,否定宪法条款的直接横向效力,但由于基本权利条款的重要性,如果完全排除其横向效力,会使公民基本权利受损,因此通过法律解释方式将宪法适用于司法实践中,间接地实现其横向效力,如德国[2-3]。还有的国家虽然一定程度上承认宪法的横向效力,但是基于宪法条款的性质,仅可以直接适用某类条款,对宪法整体横向效力有所限制。
(3)完全直接横向效力。这种模式认为宪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可以不受限制地适用于各类型主体,包括私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基本权利条款的实现也无需以国家机关为中介,如果私人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可要求私人主体提供救济。爱尔兰和南非是明显地采用完全直接横向效力模式认可基本权利条款效力的国家[4]。爱尔兰法院在霍斯福德案判决中指出: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独特地赋予给其对国家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个人的诉权。南非1996年宪法权利法案第8条第2款规定:“考虑到宪法权利及其所要求义务的性质,……(宪法)权利法案条款可以约束自然人和法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完全限制宪法的横向效力不利于基本权利保护,因此逐渐以间接或有限的方式承认基本权利条款的横向效力,以拓展基本权利保护的方式和范围,一些国家正从传统的纵向效力理论转型为一定程度地接受、适用横向效力理论,但囿于宪法审查机制和法律传统限制,在权利类型、救济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
二、国外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具体实现路径的比较
1.纵向效力理论的突破:美国宪法效力学说的新发展
在美国传统宪法理论中,宪法作为控制国家权力的最高法律,其地位不同于一般法律,适用也受到限制,“国家行为人”理论是基本权利条款适用的基本原则。该理论认为,宪法保护通常只适用于“国家行为”存在的情况下,而不在私人行为中,这一理论限制了基本权利条款效力拓展的范围。虽然这一理论现今饱受诟病[5],但仍是美国宪法效力的指导性原则。
“国家行为人”理论源于自由主义理论、社会契约和国家主权理论,主张个人应保留让渡给国家以外的剩余权利,而国家只有在正当原因出现时,才可通过立法手段处分公民已经让渡的权利[6]。宪法作为社会的至高契约,主要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适用方面应坚持公―私领域的二分法,即宪法诉讼通常仅存在于国家参与的纠纷中,而单纯涉及私法关系和个人自治领域,通过一般性法律加以调整[7]。在“国家行为人”理论指导下,基本权利法律关系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行政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如果国家立法、行政机关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那么,立法或行政法令无效,公民进而得到宪法救济。
从法律解释学的视角看,美国宪法文本主要以阐述国家机关权力和义务的方式制定,其中基本权利条款主要以禁止性义务的口吻加以描述,例如,第1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明确规定了国家是保护信仰自由的义务承担者,并未规定其他私人主体的义务。在基本权利条款中,只有第13修正案规定“禁止任何人从事奴役他人和强迫役使的行为”,涉及私人主体,其他条文均缺乏类似表述。因此,通过法律解释方式实现横向效力极为困难。在1883年民权系列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第14修正案条文只能约束州和地方政府,国会不能通过立法禁止私人间的种族歧视。也就是说,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纯粹私人的侵害,原则上不能获得宪法救济。随着“国家行为人”理论的发展,其范围正逐渐扩大,在一些情况下其界限也并非十分明确。现今“国家行为”并不限于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而指一切具有公权力色彩的行为。有学者将除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外的“国家行为”分为两种情况:有国家权力介入的私人行为和私人承担公共职能的行为等[8-9]。夏利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法院执行私人签订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合同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规定,但私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本身则不属于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尽管“国家行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该理论本质上仍是承认宪法条款的纵向效力而排除其横向效力的。
“国家行为人”理论对司法的限制可能使其实际上成为基本权利侵害者的“帮凶”[10],美国法院近年来不断拓宽国家行为的范围,试图在特定基本权利保护的实践上逐渐突破“国家行为人”的限制,有向着基本权利横向效力模式转向的趋势。言论自由一直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核心性权利,言论自由的义务主体通常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但在一些案件中,诉讼主体和责任主体表面上来看均为私权利主体,而且所涉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这项基本权利却实际影响了私人间法律关系。在沙利文案中,纽约时报刊载的广告失实地批评了沙利文监督的警察部门,沙利文以诽谤为由提出诉讼并获赔偿。纽约时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政府官员不得因新闻报道的部分内容失实而起诉诽谤,必须证明媒体的报道存在真实的恶意,并且自己的实际利益因失实报道受到伤害。可见,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可以成为诽谤、精神侵权等案件的抗辩理由,这些罪名或责任可能由成文法规定,也可以是一项普通法责任。如果说这一案件的原告是政府官员,其私人法律关系的性质还是有争议的,那么2011年辛德尔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就更为明显了。该案被告在原告儿子葬礼外公开抗议美国对同性恋的容忍,并将原告儿子之死与其联系在一起,原告提出侵权之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被告的行为受宪法第1修正案保护,在公共场合的公共言论可以成为精神侵权责任的合理抗辩,从而间接影响了两个私人主体间的侵权诉讼。这两个案件没有国家的参与,但法院在解释诽谤和侵权责任时,拓宽了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据此解释了民事或刑事责任的承担原则,以司法性的公权力间接介入了私人关系,改变了传统的基本权利纵向效力理论。辛德尔案是基本权利适用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宪法关系的界定实现了从主体到内容的飞跃——传统理论主要从主体或其行为的性质上进行分类,对言论自由的解释将公共言论整体纳入到公法关系范畴内。
2.间接横向效力实现:德国“第三人效力”理论
基本权利横向效力的产生在理论上源于对国家责任形式的重新认识。随着人权理论的发展,基本权利保障范围正逐渐扩大,在内容上从公民和政治权利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的责任形式也随之改变。国家不再是消极义务人,而是在更多场合承担积极义务,通过主动行为保护和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对基本权利的效力也应有新的认识,如果立法者未能通过立法防止第三人侵害,那国家就没有履行其积极义务,私人侵权因而带上了公权力不作为的属性。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在劳工和反歧视领域,国家明显负有监管在经济上具有优势地位的雇主或资产所有者的义务,这种私人关系本质上不再是自由市场下的平权关系,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积极义务更为突出。在这个背景下,各国逐渐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宪法的横向效力。但是,如果完全承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可能会破坏法律规范体系,因此,间接或有限承认宪法横向效力成为一种折中模式。宪法效力问题是德国宪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德国宪法理论称其为“第三人效力”理论,包括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德国传统宪法理论也将基本权利看做公民对抗国家侵害的“防卫权”,“直接第三人效力”是“二战”后基本法颁布之后在德国兴起的宪法效力新学说,该学说以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大法官尼帕代为代表[11],他认为,“倘若基本权利之条文不能直接在私人间被适用的话,则宪法的基本权利之条文将沦为‘绝对的宣示性质’罢了”[12]337-338。因此,一些基本权利“具有可在私法关系中直接拘束力之特征”[12]341,承认部分基本权利条款的完全直接横向效力。尼帕代将这一理论适用于司法实践,认为“私法规定不足,且无其他法律可以依据,而保障人权又必须时,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规定以解决私人之间的争议”[13],他在1957年“单身条款案”中直接适用了基本法的权利条款,认为疗养院雇佣合同约定实习护士不得在实习期间结婚的条款违反了基本法关于婚姻权、人格权等基本权利的规定,因此合同无效。
尼帕代的观点受到了德国主流学界的批评,联邦宪法法院也不赞同劳动法院适用宪法的方式。1958年吕特案中,宪法法院提出了间接适用宪法条款的方案。该案本身属于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吕特因在电影节活动中公开宣传抵制导演哈兰拍摄的电影而被哈兰告上了法庭。汉堡法院支持哈兰的起诉,认为吕特的行为属于德国民法规定的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进行的侵权。吕特对此提出宪法诉愿,宪法法院认为汉堡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民法中“善良风俗”的条款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言论自由这项基本权利的重要意义[13]。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权利首先是公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但德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其作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而对所有法领域发生效力”[14]。因此,基本权利条款应该约束包括司法审判的国家行为,法院并没有直接适用基本权利,而是以民法的概况性条款解释为突破点,作为基本权利条款影响民事关系的媒介,基本权利条款进而通过“客观价值秩序”在民法解释中实现了其间接效力。
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样,德国宪法法院不主张将宪法条款“部门法化”,但其处理方式和美国法院不同:第一,宪法法院并非将基本权利条款作为一种对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而是成为解释民事条款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以民法概况性条款作为中介产生效力,间接承认了宪法权利的横向效力,因此被称为“间接第三人效力”。而美国法院始终没有直接突破“国家行为人”理论的纵向效力阴影,一直试图在扩大公共行为、公共领域的范围。第二,从条文上看,德国基本法与美国宪法不同,其本身对宪法效力问题的阐述是暧昧不清的,没有明确在条文中说明基本权利的适用对象,反而以宣示权利的方式表述,如基本法第2条规定,“人人享有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但不得侵害他人权利,不得违反宪法秩序或道德规范”。这种宣示性条款在解释学上没有排除其他义务主体。第三,与美国分散式审查机制不同,集中审查将宪法问题的最终解释权赋予宪法法院,其对宪法问题的裁决权是最终、独占且排他的,因此其管辖权也受到限制,平权主体间诉讼只能在普通法院审理,基本权利受侵害者除非以宪法诉愿方式提起诉讼,否则不能由宪法法院审理。劳动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方式势必需要对具体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将基本权利的实质适用到具体案件中,这种管辖方式违背了设计宪法法院的初衷。基本权利的效力模式一定程度上与宪法实施机制有关,“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经上世纪50年代德国宪法法院解释后,逐渐成为德国宪法学界的主流学说。
3.宪法有限直接横向效力实现:加拿大宪法权利和价值二分法
加拿大的宪法秩序较为特别,基本权利主要由《加拿大人权法案》《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两部法律规定,前者的权利更多是宣示性的,后者才是保护基本权利的有效工具,其效力优先性在1982年加拿大宪法中得到肯定。对于加拿大宪章的效力,加拿大法院采取有限承认其横向效力的原则。与其他国家不同,加拿大法院采取了宪法基本权利和宪法价值的两分法,认可宪法价值的直接横向效力,要求在解释和适用一般性法律时遵守宪章中的宪法价值,但就纯粹的权利条款而言,则仍保持纵向效力模式。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多芬案判决中裁定,虽然法庭根据普通法颁发的禁令违反了表达自由,但是宪章只能直接适用于议会、立法机关、省行政机关和联邦政府,这一案件完全没有政府参与,法院禁令本身并不属于宪章约束的范围,因此不能直接适用宪章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但法院在适用普通法的时候必须要以符合宪章的方式适用普通法。总之,基本权利条款的横向效力是有限的:第一,当私人因立法行为或其他政府行为导致另一人基本权利受损的话,宪章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可以直接适用私人之间的诉讼。但如果私人诉讼是以普通法为由的话,基本权利则不适用。第二,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普通法原则过程中,要遵守宪法中的基本价值,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实现基本权利反映的宪法价值。对于宪法价值和权利适用上的差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后来的希尔案中有进一步阐述:基本权利条款规定了国家的义务,如果立法和行政机关侵犯了基本权利,那么,国家机关自然因未履行义务而承担责任,权利人获得宪法上的诉因和救济。如果宪法性法律关系存在于两个私人主体之间,且涉及的是普通法和基本权利的冲突,那么,私人主体不会对另一私人主体承担宪法义务,因缺乏义务而丧失诉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通法诉因存在,法院可以在权利人申请普通法救济时以符合宪法价值的方式发展普通法。实际上,由于法院不属于承担宪法义务的国家机构,发展普通法的行为又带有立法性质,因此,法院的态度是较为谨慎的。与德国宪法法院相比,加拿大法官在这种情况下的创造空间因其权力有限而受到限制。
三、对我国基本权利条款实现路径的启示
1.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实现
我国关于基本权利条款效力的探讨较少,这因为我国的宪法实施机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宪法实施以规范(抽象性)审查为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对法规进行审查,司法机关无权对所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中直接否定了在刑事审判中宪法作为直接定罪量刑的依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明确指出,法院应引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排除了宪法在法院的适用。因此,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很难在诉讼中实现其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审查抽象性法规且其审查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基本权利的纵向效力在我国也是受限的。
2001年的齐玉苓案也给宪法学者带来了新的思考,批复中提到宪法性的受教育权被侵害应给予民事救济,这说明基本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也曾实现过其横向效力。于是,宪法司法化或私法化的讨论曾一度不绝于耳。然而,齐玉苓案批复和判决没有清晰区分宪法权利—义务和民事权利—义务,混淆了基本权利义务主体和民事义务主体的概念,也没有像德国或加拿大法院那样通过解释原则或以部门法为中介说明基本权利的实现路径,因此,对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是模糊不清的。童之伟教授将宪法适用分为“遵守性援用”和“适用性援用”,指出齐玉苓案的批复则属于“适用性援用”,即“其行为的性质属于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适用宪法而非遵守宪法”,他认为这种行为本身无助于具体争端解决,并且横向效力相当于“抽掉宪法的骨头”[15]。齐玉苓案批复在2008年公布的最高法院决定中已被废止,至今未有其他的司法解释或者法律法规对宪法效力实现作出进一步说明。
2.对我国基本权利实现路径的启示
从对国外宪法的比较和我国基本权利实现路径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各国宪法理论都在尽量拓宽基本权利实现的路径,“有权利必有救济”,基本权利和其他法律权利一样,其实效体现在权利保障和救济的方式上。如果一般性法律中没有具体的规定,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或规定的救济不足,那么,宪法基本权利如何能实现呢?就我国现今宪法理论和机制而言,无论在一般性法律解释还是适用上,很难将基本权利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导入或辐射到部门法中。也就是说,你有这项权利,却无从实现,因为这项权利太为重要,因而无从实现,恐怕这难被认为是基本权利设置的初衷和归宿。
因此,在强调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之余,应更多关注其实现的可能性,可以强调在立法阶段主动遵守合宪性原则,也可以在法规审查阶段加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力度,甚至可以考虑适当参考德国和加拿大的经验,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适当考虑基本权利的价值,使得基本权利条款在实践中不至于落空。
(2)尽管基本权利保障极其重要,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可以看出,采取完全直接横向效力模式的国家仍少之又少。若随意将宪法等同于其他法律,无异于矫枉过正。根据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的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规范等级体系中的上位规范,为现行法律体系提供了规范性基础,下位规范是宪法权利实现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抛开其他部门法,在司法实践中不加限制地适用宪法,可能会导致部门法虚无主义。如果仅是在实践中遵守性地援引宪法条文而不实际解释其效力或赋予其有效救济,的确不利于具体纠纷的解决,也不利于宪法权利的保护。宪法的至上性决定了其适用的特殊性,宪法效力理论研究和探索是有益且必要的。
(3)宪法效力的实现与一国的宪法实施机制和法律传统密切相关,宪政正是将宪法精神融入到实际政治秩序中,让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从文字走向人们的现实生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选择,要考虑一国宪法的具体条文阐述方式、宪法解释理论、违宪审查机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不能随意照搬或抄用某一种宪法效力理论,这样反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实现效果。而且,各国对基本权利效力的认识都是在突破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发展的。就我国情况而言,完善宪法实施机制是实现基本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盲目地谈宪法司法化或私法化都难取得成效。
总之,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效力模式,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使其成为公民法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实现宪法价值的重要途径。
[1]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2010(8):112.
[2]张巍.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07(1):107-113.
[3]郭百顺.论德国宪法“第三人效力”的正当性[J].德国研究,2004(1):55-59.
[4]Gardbaum S.The“Horizontal Effect”of Constitutional Rights[J].Michigan Law Review,2003,102(3):395.
[5]Bevier L,Harrison J.The State Action Principle and Its Critics[J].Virginia Law Review,2010,96(8):1767.
[6]密尔.论自由[M].于庆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14.
[7]Kay R S.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and the Independence of Constitutional Law[J].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1993,10:329.
[8]上官丕亮.宪法在民事纠纷中的司法适用机制比较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1(4):82-88.
[9]Buchanan G S.A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the Search for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J].Houston Law Review,1997/1998,34:333.
[10]Strauss D A.State Action after the Civil Rights Era[J].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1993,10:410.
[11]Quint P E.Free Speech and Private Law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Theory[J].Maryland Law Review,1989,48(2):247.
[12]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3]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2004(2):57-58.
[14]张翔.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2.
[15]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J].中国法学,2008(6):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