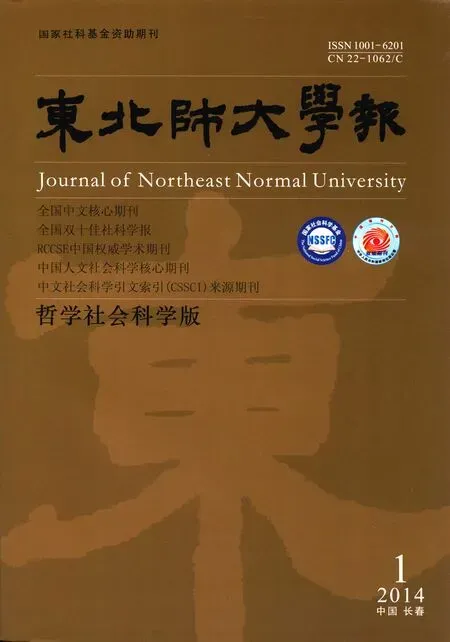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
——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张金荣,徐 佳
韦伯与桑巴特比较视角下的现代社会起源
——兼论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张金荣,徐 佳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以“俭”与“奢”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合理性,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回归至现代性困局的一致忧虑。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较之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与西方的对话与融合中,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需要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
韦伯;桑巴特;现代社会起源;现代性
现代社会的起源是社会学追问的一个本源问题,社会学家们不断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明确界定为发达的现代社会,并将社会学的实践目标指向寻求现代社会的秩序与进步。而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几乎关涉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人们关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奇迹”,并大力探讨非西方后进国家的发展及现代化进程,以期揭示这样一个经验事实的前因与后果: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产生于西欧?它的根本动力何在?社会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回应,就这一问题开始了争论不休的诠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阶级斗争与革命的作用,认为资产阶级打碎封建主义枷锁后,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改变了生产关系。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著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他们围绕着产权和激励两个重要因素,着眼于经济形态的蜕变,以此作为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基点。马克思·韦伯与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针锋相对,相互批判,但却都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出发剖析资本主义动因的。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跟随社会思想家的脚步,追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把握现代性源于西方的深层根源。与此同时,我们不禁会发问,现代性为何无法首先发端于中国,中国现代性的生发和引进有着怎样的内生逻辑,又经历着怎样的发展历程?现代文明源于起始于欧洲的现代性,现代性对现代人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以理性和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由于理性的全面殖民和主体的过度弘扬,又不断指向人们反思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
一、经典对决:“禁欲”与“奢侈”的分歧
在现代社会起源问题的论域里,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所持的观点可谓经典的对决。实际上,二者有着相同的时代与国度背景,后者较前者年长一岁,共同成长于“德国思想”时期。与马克思主义用于解释历史的、经济的和唯物的决定论所不同,韦伯和桑巴特将目光聚焦于文化、知识及心理的内在特质对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上,使得当时对现代社会起源的解释路径产生了重大转向。此外,针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丹尼尔·贝尔曾明确提出其双重起源:一面是韦伯强调的“禁欲苦行主义”,另一面则是桑巴特所突出的“贪婪攫取性”。
马克斯·韦伯以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他主张的“理解社会学”透过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但又将社会行动背后的机制与文化相整合。在他看来,西方文明之所以蕴生了资本主义,西方人的某种精神气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教伦理是根本的起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是从基督教苦行主义中产生的。”[1]148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正源于清教徒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利润的合法追求。不以享乐为目的,由正当的经济活动获取财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性。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开始了,以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和洗礼派四个教派为主的基督新教在宗教改革后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徒们为了争当上帝的选民,履行“天职”(the calling)而在日常生活中勤奋工作。每位教徒在不断问询自己是否被上帝所挑选的同时,他们深刻地领会到,在职业领域内积极有序地工作便会得到神宠,入世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宗教给予这种行为以动力支持,也将一种心理约束力赋予人们,“这种心理约束力,把劳动视为天职,视为一种最佳的、归根结底也是唯一的获得恩宠的手段。”[1]146-147于是宗教氛围辐射信仰者生活的各个层面,统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引导着人们在今世的追求。
因而,排除单项的经济导向说,韦伯用“心理”优于“逻辑”的解释,从“禁欲苦行的基督新教”中,从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中寻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新教用伦理和理性执行着对“营利欲”的限制,使人们专心致意于一己之现世“志业”,以求救赎[2]。而生自基督新教禁欲精神的理性生活态度是现代文化的构成要素。就这样,是基督新教徒信仰的特殊性,让韦伯找到了新教与“经济理性”的关联。
不仅是基督新教在某些重要的层面上相异于其他以前的宗教形式,而且现代的资本主义也以其基本的特殊性而有别于以往各种资本主义的活动[3]。实际上,在韦伯眼中,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内在亲和而成。当由于宗教信仰产生勤勉和节俭,却由这二者产生财富的时候,韦伯开始担心傲慢和情欲等俗世之爱会挣脱宗教而泛滥。于是他开始愈加强调禁欲主义,主张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同样清楚的是,韦伯在提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后,又急切地批判这一论域里的不同声音,尤其是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
桑巴特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潜心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中,对欧洲的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阶段性地细分。同样站在精神文化的视角来寻找资本主义驱动系统的主要动力,桑巴特认为,现代社会是从欧洲精神的深处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和伦理有别样的解读:他突出强调犹太教的教义和信仰,认为犹太人机智、理性、精明强干的优秀素质使得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结构有了更强的关联性,并从犹太教较于清教更早奉行理性等诸多历史渊源中不断求证。他将犹太教领袖的商业内涵、犹太教的理性主义和条文主义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生发的土壤。用桑巴特的话说,由于犹太人反对天主教会的经济教条,从而解放了现代资本主义[4]31。而在这一点上,韦伯则从传统主义、巫术和犹太教三者的关系中对桑巴特予以了反驳。他认为犹太教的作用体现在瓦解了巫术所沿袭和强化的传统主义,让社会转向非传统,渐而步入现代化。
而与韦伯强调“禁欲苦行”恰恰相反,桑巴特在其所著《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消费为出发点和关注点,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完全以奢侈为特质的高度世俗化的文化图景。没有韦伯式的比较,而是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桑巴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一个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5]215。在书中,他把论据首先建立在宫廷生活和新贵们铺张浪费的史料上,似乎只有这种奢侈的消费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发展潮流,宫廷的模仿者不只是骑士和暴发户,还渗透到其他社会阶层。人们毫不节制地在住房、服饰、食物甚至室内陈设等各个角落追求奢侈的元素,“对享乐的渴求、对快乐和充满虚荣的炫耀的追求,像瘟疫一样席卷欧洲。”[5]104他将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结为性冲动和感官刺激的满足,认为奢侈现象突出之处都是财富开始积累,而且国民的性要求能够自由表达之处。
韦伯曾做过关于人类历史早期的家族研究,在他的分析中,注意到了男女两性所承担的不同经济角色。实际上,桑巴特也十分关注社会性别这一变量对早期资本主义奢侈文化形成的影响。他强调女性的谋略和技巧,赋予当时的女性以权力,甚至一个时代,影响男性,作用于两性关系与社会发展,扩展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最终,当女人们抓到世界的权力时,满足奢侈需求的物品的生产速度都会进一步加快。”[5]123他也曾提及“女权主义与糖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发展史来说极为重要。”[5]125而政治、经济形态随奢侈消费而产生的转变更是桑巴特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在消费的拉动下城市获得了早期的发展,农业、工业、商业都受到这一革命性力量的影响,因而创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态。
虽然桑巴特重视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拓展,但他仍是极力地论证着欲望、奢侈、消费的扩张与膨胀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和建构,这也正是他与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动力判断的根本分歧所在。二者从俭与奢出发,将对现代社会起源的理论争论推向了对立的两极。而实际上,面对如魔方般变化的社会现象,每一种理论往往只能发现和解释它的其中一面,因而,也正是由于社会的多面性产生了理论的多样性,由于理论的百家争鸣不断彰显其价值。但多元的理论又总会回归问题本身,针对现代社会的发端,二者看似完全相反、趋于两极的理论实则映射的同是现代性的自反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困局。
二、现代困局:两极对立的一致忧虑
如上所述,贝尔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也正是韦伯与桑巴特的经典对决所在。实际上,二者剖析资本主义动力的基点都是文化密码,一种类似于社会基因,抑或显示为社会聚合力的文化密码。而对于文化的解码,韦伯和桑巴特都将其归结于资本化的个体,区别在于前者的特征是禁欲苦行,后者则是贪婪攫取。
在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上,韦伯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区分“合理的资本主义”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而桑巴特则反复强调经济组织或制度。对于同样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不同于韦伯,他眼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企业精神”和“市民精神”的统一体,二者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两个构成要素的精神内核前者是贪欲、冒险和勇敢征服,后者则是合理、节俭和精于计算。这源于犹太教的精神精华所在,桑巴特自己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中坦言,之所以思考犹太教徒的动力是受韦伯对于清教教义研究的启发,随之,桑巴特就得出了犹太教与清教的独特一致性。从表面看来,这与其观点自相矛盾,但实际上,这种一致性归根结底就是生活的理性化。
韦伯也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最终陷入一个悖论当中,人们大多跳进物欲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宗教的精神慢慢枯萎,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逐步实现了对世界的“除魅”过程,统一的宗教世界观由分化的世俗文化所替代,宗教思想中的理性特质,由修道院来到了日常生活世界。理性,始终是我们认识韦伯的逻辑基点。“理性的经营,理性的会计,理性的技术,理性或可计算的法律,现代科学和生活行动的理性伦理”[4]30,这是韦伯所概括的“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对于现代社会个体行为动机的性质区分,最根本的核心则落在工具理性上,而非价值理性。在韦伯那里,现时代人们的行动依据是职业责任伦理。职业伦理同时是道德评价的重要尺度,而传统伦理已经成为一个私的领域,这便是现代性伦理精神的实质。理性资本主义进而生发出科层制与自由民主思想,引领人们步入现代社会。
如上所述,在现代社会中,合理地谋取利润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传统主义对人们的控制逐渐失效;劳动虽然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却是由理性的方式所组织的。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过程即为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韦伯看来,不仅仅是经济生活受到理性的主宰,这种理性化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整合方式,个人、群体、组织、国家的行动甚至世界观层面都充满了理性的渗透和蔓延。但这理性终究是残缺的,以致韦伯不得不发出困惑:“这一秩序还要控制着他们的生活——但是造化弄人,竟然使这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1]149-150
桑巴特同样搭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分析框架,确定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理性主义原则,他同样承认理性主义已经渗透至商业、技术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也绝不单是积极的,甚至其本身就潜存着一定的破坏性。桑巴特在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结尾处说“其结果是,在下代人那里,社会主义在美国可能出现最迅速的发展。”[6]这个结论看似武断,却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悲观态度。
实际上,“个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命运究竟怎样”是韦伯和桑巴特关注的终极问题,而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伦理等所展开的讨论,勾画的是一幅现代性的图景,而这幅图景的设想建立在世俗性和理性化向度的框架上。他们同时意识到了理性是现代社会发端、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全过程的一根红线。理性的逻辑穿透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韦伯和桑巴特透过这个关键的现象,认识到了这其中所蕴涵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和恶性发展,这让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可见,俭与奢的两极是资本主义矛盾系统的两个面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彼此制约的方面又始终在寻找着必要的张力和微妙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起源的问题上,看似相互对立的理论却共同隐含着现代性的困局。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现代性是人们认识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这也使得现代性的话题充满了人文与社会的关怀。现代性正是通过不断建构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实现着它的承诺,它使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累积,它带给人们理性的、秩序的、规则的、系统的生活世界。但鲍曼同时称它为“陷阱”,正因为它所形成的非意图后果及其相应的有限性。可计算、可度量、程序化使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趋于“抽离化”;工具理性的扩张实践超越和忽视了价值理性,全面地实现着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度弘扬的主体性,反而使主体自身渐而丧失了主体,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形式越来越明显。
不断推进发展的社会,重心由“生产”向“消费”的倾斜,是社会学家们普遍关注的。个体生存的角色由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生产性消费向符号性消费过渡,消费仿佛是快乐的源泉,消费彰显着自我的身份,消费改变着人们的欲望结构。消费的社会,人们对待欲望不是克制和延缓,而是及时地追逐。欲望不断地产生消费,再回归生产,生产又在创造着新的需要。消费的社会构造让人们在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之间渐渐迷失,而被置于一种生活意义的空洞化状态。同时,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将面对无法预知的风险,同时参与风险的制造。风险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存在状态,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的社会生活的“物化”和人的“异化”,令人们一再追问自我的生存价值,并呼唤着新的生活策略。
与韦伯和桑巴特的忧虑相一致的,无论是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贝克的“第二现代性”还是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都在现代社会发端的基础之上,试图更加深入地理解其变迁与发展。实际上,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意味着一种期待,是现代性的自我矫正,抑或是他者对现代性的超越。因为无论是阻滞的希望,还是令人忧虑的困局,都是现代性诺言的未竟之处。因此,这样的现代性不应该是一个终结,而更应该期盼一个重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直面现代“单面人”的生存困境,实践对生活世界的重建,走出现代性的困局,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主题,哈贝马斯、吉登斯等社会理论家正努力对此做出回答。
韦伯和桑巴特以“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的精彩对决,从西方社会的文化密码中破解出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合理性,又共同理性地陷入了现代性发展困局的忧虑当中。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并产生疑问:现代性为何无法首先发端于中国?中国现代性的生发有着怎样的土壤,又实践着怎样的逻辑?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又如何?
三、中国现代性的发端与困境
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同样是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重大理论争论和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却不专属于西方,现代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够相互借鉴的社会生产空间。现代性没有首先发端于中国,而是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渐而被引入中国,中国的现代性存在着“后发优势”,走的是“外发型”道路,是中西现代性互动的产物,却又有着其渐进发展的内生逻辑。
韦伯和桑巴特从文化视角分析了承载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的深层原因,对于资本主义未能发端于中国的经验事实,韦伯同样给予了解释。他仍是从典型的“理想型”研究出发,将解释的逻辑基于多元文化的差异性,用“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文化结构特征做出了回答,这便是韦伯提出的“中国命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成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亲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儒教伦理为主线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恰恰排斥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此,虽然有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嫌疑,但韦伯仍是将理性作为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基点,用理性化程度和本质性的区别指出了东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关联的差异所在。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与西方宗教相对应的,儒教主宰着理性和感性。理性主义之于新教与儒教,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支配世界的力量,而后者是适应现世的依托。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了自然的法则,忽视了思想的独立,阻滞了理性的发展;主张“内圣外王”,将道德视为人之根本,倡导道德理性。儒家传统强调“有机性”人情关系和特殊化人际网络,儒教徒缺乏较强的理性化能力,“重术轻技”、“重农抑商”等传统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本身与“传统主义”有着“选择性的亲近”,有利于维持传统的社会秩序。
现代性生成由于内在顽强的文化惯性而遭到阻碍,植根于文化传统主义之上的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文化特质,形成了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与组织逻辑。“情理”的深入使得中国社会结构的非理性特征明显,费孝通和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特征的论断也是对此的明证。中国感性社会秩序的存在也与儒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感性制度成为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中较为稳定的机制,现代性的发展容易对此形成路径依赖,而感性社会秩序与理性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又显而易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相应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本土儒家文明的冲突中演变和发展。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和冲突,现代性在中国尚未成熟地成为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而对于韦伯的“中国命题”而言,我们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难免受到其话语结构的影响。因而,在文化的理论构架下,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和发展,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肯定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实践。
现代性的西方传入为其在中国的生根埋下了“殖民”的意味,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又为其增添了悖论色彩。但中国的现代性需要在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寻求特色的塑造,需要在与西方的对话和融合中不断自我追溯、自我诠释,从而具备更权威的解释力。实际上,多元的现代性正是源于文化和历史的多样化,而普遍的现代性也只有在多元的选择和转化中,才能凸显其意义。因而,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其绵长的生命力恰恰为现代性的创变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思考如何从文化内核上推进现代性的转型,建构极具自身特色,又极富时代精神的现代性,需要我们多角度、多层次、持续地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可见,这不是简单的“中化”与“西化”的问题,因为现代在消解传统的同时,也在重塑着传统,这也是我们着重分析现代性发端的意义所在。
自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现代启蒙的理性逐渐渗透至中国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拉开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得以较快地发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近30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创造着“中国奇迹”,也在改变着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国俨然成为世界的焦点。与上世纪的“东亚模式”相类似,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正日益成熟,初具“中国道路”的雏形。
但现代性于中国同样折射出诸多的社会问题,现代性经济伦理的突出地位,忽视了其与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重要关联,经济乐观主义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工具理性带来效率和利益的同时,也带来浮躁和不安,生态、资源、可持续,成为新的关键词。当消费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逐渐解构和重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桑巴特的观点开始越发显现出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消费扩大着财富的积累与再生,消费代替了生产,对社会实现着主导。贪婪奢侈的欲望与消费形成了互构,欲望拉动着消费,消费又产生新的欲望结构。消费塑造更加阶层分明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消费状况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因而,消费本身就成为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挑战,享乐主义背后的无奈与束缚、道德的相对主义、价值上的虚无,这同样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巨大难题。
现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重大结构调整与战略转型,这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与成长的挑战与使命。因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反思中西方现代性的发端与发展,有益于我们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毕竟,以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加强制度结构的建设,重建现代人崇高的心灵空间,不断建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秩序,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作出回应的时代课题。
四、讨 论
以上所述,只是在精神文化的根源上寻找、比较和讨论东西方现代性发端的动力机制及基本逻辑。实际上,就韦伯和桑巴特二者而言,其本身并非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者,单是韦伯就关注到了促成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其他几套因素,即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等社会结构因素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影响。而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及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考量,可以看出,他同样十分注重制度的因素。因而,就思想家而言,我们有侧重地分析其社会思想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我们忽视其社会理论的全貌。而说到中国现代性的发端,文化的因素也绝不是唯一的变量。我想,不论是文化,还是制度,其本身就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和相互型塑的。而理论之于思想家有时却总是两难的展现,虽然韦伯和桑巴特二人对现代文明前途的茫然悲观遭到哈贝马斯等人的批判,但现代性的困境却仍鲜活地存在着。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李修建,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18.
[3][英]纪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M].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社,2009:214.
[4][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M].何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赖海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4.
The Origin of Modern Socie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ion Between Max Weber and Werner Sombart——Concurrently Discuss with the Start of Chinese Modernity
ZHANG Jin-rong,XU Jia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The origin of modern society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o investigate in Sociology.Max Weber and Werner Sombart argued the competing theory,which comes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sceticism and avarice.They found out the reasonability that modern capitalism originated in the Europe through the culture code of Western Society.However,their polar opposites come back to the same anxiety about the plight of modernity.The wide colonization of ration and overmuch promotion of subjectivity guide us individuals to reflect the meaning,value and ideal of life.Comparing with the western modernity,in China,it is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within the conflict of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locally Confucian culture.Therefore,we should deal wel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globality.We should keep exchanging and merging with the western world to model the modernity of our ow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construct an order of modern civilization,in which the politics,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could develop at every point in harmony.
Max Weber;Werner Sombart;Origin of Modern Society;Modernity
C91
A
1001-6201(2014)01-0191-06
[责任编辑:何宏俭]
2013-1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SH004)。
张金荣(1962-),女,吉林安图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佳(1980-),女,吉林敦化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