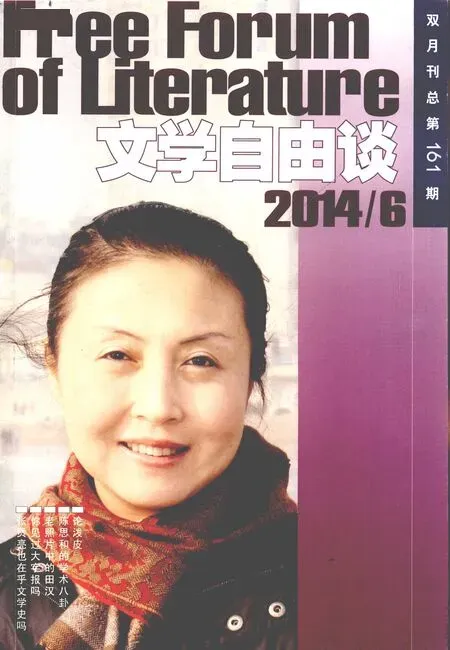她与她的时代最好不相逢
●文 肖惊鸿
关于那个时代,已然热了好久。那些个性鲜明的民国文化名人,特别得到传媒的青睐。在文化名人当中,自然有作家们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女性作家,如林徽因、张爱玲、萧红,在这股热潮里,更多了一层对其情感生活的无尽想象。各种言说纷至沓来。且不说纸媒的热度不减,仅是影视媒介,早些年就有丁亚民和曾念平执导的讲述林徽因与徐志摩情感经历的电视剧 《人间四月天》。而张爱玲作品更是数度被搬上银幕,一再被改编。热度经久不衰。继去年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萧红》以来,今年的黄金周,又与《黄金时代》偶遇。这次是许鞍华导演言说萧红。本来,我就此说事儿,在本已经有的热热闹闹当中分明有凑热闹之嫌。当然这不关许鞍华什么事儿。拍萧红据说是许导做了几十年的梦。我也不想把我对萧红与她的时代的联想搅到对一部电影的热议当中,这与我的题中之义也是相背离的。单就文学史而言,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是文学史叙事的根本所在。而仅就一部人物传记电影而言,《黄金时代》里,许鞍华们在那个时代背景中是怎样讲述这个女子的,对于看官们处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审美期待来说,本身就是危机四伏的挑战。纵是如此,我仍不能抵挡得住电影的诱惑。坐在影院里,望着那空了一半的座位,内心感慨这《黄金时代》还真不是大众的菜。来的都是该来的,不该来的也就都没来。开场前,却见一对耄耋老者,在中年子女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进来。我心里竟莫名地一热,陡然有了穿越岁月时空的感觉。
那个时代特殊,特殊到锻造出一大批现代文学大师。也特殊到出现了如此传奇的萧红。她短短的一生所有的忧患和不幸,都在她的笔下聚集。她的文字在忧郁中铺排,张开凄美的羽翼,跌跌撞撞冲向凡俗的尘世和真实的人生,那么凛冽地撕扯着现实的残酷与命运的卑微。她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关怀在那个暗淡时代独具一格,而她自己又是那个变革时代中极具勇气的独行者。她的文字,紧贴着那个时代起飞,终不能独自高飞。但她与时代不可剥离地共存于文学史中。她的作品滴着血、流着泪,在场性极强,国民性扑面而至,真切地书写着活着的众生。从这一角度看,又深具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时到今天,萧红的书写,依然是具有经典价值的文学话题,充满了警醒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她的底层写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作为作家的萧红得到永生的路径。然而,作为女人的萧红,与其笔下女性不幸的命运同样是时代的产物。这种不幸,在持续已久的民国热中,也是被津津乐道、一再热炒的。自然,探讨萧红其文自然不能脱离其人。但后世如何评说,却是各有不同。这让我想起我家社区外的早市。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之中,买的和卖的都在大声嚷嚷。谁都不会在意别人的活计。终归是人走市散,各人收了各人的银子,各人买了各人的菜。再看我自己的评说,也是闲话装了半筐吧。
1936年初冬,萧红孤身一人,在日本东京。本因疗治情伤出走异国,但又是怎样的孤寂纠缠噬咬着她,让她执着地给负心郎写信?她写道:“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心头热一阵儿,接着又冷一阵儿。萧红与生俱来的气质是凛冽的,而性格又是感伤的。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够说出这些话,也是自省到极致了。萧红对人生价值的感悟,人生哲学的升华,都汇集于此。然而此景不长,她的黄金时代很快便终结了。这时候,距离她离开人世,也只剩下五年。对于萧红的“黄金时代”,鲁迅阐明过,“天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胡适也说过,这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境界。而萧红与萧军的根本分岐,也是在于“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萧红心向往的“黄金时代”,也无非就是小我的基本生活诉求得以满足,同时精神的求索得以释放。如此实现以人为本的个人价值。倘使人人如此,这个社会也便成为理想文明的社会了。
我这会儿又想起许鞍华的电影。可见影像的力量多么强大。毕竟,萧红我是想见也见不到的了,而汤唯饰演的萧红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觉满足。假使文学都能经由影视抵达人心,那该有多么月明风清。影片的结尾,如此诠释萧红的“黄金时代”:“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显见地传达了创作者的审美维度和价值取向。
然而,亲们,对萧红来说,生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想怎么爱就怎么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带来了怎样的一个人生啊?
萧红的亲情大多夭折于未成年。母亲的早逝,父亲的冰冷,让爷爷的关爱变得弥足珍贵。亲情的缺失也许会导致人格的缺陷。后来,弟弟对姐姐的遭遇表示痛惜,但彼时的手足呵护,已无力开启萧红紧闭的亲情门扉。那个给她人生暧色的老人,对童年的她殷殷地期盼:“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可是,这个长大了的女子,果真是好起来了吗?
萧红宿命地出生在那个时代。她与她的时代狭路相逢。
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的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剧变下,社会经济文化相应发展。现代教育思想西风东渐,与社会政治变革相融合,使得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走向本土化。封建特权消除,社会各阶层机会均等。在现代教育空前发展中,女孩子萧红成为少数的受益者。萧红显然没有辜负这时代给予的机遇。当时,在西方文化思想的裹挟下,和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改变。传统婚姻制度遭遇挑战,出现冰山消融般的悄然变化。萧红的离经叛道,从某种意义来说,反映了民国社会深层的价值观念的变异。
在那个时代,萧红,以过去鲜见的女学生形象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她不顾及传统意义的婚约,爱上了表哥,并反抗旧家庭,选择逃婚,勇敢私奔。与有妇之夫同居、未婚先孕,这些,在那个时代,是足以惊世骇俗的。这些在她的那个东北小城里,无疑掀起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如果探究源头,应该叫做时代。
处在时代风暴里的萧红,像一条误游到海滩上的鱼,虽然充满了追求自由的觉醒意识,但对自己周遭的险恶浑然不知。或者,就算有个模糊的感觉,也难以提防。她全然不知前方的陷阱,仅凭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东奔西突。在新旧更替、传统与现代的角逐之下,一次又一次,这颗追求自由的心被刺得鲜血淋漓。然而,不甘的她,愈行愈远的她,却顽强地固守着那个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固守着内心的平静和对平凡世界的期盼。她用与生俱来的才华逆流而上,回望着生养她的地方,书写着“人与动物一起忙着生,一起忙着死”的故乡,那个她脱身出走的世界。这种书写与她自己与她的时代都显得不合时宜,不入大流。她也书写她梦想中的美好,那是个她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从故乡到哈尔滨,又到青岛,到上海,到日本,到山西,到西安,到武汉,到重庆,直至她被时代裹挟着去了香港。病逝于此之前,因喉癌手术,她已无法说话。然而对生的渴求仍牢牢地攫住她的心。她用她的笔,写出了最后的遗言,满是不甘。萧红曾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对于自己的命运,她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还说,“不错,我要飞,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会掉下来”。她31岁的短暂一生,浓缩了众多女性不曾有过的痛苦和不幸。这痛苦和不幸,让她成为新旧道德碰撞的牺牲,成为混乱时代的祭典。她面对生存的恐惧与挣扎,对自由与温暖的向往与奋争,正是那个时代的鲜活写照。
萧红在狭路相逢的时代里,命定会遇到一些爱。
那个叫陆哲舜的人带走了萧红的初恋。爱上有妇之夫并私奔,听起来骇人,但是对于心里装着一团火的少女萧红来说,却就那样发生了。放在今天,两个相爱男女,相携从众人视线里消失一阵子,恐不会惹得满城惊诧。但放在当时的东北小城,无啻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迫于压力,表哥陆哲舜选择了回归。为爱奋不顾身的萧红第一次被置于险恶处境。陷入精神与物质双重困顿的小女生,满心里装着纯情与浪漫的小女生,不得不向世俗低头。回头来却发现,已没有了她能够走的路。于是萧红第二次突围,迈上同样险恶的旅途,带着小妇人的温柔,回到未婚夫汪恩甲身边。假如汪恩甲的兄长不那么义愤填膺地出来搞破坏,萧红的人生会得以改写。可现实的结果却是,汪恩甲一去不返,扔下萧红一人,背负巨额债务,挺着大肚子,困居小旅馆里。
这时,萧军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萧红命中最重要的爱人的出现,让她的命运得以转折。他带着她,带着她的文学,走进了一片朗阔的天地。萧红结识了一众作家。他们对她日后的文学,产生了多或少的作用。他们亦师亦友,在她短暂的生命里,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后来,虽有不少人言说萧军的狭隘和不专,甚至在某些书写里,兼有下半身叙事之嫌。这种对人格的肆意揣摩总是不好的吧。我倒赞同,二萧的分手,实为文学观的严重不同以及性格的严重不和。性格能够折射出人性。可是人性的光辉也许照得到远方,却照不到身边的爱人。这个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但假使没有萧军,萧红还是不是这个萧红呢?
再后来,萧红一生中最后一个爱人出现了。在她与萧军的感情飘摇之际,萧红又一次服从了爱的安排,选择与端木蕻良结婚。尽管这里面也浸染着无奈。看官们都觉得萧红操之过急,当年的文学界一众文友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可是萧红那颗渴望安定的心,是那么急切地要找到可以倚靠的臂膀。尽管萧红自己也未尝不知,这臂膀并不是那么结实有力。为爱所伤的她,已伤痕累累。对这段婚姻,她并没有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然而这一次,注定的,她更觉失望。我一直在想,假使,萧红在香港没有病逝,那么,接下来的,与端木蕻良会不会分道扬镳呢?要知道,那时的萧红也刚刚31岁。那么年轻敏感的心,又怎能支撑得住浸淫着懦弱自私的一个婚姻呢?又如何能够坚持到地老天荒?“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吗?那个时代里的萧红,又怎么可能实现这个看似平凡的希求呢?
才女多蹇。萧红,一次又一次,为情所伤。
在那个时代,萧红命定地与一群人相逢。当时的东北作家群多生猛啊。这帮文学青年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作品粗犷宏大,东北风劲道十足。后来一声集结号响,在上海异军突起,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都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她和他们必然要有一些亲密接触。伤心的,痛心的,暖心的,热心的,就那么地发生了。
在萧红的爱与婚姻之外,幸运的是,聚拢了多位真情相助的仗义友朋。那么一大批左翼阵营里的革命作家们,确是构成了一个时代的蔚为壮观。鲁迅、许广平对萧红的扶持自不必说,胡风、梅志、白朗、罗峰、舒群、蒋锡金、聂绀驽、丁玲、骆宾基,等等,这些人物,与萧红都有或多或少的交集,与萧红都有或深或浅的交情。写到这里,我又得说一下《黄金时代》。至少,于我是第一次,在浩大的银幕上,看到了那一群我们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的人。虽说从电影艺术本体来看,这种众多人物群像以采访的方式纷至沓来,对影片的艺术审美多少是个损伤。尽管观众看到的是新鲜和觉醒,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要的也是这个。这本是一个在艺术创造上有争议的话题。那些同时代的同样已仙逝的作家们不时突兀地走进镜头,总结评说着萧红的人生与创作,或是对她接下来的人生转折做个点题式铺垫。这种时空倒错式的采访,给人的感觉是怪异的。从人物塑造来说,如此众多地让位给旁白,也绝对不能算是成功的尝试吧。故事片与小说一样,叙事是第一要义。叙事的魅力是无穷的。人物的行动必然推动着人物的命运。而摒弃了人物的行动,靠采访式的安排,让本来就是加长版的剧情片,就算再多两倍的长度,也无力让这么一群大人物个个光彩夺目。
萧红命中注定要和这些文学大师们相遇。萧红独有的“黄金时代”的魅力,在与她有交集的几十位文学家构成的浩瀚星空中,愈发耀眼,更凸显了萧红不走寻常路的独树一帜。同时因了她生命的短暂,让她的眩目光影如惊鸿一现,更让人生出无限怅惘。
萧红在她无法选择的那个时代,为现实所困,但又努力地想挣脱牢笼。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出生五天亲手遗弃,第二个出生三天死在身边。这对身为母亲的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也是无法磨灭的痛。但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经历了那么多情感困苦和生存困厄,选择了这样的残忍,抑或是她自认为的向自由的拼搏与抗争?一个为文字而生的柔弱女子,人生本不该背负太多。萧红也无非是想要过一个自己想过的安定的生活,爱一个自己想爱的人。萧红穷困但不潦倒,这正是她顽强个性的写照。至于后来,她为了要一个安静简单的写作环境,选择不去延安。在当时的兵荒马乱群情激昂中,这种抉择无啻于晴天里的一声雷,是足以让周围的人侧目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寻找脱离了时代的个体自由,简直是水中的月镜中的花。萧红自是用一路跌跌撞撞的累累伤痕悟出了这些。她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表达她对自由的向往时,同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现实中无助的挣扎。“这样的生活,像蛹一样,自己被卷到茧里去了。”她说自己感悟到的那个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感情、生活,自由、束缚,在那个可怜的由逃避情伤暂时获得的自由时刻,孤独寂寞而伤痕仍在的萧红,又何曾有过一刻的欢畅?那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写革命,只有萧红,那么另类地在写故乡。她想要的“黄金时代”,也只有在远离战争疮痍和情感伤害的异国一隅,才如“谎花”般突然降临在她的眼前。逆时代洪流的萧红,没有悬念地命中注定地被卷到茧里。那张迫她为蛹的茧,不正是那个时代吗?萧红用其一生与那个时代抗争,但最终被那个时代摧毁。
《黄金时代》的情节结构,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一个真实的萧红,客观立场中的萧红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量,仿纪录片的方式显然用力偏颇,对萧红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个消解。观众固然需要引导,但接受不可用强。比如影片开头,汤唯扮演的萧红出镜,气氛庄严肃穆,照片一样纹丝不动,只见嘴巴在一开一合地自我介绍,我是萧红,生于哪年,卒于哪年,享年31岁。这固然是在演电影,但这“发明”的内里却透着荒诞不经,足以让人抓狂。那是个不应该笑的时刻,影院里却分明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评说民国的人和事,和评说任意一个朝代的人与事一样,哪个时代不要紧,至于热还是不热,相信不少人如我一样绝非要跟风。但是请笔下留情。任何指向历史人物的言说,我都希望是从他(她)的行动得来的理由,也是从行动得来的结果,从而指向挖掘人物命运更具深层意义的渊薮。使得这种种言说不至于尽是闲话甚至废话。人物的行动才是呈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的根本。也只有这样,在对萧红的众说纷纭中,才能对女人萧红更多一些情感庇护,藉此提升对历史人物的人性关照,用温暖情怀纪念那个时代的文学。
对自由的追求,让萧红在现实中走到生命的绝境。她却把对自由的向往用极美的文字留存下来。萧红的生命虽短暂,文字却得以永生。没有那么坎坷的经历,也许就不会有那么渴望的文字。在《呼兰河传》中,她写道:“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段话我是极喜欢的。绝妙的微言大义,突出了萧红对以自由为主旨的“黄金时代”的倾心渴求。
不知怎地,写到这里,我仿佛看见,满头白发的老年萧红,眼神柔和,坐在冬日温暖的书房里,书写着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写,只是安宁地坐着。一任光阴温柔地流淌。一如世间所有的年老妇人。我分明看见,她脸上刻满故事的皱纹。我也分明看见,她那不肯停息的,不设防的,朝圣者的灵魂。
我宁愿这样假设,萧红与她的时代,最好不相逢。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